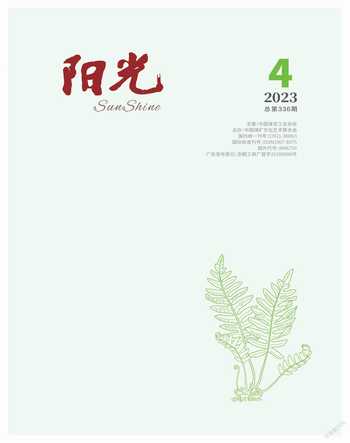在雄渾與壯美中留連(創作談)
2019年9月,我走過了河西走廊。在此之前,我只在地圖上認識這片土地。記得小時候,我對地理特別感興趣,父親騎行去串聯,每一天,我都會在地圖上找到他應該到達的地點,做上標識。而對于河西走廊,我也無數次地神游過,在影視劇里、在文學作品里,也在我的想象里。但當我自駕近兩千公里從蘭州抵達敦煌,我覺得已經走到了世界盡頭。當然,我并非直線而行,而是迂回繞道經過了無數的小鎮村莊,那些在地圖上無法找到的所在,正是我心心念念的心靈歸處。那古長城斷斷續續地一直伸向西天,像一首長歌余音未了。我從未見過那么雄奇的大漠與戈壁,更沒見過那么神奇的綠洲清泉。我覺得這太像我在詩里的追求了,大西北在大悖論里風光了經年,依然存活著,而且更加具有生命力。
蕭索的陽關、壯闊的荒漠、殘敗的玉門、雄壯的嘉峪關,每一處風光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那些站在懸崖上的羊,雄渾的落日下的蒼茫,大戈壁上突然涌出的河流,抬頭可見的雪山,更不必說天堂寺、鳩摩羅什寺、驪靬古城、山丹、張掖、高臺鎮、酒泉、榆林石窟、陽關、鎖陽城、瓜州,單單是阿克塞,都那樣的魔幻。一座廢棄之城,因為一位詩友曾在這里任教,找到他住過的房間,如今已成殘垣斷壁,不勝唏噓。一只蝴蝶一直繞著我起舞,斑斕輕盈,不知它是沿著哪一行詩句飛來的精靈?
是的,在這條路上,走過那位身披雕裘手持旌節的人、走過那位以錫杖插地鄭重發愿的人、走過那位九九八十一難而終不悔的人、飛馳過那位策馬揚鞭把自己也變成一把利劍的人……而今我再走時,歲月遠去,體會的只是那一種孤獨——赫赫雄關下多少隱去的身影,黃沙古道掩埋著多少將士、商旅和墨客。
西行的路上,是那樣的孤寂,看不到邊的荒蕪,難得一見的飛鳥,藍得令人絕望的天空,但都被那一朵小小的花兒震撼,被那突然出現的一抹綠而撫慰。最讓我激動的是一路打電話尋找,終于在酒泉找到了林染先生。記得90年代初,林先生已詩名大震,卻為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我寫下詩評。我把這段評語印在自印的小冊子上,足見對此評語的認同。我坐在酒店的大堂里等他,他走進來,我一眼便認出他,雖然歲月的風霜浸染了他的面容,但他如我想象中的一樣,依然還是西部硬漢。
我終于來到了莫高窟。只為那一瞬間的燦爛,已經感動到血淚滿眶了。如果能一個人,獨坐在窟中,與那些“飛天”默默相對,該有多好。不過一生能到過一次敦煌,足矣。寫這趟旅行,我當然選擇了詩歌,因為只有詩才與這遼闊的孤獨如此契合,只有詩才能深入到靈魂的深處,不只為記錄,更為那些河流:疏勒河、黨河、榆林河;為那些城池:昌馬、鎖陽城、石包城、淵泉、瓜州;為那些關隘:玉門關、陽關、嘉峪關;更為那些消失的身影與不死的靈魂:張騫、霍去病、鳩摩羅什、玄奘……
我從2020年初開始陸陸續續地寫西行之詩,在那樣的寂靜中書寫西部,是多么好!我需要雄壯與豪邁的氣質,那種硬朗,充盈著我的血脈。我更需要那種遼闊的孤獨,那神性的照耀,因為,這種時刻,是多么需要風骨與壯闊!寫這些詩時,那些邊塞詩不停地閃爍,仿佛我再一次走到了天邊,而以敦煌為終結,是為大美。這組詩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許我還會繼續。
李輕松:女。一級作家,職業編劇。曾參加第十八屆青春詩會,2007—2008年度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榮獲第五屆華文青年詩人獎,中國詩歌排行榜雙年度女詩人獎等獎項,著有各類圖書20余種。在《南方周末》開設個人專欄,戲劇影視作品2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