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女英雄傳》中十三妹形象轉變的合理性
陳玨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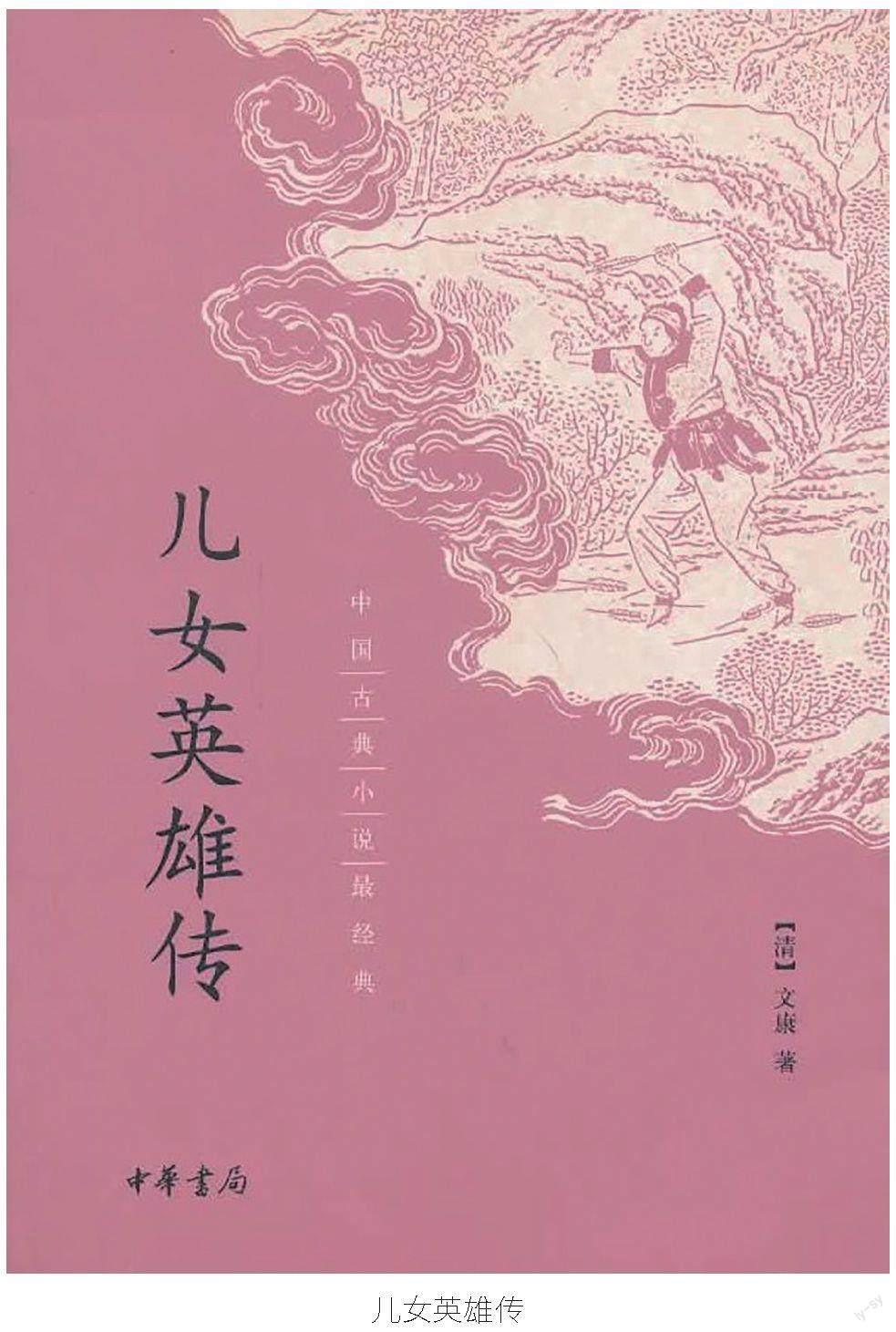


《兒女英雄傳》原稱《金玉緣》,經后世文人的補寫而改名,是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在光緒年間刊行,敘述方式采用評書體。其作者文康,字鐵仙,費莫氏,清代滿洲鑲紅旗人,曾出仕,自稱“雁北閑人”。馬從善有序:“先生為文襄公大學時勒保次孫,以貲為理藩院郎中。出為郡守,洊濯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為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魯迅也曾提到文康出生富貴人家,但后來因為“諸子不肖”而變得家境貧窮,到了晚年“塊處一室”,只得以寫書自遣,將自己經歷的人生興衰、世事變遷寫進小說中。因此,《兒女英雄傳》借敘述他人之事,表現作者文康的理想追求,這一點就不同于此前的大部分小說。文康的晚年過得艱苦潦倒不說,又恰逢政治、文化即將迎來巨變。道光、咸豐年間,古代白話小說進入終期,此時的小說在故事情節和人物上“多用傳統的模式,缺乏作家自己的創作個性”。在此背景下,文康創作的《兒女英雄傳》也被視為舊小說在新時代來臨前的一次無力突圍。
《兒女英雄傳》誕生于舊時代尾聲,被稱為“清代小說的后勁”,自問世以來一直廣受爭議,稱贊者如陳寅恪認為其“轉勝于曹書”,貶斥者則認為其思想淺陋、內容不夠豐富。
《兒女英雄傳》的主角十三妹是古代小說中最后一位有影響力的俠女形象。她聰慧果敢,在能仁寺救下張金鳳和安驥;仗義好強,在得知安公子為父奔走后被其孝心打動,毅然決定出手相助。十三妹兼具俠義與柔情,成為清代俠女形象的代表,得到肯定的同時,其身體建構的多重性、前后不統一的性格也引起了爭議。
十三妹這一人物的身體是由舊小說各種人物模式重新組合疊加而來的,往前追溯,建構這位晚清俠女身體的材料在小說史上清晰可見,有唐宋劍俠小說中超越常人生理極限的神性身體,如胡適先生所說的聶隱娘、紅線一流的劍俠“超人”,也有話本中綠林世界神勇的血肉之軀。治家賢惠的形象則是對明清世情小說人物的優化組合。這種身體的多重建構受到了晚清小說題材合流的影響。彼時,文康知道無人可以挽回即將解體的舊秩序,在他的想象中,只有十三妹這樣“完美”的俠士才能挽救危局。盡管文康力求突破和創新,最后也難免落入俗套,沒有跳脫出傳統俠女的模式,而是對前代俠女形象進行擇優重塑,希望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一個理想的俠女。因此,十三妹這一形象并不是文康原創。這種身體建構的多重性也給十三妹的性格邏輯帶來了混亂感。
歷來學者主要的爭議點是十三妹的性格前后是否具有統一性。以創作意圖和創作目的為出發點,部分學者認為從十三妹到何玉鳳的轉變,不僅是人物從“英雄傳奇”里的“江湖”走進了“世情小說”中的“家庭空間”,更是俠女形象被嚴重削弱、清高俠女形象被顛覆的過程。也有人認為十三妹的“性格失常”是文康庸俗世界觀的具象和腐朽思想的體現。亦有學者分析,文康的創作意圖是“圓夢補恨”,是為了與《紅樓夢》進行“對壘”。與敢于直面自己家庭罪惡的曹雪芹不同,文康不但不愿意寫自己家庭衰敗的原因,反而渴望塑造一個理想的圓滿家庭,頗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之意。
十三妹是晚清最后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俠女形象。她身上既有俠士共有的武功蓋世和雄心俠氣等特點,也有大家閨秀的知書達理。不管是豪俠還是情俠,文康筆下的十三妹注定不同于前代任何俠女形象。這不僅是因為十三妹身體構造的復雜性,更是因為十三妹性格前后的不統一,但這種前后沖突又有其必然性。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十三妹原生家庭對其性格形成的影響。
性格是人們對某事、某人所表現出的不同思想、情緒、行為、態度的總稱。性格雖然一旦形成就會穩定,但并非一成不變,相反,它具有可塑性。性格主要表現在“做什么”和“怎么做”兩方面,“做什么”反映了個人對現實的態度,“怎么做”反映了個體的行為方式和特點。性格是包含在人格結構中的,體現了人的本質屬性,并且最能表征一個人的道德行為特征。影響性格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原生家庭、固有性格、外在環境和自身閱歷等。日本學者太田辰夫認為十三妹形象前后的不同是由環境的不同造成的,“就以兒女與英雄一身兼備來說,也是理所當然地要適應環境的變化,兩者哪一個是明顯化,哪一個不是明顯化,何玉鳳前半部作為英雄形象出現,后半部是作為兒女情形象出現,這是由于環境的不同而形成,由此而堪稱張冠李戴一樣的不自然,那是不恰當的”。從十三妹到何玉鳳,并不是俠女性格不真實。太田辰夫的這一觀點被眾多學者作為分析十三妹婚前婚后性格轉變合理性的主要依據。但這只是簡單地從外在環境進行分析,忽略了內在環境即十三妹家庭環境對其性格形成的影響。
十三妹在第四回以一個神秘的形象登場:從路南那邊,騎著一頭黑驢,慢慢悠悠地走了過去。這種出場方式不同于以往的舊小說,更像是西方小說的手法,在描寫中逐漸交代人物。在悅來客棧,十三妹抬起巨石第一次展示了自己的神通。隨后在能仁寺,十三妹憑一己之力殺惡僧數十人,救了張、安兩家,并周全地替他們考慮了后路。十三妹的性格特征在這些事件中逐漸顯露。如安公子騙十三妹自己是保定人,但十三妹心思縝密,推測出安公子是京都人;在解救了張家和安公子之后,十三妹并未一走了之,而是仔細慎重地考慮了怎樣善后以及兩家四口人該如何上路的問題。她言語犀利、行事干凈利落,已經展現出婚后“何玉鳳”的雛形。特別是其中關于十三妹身世的情節,為十三妹從俠女形象到賢婦形象的合理轉變埋下了伏筆。
文康在小說寫道:“天下作女孩兒的,除了那班天日不懂、麻木不仁的姑娘,是個女兒,便有女兒情態,難道何玉鳳天生便是那等專講蹲縱拳腳、飛彈單刀、殺人如麻、揮金如土的不成?何況如今事靜心安,心怡氣暢!再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怎叫她不露此女兒矯癡情態?”文康也在小說中簡單解釋了人物這種轉變的社會原因以及由此產生的人物心理變化與行為變化。他一方面歌頌十三妹的俠肝義膽,另一方面竭力追尋她由兒女變為英雄的社會動因以及與之相契合的心理動因。小說中人物心理動因的改變與社會動因的變化緊密相關,我們從小說中也能找到十三妹性格轉變的基礎—內在性格。
張、安兩家詢問十三妹的身世,她回答說自己也是好人家的女兒,父親曾經做過朝廷二品大員。提到她超乎常人的武藝,“這也有個原故,我家原是歷代書香,我自幼也曾讀書識字。自從我祖父手里就有了武職,便講究些兵法陣圖,練習各般武備,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真傳。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便無般的不愛。我父親膝下無兒,就把我當個男孩兒教養。見我性情合這事相近,閑來也指點我些刀法槍法,久之,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十三妹幼年就開始學習各種武藝,十八般兵器她都熟悉,在拳腳、彈弓、槍法等方面更是得到了父親的“口傳心授”。“因此任我所為,就把個紅粉的家風,作成個綠林的變相。這便是我的來歷,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著黎山老母學來的。”十三妹從小被當作男孩兒教養,便是性格也是如男子一般。女兒家該學的針線活兒她不會,也不能以此作為生財之道供她們母女倆生活,十九歲了還不清楚針線是橫是豎,無奈只得靠著一把刀和一張彈弓行俠仗義、劫富濟貧。
十三妹生在書香世家,幼時就讀書識字,頗有才氣,故可以在能仁寺墻上寫下令安公子拜服的豪語。又因她祖父這一代開始得了武職,家中研究兵法、練習武藝。受家風影響,十三妹開始練習武藝,并被當作男子教養,有了男子的雄心俠氣和慷慨大義,“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瀝膽訂交。見個敗類,縱然勢焰熏天,他看著也同泥豬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愛的也同威凰祥麟”。行事作風也如男子一般豪爽仗義,這是她與生俱來的性格,做不來像一般女子那樣含蓄扭捏。家庭環境讓十三妹的性格成形:既有大家小姐的知禮節、懂才學,又有男子的豪爽不羈、直言不諱。婚后的何玉鳳想要有所作為的志氣,比起俠女十三妹在能仁寺拯救安公子等人的果敢并未改變,她的英雄氣概不曾消退,不過是因為環境發生了變化,所以表現的方式不同罷了。
文中多次提到十三妹性格的“天生”:“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個脂粉堆里的豪杰,俠烈場中的領袖。……雖然是個女孩兒,激成了個抑強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大約他自出娘胎,不曾屈過心,服過氣,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罵,有個不翻臉的么?誰知兒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張金鳳等人被救下后感謝十三妹,十三妹只說:“你我今日這番相逢,并我今日這番相救,是我天生好事慣了,你們倒都不必在意。”這種“天生”其實是原生家庭帶來的。十三妹與生俱來的兒女情長讓她對安公子千里救父的孝心感到動容,于是在能仁寺救下張、安兩家,她自小接受的官家小姐教育也讓她對如何侍奉公婆、持家理財頗有心得。不管是作為俠女還是作為人婦,十三妹身上兼具的英雄俠氣與兒女情長并未減少,其形象并未發生變化,不過是婚前、婚后的側重點略有不同。
“十三妹”無疑是一個合格的俠女形象:機智勇敢,膽大心細,獨立反叛。她不受束縛,自有一套生活哲學。生存環境的惡劣并沒有讓她屈服,她依舊是那個桀驁不馴、無比灑脫的俠女。自古忠孝難兩全,但她做到了,她以女性的柔弱軀體承擔重任,這是很多男性角色都做不到的。因此,十三妹這一形象具有表現男女平等的意義。文康把她寫得活靈活現、不讓須眉,這不僅是展現文康對女性態度的典型,還是其肯定女性地位的表現。此外,何玉鳳式俠女出現在晚清,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點。一是被平民意識改造的文學題材。文康嘗試重新把俠女形象放到“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里,使其從神異化的模式中解脫出來,嘗試恢復女性的正常倫理訴求,將俠義精神和日常倫理、民間道德結合起來,形成了近代平民意識。二是隨著晚清小說創作中各類題材的合流趨勢,出現了各種人物模式重合于一個人物的現象。何玉鳳式俠女可以視為一個特殊階段的文學現象,值得給予更多的關注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