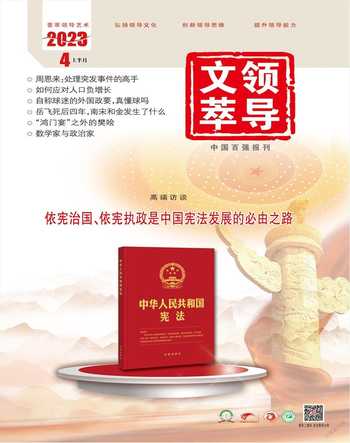清朝的奏折制度
王志強

奏折是清朝時期獨有的一種上行官方文書形式,皇帝與群臣之間通過一道道奏折文書來溝通、處理國家日常政務。明朝舊制,群臣向皇帝奏事,采用“公題私奏”之制,即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凡錢糧兵馬、命盜刑名等例行公事,皆采用題本奏報,須加蓋官印;凡官員私事,皆采用奏本,不用印。清初承明制:凡京內外各衙門,一應公事俱用題本,凡官員請安、謝恩等事概用奏本。
按照文書流轉制度,凡地方各級衙門所上題本、內外臣工所上奏本,通常由通政使司轉交內閣票簽處票擬貼黃(中央部院題本不經過通政使司直接送內閣票簽處),內閣票擬辦理意見,經大學士等審定后才能呈供皇帝御覽。皇帝對票擬的意見予以認可,批本處用朱筆謄錄于題本首頁(此稱之為“批紅”),再送回內閣六科發抄相關衙門。然而在實踐過程中,題本與奏本運轉程序十分煩瑣,不利于國家政務情報的及時上達,影響決策效率。在此過程中,題本或奏本的保密性極差,有時題本還沒到達皇帝手中,國家事務已經播揚在外;有些大臣顧及保密性,在題本或奏本中不能真實反映各處情況。在此背景下,一項新的文書制度——奏折制度應運而生。
奏折制度創立之初,僅為在京衙門和少數親信大臣向皇帝報告公、私事務的一種形式。大臣繕寫好奏折,封好后裝入專門的報匣,多由大臣親信家丁等親自遞送,經奏事處可直達皇帝手中,由皇帝親自拆閱,并將處理意見親自以朱筆批示在奏折之上,謂之“朱批”,此類奏折即所謂“朱批奏折”。然后遣人將奏折發還具奏者,按朱批辦理施行。后來,康熙皇帝選派親信家奴到地方任職,如蘇州織造、杭州織造、江寧織造等,他們也被允許使用奏折向皇帝報告所在地方事務及情報,成為皇帝了解地方官員與事務的秘密通道。
康熙中后期,朝廷將奏事權進一步擴大,凡朝中大學士、各部尚書等中樞機構官員,地方駐防將軍、督撫、提督、總兵等具有直接向皇帝具折奏事的權力。
雍正時期,朝廷將官員奏事權進一步擴大至科道、翰林、藩臬副參等以下微員。雍正皇帝有時還特別給予品級低下、沒有奏事權的“效力微員”具折奏事的權力,以便更加全面真實了解各處事務。
由于密折可以直達皇帝手中,所以具奏者多能秉筆直書、暢所欲言,且其中多有彈劾、告密上司等秘密材料,留存在各處,具有很大的政治風險。雍正皇帝甫一即位,即著手實行朱批奏折回繳制度,要求內外大臣按朱批辦理后,要將“朱批奏折”呈交于中央統一貯存。雍正皇帝首先諭令收繳康熙皇帝時期的朱批奏折:
軍前將軍,各省督撫、將軍、提鎮,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謹查收進呈。或抄寫存留、隱匿焚棄,日后敗露,斷不肴恕,定行從重治罪。
并言明:“嗣后朕親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內,務須進呈,亦不可抄寫存留。”對凡因升轉、降調、病故的官員有未繳回的朱批奏折,規定可由本省督撫代繳。雍正七年(1729),為便于留檔備查,雍正皇帝又推行奏折副本制度,即由軍機處負責謄錄“朱批奏折”副本,故稱“錄副奏折”或“軍機處錄副奏折”。
奏折制度創立之初,多由親信大臣派家人或心腹之人親自送交奏事處,再由奏事處轉交皇帝閱看。隨著奏事權的逐步擴大,地方各員被允許使用國家驛遞系統呈送奏折。為避免各官員濫用驛遞,特別規定:各處督撫、提鎮及駐防將軍都統,只有在上奏“緊要”奏折時,才準差人通過驛遞系統呈送奏折,但規定使用馬匹不得超過兩匹;“尋常”奏折則不得擅自使用驛遞系統,必須自行差人呈送。待各省奏折奉朱批后,統一由軍機處調度使用驛遞系統發遞給具奏者。
清代奏折所涉內容主要有請安、謝恩、繳批和奏事四類。其中奏事類內容十分駁雜,上自國家政事,下至百姓日常事件,事無巨細。由于奏折所涉內容往往較為機密,所以皇帝一再要求各大臣務必親自繕寫,不可找人代寫,以免泄密。在奏折制度之下,內外大臣都可成為皇帝的耳目,他們不論公私,暢所欲言,凡有見聞皆可據實奏聞(即“風聞言事”)。
如此,皇帝建立起了一張巨大的資訊網,隨時可以掌握全國各地輿情、各官員優劣等情況,對于鞏固皇權,加強統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臣遇有各類節慶時向皇帝具折請安,或遇有晉升、受皇帝賞賜等情況向皇帝具折謝恩,加強君臣之間的私人情感,對鞏固統治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摘自《天地清風:圖說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