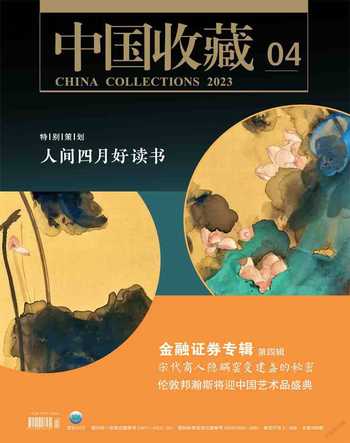王莽執政時期“尊堯”鏡銘考
王綱懷 鵬宇

近日,筆者新見一博局紋銅鏡(圖1),實物雖殘,但涉及主題的紋飾與銘文仍可辨識。從殘存部分看,該鏡為圓形,四蒂四瓣花鈕,座外雙線大方格,內飾12個乳釘紋,乳釘間十二地支銘。方格外分四區,每區內置兩個帶連弧紋底座的乳釘,主紋為四靈。近緣處置銘文圈帶及櫛齒紋,鏡緣飾鋸齒紋帶及辟雍(水波)紋。由形制觀察,左青龍、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的四靈布局規矩,子在下,子午線穿鈕孔而過,其斷代可認為是西漢晚期王莽開始全面掌權至新莽,可謂“王莽執政時期”。
除紋飾外,此鏡銘文罕見,字體為懸針篆,其文曰:“大哉,堯為君也。美哉,大官食也。富哉……子孫,得天道,物自然,富貴昌,樂未央。”

從存世實物看,同類六言鏡共有4面,“大”字前有起止符號,從句式上看,此類鏡銘文6字一句,格式為“×哉×××也”。句首一字為對“哉”后半句的概括,每句以“也”字結束。其中3面為“尊孔”鏡銘、1面是“尊堯”鏡銘(似為僅見),現分別敘述如下。
在存世所見之王莽執政時期的鏡銘中,可見句式多種,主要是三言、七言、三言間加“兮”之七言、雜言等,六言句式少見。據筆者所知,除圖1鏡外,迄今所知尚有3面(圖2、圖3、圖4),而且內容幾乎相同或相近,首句皆為“大哉孔子志也”。詳見下表:

曹錦炎先生引《論語》指出,“孔子之志”出處為《公冶長篇》: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愿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愿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志”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對此,曹文進一步闡釋說:孔子回答的志向,是希望年老的人得到照顧,使之安樂,和自己同輩的朋友得到信任,年少的人得到關心。其實,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修己以安人”(見《論語·憲問》)。孔子論人,有三個境界:圣人第一,仁人第二,君子第三,“修己以安人”是“仁人”的境界,亦即孔子之“志”。
筆者認為,圖2、圖3、圖4等銘文完全是當時社會“尊孔”的實際反映。這里的孔子之志是孔子與弟子聊天時,對自己志向的一種引發,是對弟子提問的倉促應答,說其至高至極未免有些夸張。漢鏡中此處的“大”字,我們認為與漢鏡中他處常用的“善”字的意思應該一致。如“尚方作竟善毋傷”,常做“尚方作竟大毋傷”,這是典型的辭例。
筆者認為,“大哉堯為君也”中的“大”字應該也是“善”字之義。眾所周知,儒家極力推崇三皇五帝、堯舜禹湯,在《論語》與《孟子》等儒家典籍中不乏關于堯舜的記載。《論語》更是始以《學而篇》,終于《堯曰篇》。孔子輕易不以“善”許人,但是在夸贊堯舜的功績時,卻會以“至善”贊之。
《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相傳是舜時所作樂章,哪怕僅僅是一點遺存也足以讓孔子感到如癡如醉了。而對于堯帝本人,孔子則更是不吝贊美之詞。《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這即是圖1鏡銘首句的文獻出處。堯舜之所以被孔子如此推崇,應與堯帝首創禪讓制,舜帝維護禪讓制有關。在歷朝歷代的權力交接過程中,父子、兄弟之間的繼承相替都常常充滿血腥殺戮。而堯舜所進行的異姓禪讓傳承,非其大公無私,不能如此。孔子生活在紛爭不休的春秋時期,對此有更多感觸。依據歷史文獻,可知歷朝歷代的“尊堯”思維與實踐持續不斷。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稱堯帝中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權授舜(禪讓)。”
漢代王褒《九懷·陶壅》說:“思堯舜兮襲興,幸咎繇兮獲謀。”
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贊美堯帝與舜帝:“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詠于元后,爛云歌于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
唐代張說《東都酺宴》曰:“堯舜傳天下,同心致太平。”李白《遠別離》:“云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杜甫更是直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牧《東兵長句十韻》:“屈指廟堂無失策,垂衣堯舜待升平。”白居易《太平樂詞·歲豐仍節儉》:“愿同堯舜意,所樂在人和。”

到了宋代,人們還將“尊堯”理念融入鏡銘之中。圖5是一面“媯汭傳家”銘勉誡鏡。媯,古水名,位于今山西省永濟縣。汭,即河流彎曲處。《尚書·堯典》:“鰲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孔傳:“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于虞氏。”孔穎達疏:“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人于河。舜居其旁。”《史記·五帝本紀》載:堯在選擇繼任人時,為考察舜的德行,“于是堯妻之二女(娥皇、女英),觀其德于二女。舜飭二女于媯汭,如婦禮”。
在王莽執政時期的這面銅鏡(圖1)中,為什么會出現“大哉堯為君也”的銘文呢?當與王莽心心念念的禪讓制有關。據《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其人好古、信古、復古,崇尚以古為法,在一步步走上權力巔峰的途中,更是將諸多權力規則運用得滾瓜爛熟。如效仿周公攝政輔佐成王的故事(“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萬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成為攝皇帝,改年號為“居攝”,“用應天命”。
以后,他又指使梓潼人獻上銅匱,(內為“天帝行璽金匱圖”與“赤帝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并在戊辰這一天,親自到漢高祖劉邦的祭廟里接受“金匱神禪”,然后“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并下詔云“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王莽及其擁躉者們,通過一系列的“托古”操作,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天道”“符命”而進行帝位禪讓的先河。圖6之銘:“上太(泰)山,見神鮮(仙),食玉央(英),飲澧(醴)泉,宜官秩,保子孫,得天道,物自然,貴富昌,樂未央載(哉)。”這又是一例實證。

“天道”,指運作永恒一切的道。按照道家觀點,道生萬物,又以百態存于自然之中。早在《周易》《尚書》等古書中已有對天道的記載,如《周易·謙卦》:“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尚書·湯誥》:“天道福善禍淫。”“物自然”,即順物自然,《莊子·內篇·應帝王》:“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據此看來,“得天道,物自然”不僅是古人于自我修行的至高追求,還是天下大治的重要標志。
《漢書·王莽傳》詳載其結果:“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韨,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順符命”“皇天革漢而立新”,也就是鏡銘中所謂的“得天道”了。據此可知,原來在這幾句鏡銘之后竟然還藏著這樣一段“皇天上帝”顯靈、“高皇帝”劉邦之靈“禪讓”帝位于王莽的故事。
圖1鏡銘第二句“美哉,大官食也”與圖2、圖3、圖4之鏡的“美哉,廚為食也”,內容相當,但內涵更為豐富。“美哉,廚為食也”,僅敘說此美食為廚師所作,而“美哉,大官食也”則直接點明此珍饈佳肴為職位較高的“大官”所食。“富哉”之后因鏡銘殘缺而不存,但據前兩句的稀見程度及“富哉”的第一次出現來看,遺失的鏡銘應該也是極為精彩的內容,但也正是因為這些遺憾,給我們留下了更多的遐想空間。
“千秋功罪,誰人曾予評說”?王莽的功過,歷史上多有議論。王莽執政時期距今2000年,在留下了難能可貴的度量器、錢幣的同時,還留下了這些可以印證歷史的寶貴文物——具銘銅鏡。讓我們每個華夏兒女,深知“尊孔”“尊堯”等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