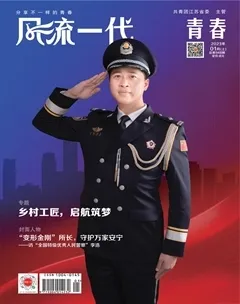鄉村工匠的傳承與堅守




在2022年12月23日至24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新時代建設農業強國的重要任務,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財力保障都要轉移到鄉村振興上來。要全面推進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個振興”,統籌部署、協同推進,抓住重點、補齊短板。
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22年11月,國家鄉村振興局、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推進鄉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導意見》,為鄉村工匠們的未來提供了堅實的政策保障,散落在縣域、鄉間的手藝能人和傳統技藝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把傳統手藝“請”進校園
每周一和周四,無錫宜興丁蜀鎮正新小學三到六年級的學生都會上兩節陶藝教育課,這是學校的特色課程。
丁蜀鎮以盛產紫砂而聞名中外,陶文化源遠流長,制陶歷史可追溯到5000多年前。在這里開展陶藝教育,可謂占盡天時地利。
據學校相關負責人介紹,在學校開設的陶藝課上,老師會教學生做陶刻、杯子、紫砂壺。學校有6間工作室,專門用于學生開展課外實踐。學校聘請制陶名家指導學生制作紫砂壺,從小鍛煉學生的動手能力,對于學得比較好的學生進行重點培養。
學校還開設抖音賬號,宣傳陶藝教育;建起藝術館,展陳學生制作的陶藝作品,邀請宜興當地的陶藝大師在藝術館里做陶藝,成品會對外銷售;專門出版關于陶藝的書籍,拍攝與陶藝相關的電影。
正新小學的陶藝教育已開展多年。2022年秋季學期,勞動教育在中小學獨立成課,學校的陶藝課程被賦予新的含義。
開展勞動教育,對鄉村孩子來說,不只是干農活,還要體驗其他生產勞動、服務勞動,通過這些勞動,掌握獨立生活的勞動技能,并且拓寬視野,進行職業啟蒙。
《意見》出臺后,鄉村工匠與勞動教育或將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有評論指出,培育鄉村工匠,可以和鄉村學校的勞動教育結合起來。一方面,鄉村學校可以結合勞動教育,聘請當地各行各業的能工巧匠作為學校的勞動教育兼職教師,并把他們的工作場所作為鄉村學生接受勞動教育的體驗基地,開設有特色的勞動課;另一方面,鄉村工匠也可把學校作為展示、傳承基地,加強對鄉村傳統手工藝的推廣,培養學生對傳統手工藝的興趣,并在培養學生過程中,促進自己的事業發展。
不光是小學,職業院校也將在培育鄉村工匠的過程中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鹽城大豐的朱玲玲和丈夫都是做瓷刻的,朱玲玲是受丈夫的影響入行的。
瓷刻就是在瓷器上進行雕刻,這門手藝起源于18世紀,由鹽墾文明和集鎮文化滋生,經過幾代人的傳承,大豐瓷刻早已成名。不同于創作在紙上的書法、繪畫作品,瓷刻是將書法的線條、繪畫的構圖、雕刻的刀痕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朱玲玲拿到一件瓷器后,得先構思一下,設計什么畫面,畫什么樣的圖稿;圖稿確定后,把圖稿拓印到瓷器上;下一步就是雕刻,這是關鍵的一步;雕刻完之后,有的瓷器需要著色,有的不需要著色;之后進行修飾整理;最后再對瓷器的呈現效果進行裝飾。
朱玲玲和丈夫運營著一家公司,公司的瓷刻產品有藝術品、文創產品、家居產品,丈夫做的高端產品比較多。要想傳承好這門手藝,還得跟市場結合起來,根據不同的生活場景,推出不同種類的瓷刻作品。
朱玲玲的丈夫還在高職院校任教,教學生怎么做瓷刻。他是江蘇省教育廳選聘的“產業教授”,鹽城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專門為他成立瓷刻工作室,同時開設瓷刻專業,從2021年開始,他就給學生講授瓷刻的理論和實踐知識。
把傳統手藝“請”進校園,是培育鄉村工匠的渠道之一。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農創學院創始院長付文閣表示,要從文化中國的高度認識鄉村工匠培育的重要性,全面抓好培育工作。一方面,鄉村工匠培育要從娃娃抓起,把鄉村傳統工藝相關知識和技能培育融入到中小學教育體系中,讓鄉村學子從小接受傳統工藝的文化熏陶;另一方面,學術型高校要加強理論研究,不斷完善鄉村工匠培育理論體系。此外,有關部門要積極推進鄉村工匠培育模式創新,比如可以將過去手藝人的“師承”模式與現代規模化、職業化培訓模式相結合,不斷提高鄉村工匠培育體系的針對性、適應性、豐富性。
領軍人物帶動產業發展
揚州亂針繡代表性傳承人莫元花稱得上是揚州寶應魯垛鎮的名人。
2001年,莫元花從連云港外事學校畢業,她放棄一份令人羨慕的外企工作,回到家鄉承繼父親的刺繡事業,從事跟自己專業并不對口的亂針繡工作。
亂針繡是一種“以針代筆、以線為墨”創作繡畫的民間藝術形式。對于只拿過筆沒拿過繡花針的莫元花來說,剛開始學習刺繡很不容易。手戳破了不喊疼,腰坐酸了不叫苦,經年累月,她終于練就一手扎實的基本功。
莫元花不滿足于已有的工藝流程,為逼真表現花的色彩、山川氣象和人物造型,她曾對著實景和鏡子用心揣摩,經過多次嘗試,在前輩的四十余種針法的基礎上,研發出適合人物肖像表達的“16系環節操作法”。2013年,莫元花的“亂針繡針法與色彩搭配”得到了蘇州刺繡研究所專家們的充分肯定。
手藝學成了,莫元花沒有獨享,而是決定開枝散葉。
莫元花所在的魯垛鎮與其他鎮村沒有什么不同,男勞動力外出務工,逢年過節回家團聚,留下老人、兒童及部分婦女在老家生活。這些留守婦女的就業機會并不多。
莫元花下決心把這些留守婦女培養成有一技之長的繡娘。她先后開辦亂針繡職業技能培訓班,多次邀請蘇州、常州等地的刺繡大師來魯垛傳授技藝,把自己總結、研發的“16系環節操作法”傳授給家鄉的姐妹們。
在莫元花的幫扶和引領下,3000多名留守婦女成了繡娘,建成了諸多家庭小作坊式亂針繡基地。魯垛鎮有了亂針刺繡產業園,刺繡手工業成為魯垛鎮一項重要的經濟支柱,寶應縣的亂針繡在全國所占份額在70%左右。
建設家鄉的同時,莫元花還伸出援手,扶助陜西榆林定邊縣的“半邊天”。寶應縣和定邊縣是結對幫扶關系,當地有刺繡手藝,有技術底子,有富余勞動力。定邊縣邀請她去傳藝,她不但教當地刺繡手藝人技術,還思考如何把寶應縣的刺繡和定邊縣的刺繡結合起來進行創作。
作為傳承人,莫元花始終為“亂針繡”的價值鼓與呼,她考慮的不僅有傳承問題,還有這門技藝對鄉村振興的意義。
莫元花認為,傳承難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傳承人如何傳承手藝,是專心鉆研技術,還是傾力開拓市場?這是兩個不同的目標。對手藝人來說,把老手藝做好,做大做強,并且能夠變現,這是他們的短板,兩者兼顧很難。二是如果經營不好,效益就不好,效益不好,反過來對想學手藝的人就沒有吸引力,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三是得思考非遺產品能不能被社會接納,能不能適應現在的社會。
社會發展的速度太快了,年輕人很難定下心來學一門手藝。任何傳統手工技藝,都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學會的,需要長期磨練才行。莫元花說,年輕人只要愿意學,公司負責傳授技藝沒問題,但是學習是有過程的。以亂針繡為例,學徒既有悟性,也聰明,上手最快也得一年。學徒這一年誰來發工資?如果讓公司來承擔,公司可能承擔不了。
2022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莫元花提交了《關于推進區域農業優勢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建議》的議案。她認為,鄉村振興,離不開人才的支撐,離不開區域農業優勢特色產業、綠色低碳產業的發展等重要支撐。只有這些產業得到了發展,才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高質量發展。
這幾年,莫元花圍繞鄉村振興開展了多次調研、走訪,提出了《關于加強對鄉土人才的重視和培養》等建議。
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才。莫元花說,人才代表著未來,打造合理的傳承梯隊對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長遠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未來,像莫元花一樣的領軍人物在傳承手工技藝、助推鄉村振興方面將持續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意見》,“十四五”期間,全國推出百名鄉村工匠大師,鼓勵設立百個大師傳習所;遴選千名鄉村工匠名師,鼓勵設立千個名師工作室。著力打造一批技藝技能水平精湛、帶動產業就業作用明顯、善經營會管理的高素質鄉村工匠名師和鄉村工匠大師隊伍。積極探索鄉村工匠特色學徒制,依托名師工作室和大師傳習所,開展師徒傳承、提升鄉村工匠技藝、創作傳統工藝精品、轉化技藝研究成果,發揮鄉村工匠領軍人才作用,帶動特色產業發展,為推動鄉村振興提供人才保障。
依托民俗文化,培育鄉村手藝能人
如果來到徐州賈汪馬莊村,你可能會被一樣東西吸引,那就是香包。
香包,又稱“香囊”“香纓”,俗稱“香布袋”“料布袋”。制作和佩戴香包的習俗在我國由來已久。
馬莊香包從造型上看,以新、奇、美、真為特色,形狀敦實淳樸,色彩對比強烈,立體造型栩栩如生。它形狀非常多,有心形、圓形、菱形、元寶形、蝴蝶形、花瓶形(保平安)、水滴形、長方形、人物娃娃等。
香包曾是在徐州農村廣為流傳的民俗工藝產品,每逢春節、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人們都會縫制香包。
2017年12月,在徐州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賈汪區馬莊村,參觀了王秀英香包工作室,對老人帶動村民發展香包產業致富的行為大加贊賞,還自己花錢買下一個香包給老人“捧捧場”。
習近平總書記當年購買的同款香包,成為馬莊村的暢銷產品,“香”飄世界。
在王秀英的影響下,兒子和兒媳辭了職,跟她學習香包制作技藝。2020年,畢業于大連藝術學院的孫女也跟著奶奶學習香包制作以及蘇北地區獨有的刺繡技藝,同時還學習蘇州發繡,不斷拓展自己的技能。
馬莊村于2018年成立王秀英香包培訓基地,為中小學生和游客展示、傳授香包制作全流程。
王浩是馬莊村黨委副書記,已在村里工作五六年了。他介紹,馬莊村現在做香包的有400多人,基本是以本村或鄰近村莊的女性為主。香包銷售以線下為主,發展到現在,年產值大概在800萬元。
如果想學做香包,在馬莊村學習一到兩周,一般都能上手制作。只要愿意學,村里有專門的師傅教。
不過,香包不能固守傳統制作技藝,要推陳出新,設計要新,理念要新,還得跟市場需求結合起來,推出國潮化、年輕人喜歡的品類。“時代在發展,市場需求也在不斷變化,如果還按照傳統的路數進行生產,香包可能在市場上就不那么受歡迎了,所以一定要創新,通過創新進一步打開銷路。” 王浩說。
馬莊村一方面跟藝術院校合作,另一方面聘請專業的設計公司操刀,以民俗文化為基礎設計新產品。
香包是實用和美觀相結合的產品,除了裝飾作用,還有一些中藥的藥用功效。馬莊村同專業的院校和中醫學家對接,形成一些配方,以產生不同的功效,像安神助眠、驅蚊驅蟲等。王浩說:“香包是大眾化的產品,并不針對某一個特定群體,否則銷路就更窄了。”
為補齊銷售短板,接下來,馬莊村準備進軍電商,在線推介香包產品。
為了將小香包變成百姓致富的“金荷包”,近年來,馬莊村成立民俗文化手工藝合作社,培育香包制作能手;賈汪區相繼建起馬莊香包文化大院、馬莊文創綜合體、馬莊中草藥園,吸收有想法、有能力、有干勁的年輕人加入香包產業隊伍。
《意見》提出,鼓勵各地圍繞鄉村振興戰略,打造一批“工匠園區”,結合當地實際成立鄉村工匠產業孵化基地,打造眾創空間。扶持一批基礎條件好、有一定經營規模的就業幫扶車間、非遺工坊、婦女手工基地等轉型升級、發展壯大。培育鄉村傳統工藝龍頭企業與新型經營主體,推動縣域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支持鄉村工匠自主創業,領辦或創辦特色企業。馬莊村的香包產業正沿著這一思路探索。
接力傳承,把手藝學精學透
夏雯是揚州人,畢業于鄭州輕工業大學繪畫專業。
她沒想過留在外地,因此,畢業后回到家鄉,入職揚州漆器廠有限責任公司,負責漆器制作的雕漆工作。
表面上看,繪畫和漆器制作好像是兩個不同的專業,但夏雯認為,這兩個專業有相通之處,雕漆涉及對稿面的理解,需要一定的繪畫基礎。
在揚州,自古就有“髹漆成器”之說。漆,指漆樹傷口流出的樹脂;髹,以漆漆物之意。髹漆成器,就是把樹漆涂抹在器物表面而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藝品,有屏風、衣柜及各式桌、椅、盤、盒及陳設用品。
揚州漆器包括諸多工藝,其中技術難度最大的是雕漆。
雕漆就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紋的技法。由于漆的色彩不同,有剔紅、剔黑及剔彩等名目。雕漆的工序非常繁瑣,分為審稿、雕刻和打磨。審稿時要把稿件一遍一遍核對,如果有不完美或者不好創作的地方,需要調整。雕刻時通過開、剔、鏟等幾個步驟,使雕刻出來的畫面生動完美;打磨則是在雕刻的部分結束后,等表面硬了再用砂紙打磨,使其表面沒有刀刻的印記,最后再用刷子和瓦灰在表面揉搓進行拋光。
揚州漆器曾有輝煌的歷史,起源于戰國時期,此后歷朝歷代,其制作技藝均有所發展。進入近現代,由于政局動蕩,揚州漆器制作走入蕭條,很多工藝相繼失傳,生產作坊相繼歇業,好在仍有少數匠人在夾縫中生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關懷下,揚州傳統的漆器工藝再次復興。
夏雯從入職到現在一直在做雕漆,屏氣凝神,力爭把這門手藝學精學透。雕漆之外,她還要了解漆器制作的其他環節。
制作漆器要花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不是急于求成的事情,夏雯說:“如果不能深入鉆研,不耗費一定的時間,作品是出不來的。我工作幾年了,仍很難看到有成就的東西。”
公司會組織員工外出學習漆器制作技藝,但這門手藝仍遵循古老的師徒傳承模式,一代傳一代。夏雯剛入職是一個師父教,后來技術有所提高,由現在的師父張飛洋帶她。
工作至今,夏雯還在學習摸索中,很多知識需要消化、吸收,融會貫通。
學手藝,如果沒有家里的支持,夏雯可能也做不下去。她說:“現在生活壓力大,年輕人畢業了,總得先解決生活問題。”
對于未來,她暫時沒想太遠,腳踏實地,把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才是最重要的。她現在是工藝師,跟公司里其他“段位”較高的能人相比,還是“小不點”,進階道路還很漫長。
不過,隨著培育鄉村工匠的工作逐步推進,像夏雯這樣的年輕人前景可期。
《意見》為有志扎根縣域、鄉村從事傳統手工藝的年輕人提供了進階的通道:支持鼓勵返鄉青年、職業院校畢業生、大學生、致富帶頭人等群體參加鄉村工匠技能培訓,列入鄉村工匠后備人才庫。鼓勵符合條件的鄉村工匠參加職稱評審,文化和旅游部門優先將符合條件的鄉村工匠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鄉村文化和旅游帶頭人評選范圍,婦聯可按照有關規定在進行城鄉婦女崗位先進集體(個人)評選表彰活動時對鄉村工匠適當傾斜。在全國鄉村振興職業技能大賽、巾幗創新創業大賽等比賽中設置鄉村工匠大師、名師展示環節。
學手藝不容易,后繼乏人是大問題
黃佳麗是蘇州吳中區的緙絲手工藝人。
緙絲織造技藝是蘇州一門極具特色的傳統技藝。與其他絲織品不同,緙絲的緯線并不橫貫全幅,其織造技藝主要是使用木機及若干竹制的梭子和撥子,經過“通經斷緯”,將五彩的蠶絲線緙織成一幅色彩豐富的織物。
黃佳麗從小就接觸過緙絲,2015年真正開始學習緙絲織造技藝。
業界有個共識,緙絲學藝三年才能基本上手,耐不住寂寞、吃不了苦的人學不了緙絲。緙絲要手腳并用,過程中有很多變化,一些特別復雜的作品需要動腦筋研究。黃佳麗從最簡單的開始學,光是打底的基本功,她就學了很長時間。一開始,她感覺非常枯燥,一梭一梭的重復讓她覺得很無聊。
好在黃佳麗不是輕易放棄的人,對緙絲技藝的喜愛讓她堅持了下來。等開始學著做花紋、圖案,她找到了樂趣,開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并沉浸其中。
緙絲有10多道工序,最后一道是修毛頭。做工越細致,毛頭就越多,修起來也會更加繁瑣。但每當看到成品下機,黃佳麗就會有心跳加速的感覺,成就感油然而生。
緙絲是純手工技藝,工作量很大,費工費時,作品以屏風、臺屏、掛畫為主。織造一幅作品的時間動輒以年來計算,尺幅大、工藝復雜的作品得好幾年才能完成。
與快節奏的工業化產品相比,緙絲似乎不具備競爭優勢,但這恰恰是手工藝產品的魅力所在。
從開始構思到作品完成,時間漫長,緙絲手工藝人收入如何保證?黃佳麗說,要根據不同的作品來區分,大尺幅的作品價格昂貴,一般是客戶預訂了,她才開始做,因為純手工作品產量是有限的。平時她也會做一些小尺幅的作品推向市場,如放在桌上的擺件、手鏈等日常使用的東西。
黃佳麗想嘗試設計更多日常所需的作品,打破人們對緙絲的刻板印象,讓緙絲這項技藝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近年來,黃佳麗多次參加國家級、省級工藝美術大賽并收獲榮譽。2019年,她的緙絲作品《五倫圖》榮獲第十屆“藝博杯”工藝美術精品大獎賽金獎。
緙絲慢工出細活,需要極強的耐心,每天都得織,黃佳麗算是熟手,每天的進度也只能按厘米算,這門手藝學起來實在不容易。黃佳麗說,吳中區現在從事緙絲織造技藝的人也就三五百人,且都是40~50歲的中年人,她是“小字輩”。有的年輕人對緙絲感到好奇,就來了解緙絲是怎么回事,但看完了,愿意從事緙絲織造技藝的年輕人幾乎沒有。
緙絲早已成了黃佳麗生活的一部分,她會在這個行當里堅持下去。如果有年輕人想學,也愿意堅持,她會考慮收徒傳藝。其實,黃佳麗遇到的問題也是傳統手工技藝普遍存在的問題。當前,我國鄉村工匠的發展現狀不容樂觀。首先,鄉村工匠老齡化嚴重,部分傳統手藝處于瀕危狀態。其次,鄉村工匠傳統技藝有余,產品市場化技能欠缺。當前,傳統手工藝產品多是以鄉村工匠個人或小作坊形式生產,并且很多手工藝的產品屬性決定了其很難由機器進行標準化量產,導致傳統手工藝品的銷路和銷量很難提升。年齡偏大的鄉村工匠缺乏利用互聯網等數字化新媒體對傳統技藝進行展示與宣傳的技能,導致傳統手工藝品品牌的獨特價值發掘不足,產品市場價值較低。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農創學院創始院長付文閣認為,地方在出臺培育鄉村工匠的利好政策時,要把握深挖文化內涵、注重融合發展、吸收時尚元素三大方向。傳統手工藝的發展要重視年輕人參與,只有不斷與時俱進,注重創新,在傳統工藝中引入契合年輕人品味的現代化、時尚化元素,才能更好地融入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