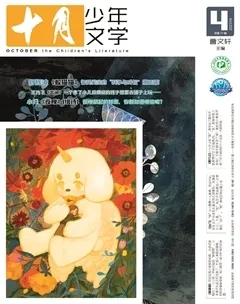兒童游戲視域下的戰爭書寫
《躲貓貓》是舒輝波繼《老狼老狼幾點鐘》之后又一部抗日戰爭題材的兒童小說,在歷史書寫與兒童經驗的呈現之間,作者延續了《老狼老狼幾點鐘》的處理方式——以兒童游戲為載體,來書寫宏大的戰爭主題。具體說來,躲貓貓承擔了雙重的敘事功能。先來看作為游戲的躲貓貓,在秋水河村,心安躲在麥秸垛的洞穴中等待伙伴們和奶奶的尋覓,與田野間麥子躲在雪被子下面睡覺過冬形成了某種呼應,躲貓貓在“序幕”中是以一種充滿詩意的形態出場的,它承載的是一種古典形態的鄉村經驗,麥子的生長,四季的輪回,躲貓貓在時間的流逝中平添了些許童趣。躲貓貓的游戲傳遞出心安內心深處的孤獨感,這種與生俱來的孤獨在奶奶的關愛與理解下多了一絲溫情。耐人尋味的是,在小說的第一部中,作者饒有興致地記錄了心安、保慶、子聰在打谷場上的躲貓貓經歷,“攻占”“攻擊”“佯攻”“掩護”“迂回”“敵人”“襲擊”等詞語令這場游戲具有某種戰爭沖突的意味,軍事術語的修辭和運用預示著作為寵物狗的“躲貓貓”與戰爭之間的隱秘關聯。
在小說中,作為寵物狗的躲貓貓充滿了傳奇性。與它的母親白靈一樣,這只來自叔叔徐佩玉家的小狗天生會捕魚,實屬狗中翹楚。對于心安而言,躲貓貓拯救了被馬蜂蜇傷的心安,即使它的嘴巴被馬蜂蜇后腫得老高,也毫無怨言。躲貓貓與心安之間的友誼因馬蜂事件而變得更加牢靠,心安對躲貓貓的喜愛與感激是不言而喻的。在與敵人的斗爭中,躲貓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機智地幫助大家偵察敵情,在緊要關頭克服重重困難精準地傳遞了慶余叔一行人平安的消息。毫無疑問,躲貓貓身上聚集了勇敢、忠誠、機智等品格,經過戰爭的磨煉,它從一只被心安父親嫌棄的小狗,成長為眾人得力的助手。
同時,躲貓貓還是審視心安與父親徐先生之間代際沖突的絕佳窗口。心安從叔叔徐佩玉家領養了躲貓貓,招致了父親強烈的反對。在躲貓貓拯救心安于危難之后,父親的態度才有所緩和,“約法三章”(不許進祖屋、不許與家禽搶食物、在院子里守家)嚴格地限制了躲貓貓的生存空間—牲口棚。表面上看,父親極度排斥躲貓貓,是因為他對之前那只名叫玳瑁的貓打翻祖宗牌位的行為十分不滿。從深層的心理動因來分析,實則是作為私塾先生的父親的文化性格使然,儒家的禮教早已刻入這個中年男人的骨子里:他從始至終竭力維護宗族祖先的至高地位,他應兄弟徐佩玉之邀做“村民自救會”的會長,在心安母親下山連摔兩跤時他甚至發出了“這雙小腳啊”的感慨……大男子主義與愛國精神有機地統一于徐先生身上,他的性格是一種復雜、矛盾、多樣的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游戲的躲貓貓再現的是一種緩慢的、充滿詩意的鄉村生活,作為寵物狗的躲貓貓則代表了一種暴力的、血腥的、反人性的戰爭狀態。如果說小說的前兩部重在呈現戰爭來臨前人們的心理嬗變的話,那么小說的第三部則是聚焦戰爭狀態下人們的生存處境,那是一部包含著家破人亡、生離死別、家仇國恨的血淚史。在小說中,既有如“蝌蚪”般投靠日本人的漢奸土匪,也有與日本人積極戰斗的張隊長、年輕人“兔子”等英雄,還有徐先生、慶余叔等寧死不屈的錚錚鐵骨形象,他們共同構成了《躲貓貓》的人物畫廊。同樣,我們更不能忘記慘死日軍刀槍火炮下的九香嬸、保慶奶奶、庵生娘、庵生爹……這些底層人物的悲劇性命運,揭示出戰爭的殘酷與無情,促使我們不斷地反思戰爭,并以此來喚醒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