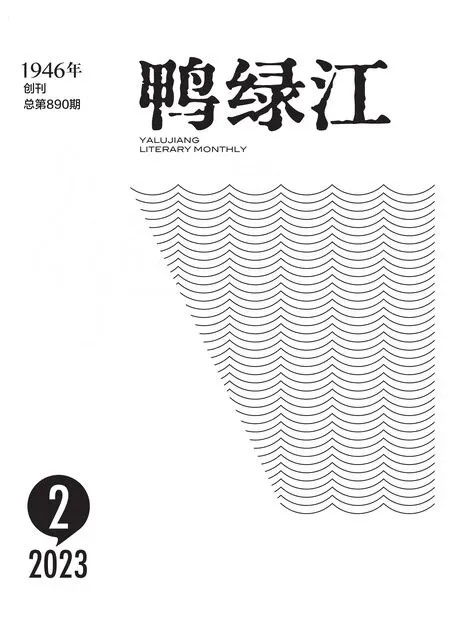怡紅夜宴圖(隨筆)
高海濤
中國(guó)人好像很喜歡夜宴,詩(shī)詞中多有描寫,如李白《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會(huì)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lè)事”,堪稱千古名篇。還有白居易的《宴散》:“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tái)”,曾為魯迅先生所贊賞,說(shuō)真會(huì)寫富貴景象。實(shí)際上,白居易的《琵琶行》也是寫夜宴的,只是在船上:“移船相近邀相見(jiàn),添酒回?zé)糁亻_(kāi)宴”,清歌當(dāng)酒,弦上濺淚,讓人一曲難忘。
繪畫也有,最有名的是《韓熙載夜宴圖》,是南唐畫家顧閎中所作,構(gòu)圖完整,色彩恢麗,場(chǎng)面宏大,人物眾多,畫里畫外都有許多故事。前些年有個(gè)女作家叫吳蔚,還據(jù)此寫了一部小說(shuō),就叫《韓熙載夜宴》,曾經(jīng)讀過(guò),印象不是很深。
就小說(shuō)而言,寫夜宴最有意味的,我覺(jué)得還是《紅樓夢(mèng)》,即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kāi)夜宴。”這是接前一回講述,賈寶玉過(guò)生日。本來(lái)已在白天慶過(guò)生日了,很正式,很熱鬧,各種應(yīng)酬、禮節(jié)、講究,而這一回是到了晚上,意猶未盡,怡紅院的丫頭們也要替主人慶生,從襲人、晴雯、麝月、秋紋等大丫頭到芳官、碧痕、小燕、四兒等小丫頭,分等級(jí)實(shí)行AA制,湊份子備了酒果,擺上花梨圓炕桌,覺(jué)得人少了沒(méi)趣,于是又差人打著燈籠,分別去把寶釵、黛玉、探春、李紈、湘云和寶琴也都請(qǐng)來(lái),然后夜宴才正式開(kāi)始。
“怡紅夜宴”寫得如詩(shī)如畫,意味深長(zhǎng)。德國(guó)漢學(xué)家顧彬說(shuō),《紅樓夢(mèng)》是“為中國(guó)年輕人寫的生活祈禱書”,而這種祈禱,就況味別傳地體現(xiàn)在“怡紅夜宴”中,如同全書的縮影,不僅是人生禮儀的藝術(shù)展現(xiàn),也是少女們集體的青春祈禱與嘉年華。
這真是謎一般的夜宴,不僅女孩子們的“占花名”游戲大有深意,各自抽到的花簽及詩(shī)句對(duì)每個(gè)女孩的性格命運(yùn)構(gòu)成了隱喻和象征,而且,就連參加夜宴的人數(shù)和座次排列也眾說(shuō)紛紜,頗費(fèi)猜測(cè)。于是就有了“怡紅夜宴圖”——紅學(xué)家們根據(jù)小說(shuō)的敘述,做出了不同的推算,繪出了不同的圖示。
這些圖示,本身有多大意義姑且不論,據(jù)說(shuō)還都不夠完美,和書中的描寫多少總有差異,或差在人數(shù)上,或差在酒令點(diǎn)數(shù)上。我覺(jué)得這很正常,一場(chǎng)夜宴,當(dāng)時(shí)是怎么坐的,誰(shuí)挨著誰(shuí),誰(shuí)擲了幾個(gè)點(diǎn),即使全憑記憶來(lái)寫,也難免有所疏漏。西諺有云:“To err is human(出錯(cuò)是人性的)”,更何況這是小說(shuō),也談不上錯(cuò)不錯(cuò)的。但有人偏要上下求索,志在創(chuàng)新,把有關(guān)數(shù)據(jù)輸入計(jì)算機(jī),用計(jì)算機(jī)模擬這次夜宴的布局和座次。結(jié)果出來(lái)之后,人人稱奇,說(shuō)還是人工智能厲害,計(jì)算機(jī)模擬的怡紅夜宴圖竟恰到好處,從整體到細(xì)節(jié),找不出任何瑕疵。
作為一個(gè)傳統(tǒng)的讀書寫作者,我對(duì)諸如此類的實(shí)驗(yàn),總是不愿相信,也缺乏興趣。但閑來(lái)無(wú)事,出于好奇,就把那幾張圖示查到,反復(fù)比較,看了又看。而看過(guò)之后,仍不甚了了,遂拍照轉(zhuǎn)發(fā)到某個(gè)微信群,向群里的一些師友們請(qǐng)教。大半天沉寂之后,有位大學(xué)教授關(guān)注到了,發(fā)表意見(jiàn)說(shuō),這些圖雖然簡(jiǎn)單,卻也值得討論,宴席座次的排列,總該和傳統(tǒng)禮儀、歷史文化有點(diǎn)關(guān)系吧?
此言一出,響應(yīng)者漸多,有考證的,有思辨的,著實(shí)讓這個(gè)群熱鬧了兩天。綜合大家的看法,以下觀點(diǎn),都是針對(duì)計(jì)算機(jī)模擬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中國(guó)是禮儀之邦,凡重要的節(jié)慶場(chǎng)合,包括宴會(huì),每個(gè)人的位置都是有講究的。按周代禮俗,最重要的位置是坐西朝東,這是主人的位置,看《史記》鴻門宴的描寫就知道了,項(xiàng)羽就是坐西朝東的:“項(xiàng)王、項(xiàng)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余英時(shí)有《說(shuō)鴻門宴的座次》一文,指出項(xiàng)羽不以賓主禮招待劉邦,卻似當(dāng)成了自己的臣屬,云云。而經(jīng)過(guò)時(shí)代演變,到了清代,餐桌禮儀已有所變化,與漢代不同,坐北朝南才是最重要的位置。以《紅樓夢(mèng)》七十一回為例,賈母宴客,“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敘便是眾公侯的誥命。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xiāng)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一席,方是賈母主位。”即主賓以面南為尊,次者再東西分坐,陪客在東,主人在西。
《紅樓夢(mèng)》中還有幾次宴會(huì)的描寫涉及座次,如三十八回賞桂吃蟹、五十三回元宵家宴,也大致循此禮俗,雖是家人宴請(qǐng),還是要以北為尊,以東為上。
以這樣的習(xí)俗規(guī)矩來(lái)看怡紅夜宴圖,就不難發(fā)現(xiàn),計(jì)算機(jī)模擬的圖示大可質(zhì)疑,因?yàn)榘催@個(gè)圖示,正北面南而坐的是晴雯,正南面北的是寶玉,正東面西的是寶釵,正西面東的是四兒。主要問(wèn)題是在那個(gè)正北朝南的座位,究竟該誰(shuí)來(lái)坐?按道理是給寶玉過(guò)生日,不說(shuō)他是怡紅院主人的身份,作為壽星他也應(yīng)該在上座。而如果按賓主之位,那當(dāng)時(shí)的主賓則應(yīng)是李紈或?qū)氣O,李紈是長(zhǎng)嫂,寶釵是外客,這一點(diǎn),紅學(xué)家們已充分考慮到了。如在俞平伯的圖示中,正北是李紈和寶釵;在周紹良的圖示中,正北則是寶釵。還有一些其他研究者的圖示,正北而坐者也基本上是李紈,或?qū)氣O、黛玉等小姐身份的女孩。顯然,這是情理之中的座次,但卻被計(jì)算機(jī)給顛覆了。讓“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丫鬟晴雯坐在上座,我們當(dāng)然贊同,一千個(gè)贊同,一萬(wàn)個(gè)贊同,但關(guān)鍵是有點(diǎn)不合情理,像賈府這樣的“詩(shī)禮簪纓之族”,雖然是夜宴,也不太可能讓一個(gè)丫鬟——不管她多么聰明美麗,坐在這個(gè)位置上吧?
總之,大家意見(jiàn)比較一致,都是不太相信人工智能,而更愿意相信人本身。這個(gè)群是人才密集型的,有多位教授和作家、評(píng)論家,可謂舊學(xué)邃密,新知深沉,各抒己見(jiàn),精彩紛呈,不說(shuō)別的,僅那種學(xué)術(shù)態(tài)度、人文立場(chǎng),就足以令人感動(dòng)。最后,還有人做主旨性發(fā)言,說(shuō)計(jì)算機(jī)也好,機(jī)器人也好,你能輸入知識(shí)和數(shù)據(jù),卻很難輸入智慧和情感;你能輸入智慧和情感,卻很難輸入各種講究、面子、道德、禮儀、風(fēng)俗、信仰、想象力和價(jià)值觀。不是嗎?凱文·凱利認(rèn)為,計(jì)算機(jī)和機(jī)器人是“人類的孩子”,我們必須首先給它們輸入價(jià)值觀,而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
和師友們達(dá)成這樣的共識(shí),我的心情很透亮,有幾次出去講課,還以此為例,講什么是人文精神,侃侃而談的架勢(shì)。但去年春節(jié)前回老家一趟,這種好心情卻被破壞了。那次是順便到同學(xué)家看看,正趕上殺豬,人不少,堅(jiān)持讓我留下吃飯,同去的還有鄉(xiāng)里的一位副書記。放好桌子擺上菜,同學(xué)就讓我和副書記脫鞋上炕,坐里面。我再三推辭,說(shuō)老親少友的,按輩分吧,同學(xué)說(shuō)不在你,這不有鄉(xiāng)領(lǐng)導(dǎo)嗎?于是就安排我和副書記坐在炕里,然后開(kāi)席,親友們逐個(gè)敬酒,很講究的。我在外工作多年,突然被讓到炕里盤腿坐,不太習(xí)慣,就左顧右盼的,偶一回頭,發(fā)現(xiàn)自己實(shí)際上是背對(duì)南窗戶,也就是說(shuō),我和副書記都是面向正北的。
這不啻為一次轟毀和頓悟,是啊,大觀園里會(huì)不會(huì)有炕呢?怡紅夜宴,假如那些如花似玉的少男少女,都是圍坐在炕上,賈寶玉和金枝玉葉的小姐們坐在炕里,而晴雯作為丫鬟,端張椅子,近炕坐下,那不更合情合理嗎?禮儀要看具體情境,實(shí)踐才是檢驗(yàn)的標(biāo)準(zhǔn),而這樣看來(lái),不管你多么不想承認(rèn),關(guān)于怡紅夜宴,計(jì)算機(jī)的模擬才是唯一正確的,甚至幾乎是完美的。
為了求真,我把這次還鄉(xiāng)的經(jīng)歷也發(fā)到群里,征求大家的看法。開(kāi)始還是沉寂,幾天之后,才有回應(yīng),抉幽發(fā)微,有理有據(jù),看來(lái)懂紅學(xué)的還真不少——
原來(lái),《紅樓夢(mèng)》中果然是有炕的,如第三回寫林黛玉初進(jìn)榮國(guó)府,拜見(jiàn)王夫人時(shí),就有對(duì)炕的描述:“臨窗大炕上猩紅洋,正面設(shè)著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shè)一對(duì)梅花式洋漆小幾。”其實(shí)不僅是王夫人等年長(zhǎng)者的居室有炕,連鳳姐這樣年輕的奶奶也是如此,如書中寫劉姥姥一進(jìn)榮國(guó)府,周瑞家的引她到鳳姐屋內(nèi):“只見(jiàn)門外鏨銅鉤上懸著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氈條,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gè)鎖子錦靠背與一個(gè)引枕。”
總之不僅有炕,而且是南窗下的炕,也就是南炕。顯然,這樣的南炕在大觀園,至少在怡紅院中,也是必有的。不說(shuō)別的,僅開(kāi)頭提到的那張“花梨圓炕桌”就足可證明了,為賈寶玉慶生的夜宴就在炕上舉行的。至于賈府作為貴胄之家,是否風(fēng)俗融南北,有床也有炕,而炕主要是木炕,不生火,僅作為某種豪門裝修的形式,則都不必詳引細(xì)論了。
實(shí)際上,有人指出,炕在《紅樓夢(mèng)》中不僅是裝修的形式,而且是文化的形式,禮出大家,必須有炕,客人來(lái)了,先讓上炕,讓至炕里,端水遞煙,這種以炕為尊的習(xí)俗,既是風(fēng)情畫,也有儀式感,就連普通的鄉(xiāng)野人家、小門小戶也是如此,作為北方民俗的鮮明標(biāo)志,很多地方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
是啊,必須有炕,以炕為尊,我的老家就是這樣,從童年到青少年時(shí)期,對(duì)故鄉(xiāng)的記憶如夢(mèng)如幻,都是和炕分不開(kāi)的,就像我年前去同學(xué)家的情形,姐姐們住家,親戚們來(lái)家,包括讓我們受寵若驚的客人光臨,老師來(lái)訪,接兵的班長(zhǎng)來(lái)訪,家中何所有,唯有熱炕頭,先把客人讓到炕里,講究的還要鋪一條氈子,就算是最高禮遇了。而這么多年,我怎么把炕淡忘了呢?不僅我,還包括那些紅學(xué)家,雖然他們不一定生長(zhǎng)在北方農(nóng)村。
因?yàn)楹雎粤丝唬t學(xué)家們的怡紅夜宴圖難免多有紕漏,而因?yàn)轭A(yù)設(shè)了炕的存在,計(jì)算機(jī)實(shí)現(xiàn)了唯一正確的模擬。也許給計(jì)算機(jī)輸入價(jià)值觀是不太可能的,但畢竟可以給它輸入天文地理和民俗學(xué)的知識(shí),如《清稗類鈔》之類:“炕之為用,不知其所由起也。東起泰岱,沿北緯三十七度,漸迤而南,越衡漳,抵汾晉,逾涇洛,西出隴阪,凡此地帶以北,富貴貧賤之寢處,無(wú)不用炕者。”
“夜宴圖事件”——正像有人在群里說(shuō)的,這幾乎稱得上是一個(gè)事件,它讓我們重新思考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與其創(chuàng)造物的關(guān)系,人創(chuàng)造的計(jì)算機(jī)、機(jī)器人或人工智能,將來(lái)會(huì)不會(huì)覬覦人作為萬(wàn)物靈長(zhǎng)的地位,進(jìn)而取代人、戰(zhàn)勝人、驅(qū)使人呢?
有人說(shuō)不至于,這只是紅學(xué)研究中的小問(wèn)題,微不足道;也有人說(shuō)細(xì)思恐極,這關(guān)乎人存在的價(jià)值和意義。還有人引木心,說(shuō)木心先生曾感嘆“《紅樓夢(mèng)》仿佛是紅學(xué)家寫的”,而如今更要換一種說(shuō)法,這部書還可能是計(jì)算機(jī)寫的,機(jī)器人寫的。這其實(shí)也并非不可思議,已經(jīng)有很多實(shí)驗(yàn)了,從深藍(lán)、阿爾法狗到ChatGpt,證明機(jī)器人不僅可以下棋博弈,也完全可以從事文學(xué)寫作,包括賦詩(shī)填詞。
幾天后,誰(shuí)把一位資深的研究員也拉進(jìn)群里,說(shuō)有紅學(xué)方面的著作,還是全國(guó)紅學(xué)研究會(huì)的理事,很權(quán)威的。他對(duì)我們討論的問(wèn)題似乎有點(diǎn)不屑,只淡淡地說(shuō),計(jì)算機(jī)模擬所參照的是比較新的《紅樓夢(mèng)》版本,和紅學(xué)家們依據(jù)的版本都不一樣。
這幾乎是一個(gè)及時(shí)的拯救,讓我們心里都松一口氣。而且,這位紅學(xué)家還發(fā)來(lái)一張圖片,是清代無(wú)名氏所畫的《怡紅夜宴圖》,解釋說(shuō)這可以在網(wǎng)上查到,屬于工筆畫,色調(diào)清雅,筆法流暢,整體感和細(xì)節(jié)描繪都好。畫中的座次,更是明白無(wú)誤,面南而坐的是寶玉、黛玉、寶釵三位,所謂金玉良緣,木石前盟,在此青春將暮、芳華薈萃之際,一并得以歷歷展示。
但幾天后又有人質(zhì)疑了,說(shuō)繪畫不是地圖,方位是不確定的,未必是上北下南,而且畫家作這幅畫,也不過(guò)是迥得情趣而已,并非為了確證方位,所以此畫不足為據(jù)。還有小說(shuō)版本問(wèn)題,也無(wú)足輕重,因?yàn)椴还苁切掳姹具€是舊版本,只要是怡紅院有炕,只要是群芳都圍坐在“花梨圓炕桌”旁邊,那人物就基本上是這樣的排序,不可能推翻計(jì)算機(jī)模擬的準(zhǔn)確性。
討論到這里卡住了,紅學(xué)家沒(méi)有繼續(xù)發(fā)言,后來(lái)悻悻而去,退群了。不過(guò)退群前加了我私聊,說(shuō)有機(jī)會(huì)還可交流。
我本想就此沉默,想起哲學(xué)家維特根斯坦的教誨:“對(duì)于不可言說(shuō)的事情,我們只能保持沉默。”怡紅夜宴圖,也許就屬于不可言說(shuō)的事情。但總是心有不甘,況且事情是我引起的,一連幾周時(shí)間,自己都在耿耿于懷,意猶未盡。美國(guó)有個(gè)斯金納(B. F.Skinner)教授說(shuō)過(guò),真正的問(wèn)題不在于計(jì)算機(jī)是否會(huì)思考,而在于人是否會(huì)思考。說(shuō)得好,但怎么才算是會(huì)思考呢?
紅學(xué)家給我發(fā)來(lái)了微信,說(shuō)他想就“夜宴圖事件”寫篇文章,主要從版本學(xué)入手,分析計(jì)算機(jī)模擬的圖示所存在的問(wèn)題,寫好后準(zhǔn)備在《紅樓夢(mèng)研究》上發(fā)表,希望我能談?wù)勛约旱挠^點(diǎn),也許對(duì)他會(huì)有啟發(fā)。
我說(shuō)是這樣,我不認(rèn)為計(jì)算機(jī)的模擬是對(duì)的,但毫無(wú)疑問(wèn)的是,這個(gè)模擬是準(zhǔn)確的,而且應(yīng)該說(shuō)是太準(zhǔn)確了。
原來(lái)你是這樣看!紅學(xué)家有點(diǎn)失望。
是的,我發(fā)個(gè)笑臉:借用一個(gè)英文句式吧:too correct to be right(太準(zhǔn)確了,所以不夠正確)。
怎么理解呢?
沒(méi)什么,我說(shuō),這只是看問(wèn)題的一種方法。就像太聰明了,反而不夠高明(too clever to be wise)。
你好像在談?wù)撜軐W(xué)。
是啊,我覺(jué)得也像,但請(qǐng)聽(tīng)我把話說(shuō)完吧。人生有許多過(guò)猶不及,計(jì)算機(jī)也是。計(jì)算機(jī)的問(wèn)題在于它有一個(gè)天生的盲點(diǎn),那就是忽略了人是會(huì)出錯(cuò)的。不僅人的生命記憶不可能像計(jì)算機(jī)那樣準(zhǔn)確,而且也不屑于追求那種準(zhǔn)確。
等一等,紅學(xué)家說(shuō),我覺(jué)得有點(diǎn)亂。
不是有點(diǎn)亂,是特別亂。有個(gè)西方哲學(xué)家說(shuō)過(guò):出錯(cuò)是人性的,但要把所有的事情搞亂,則需要一臺(tái)計(jì)算機(jī)。
能告訴我是哪位哲學(xué)家說(shuō)的嗎?
對(duì)不起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不想去查,因?yàn)檫z忘也是人性的。也許未來(lái)的什么時(shí)候,就像某些人所預(yù)言和擔(dān)心的那樣,當(dāng)計(jì)算機(jī)或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了人,人也仍然是不可取代和戰(zhàn)勝的,因?yàn)椋说淖詈罅α颗c尊嚴(yán),可能就在于他會(huì)出錯(cuò),會(huì)遺忘,會(huì)忽略,會(huì)記不準(zhǔn)……
已經(jīng)快到午夜,紅學(xué)家已經(jīng)不再回話。我知道對(duì)他而言,我上面的感想沒(méi)有任何意義,但他如果真想就“夜宴圖事件”寫一篇像樣的論文,下面這句話也許還不乏啟示,于是就一并發(fā)給了他:
——至少計(jì)算機(jī)是寫不出《紅樓夢(mèng)》的,因?yàn)檫@樣的書是充分展現(xiàn)人性的,體現(xiàn)著人的全部自由、價(jià)值、尊嚴(yán),以及生命之脆弱和過(guò)失的語(yǔ)言藝術(sh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