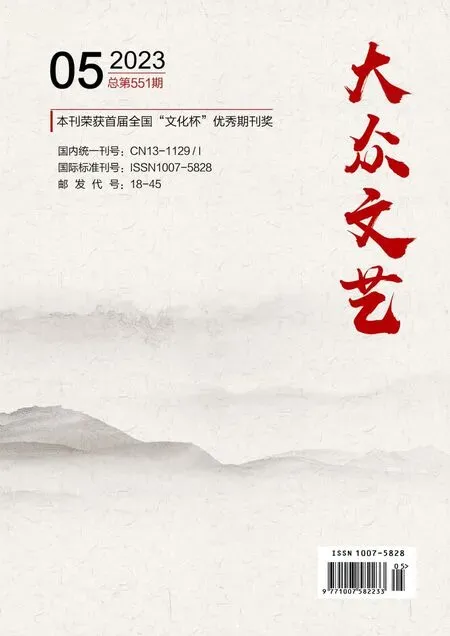新世紀鄉土文學中農村女性困境研究
瞿 靖
(湖南文理學院芙蓉學院,湖南常德 415000)
21世紀以來,鄉土文學的創作十分繁榮。它是20世紀20年代鄉土小說的變種。隨著打工浪潮的出現,城鄉遷移更加頻繁,鄉下人進城成為焦點。由于城市優厚的物質條件,導致鄉下人雖然非常努力想要扎根城市,但是始終處于邊緣的他者地位,生活和精神層面都面臨著困境;而且對于留守農村的鄉下人而言,也同樣面臨著生活和精神的雙重困境。由于農村女性作為特殊的文化符號,有著地域和性別的雙重身份,這種城鄉困境在她們身上表現尤為突出。究竟是去是留,這些女性應該做怎樣的抉擇?鄉土文學又將如何發展?作家也在試圖為之尋找出路。
一、進城農村女性與城市主體的矛盾
城鄉關系在不同時期的鄉土文學中,隨著時代發展,也在發生著變遷。現代鄉土文學中,城市只是作為背景和參照物而存在,往往與鄉土世界呈現對立的關系,沈從文堅定以“鄉下人”自稱可窺見一二。20世紀80年代以后,城鄉互動加強,城鄉地位也逐漸趨于不平衡。城市開始成為文明、先進的文化隱喻,農村人開始向往能夠扎根城市。21世紀以來,以打工文學為主體的鄉土文學更是屢見不鮮地思考著城鄉關系下的人的存在。在這些文本中,城市依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讓農村女性心生向往,渴望扎根城市,但是由于地域和性別的差異性,這些女性面臨著生活與精神的雙重困境。
進城的農村女性往往作為城市的他者而存在。“外地人”“外來工”等這些常見的詞最明顯地指示了一個外來者的身份。由于性別和地域的雙重身份,加之知識水平和職業技能低下,農村女性進入城市只能游走在城市的邊緣之地。縱觀她們的職業,基本上屬于服務業:酒店服務人員、住家保姆以及工地勞動者……即使與城市格格不入,但是她們的共同目標是將城市視為人生最理想的境地。孫惠芬《舞者》中的主人公“我”慶幸農村放映員不娶“我”,因為“我”要嫁到城市里去。王安憶《富萍》里的富萍,歷經艱難險阻最終扎根上海。
這些女性只身來到城市,身處底層,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十分糟糕。她們工作十分艱辛,要么出賣體力;要么面對客人的挑剔委屈接受;要么忍受著老板的無理壓榨。周大新《湖光山色》主人公暖暖在北京從事清潔家政工作,一個月工資五百多,和姐妹們擠在一起,中午吃一塊五的盒飯。盛可以的《北妹》錢小紅進了玩具廠,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八個人一間房。《穿過憂傷的花季》向華萍初中輟學,和父母一家人擠在狹窄的建筑工棚中,衛生間和浴室都是公共空間,沒有女性私人空間。
對于這些進城的農村女性而言,更悲慘的是面臨精神困境。斯皮瓦克在《底層人能說話嗎?》中,尖銳剖析了第三世界女性受到白人中心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的雙重話語霸權的壓制,二者都會導致女性失語,“在父權制與帝國主義之間、主體建構與客體形成之間,婦女的形象消失了。”[1]借用斯皮瓦克的女性批判理論,可以從城/鄉、男性/女性兩個角度來解讀雙重精神困境。
第一重精神困境指的是這些女性作為農村人,并沒有得到城市主體的身份認同,始終作為他者而存在,在城/鄉沖突中便產生了焦慮和危機感。這些進城的農村女性熱愛城市,但是她們并沒有掌握城市話語權,依然游走在城市邊緣,不能得到城市的認同。社會學中認為“社會群體有一致的群體意識和規范。群體成員在交往過程中,通過心理與行為的相互影響或學習,會產生或遵守一些共同的觀念、信仰、價值和態度。”[2]城市作為權利的一方,也會無形中規訓這些女性。為了獲得社會身份認同,進城的農村女性首要任務就是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讓自己同城市人趨于一致。《湖光山色》中的暖暖在北京學會穿衣打扮,渴望嫁給城市青年。孫惠芬《吉寬的馬車》中的許妹娜嫁入城市后,一改農村中進屋不脫鞋的習慣,嫌棄吉寬的不文明行為。《明惠的圣誕》中明惠進入城市后將自己更名為圓圓,也寓意著放棄與農村的關系,選擇融入城市。而王安憶《富萍》中的保姆奶奶更是城鄉結合的產物:臉色是黃白,既不屬于城里人的白,又不屬于農村人的黑,口音夾雜著變味的家鄉話和上海話,并且奶奶心氣很高,認為只有淮海路當屬上海城市中心,所以她只在淮海路人家里當保姆。
第二重精神困境是從男女性別出發,她們作為女性,面對城市的男性群體,依然是他者的存在。這意味著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與沖突。進城的農村女性想要扎根城市,比男性更加困難。波伏娃《第二性》里曾提到“女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對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體(the Subject),是絕對(the Absolute),而她則是他者(the Other)。”[3]《吉寬的馬車》中許妹娜用無愛的婚姻交換了城市身份;《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的李平與酒店老板相愛,但是最終遭到拋棄。
二、留守農村女性與農村社會的沖突
很多鄉土文學濃墨重彩地描寫了進城務工的女性形象,但是隨著打工浪潮的出現,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村的社會結構、人際關系以及家庭倫理道德都無一避免地受到沖擊,農村社會發生了轉型。那么對于留守女性而言,在轉型的過程中自然也會受到影響,同樣面臨著生活與精神的雙重危機。
農村留守女性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城市退守農村的女性。例如《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的李平,她在城市中受過情傷,最終選擇了老實巴交的進城務工者成子。原本以為逃離了城市,逃離了傷痛,但是在農村,李平依舊是一個受害者。另一類原本就是本土居民,包括留守兒童與留守成年女性。
留守女性的第一重困境是作為女性,在農村,依然會遭受到很多束縛。相比男性,農村對女性更為苛刻。《北妹》中錢小紅由于身體豐滿,在農村飽受非議。何慶邦《家園何處》中19歲的停之所以外出打工,主要是因為三哥出事,三嫂認為是主人公停的到來導致災難,所以對她態度言語不好,被迫離開家鄉。
在農村,留守女性除了面對性別所帶來的困擾以外,還要面對沉重艱辛的生活困境。城市相比農村,在經濟、教育、醫療等各方面都占據著巨大的優勢,這導致很多農村青壯年紛紛去城市尋找出路。孫惠芬筆下的歇馬山莊幾乎所有的男性都選擇外出務工,只有年末才會短暫回鄉。男勞動力的缺失,使得留守女性除了一年到頭在田間地頭干著沉重的農活,還要承擔照顧一家老小的重擔。《歌者》中的母親坐月子還要照顧小孩。《下山去充電》這部小說更是毫無保留地展現了留守女性的生活困境,主人公桃花既要拉車套馬,又要背石頭砌豬圈,還要照顧一家老小。
除去沉重的生活困境,留守女性還會面臨家庭代際關系所帶來的沖突與壓抑感。隨著城鎮化發展,過去的傳統家庭人際關系也在慢慢發生著變化,最為明顯的便是婆媳關系。鄉土中國里的婆婆具有絕對的話語權。但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與發展,這種關系出現了逆轉,為了爭奪話語權,雙方自然會產生矛盾和沖突。孫惠芬作品《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潘桃與婆婆的關系就發生了變化。二人矛盾焦點就是采用何種結婚方式。這背后折射著農村生活方式的轉變。婆婆想要舉辦一場盛大的農村喜宴,但是潘桃向往城市的旅行結婚,最終以婆婆失敗告終,但是婆媳矛盾的星火就此埋下。反觀選擇逃離城市的李平,以為退守農村就能找到幸福的樂園,可是事與愿違,姑婆對李平提出了諸多苛刻的要求,以至于最后由于謠言,李平遭受丈夫的毒打,這一切都在印證著留守女性的悲劇命運。
留守女性的精神困境,還體現在她們的情感的訴求。丈夫的缺失無疑給農村家庭增加了家庭危機,也折射出農村留守女性的情感危機。由于丈夫一年外出打工,留守女性一方面擔心丈夫安全與健康,另一方面又要擔心聚少離多,加之婆媳關系緊張,受了委屈無人傾訴,心理壓力無疑增大,由此產生了無法填滿的孤寂之感。《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潘桃和李平之所以能成為知己,關鍵點就在于二人的丈夫外出打工,婚后的寂寞無處排遣,最終發現了彼此。《吉寬的馬車》中以二嫂子為代表的農村留守女性經常會逗弄嬉笑村里唯一的男性青年——吉寬,這些舉動皆可窺探到留守女性的孤獨寂寞之濃。《下山去充電》濃墨重彩地描寫了留守女性的細微的心理世界。當家里老人孩子生病,盜賊偷東西時,桃花便沒有了主心骨,更重要的是為了能和丈夫打一通電話,獲取一點情感慰藉,還必須得拿著手機去鎮上充電,當她弄丟了別人的手機時,那種彷徨、焦慮和痛苦的心理刻畫得非常成功。
新世紀鄉土文學大多講述著已婚的成年留守女性的故事,但是在為數不多的文本中,依然還涉及了一些留守兒童的生命情感經歷。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4]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902萬人。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于1943年在《人類動機理論》中認為人有歸屬和愛的需求,由于留守兒童長期與父母分離,缺少安全感,《穿過憂傷的雨季》女主人公陳星兒和奶奶留守在家,相依為命,為了上課不遲到,買了一輛自行車,可是當視為生命的自行車丟失后,陳星兒顯得孤獨無助,同學陳軍給處于人生黑暗中的星兒帶來些許溫暖,二人惺惺相惜,然而這種無比珍貴的友誼卻被村里的閑言碎語所擊碎,朋友的離開,星兒更加孤獨無依。而好朋友向華萍也是留守兒童,家庭親情缺失,導致她只能借助異性的情愛,來彌補缺失的家庭之愛,最后的命運便是被強制輟學去城市打工。
三、路在何方——關于新世紀鄉土文學及農村女性命運的思考
新世紀鄉土文學中,隨著更多人關注到這些進城務工者的生活和精神困境,國家從經濟、政治、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發力,使得進城務工者的生活以及精神困境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面對扎根城市的農村女性悲慘遭遇,作家表達了他們的關愛與思考。作家鼓勵進城女青年腳踏實地地奮斗與生活,時刻保有一顆純善之心。王安憶《富萍》中的女主人公富萍雖然是保姆,但是憑借自己的誠實勞動最終收獲了愛情和家庭,在上海扎下根。同時這些作家也在告誡進入城市的女性不能墮落,需要提升自己,自強不息。盛可以《北妹》中的錢小紅和李思江兜兜轉轉,輾轉無數個城市和工廠,遭遇過男性的情感背叛,最終決定提升自身價值,打算讀自考,而她們的同事吳櫻則參加了電腦培訓,還學習了企業管理。
但是在振興鄉村的時代背景下,對于留守農村的女性而言,應該如何抉擇呢?周大新《湖光山色》主人公暖暖的經歷可為農村女性尋找到出路提供一些借鑒方法。暖暖作為返鄉者,在機緣巧合下,她發現了楚長城,還接待了北京高校的專家,最后暖暖結合當地的生態和旅游資源,開始了創業之路:接待研究者和游客,開民宿,當導游,搞旅游,開游船,辦采摘園,大興度假村,進行舞臺戲劇表演等等。當然周大新還對農村的道德和人性進行了一定思考,暖暖和丈夫面對利益,二者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暖暖堅守了道德與人性。這些都是作家對農村留守女性如何進行命運抉擇的思考,也是對如何振興鄉村的一些思考。
當然,如何解決留守女性的精神困境,可以借鑒《拯救文化站》這部小說里的做法:米鄉文化站老陳辦了圖書館,館藏了很多科技相關的書籍,文化站還會組織放電影等娛樂活動,其中農村女性王銀花還進行剪紙活動。這些措施都可以增加農村生活的豐富性和娛樂性,為農村留守女性提供有營養的精神食糧。當然,最主要的還是要大力促進農村經濟建設,吸引農村勞動力返鄉創業或就業,這樣既能解決家庭生計問題,又能解決留守問題。
然而除了關注農村女性的去留出路問題,還需要新世紀鄉土文學的出路問題。鄉土文學關注現實,關注農民工等群體,具有人道主義價值與意義,但是由于質量良莠不齊,在某些方面也為人所詬病。以下將是淺略的建議:
1.文本內容需要更加多元化。新世紀鄉土文學最主要的是關注城鄉關系下的人的存在。作家對于城鄉二者的關系不能簡單處理,應該跳脫出簡單刻板的二元對立下的城鄉沖突樊籠,變為多元化的城鄉一體化書寫。主題也應該多元化,不僅要關注農村的轉型與發展,更要關注農村的道德價值建構。
2.構建農村女性主體性。鄉土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不能僅僅停留在初期的扁平人物階段,而應該具有立體性和豐富性,更能體現女性主體性,要展現這些女性鮮活的生命力,挖掘生命本體的本質,構建主體性。
3.敘事手法多樣化。傳統的鄉土文學敘事偏重現實主義手法,雖然很契合現實社會,但是很容易造成審美疲勞,可以多借鑒其他的藝術手法。改變陳舊老套的情節敘述,打破單純第三人稱或者第一人稱講述,多種敘事方式相結合,突破時空限制,虛構與非虛構交融,跨學科跨文體交互式寫作。
結語
在振興鄉村時代語境下,關注農村,關注城鄉一體化發展,關注農村女性抉擇和命運都是文學應該思考的命題。雖然新世紀鄉土文學在有關城鄉的書寫中,更多是羅列和陳述農村女性困境,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它的現實價值和社會意義。至于這些女性要走向何方,怎么走,鄉土文學又將如何發展,還需要進一步思考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