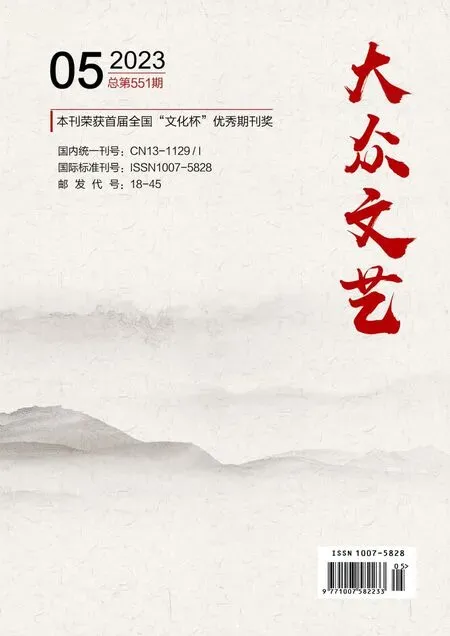論戲劇人物造型設計的意象營構
王 婧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浙江杭州 310053)
意象一詞來源于中國傳統哲學與詩學,顧名思義,意,指心意;象,指物象。學術界眾多學者一直將意象認為是藝術的核心要素,認為藝術即意象。意象范疇的內涵相當豐富,國內外從文化學層面、心理學層面、符號學層面、藝術與審美層面均有大量的理論研究。本文所論述的“意象”,是從審美意象和文化意象的角度出發,基于二者之上而貫穿于藝術創造之中的藝術意象——探討戲劇人物造型設計的意象營構,即如何將朦朧的視像與意念、情感等綜合在一起有秩序的組織起來、創造出一個鮮明生動舞臺藝術形象。
戲劇人物造型設計是戲劇舞臺演出的重要一環,它以角色的外部形象的視覺形式呈現,是具體的舞臺符號表現中的表現性的“形象”,必然蘊含具有舞臺表現性的特質,即經過藝術化處理的人物形象。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主觀的“意”和客觀的“象”的結合與轉變的過程,也就是融入藝術家情感的“物象”,是賦有某種主觀意味的具體人物形象,[1]本文將從戲劇人物造型的意象構思、戲劇人物造型的詩化意象營構、戲劇人物造型的間接意象營構三方面進行論述,探討戲劇人物造型創作如何運用文化意象的材料與審美意象的表現手段與方式進行意象營構。
一、形象種子——戲劇人物造型的意象構思
演出形象的種子是徐曉鐘提出的導演總體構思中的一個概念。又稱演出的總體形象立意,是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中的“角色性格種子”生發而來,意指戲劇舞臺的總體意象,是導演構思的產物,在全劇中處于主導地位,貫穿全劇的核心意象。徐曉鐘說:“形象種子……是生發整個演出的各種具體形象的種子”。[2]形象種子的重點并不在于生發形象,而是生發舞臺意象。
本文中所論述的“形象種子”概念特指戲劇人物造型設計對角色的外部形象(服裝造型和化妝造型)意向構思的過程,這個形象種子必須能夠觸發設計者的靈感,能夠準確形象地概括主要人物的性格、氣質、處境、命運等。戲劇人物造型設計的意象構思需要將文本視象轉化為舞臺視象,將思想意蘊的東西轉化為可視的人物形象,這需要創作者具備豐富的生活經驗和藝術儲備,從浩瀚的生活細節中提煉出典型、準確的人物外部形象,并且能夠從情感上與觀眾產生共鳴,誘發觀眾的聯想。這個過程是創作者基于生活、從量變到質變的藝術呈現。當然,戲劇人物造型的創作意象構思必須在導演構思的總體意象的統攝下進行。
戲劇人物造型是有著某種現實基礎的,或者是對實相的模擬,或者是對現實的變形,但亦離不開其總體上的藝術假定。我們以易卜生經典戲劇作品《海達·高步樂》中的海達和泰勒兩位女性的造型為例。海達是一個貴族女子,父親是將軍高步樂,從朱黎阿姑姑對海達的描述中:“你不記得從前咱們時常看見她騎著高頭大馬,跟著將軍在大路上飛跑?她穿著那套黑色的騎馬裝束——帽子上還插著翎毛。”我們可以勾勒出海達美麗大方,舉止優雅,性情高貴的外部形象。“帽子上插著的翎毛”這個形象種子是形象且準確的,它表現出了海達的出眾、優越和驕傲。這為本劇的基本矛盾——詩意的海達與乏味的生活之間的矛盾做了鋪墊。而劇中的另外一名女子——海達的同學和情敵泰遏的形象,則與海達截然不同。劇本中的泰遏“體質較弱,容貌秀麗,兩只淺藍眼睛又圓又大,有點突出,臉上帶著驚疑的神情。頭發淺黃而多。穿著精致而不十分入時。”出身貧賤家庭的泰遏似乎與高貴的海達是丑小鴨與白天鵝的區別,卻成了情敵,這讓驕傲的海達無法忍受,構成了本劇的另一個戲劇矛盾。柏林德意志劇院上演的同名話劇中,女主海達的人物造型設計摒棄了劇本中的時代特征,強化了人物的內在性格特征。第一幕,度蜜月歸來的海達身著一件黑色蕾絲長裙,內襯白色的絲綢抹胸裙,勾勒出海達美麗窈窕的身姿,優雅中透著性感,干凈的盤發上帶著形似王冠的珍珠發飾,人物的整個形象就像一只驕傲高貴的黑天鵝。而造型中最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裙子夸張高聳的肩部設計,輪廓像是天使的翅膀,又像是一顆心的形狀,而鏤空黑紗質地給人的感覺又華麗而脆弱的,仿佛一戳就破,似乎在暗示人物矛盾的內心世界。舞臺上泰遏的造型是一條紅白咖抽象條紋相間的波希米亞風格的連衣裙,粉紅色的高跟涼鞋,微卷的齊耳短發,體態略顯豐腴,這樣的穿著打扮無疑是普通的,與高貴的海達在舞臺上對比確實有雅俗之別。
話劇舞臺演出無疑將兩位女性這種外形上的差距夸大了。文本中“帽子上還插著翎毛”的海達與“精致而不十分入時”的泰遏,這樣的描述濃縮了作者對這兩位女性形象的出身、經歷、性格等方面的定位和寓意,對于舞臺人物造型的設計創作而言,可以視為對人物外部形象意象構思的“形象種子”。柏林德意志劇院版的舞臺人物造型創作抓住了這個形象種子的思想核心,大膽地跳脫了時代背景,并沒有將人物的外部形象運用現實模擬的方法進行創作,從視覺形象上更有力的強調全劇的思想主題。可見,形象種子并不一定要直接作為人物具體形象進行展示,它誘發設計者的創作意象,更作用于觀眾的心理觀感,使其產生意象,而非單純的展示視覺形象。
二、不似之似——戲劇人物造型的詩化意象營構
戲劇藝術具有詩性的特質。蘇珊·朗格曾指出:“戲劇是一種詩的藝術,因為它創造了一切詩所具有的基本幻想——虛幻的歷史”馬丁·艾思林在《戲劇剖析》中也曾說:“我們在舞臺上看到的戲劇,是一種精心制造的假象”。戲劇是人類生活的“鏡像,”是對自我、對生活的映射,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戲劇意象的營構,本質上就是為了追求一種真切的詩意,營造出一種動人的意境。基于此,戲劇人物造型設計的意象營構,其主旨也是舞臺視覺形象的詩化意象營構——一種獨特的“不似之似”藝術表達。
中國戲曲的裝扮藝術正是詩化意象的濃縮,它的核心是“離形得似”的藝術內涵。化妝臉譜化、服裝圖案化,這些戲曲獨有的寫意化的內在特征,是將客觀現實的主觀化。尤其是戲曲的臉譜藝術,高度凝練的運用圖案化的線條和色彩,從人的五官部位出發,運用夸張、變形、象征等手法以突出性格特征,兼有寓褒貶,辨忠奸,示身份、示年齡、示血親等功能,使觀眾能目視外表,窺其心胸。戲曲臉譜重在形、神、意等方面,不拘于現實生活的自然形態——大膽地進行夸張、裝飾,而又取形于生活——把現實生活中的某物象的自然形態取來,加以變化,使其圖案化、裝飾化,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在里面,通過“取形”來達到“離形得似”,突破形似以達到神似,正是戲曲藝術千錘百煉的藝術精髓。如京劇《華容道》中關羽的臉譜,關云長綽號美髯公,身高八尺,面如重棗,臥膽眉,丹鳳眼半睜半閉,五縷墨髯飄灑胸前。他的臉譜屬于整臉勾畫,由暖色紅為主色基調,黑色為對比襯托色,深黑色的臥蠶眉如春蠶橫臥,丹鳳眼細長似睜非睜,因關羽有“美髯公”之稱,會加上演關羽時專用的大髯口,這樣的裝扮造型生動的表現關公剛毅、肅穆的凜然正氣和高傲神態。關羽的臥蠶眉、丹鳳眼經過藝術化的夸張,通過過色彩、線條的組織設計,歸納到“形”的圖案中來,裝飾性的刻畫出人物的性格和神態,即是取于自然形態的藝術化創作、似與不似之間的生動意象。
如何營構“真實”而詩化的戲劇人物造型?戲劇人物造型設計是視覺意象的營構,訴諸觀眾的感官,舞臺上的人物外部形象必須要讓觀眾感到“真實”,以使觀眾全身心地投入于演出當中,這是人物造型區別于其他造型藝術的本質特點。那么,如何在“真實”的塑造人物的外部形象的同時,營造出真切的詩意?什么才是能夠讓觀眾信服的真實性?戲劇舞臺的藝術形態不同于生活形態,因此這種真實性同時也具有假定性。2007年在解放軍歌劇院上演的英國原版話劇《霧都孤兒》,舞臺上僅有三男兩女五個演員,扮演了二十余個角色,甚至主角奧利弗是由一位女演員扮演。這說明了人物的外部造型對于人物身份指示的重要性,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讓觀眾相信換了造型演員就變成了另一個角色。化妝師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時候,一定是注入了自己的審美情趣和藝術理想的,是藝術創作的產物,區別于自然形態。因此,寫實主義戲劇的化裝形象要求與“自然形態”沒有區別的、如同生活中的真實的人的形象一樣的“真實”,往往是在技術手段上力求真實,不能讓觀眾看到破綻和虛假,而呈現出的舞臺人物形象則是藝術化的,是經過加工、提煉,蘊含著藝術家理想的“真實”舞臺人物形象,這樣的舞臺人物造型是性格化的、典型化的。導演盧克·帕西瓦爾2014執導的《麥克白》是以當代戲劇手法闡釋麥克白“內心戲”的風格之作,劇中的言語、情節動作或被消解或被模糊,服化與造型都極盡簡約,色彩也僅呈黑白兩色,全然把戲劇重點放在麥克白的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變化與掙扎上。劇中唯獨使用了一頂紙做的王冠來示意麥克白的身份和整個故事的源起,而紙質地的王冠充滿了嘲諷的意味。這里的紙王冠在舞臺上,且戴在麥克白的頭上,對于手持票根來觀看莎士比亞戲劇的觀眾而言,它就是一頂真正的王冠,這有賴于具體的戲劇語境,有賴于人們約定俗成的想象。
人物造型作為一種舞臺符號承載著信息的傳達功能。創作者在文本中找到形象種子,進而在意象生成的創造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審美傳統所賦予的先在圖式,在戲劇人物造型設計中,這種歷史規定前提更為明顯。人物的裝扮和造型要受到其所處歷史環境、身份地位、地域特點等各方面的影響,尤其在寫實風格的戲劇中,這種影響更為突出。但誠如前文所述,歷史或審美的先在規范并不等同于原物的直接呈現,寫實主義并非自然主義。戲劇人物外部形象或形神兼備或離形得似,不似之似、是相非相之間的創造,是“真實”含義的深廣解讀,這正是戲劇人物造型意象營構的核心所在。
三、心理視像——戲劇人物造型的間接意象營構
藝術意象的生成,是在主客體的審美交流中呈現、在具體審美關系中實現的。在戲劇人物造型設計的創作過程中,從某種“形象種子”開始對舞臺角色進行意象化的構思,構思的內容不僅要包括角色外部形象必須傳達的身份信息等直接感知到的舞臺形象,即直接意象,還包括由直接意象的延伸和擴展,既非視覺化的想象的間接意象,進而達到傳神寫照的藝術目的。這里的間接意象,可指為觀眾通過對各種舞臺視覺形象的視覺感知、所構筑起的無窮無盡千變萬化的心理視像。
由此可知,戲劇人物造型設計的意象營構,是戲劇觀演過程中雙方共同創造的產物、是戲劇觀演之間審美交流的結果。人物的外部形象造型包括服裝造型和化妝造型,有指示人物身份、性格和命運的功能,準確的細節表達還可以揭示人物的特性。《龍須溝》中的丁四嫂這個人物,她的生活在龍須溝的小雜院里是最苦的,她的丈夫丁四沒有什么正經工作,還得靠她替人縫補衣服掙錢。在多個版本的《龍須溝》中,丁四嫂的衣著都是用大補丁來表現人物的生活的困窘,北京人藝版的話劇《龍須溝》則讓丁四嫂穿了一件男人的褂子,甚至還系錯位了褂子的扣子,把丁四嫂生活的艱難、忙亂,一切以丈夫孩子為先的生活境遇和性格準確的表現出來,這樣的造型細節是藝術化的,精煉的將人物的生活提煉,濃縮成典型的舞臺細節,足以說明很多問題。我們可以將這個細節看成是一個直接的戲劇意象表達,而觀眾在接收到這個細節后,會展開聯想和思考,在他們的腦海里形成對戲劇的間接意象,這就形成了觀演雙方對戲劇氛圍的共同營構。
從浸入式戲劇的經典之作《不眠之夜》中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觀演關系對戲劇意象營構的影響。《不眠之夜》改編自莎士比亞經典作品《麥克白》,故事發生在麥金儂酒店內。觀眾步入劇場必須帶上統一的面具,同演員一起站在舞臺中間、甚至被演員包圍。觀眾可以選擇任何一個場景探索,也可以選擇任何一個演員跟隨,自由的選擇決定了他所看到的那個故事,因此每一位觀眾的體驗歷程都是獨一無二的,它打破舞臺的約束,觀眾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參與其中自由探索的冒險者。在這部戲劇中言語并非主要表達方式,演員的人物造型就成了與觀眾交流的一種方式。在沒有一個所謂的“后臺”的舞臺,演員所有的換裝都在觀眾眼皮底下進行,角色的服裝、發式、妝容等造型,可以幫助觀眾勾勒出他們所處的時空,所在的階層,所處的文明等人物背景。觀眾可以從男巫的燕尾服套裝背心上的孔雀毛紋路和藍綠色的色調以及胸前的羽毛裝飾解讀他的身份和寓意;麥克白夫人的黑色蕾絲露背旗袍禮服、麥克德夫夫人藍灰色的天鵝絨質地的垂墜連衣裙、女巫赫卡特的裙擺加上羽毛的血紅色禮服長裙等等,無不對人物進行了對比和暗喻,這些都是通過觀眾的聯覺才能達到的戲劇氛圍。
人物造型雖然是戲劇中通過視覺形象直接的意象表達,而戲劇所蘊含的戲劇詩化的內涵的解讀和呈現,還需要觀者的思考和互動。如貝克特的荒誕派戲劇代表作《等待戈多》,在這個沒有連貫的劇情、沒有明顯沖突、對話似乎也語無倫次的故事里,“戈多”究竟是誰是一個懸置的意象,這個自始至終沒有出場的人物,存在于演員的語言中,也存在每個觀者的心中的。劇中提供的隱喻意象,在每個觀者心中都有自己的解讀,觀者會用自己的切身經驗來注釋它,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一直等待卻未得的人或事。這就是戲劇舞臺的獨特性,創作者營構出的意象和詩意必須在觀演之間鮮活的審美交流中實現。
結語
在戲劇人物造型的創作意象不是簡單的“摹象”,而是一種審美的創造,是藝術創作者和鑒賞者情感凝鑄的結果。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不僅僅是“意”與“象”的簡單結合,而是在特定的戲劇語境中將視像與意念、情感等綜合在一起的整合過程,把創作者的“意”融入“象”中,當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呈現在舞臺上,讓觀眾看到“象”,還能夠品得出“意”。造型師從文本中、從想象中、從藝術積累中、從生活細節中尋找……靈光一閃,獲得寶貴的“形象種子”,然后將這個種子延伸、變形、深化……直到塑造出生動、豐滿、詩意化的人物外部形象鮮明靈動地呈現在舞臺上,與舞美、燈光、音響等視聽覺意象共同營構出一個詩意動人的舞臺。戲劇人物造型設計作為戲劇舞臺藝術的一環,意象的營構必然受到導演總體意象的統攝,亦受到文本、舞臺等多方面的影響,但戲劇人物的外部形象造型藝術仍然是獨立的、獨特的創作,它最終將與演員的表演融為一體,成為舞臺藝術表現的視覺中心。作為一種心靈營構之象,戲劇人物造型的意象營構,是創作者與觀賞者相互作用、交融一體的產物,是戲劇舞臺溝通、鑒賞、傳播交流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