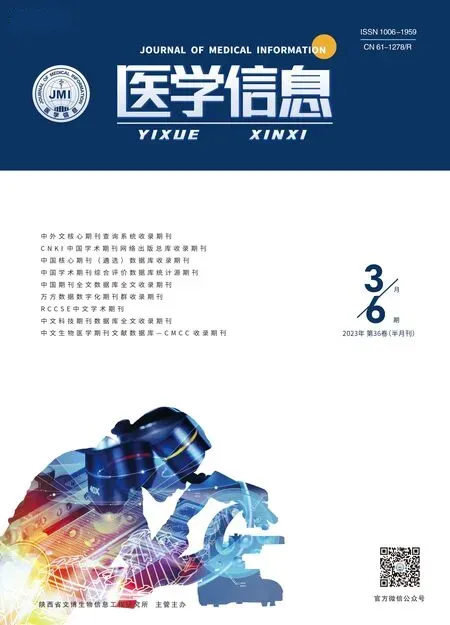精準肝切除時代下肝臟切面的選擇
牟曉峰,王毅軍
(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肝膽外科,天津 300170)
自董家鴻教授提出精準肝切除(precise liver resection)的理念后,我國肝臟外科已逐漸進入了精準肝切除的時代。精準肝切除旨在追求徹底清除目標病灶的同時,確保剩余肝臟解剖結構的完整和功能性體積最大化,并最大限度控制手術出血和全身性創傷侵襲,最終使手術患者獲得最佳康復效果。其包含精確的術前評估、精密的手術規劃、精工的手術操作以及精良的術后管理[1]。而在手術操作中,尤其是針對肝癌患者,術中肝臟切面的選擇仍是困擾肝臟外科醫生的難題,目前應用的主要方法有術中觸診法、術中超聲引導、以肝靜脈為導航的肝實質離斷法、選擇性肝門阻斷及目標肝段的門靜脈染色法、吲哚菁綠染色法及基于肝臟流域學說下的肝實質離斷法,本文現就上述判斷方法進行綜述,旨在為該病的手術治療提供參考。
1 術中觸診
延腫瘤邊緣切除是比較傳統的方法,術中通過對肝臟及腫瘤的視覺觀察及手部觸診來判斷腫瘤的位置、邊界進行切除。但此法對于位置深、未突出表面的腫瘤,或腫瘤較小、患者肝硬化導致肝臟質地硬、多發肝硬化結節等,都會影響醫生對腫瘤確切位置的判斷。此外,質地較軟的肝臟良性腫瘤依據術中觸診來確定具體位置也非常困難[2]。我國肝癌患者多有肝炎史,85%以上具有不同程度的肝臟硬化[3],位于肝臟內部直徑5 cm 以下的小肝癌通過視、觸的方法定位極其困難,而對于2 cm 以下的微小肝癌通過此法判斷位置更加困難。雖然術中的腫瘤觸診是腫瘤外科手術中重要的探查方式,但該法受患者肝臟因素、腫瘤大小和位置因素,以及外科醫師經驗因素干擾較多,單純依賴此法切除腫瘤有導致術中切入腫瘤內部、術后病理學診斷切緣陽性等可能。
2 術中超聲
術中超聲(intraoperative uhrasonography,IOUS)技術于上世紀60 年代已應用于臨床,該技術已被眾多的外科醫師學習接受,并開展于外科工作中[4,5]。術中超聲在肝腫瘤外科治療中主要可發揮以下作用:①可以針對術前診斷時未明確的微小病灶進一步診斷,且可以針對微小的病灶來進行更加準確的定位,目前有文獻報道術中超聲可識別的病灶大小最小直徑為2 mm[6];②可以協助判斷腫瘤侵襲的范圍,能夠檢查腫瘤與主要管道如血管、膽管、甚至分支管道的關系;③可于超聲引導下進行腫瘤的射頻消融或微波治療[7-9]。隨著科技的進步,超聲設備、高頻率探頭的發展和使用,已有文獻報道IOUS 對直徑<1 cm 病灶的敏感度可達到90.7%[10]。因此,應用IOUS 后肝癌切緣的陽性率和術后肝內肝癌復發率均低于未應用IOUS 者[11]。IOUS 的局限性:在精準肝切除的時代下,對于肝段的解剖已深入到門靜脈供血的流域,對于多肝段或單個肝段的切除,超聲仍只能依靠傳統的門靜脈、肝靜脈的解剖關系于肝表面的投影來判斷肝段邊界,且超聲探頭于肝中表面多個不同位置均可定位同一目標血管,因此會造成對肝段邊界標記不精準、不客觀。所以該項技術對于IOUS 的操作者有較高要求,需對肝臟內、外的解剖均有較深刻的認識水平,能熟練結合肝臟的解剖與超聲應用的技術。
3 以肝靜脈為導航的肝實質離斷
Makuuchi M 教授認為[12]肝靜脈的顯露是肝切除術的精華。肝靜脈貫穿于各肝段之間,其在肝內的走行路徑與缺血肝段的分界面毗鄰,且肝靜脈的間隙為一個相對無血管區域,其內不存在Glisson 系統分支。延該間隙進行肝實質的離斷可以明顯減少出血,是較為理想的肝段解剖界線。肝靜脈亦是肝臟天然的解剖標志,循肝靜脈路徑離斷肝實質可作為一種術中導航方式,避免在離斷肝實質深部時發生迷路、偏移等現象,可以避免損傷肝內Glisson 蒂和影響殘余肝臟的靜脈回流[13]。亦有研究表明[14],以肝中靜脈為導航的肝實質離斷可顯著減少肝門部膽管癌患者的病死率。還有研究表明[15],以肝中靜脈作為導航路徑的肝切除雖未能顯著改善總體預后,但卻明顯降低了肝癌的早期復發(術后1 年)風險,尤其是肝臟切緣附近的腫瘤復發。但暴露肝靜脈本身亦存在一定風險,在暴露肝靜脈的過程中,容易導致肝靜脈的破裂出血,從而增加出血量及手術時間的延長,術中使中心靜脈壓(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降低至≤5 cmH2O 的低中心靜脈壓技術可明顯的減少肝切除術中的肝靜脈出血。
4 選擇性肝門阻斷及目標肝段門靜脈染色
對于預切除的目標肝臟行選擇性肝門阻斷后,可延肝臟表面的缺血線來進行肝實質離斷。此法優勢為于第一肝門解剖肝蒂較為簡單,并可減少保留側肝臟的缺血再灌注損傷。但在肝硬化嚴重時、黃疸時,肝臟表面缺血線不明顯,且如進行單個肝段切除,目標肝段肝蒂解剖位置深,解剖困難。尤其在進行肝實質深部離斷時,由于缺血線僅僅于肝表面出明顯,沒有內部導航指引,切肝路徑容易偏航。Makuuchi M 等[12]將術中超聲定位后向選擇的目標肝段的門靜脈進行穿刺后給予注射美藍使目標肝段被染色,其表面肝臟呈地圖樣藍染,用以著色邊界的標記,再結合術中超聲技術實施解剖性肝段切除。為克服該染色法在肝實質中持續時間的較短,進入肝實質后邊界不清。蔡守旺等[16]對此項技術進行了進一步的優化,提出了持久美藍染色精準肝段切除技術,即解剖出目標肝段的門靜脈后,直視下推注數毫升美藍溶液后給予結扎目標肝段的入肝血流,避免血流持續沖刷,使靶向肝段能相對持久地顯示藍染的狀態,以便導航深部肝實質切除。但此兩種方法在在手術中均為肝臟表面染色邊界明顯,深部肝臟染色效果欠佳,容易導致“迷路”現象。
5 吲哚菁綠染色法
吲哚菁綠(indocyanine green,ICG)主要由肝細胞攝取,通過毛細膽管上的載體系統進行排泄,且在其排泄后不參與到腸肝循環[17]。在正常的肝臟組織中,ICG 入血后可以被肝臟細胞快速的攝取,予以外源光的激發后能夠顯示熒光現象,在經膽道系統排泄后,熒光現象也隨之漸漸的消退。尤其在目前快速開展的腹腔鏡手術上得到了很好的應用。ICG 最大的優勢是被熒光染色后的肝段效果顯著,肝臟表面及肝實質內部均可表現出與未染色的肝臟顯著的熒光差異,從而可以在離斷肝實質深部時避免迷路,且能實現腫瘤與正常肝臟組織的對比成像,可隨熒光邊界做為明確的引導目標[18]。亦可用反染的方法進行特殊肝段的切除。但在肝硬化患者中,部分肝硬化結節可能與小肝癌染色效果相似[19],產生混淆,并且因肝臟的交通支、側支循環等導致的二次循環分布,可能導致部分肝臟區域差異下降。另外ICG 的顯象效果亦受肝功能情況、靜脈癌栓、膽道梗阻等多因素的影響。
6 基于肝臟流域學說的肝實質離斷
近年來隨著對肝臟解剖更深入的研究及認識,對于肝切除已逐漸從解剖學的理解到功能學的重視,傳統Couinaud 八段法亦存在較多的爭議。Couinaud 分段法為門靜脈左右支與主肝靜脈把肝臟分為八段,僅為解剖學分段,而實際臨床工作中也能觀察到肝臟血管與染色邊界不在同一平面的情況。如半肝的切除,結扎一側肝蒂后的缺血線或半肝的熒光染色邊界,與肝中靜脈常不處于同一平面。Makuuchi 教授定義的解剖性肝切除中,對肝臟斷面具有重要意義的肝靜脈予以顯露,而目前的肝臟流域學說則更強調以門靜脈供血區域為切除目標、目標肝段肝臟供血區域的完整切除,而不是刻意暴露肝靜脈。劉榮教授提出的另一種流域學說與以上的流域學說略有區別,認為肝段的流入、流出道均不是由單一肝蒂供給或單一肝靜脈引流,而是由該肝段附近的肝蒂及肝靜脈共同提供流入、流出道,更強調“流”的特點。如結扎一側肝蒂后缺血線位置的變化,TACE 給予腫瘤供血血管栓塞后新生血管的形成,對于肝臟的解剖更強調“區域”而非“肝段”[20]。并且認為肝段并非為獨立的單元結構,在肝段的出、入肝血流改變后,該肝段的流入、流出道也會隨之發生迅速且明確的變化,各肝段及血管間,以及肝周的韌帶和神經結締組織內亦存在著較為復雜的潛在的相關交匯的通路[21,22]。因此,該學說針對傳統的手術風險更大、操作過程更復雜的解剖性肝切除[23],尤其目前諸多單位進行的復雜的、精細的解剖標志顯露肝切除手術提出了疑問[24-26],此學說更強調切緣的重要性,而非一味的追求顯露肝靜脈,但對該學說的認可及應用仍需進一步的臨床研究佐證。
7 總結
肝臟外科已進入到精準肝切除的時代,從對解剖的認識,剩余肝臟體積的保留到對功能的重視;從開腹的、失血多的高風險手術,到腹腔鏡、機器人下的更精細化的手術,肝臟外科對肝切除手術的研究和理解仍在不斷探索、學習。而在肝切除術中,如何選擇斷肝平面,不可一個模式、一概而論,應采取個體化方案。上述方法均有其利弊,肝臟外科醫師應掌握多種方式方法,在手術中綜合判斷甚至聯合應用。如循肝中靜脈行半肝切除的方式,雖在腫瘤學意義上有待研究,但其天然的路標作用可用于無熒光技術的單位來施行半肝切除術中的斷面判定;在無條件行超聲引導下門靜脈穿刺的情況下,亦可選擇目標肝段門靜脈的結扎、染色;而在因肝功能差、嚴重肝硬化等情況下導致的吲哚菁綠染色效果欠佳、范圍不準確時,可施行延腫瘤邊緣聯合術中超聲的方法施行斷肝切面的判定。對于肝功能差、剩余肝體積較少的情況,盲目的追求顯露肝靜脈的解剖性肝切除會造成術后肝功能不全的風險,此種情況選擇超聲引導下或單純延腫瘤邊緣切除,保證足夠的肝體積是防止術后肝功能衰竭的手術方式。流域性肝切除的部分理念也與解剖性肝切除的要求不相符,在臨床工作中也在逐漸的探索新學說,不斷的對既往的理念提出新的挑戰和探索。總之,對于肝臟腫瘤的切緣問題還在不斷的探索,對于肝切除術中切除邊界的判定方式雖有多種,但肝臟外科醫生不能固化思維,應掌握多種方式,對不同的患者采取個體化的手術方式,最終目標仍為完整去除病灶的同時最大程度的保留剩余肝臟的功能,并且進一步的在切除與保留間做平衡,取舍,以及進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