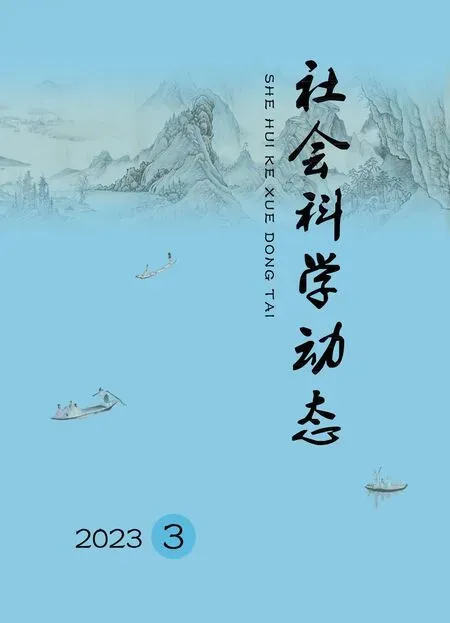數字資本的唯物史觀審視
余沐嵐
隨著互聯網數字時代的到來,數字資本這一社會現象逐漸浮出水面。“數字”實際上指的是“數據”,它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互聯網的核心就是數據。如果一旦對數據形成了壟斷,就可以利用數據獲利,這就是數字資本的由來。當今世界正是如此,目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體系建構和市場擴張實際上都根植于對互聯網數據的利用和獲取,而數據資源一旦被資本化,進入資本積累過程,為資本帶來利潤,數字資本就應運而生。在這個數字化時代,數據資本的產生對于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乃至人的生存交往等方面都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巨大影響。因此,對數字資本加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分析,有利于我國厘清數字資本的本質,從而采取相應措施對其加以規范利用,以服務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
一、數字資本的表現:數字拜物教
數字資本表現為互聯網時代科學技術與資本的結合,不過這種結合與傳統技術與資本的結合不同,呈現出數字化時代的諸多新特征,并集中體現為“數字拜物教”這一現象。
與傳統資本主義不同,當今世界以數字為基礎的數據經濟時代已經徹底展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起來似乎不再是傳統的生產、交換、消費以及生活交往的現實場景,數字化、虛擬化的方式代替了這一切。生產交換以及人際關系等徹底表現為一種“物”的關系(這也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而這種“物”不是傳統資本主義社會所說的商品(或現實貨幣),而是“數字”。因此,商品或貨幣拜物教在當代表現為“數字拜物教”這一現象。數字拜物教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非常盛行,這不僅僅表現為人們對一切數據、數據商品、數字資本的崇拜,而且還表現為在新技術主義革命的浪潮下,整個社會對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智能技術的崇拜。“數字驅動一切、決定一切”似乎正在成為西方社會的信仰。
數字拜物教折射了數字資本在當今世界的存在和運行方式。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不變的部分即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并通過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①。數字拜物教的產生與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類似,當傳統的資本生產模式逐漸被互聯網時代的諸多新方式所替代時,當互聯網數據這一逐漸被人們所接受的看似平常、與資本增值似乎無關的現象出現時,當數字勞動及其消費逐漸成為勞動消費的新模式時,資本增值、創造剩余價值的本性使資本家不可避免地將互聯網數據視為一種潛在的商品加以關注和運作。于是傳統的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方式走向了數字資本時代,數字拜物教也就誕生了。
“數字拜物教”的焦點是“數字”。正如馬克思對“人”的現實性界定是“一切生產關系的總和”一樣,這里所說的“數字”的特性,不是指紛繁復雜的具體數據,而是指反映了一般商品本性的所有具體數據的抽象總和。數字之所以被人們崇拜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能夠帶來資本增值,因此在數字資本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社會中,數字就必然被賦予某種神奇的魔力,成為崇拜的對象。客觀來說,就數字這一現象的樸素意義而言,并不能稱之為商品,當數字與資本結合才能稱之為商品。隨著網絡時代的迅猛發展,人們的一切活動都被“數字化”了,或者說,互聯網時代的人們首先表現為一種數字化生存,當這種數字化浪潮將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都席卷其中時,數字必然會商品化,數字資本必然會出現。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數字資本對包括社會生產在內的人類社會的幾乎所有細節都進行數字編碼,并將這種編碼視為壟斷性資源,在這種資源壟斷中通過數字商品的交易獲得剩余價值。
隨著網絡化、數據化時代的發展,似乎整個社會都表現為一種神秘的數字化生存,對于數字的重視和崇拜無以復加。對于這種神秘性,正如馬克思所說,“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②,因此,“創造剩余價值并占用剩余價值”是資本的直接目的,這在數字資本時代也是如此。不過由于數據化時代的特殊性,使得剩余價值的產生和存在方式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一方面,就技術要求來看,數字化時代的生產效率更高。因為智能化時代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能夠將勞動力和信息技術、生產設備等進行快速有效配置,所以生產效率大大提高,這為資本家攫取剩余價值提供了更有效手段;而且由于數據化時代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使得壟斷關鍵技術的資本家能夠獲得超額利潤。相對于傳統生產而言,數字勞動的成本降低,而掌握關鍵技術的資本家壟斷性更強,所以能夠獲得的利潤更多。另一方面,就生產關系來看更為復雜。數字資本仍舊反映了一種生產關系,但是這種生產關系與傳統不同,由于現實空間與網絡虛擬空間的并存以及數字生產的多樣化和復雜化,使得數字時代的生產關系比以往更為復雜多變。在這種難以把握且復雜多變的生產關系中,“數字”這一商品本身成為焦點,催生了數字拜物教的產生。
馬克思曾說:“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③因此對于數字資本的現實表現而言,數字拜物教的本質仍舊是商品拜物教,表現的仍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并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范圍。
二、數字資本的本質:數字帝國主義
數字資本表面上是一種“數字拜物教”,究其實質,體現的是數字帝國主義的本質。數字資本的出現與互聯網智能新技術的出現是密不可分的,對這種新技術的壟斷往往就會走向數字帝國主義。半個世紀前,列寧就已經注意到了科學技術發展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緊密關系,他這樣說:“競爭轉化為壟斷。生產的社會化有了巨大的進展。就連技術發明和技術改進的過程也社會化了。”④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當數字成為商品之后,數字技術就不再成為某種看似中立的純粹科學技術,而是成為促進資本增值、創造超額利潤的手段,而且這一手段在資本的利用下變得更加隱蔽且更有剝削性。就當今世界而言,西方國家的數字資產階級正在通過對智能技術及其數字媒介等方面的壟斷,不僅形成技術優勢以謀求高額利潤,而且謀求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操縱,在維護自身壟斷地位的同時剝奪其他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機會,以形成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依附西方國家的狀態,從而實現數字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
數字帝國主義首先表現為一種數字政治或數字統治現象。數字技術出現之初就逐漸被應用于政治領域,甚至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開始應用于“冷戰”。隨著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西方國家利用其維護統治,加大對其他國家的控制和干預的趨向越來越明顯。依托于對數字技術的壟斷,西方國家很快完成了數字資本積累并開始大規模的擴張。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互聯網在全球影響的加大,西方數字資本的優勢變得越來越明顯,其對外擴張的意圖也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在這一擴張的過程中,憑借技術和人才方面的優勢,數字資本采用隱蔽而高效的手段對人們進行潛在的剝削和壓迫,這種現象甚至可以稱之為“數字奴役”。西方數字資本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和操縱更是如此。由于技術及其創新發展上的壟斷優勢,西方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變得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很難將其打破。由此,數字國際秩序變成了一種隱蔽的剝削鏈條。這實際上和傳統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壓迫并無兩樣。
與數字技術成為剝削工具同時進行的是,數字帝國主義還表現為對強權政治的追求。從技術層面來說,數字技術已經成為一種人們甚至意識不到的剝削工具。由于社會的全面數字化以及數字網絡空間的虛擬化性質,使得數字剝削或數字奴役很難被人們所察覺,而且就算被察覺,西方數字資產階級仍舊可以利用技術上的壟斷優勢將這種剝削或奴役保持下去。在這個全面網絡化的時候,數字資本甚至可以操縱輿論,在網絡上讓反對者無法發聲,甚至混淆黑白為自己的行為洗白。在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數字壟斷的全面擴張中,數字資產階級的網絡話語權逐漸成為一種話語霸權,從而催生了數字帝國主義對強權政治的追求。這種強權政治體現在多個方面,譬如對全球(他國)意識形態的影響就是一個典型。通過對數字霸權的壟斷,西方數字資本以占統治地位的話語權為途徑,向他國輸入自己的價值觀,以進一步加深對其他國家的控制。在這個全球互聯網的時代,防止西方價值觀對本國的影響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西方資本具有技術優勢、掌握網絡話語權的時候更是如此。西方資本輸入價值觀的方式很多,一個典型手段就是通過對網絡族群的培養,使其滲透到數字社會的各個層面,在散播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同時激化社會矛盾,從而實現干涉內政甚至“和平演變”的目的;或在某一特定時期,利用網絡族群掀起大規模的輿情以影響國際政治博弈,為西方資本的政治操盤服務。隨著數據化時代的發展以及“數字拜物教”影響的日益加大,西方資本通過數字領域實現帝國主義的傾向日益明顯。這一傾向并非只是理論上的預設,實際上已經反映在全球數字領域,如當今世界頻繁出現的國際沖突、國內權力重組等現象,背后往往都有數字帝國主義的影子。
數字拜物教是數字資本的表象,數字帝國主義是數字資本的本質。數字帝國主義掌握著互聯網時代的數字霸權,一直以來致力于對世界各國政府和公民的數據進行收集和監控,在壟斷性技術優勢下將這些數字變為商品,變為干擾他國內政的工具。可以說,數字帝國主義延續了傳統帝國主義的剝削本質,并基于數字技術實現了新的數據剝削,實現了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新的操控。
三、當代中國如何看待數字資本
在數字時代,當代中國如何看待數字資本?首先,我們要看到,西方的數字資本盡管有著不同于傳統資本的運作方式,但究其根本仍舊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表現形式。因此盡管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數字壟斷等方式獲得了新的發展,甚至有發展到數字帝國主義的傾向,但是從本質上來說仍舊沒有脫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框架。正如馬克思所說,盡管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沒有完全釋放其力量之前仍舊還在(數字時代)發展,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客觀規律并不會被改變。所以,我們要堅定信心,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范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發展,體現中國制度的優勢所在。其次,對于數字技術及其數字資本我們要認清其本質,即價值是由工人(勞動者)創造的,不是由資本家創造的,因此資本技術及數字資本在當代中國最終只能服務于增加人民福祉,而不是服務于資本剝削。馬克思曾說:“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一切,……工人甚至創造了人。”⑤馬克思進一步認為,勞動人民不僅創造了財富,而且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毛澤東曾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⑥對此,習近平也明確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⑦。因此,對于數字技術及數字資本的利用或規范,需要把握一條根本指導原則,即為人民服務。
具體而言,首先需要防范數字風險,反對一切形式的資本帝國主義。當前,數字資本競爭已經成為關系國家安全的新領域。在這一領域中,有著數字資本優勢的西方國家正在利用這一強大工具對全世界進行數字奴役。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在積極參與數字技術發展以及數字經濟競爭的情況下,更要特別注意數字風險,反對一切形式的資本帝國主義。譬如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華為公司(及其5G技術)的圍剿,就充分暴露了這種資本帝國主義行徑。因此我們需要加強互聯網的監管,防范一切可能的數字風險;同時在國際交往中積極參與數字技術發展及數字信息使用等方面的規則制定,擴大數字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抵制數字霸權,推動全球數字技術的良性發展。
其次需要重視數字技術開發,規范數字資本發展,實現智慧治理。數字資本的基礎是數字技術的發展,重視數字技術是實現智慧治理的根基。數字技術是新技術革命的代表,積極發展數字技術、搶占數字高地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的重視和發展才能形成一種良好的智慧治理。數字技術的應用意味著以智能化賦能現代化治理,能夠有效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這就是智慧治理的指向。智慧治理的實現需要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資本的規范發展,因為當代中國也存在數字資本這一形式,所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數字資本需要得到規范、引導、整合,以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對數字資本的規范有利于在全社會更好地實現數字資源共享,從而能夠推動智慧治理的進一步發展。
最后需要制定法律規范,體現制度優勢。“資本是生產的,也就是說,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系。”⑧在重視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的基礎上,需要對數字資本加以規范引導,這種規范和引導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規范,以體現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優勢,使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為人民服務,增進人民福祉。針對于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的特點,一方面,需要建立數字經濟法律規范。數字資本發生作用的主要領域是經濟領域。在數字技術的刺激下,當前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往往比傳統經濟領域的競爭更為激烈,其競爭形式也與傳統完全不同。面對這種全新的經濟競爭形式,傳統的法律規范往往難以應對。因此必須建立一整套比較完善的數字經濟法律規范,才能規范和引導數字經濟領域的良性競爭,使數字資本的發展不至于偏離社會主義建設大業的發展,更不至于被西方數字帝國主義影響,成為西方國家干涉我國內政的工具。另一方面,要打破數字壟斷,服務民生福祉。西方數字資產階級進行數字剝削的主要手段是對數字的壟斷(包括對數字技術的壟斷以及對數據資源本身的壟斷),由此造成了全球性“數字鴻溝”的出現,數字帝國主義也由此謀求全球性的數字奴役和數字殖民。當今中國決不允許數字帝國主義的出現,所以打破數字壟斷,使之服務于民生福祉的實現是必有之義。作為技術和資源的數字(數據)必須由人民共享,而絕不能像西方社會那樣成為剝削人民的工具。當前,數字資本日益體現出與金融資本融合的傾向,數字貨幣(如比特幣)體系也已開始出現,防范風險、加強管理是我國當前的重要工作。對于目前正在發展的數字創新金融,我國予以了積極引導和謹慎發展,取得了良好的規范效果;對于目前西方社會日益風靡的數字貨幣,我國更是加以了嚴格管理,使其難以影響我國的金融貨幣體系,保障了國內數字經濟的平穩發展。總而言之,在重視數字技術、規范數字資本發展的情況下,在不干擾企業創新機制的前提下,制定一整套數字法律體系能夠在規范管理的前提下,體現人民至上、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是當前我國促進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發展的必經之途。
綜上所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對于數字資本,我們要始終堅持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立場,認清數字資本的本質,反對數字拜物教,反對一切形式的數字帝國主義。同時,結合中國具體發展,在積極發展數字技術的基礎上,防范風險,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以人民至上為指導,讓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造福于民。
注釋: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頁。
②③⑧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9、508頁。
④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頁。
⑥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⑦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