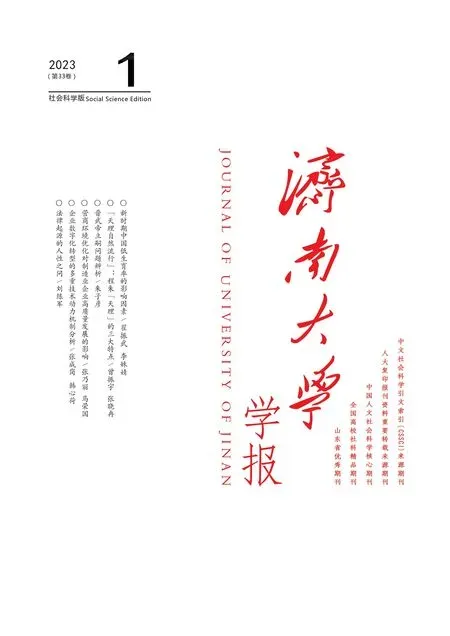“天理自然流行”:程朱“天理”的三大特點(diǎn)
曾振宇,張曉冉
(1.山東大學(xué) 儒學(xué)高等研究院 山東 濟(jì)南 250100;2.山東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山東 濟(jì)南 250100)
一、理是“凈潔空闊底世界”
在中國哲學(xué)史上,真正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在其思想體系中,必定有幾個(gè)獨(dú)創(chuàng)性的概念。在二程哲學(xué)體系中,“天理”無疑是最具標(biāo)幟性的概念。雖然《莊子》、《韓非子》、《禮記》等典籍已出現(xiàn)“天理”一詞,“能指”雖同,但“所指”與哲學(xué)意涵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程明道頗為自豪地說:“吾學(xué)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1)程顥,程頤:《河南程氏外書》卷第十二,《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24頁。“自家體貼出來”的“天理”,在哲學(xué)性質(zhì)上,無生無滅,猶如華嚴(yán)宗所言:“涅槃無生無出故。若法無生無出,則無有滅。”(2)高振農(nóng):《華嚴(yán)經(jīng)譯注·如來出現(xiàn)品第三十七之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82頁。既然天理不可以“生滅”界說,自然沒有空間的特性,“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3)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二程集》,第1205頁。。“道體物不遺,不應(yīng)有方所。”(4)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第21頁。“理無形”的表述在程伊川文章中多次出現(xiàn),“有方所,則有限量”(5)程頤:《周易程氏傳》卷第三,《二程集》,第913頁。,天理無方所,不存在具體存在所具有的空間特性。先秦莊子明確點(diǎn)明“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莊子·秋水》)。道與物截然相分,形上層面的“道”,不可以“終始”來界說。道沒有具象那種度量時(shí)間屬性,具體之物才有度量時(shí)間屬性,因?yàn)闀r(shí)間與空間只是具體存在才具有的存在方式。天理無形,天理無終始,甚至“天理”這一概念本身之“能指”與“所指”,也是“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6)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第38頁。。天理在邏輯上“難為名狀”,使用“天理”這一概念也不過是“強(qiáng)為之名”(《老子·二十五章》),這一觀點(diǎn)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二程一樣,在朱熹思想體系中,位階最高的概念是“理”。理是天地萬物存在所以可能的普遍根據(jù),理決定了某物之所以為某物的本質(zhì)。理是存在的第一原理,理是存在的“所以然”。有人問朱子:“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朱子回答:“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7)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頁,第4頁,第2-3頁,第1頁,第3頁,第3頁。理先于天地人而存在,理在邏輯上有“天地之先”的特點(diǎn)。在天地萬物沒有產(chǎn)生之前,理“亙古今常存”(8)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三,第46頁。。在一次與學(xué)生的對話中,朱子甚至說:“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里。”(9)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頁,第4頁,第2-3頁,第1頁,第3頁,第3頁。“陷”意味著天地萬物不復(fù)存在,有時(shí)空限定的具體存在消亡,作為本體的理,仍然可以獨(dú)立存在。有人問:“未有人時(shí),此理何在?”朱子答:“也只在這里。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dān),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10)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頁,第4頁,第2-3頁,第1頁,第3頁,第3頁。朱子以有形體、有質(zhì)量的“海水”比喻理,多少會使人有些誤解。誤以為本體論意義上的理,也有空間特性。恰恰相反,朱子想要表達(dá)的一個(gè)觀點(diǎn)是:理“無形體”(11)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頁,第4頁,第2-3頁,第1頁,第3頁,第3頁。。理不具有具體存在才具備的時(shí)間特性與空間特性。換言之,不可以用時(shí)間與空間來界定理,因?yàn)槔硎浅綍r(shí)間與空間的本體性存在。不僅如此,理“無情意,無計(jì)度,無造作”(12)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頁,第4頁,第2-3頁,第1頁,第3頁,第3頁。。理不是至上人格神,理沒有生命意識與情欲,也不會具體生成天地萬物。正因?yàn)槿绱耍聿攀且粋€(gè)“凈潔空闊底世界”(13)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頁,第4頁,第2-3頁,第1頁,第3頁,第3頁。。在《答楊子順》一文中,朱子特意點(diǎn)明理是“形而上者”:“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為形而下者,恐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者也。”(14)朱熹:《答楊子順》,《朱熹集》卷五十九,郭齊等點(diǎn)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6頁。陰陽五行屬于形而下,理是陰陽五行背后隱藏的“所以然”,因此屬于“形而上者”。在《易傳》思想架構(gòu)中,陰陽之氣是天地萬物生成何以可能的本原,氣顯然是形而上的第一概念。但是,在朱子哲學(xué)架構(gòu)中,氣已下降為“形而下者”,代之而起的是“理”。由此可見,天理具有客觀獨(dú)立性,可以脫離人的意識獨(dú)立自存。這與王陽明哲學(xué)中的“天理”顯然有所不一。王陽明的“天理”在心中,而不在心外。把外在客觀性的天理,拉回至內(nèi)在的心中,從而使天理具有內(nèi)向性特點(diǎn),這是王陽明哲學(xué)一大特色。
或許是為了更圓融地詮釋理是“形而上者”,朱子別出心裁地從周敦頤哲學(xué)中借用了“無極”與“太極”兩大范疇。“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fù)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15)周敦頤:《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4頁,第5頁,第5頁。周敦頤的“太極圖”以及對太極、無極的詮解,顯然汲取了陳摶等人的思想,但也作出了顛覆性的界說。由于版本不同的緣故,首句“無極而太極”在九江本中寫成“無極而生太極”,在國史本中作“自無極而為太極”。但是,無論周敦頤是否受到道教思想的浸潤,也暫且不論版本的異同,有一點(diǎn)是可以肯定的:無極與太極不離陰陽,“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16)周敦頤:《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4頁,第5頁,第5頁。。無極與太極不是一觀念性本體,天地客觀事物,乃至一花一草都能澄顯宇宙本原的存在。正如朱子所言,“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17)周敦頤:《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4頁,第5頁,第5頁。。形而上的無極、太極沒有與形而下的世界徹底割離,無極與太極寓含于天地萬物之中。直觀經(jīng)驗(yàn)的世界背后,透顯出一個(gè)宇宙本原的世界。
令人驚訝的是,少年時(shí)代就拜周濂溪為師的二程兄弟,在其思想體系中,完全棄絕太極圖、無極與太極思想(18)《周易程氏傳》前之《易序》中提到:“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fù)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缊交感,變化不窮。”(見《二程集》,第690頁。)另外,《河南程氏文集·遺文》也收有《易序》一文。在學(xué)術(shù)史上,不少學(xué)者考證《易序》并非程頤之作。譬如,陳來在其論文《關(guān)于程朱理氣學(xué)說兩條資料的考證》中指出《易序》來自《性理群書》,《易序》非程頤所作。。對于二程兄弟為何不談及太極圖,黃百家在《濂溪學(xué)案》案語中引述豐道生的觀點(diǎn):“至于《太極圖》,兩人生平俱未嘗一言道及,蓋明知為異端,莫之齒也。”(19)黃宗羲:《宋元學(xué)案》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24頁。豐道生認(rèn)為二程兄弟認(rèn)定周敦頤太極圖和太極無極之說屬于“異端”,所以二程終其一生不愿提及,“莫之齒也”。對于這一學(xué)術(shù)史上的懸案,朱子有幾個(gè)說法,其中一個(gè)解釋是“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只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而主靜’”(20)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三,第2358頁。。雖然程伊川曾經(jīng)說過“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21)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二程集》,第1180頁。,在宇宙生成論上,理與氣合一,道不離陰陽。但是,在本體論層面,理與氣又是不雜不混,形而上截然有別于形而下。“二程不言太極”的真實(shí)原因,既是對異端的“莫之齒”,也是對張載“清虛一大”氣論有所貶謫,對張載所言既散之氣復(fù)歸太虛之氣多有批判。因?yàn)橹苠ハ臒o極與太極學(xué)說本質(zhì)上是氣,因此,二程兄弟對張載“太虛即氣”的直接批判,也是對周濂溪無極太極思想的間接否定。在二程兄弟看來,本體論上的理本論以及宇宙論層面的理氣說,完全可以圓融無礙地詮釋世界的誕生以及世界誕生在邏輯上何以可能。在理本論架構(gòu)中,再引入無極太極學(xué)說,無異于疊床架屋、畫蛇添足。
與二程兄弟相左,朱子大張旗鼓地在理本論架構(gòu)中引入太極無極學(xué)說。朱子特意指明,太極與無極范疇本來就是儒家自家固有的“寶藏”,與《老子》和道教沒有絲毫關(guān)聯(lián)。“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22)朱熹:《答陸子靜》,《朱熹集》卷三十六,第1574頁,第1577頁,第1575-1576頁,第1576頁,第1576頁。朱子認(rèn)為“太極”是孔子發(fā)明的概念,“無極”是周敦頤首先提出來的。朱子認(rèn)為《老子》中的“無極”的內(nèi)涵是“無窮”(23)朱熹:《答陸子靜》,《朱熹集》卷三十六,第1574頁,第1577頁,第1575-1576頁,第1576頁,第1576頁。,因此與儒家的思想南轅北轍。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朱熹聲明太極與無極直接源自周敦頤哲學(xué),卻對無極與太極的本質(zhì)內(nèi)涵作了顛覆性的詮釋。太極與無極不是氣,而是理!舊瓶裝新酒,“城頭變幻大王旗”。朱子晚年弟子陳淳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個(gè)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朱子回答說:“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24)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第1頁,第2頁,第2頁。在回答另外幾位學(xué)生的類似提問中,也一再言之鑿鑿地標(biāo)明“太極只是一個(gè)‘理’字”(25)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第1頁,第2頁,第2頁。。“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26)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第1頁,第2頁,第2頁。既然太極就是理,基于周濂溪“無極而太極”的邏輯,朱子思想中的無極也應(yīng)該是理。“圣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后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27)朱熹:《答楊子直》,《朱熹集》卷四十五,第2154頁。朱子答《楊子直》一信寫于40至41歲之間,屬于中年時(shí)期的觀點(diǎn)。乾熙十五年,朱子59歲,在《答陸子靜》一文中,仍然一如既往闡述同樣的思想:“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后;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無臭影響之可言也。”(28)朱熹:《答陸子靜》,《朱熹集》卷三十六,第1574頁,第1577頁,第1575-1576頁,第1576頁,第1576頁。太極即理,無極也即理。將無極太極范疇引入理本論體系之中,果真不是“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朱子對此有專門的解釋,在幾封書信中都一再聲明:“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29)朱熹:《答陸子靜》,《朱熹集》卷三十六,第1574頁,第1577頁,第1575-1576頁,第1576頁,第1576頁。在朱子看來,援無極太極入理本論思想架構(gòu),只是一種隨時(shí)設(shè)教的“方便法門”。在向蕓蕓眾生宣講理本論時(shí),如果不講無極,蕓蕓眾生往往會將太極錯(cuò)認(rèn)為有空間與時(shí)間局限的存在;如果不講太極,眾人又有可能將無極等同于絕對的空無。“聞人說有即謂之實(shí)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30)朱熹:《答陸子靜》,《朱熹集》卷三十六,第1574頁,第1577頁,第1575-1576頁,第1576頁,第1576頁。
二、天理至善
以天理為代表的儒家本體論,真正目的在于為人類、甚至為宇宙萬物奠定一個(gè)共同的道德根基,論證一個(gè)亙古不移的“共同善”,建構(gòu)一個(gè)以“天下”為基礎(chǔ)的文明共同體。《宋元學(xué)案》講述程伊川與邵康節(jié)討論天地間為何有電閃雷鳴自然現(xiàn)象,程伊川的回答是“起于起處”。程伊川的這一回答表面上看似乎有些敷衍了事,實(shí)際上程伊川是想告訴邵康節(jié):儒家最高的使命,并不在于單純探究自然現(xiàn)象背后的自然原理,更重要的在于為宇宙生命創(chuàng)建一個(gè)價(jià)值世界和意義世界,建構(gòu)一個(gè)普世性的共同善。由此而來,天理至善是儒家力圖證明的哲學(xué)課題。
漢學(xué)家葛瑞漢指出,程伊川在論證“天理善何以可能”思路上,其問題意識與邏輯路向可梳理為:從天理落實(shí)到性,性善因?yàn)樘炖砩啤!爸劣诙蹋链ê敛华q豫地把善歸于理,因而也歸于性。”(31)[英]葛瑞漢:《中國的兩位哲學(xué)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學(xué)》,程德祥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頁。葛瑞漢這一詮釋應(yīng)當(dāng)是“原樣理解”,從天理至善落實(shí)到性善仁善,確實(shí)是程伊川一以貫之的運(yùn)思路向:“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個(gè)誠,更有一個(gè)敬也。天理云者,這一個(gè)道理,更有甚窮已?”(32)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第31頁,第31頁。天理是天地萬物“所以陰陽者”,是“事物之所由成為事物者”(3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xué)》,吳壽彭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版,第100頁。。既是天地自然存在之最終依據(jù),又是人類社會應(yīng)然法則,所以稱之為“百理具備”(34)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第31頁,第31頁。。不僅如此,天理還是性善何以可能之形而上學(xué)根據(jù):“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35)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二上,《二程集》,第292頁。“蓋天道運(yùn)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36)朱熹:《論語或問》卷三,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頁。天理“至善”!程頤、朱熹這一觀點(diǎn),在中國哲學(xué)史上非常重要。從形上學(xué)高度論證本體“至善”,可能肇始于《莊子》。《齊物論》中的“無己”、“無功”、“無名”,表面上是贊頌真人之德,實(shí)際上是表述“道”之德性,因?yàn)檎嫒恕⑹ト恕⒅寥硕际堑乐烁窕[喻。道至善,在《駢拇》篇中直接表述為道“臧”:“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臧”即善,成玄英《疏》云:“臧,善也”。德源出于道,德“臧”自然以道“臧”為前提。“臧于其德”和“任其性命之情”,都是指道在人性之彰顯。道善決定了人性善,人性(“真性”)中的仁義是“道德不廢”意義上的仁義,這種仁義是“大仁”、“至仁”。在儒家譜系中,尋找并證明“至善”,也是自孔子以來歷代儒家矻矻以求的哲學(xué)使命。《大學(xué)》“止于至善”,還停留在生活倫理的視域論證,尚未上升到形上學(xué)的本體論高度證明。周敦頤以“誠”論太極之德,太極本體已蘊(yùn)涵“純粹至善”的超越德性,但尚處于發(fā)軔時(shí)期。一直到程明道、程伊川和朱晦庵,才系統(tǒng)、深入從哲學(xué)形上學(xué)高度證明“至善”何以可能。天理至善也為華夏之品格找到了合理性依據(jù),有論者指出:“南宋理學(xué)以‘天理’確立‘中國’的正統(tǒng)性,以綱常倫理確立華夏文化的品格特征”(37)劉培:《南宋華夷觀念的轉(zhuǎn)變與梅花象喻的生成》,《文學(xué)評論》,2021年第5期。,這值得我們深思。
緣此,程朱是如何從形上學(xué)層面證明“天理”至善的呢?粗略分析,可分為兩個(gè)層面:
其一,以用證體,從“生生之德”入手,證明天理本體至善。在程頤、朱熹思想邏輯結(jié)構(gòu)中,對“天理至善”何以可能的證明,首先從《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論斷中尋求理論資源。“‘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個(gè)元底意思。”(38)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第29頁。“造化所以發(fā)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為‘成之者性’。”(39)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四,第1897頁。《易傳》作者所言“生生”之德,是從宇宙生成論視域立論,“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本原化生萬物,宇宙之間一片春意盎然。云卷云舒、花開花落,每一種物體都按照其本性自由自在生長。但世界本原從不居功自傲,世界本原有“生生”之德,“生生”之德即是善。在傳統(tǒng)思想資源意義上,除了《易傳》之外,程頤、朱熹思想與老子“道”論有幾分相通之處。老子“道法自然”即“道不違自然”。道生成萬物,但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十章》),道并不居功自傲,也不干預(yù)天下萬物,而是遵循萬物之本性(自然),讓天地萬物自身如其自身地存在與變化。道不僅是本原,而且道有大德。換言之,道是價(jià)值本源與根據(jù)。嚴(yán)靈峰認(rèn)為老子之道有四重義項(xiàng),其中之一就是道乃人生修身養(yǎng)性之應(yīng)然法則。(40)嚴(yán)靈峰:《老莊研究》,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378頁。唐君毅也認(rèn)為,老子之道蘊(yùn)涵“同于德之義”:“道之義亦未嘗不可同于德之義。蓋謂物有得于道者為德,則此德之內(nèi)容,亦只是其所得于道者;此其所得于道者,固亦只是道而已。”(41)唐君毅:《中國哲學(xué)原論·導(dǎo)論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頁。道是一“德性”的最高存在,程子和朱子的天理也先驗(yàn)性具有德性。
其二,進(jìn)一步從超越的意義層面立論。周敦頤《通書》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42)周敦頤:《通書·誠上第一》,《周敦頤集》卷二,第13-14頁。周敦頤以“誠”貫通天人,以形上本體之誠,論證人之心性之誠何以可能。價(jià)值本體已蘊(yùn)涵“純粹至善”的先在德性。二程思想中“善便有一個(gè)元底意思”,應(yīng)當(dāng)是對周敦頤思想的“接著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辟謂之變。”(43)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三,《二程集》,第67頁。“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44)朱熹:《答丘子野》,《朱熹集》卷四十五,第2147頁。
程頤、朱熹在運(yùn)思路向與觀點(diǎn)上,顯然與《易傳》作者大異其趣:一是以“天理”取代了陰陽氣論,理是“所以陰陽者”;二是不再局限于從宇宙生成論角度立論,而是從價(jià)值本體論高度證明。作為非對象性存在的天理,其自身之善天然具有“元”的特性:“善便有一個(gè)元底意思”。天理之善是“元善”,“元善”之善屬于至善,“元善”不是與惡對立的善,而是超越了善惡對立的善。天地萬物“無獨(dú)必有對”,皆是對象性存在。但是,天理是“獨(dú)”,“獨(dú)”也就是“元”,“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45)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二,《二程集》,第1268頁。。如果說“未有不善”還屬于正言反說,以否定句形式表述天理至善(元善)的正面含義,那么以下師生之間的問答已跨越倫理學(xué)高度,直接從本體論視域討論天理何以至善:“或曰:‘《大學(xué)》在止于至善,敢問何謂至善?’子曰:‘理義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識可也。’”(46)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二程集》,第1208頁。《大學(xué)》中的“止于至善”還只是倫理學(xué)層面的概念,與生命理想境界相牽連。但是,二程于此所回答的顯然已不是倫理學(xué)意義上的“至善”,而是本體世界層面的“至善”。天理至善不可以概念、范疇界定,也不可以語言表述與界說,只可以“目之”與“默識”。或許這正是東西方舊形而上學(xué)共同面臨的一道哲學(xué)之“坎”,所以康德會為人類理性劃定一范圍。人類雖不能認(rèn)識與證明,但可以信仰。信仰雖不能證明,但可以相信。“目之”與“默識”,既有求諸普遍證明的特點(diǎn),也蘊(yùn)含直觀體悟與信仰的成分。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天理至善(元善)也是“命”。“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47)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一下,《二程集》,第274頁。理是“命”,天理元善也是“命”,這是程朱哲學(xué)上接孟子思想的一大命題。此處之“命”,蘊(yùn)涵兩層義旨:
其一,命意味著普遍性、平等性。“人之于性,猶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動之物。”(48)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三,《二程集》,第67頁。天、理、性、命在朱熹哲學(xué)體系中,環(huán)環(huán)相扣、相互說明。有人向朱子陳述天與命、性與理四者的區(qū)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于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49)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五,第82頁,第82頁。朱子對這一界說表示肯定,并進(jìn)而解釋說:分而言之,各各不同,在天為命,理落實(shí)于人心為性,已發(fā)為情。因此,命強(qiáng)調(diào)的是天理“流行”。儒家自孔子“仁者安仁”、孟子“四端”肇始,就開啟了人性平等之先河。程頤、朱熹起而踵之,從天理高度論證人性源出于天理,因此天地萬物和人類皆在性理層面存有共同的性,“‘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50)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四,《二程集》,第313頁。。自堯舜以至平民百姓,皆本來就具有共同的性理,皆擁有生命的尊嚴(yán),皆具備內(nèi)在自我超越的道德性命。
其二,“命”意味著無條件性、絕對性。“天之賦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于事業(yè)謂之理。”(51)黃宗羲:《宋元學(xué)案》卷十五,第630頁。“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52)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五,第82頁,第82頁。程頤、朱熹用性溝通天人,貫通形而上、形而下。性源自天理,所以又稱之為性命。性命觀念表明:作為“天之賦與”的性命,在本體層面與天理無二,只是在生活倫理領(lǐng)域有本與用的區(qū)分。天理與性理恒常自存而遍在,先天地而獨(dú)立,即使天地山河塌陷,理、性、命仍然“顛撲不破”。天理至善是自然意志的體現(xiàn),源出于自然運(yùn)行的法則。由此而來,天理至善是一個(gè)定言命令。理善不與惡對,善是超越性的、獨(dú)立的、固有的、先在性的“元善”。
程朱道德形上學(xué)中證明天理至善是及其必要的,因?yàn)樘炖碇辽频臒o條件存在,“性善”、“仁善”等觀念的存在才獲得存在的正當(dāng)性。天理至善是一個(gè)事實(shí)判斷,而且這一事實(shí)判斷又可以自動轉(zhuǎn)換為價(jià)值判斷。天理至善,在整個(gè)程朱理學(xué)體系中,無疑起著一個(gè)十分重要的“拱心石”的作用。
三、仁是“天理自然流行”
“仁”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觀念。孔子之仁,是“愛無差等”與“愛有差等”的辯證統(tǒng)一。在哲學(xué)性質(zhì)上,“仁者愛人”是人類普遍之愛,對陌生人社會有所涉及與設(shè)計(jì)。在工夫論層面,孔子儒家講究一個(gè)“推”字,由家到國,推己及人。“立愛自親始”,由孝親之情向外無限擴(kuò)充,從親親到仁民,從仁民到愛物。孟子的“愛物”,馮友蘭稱之為“天地境界”。此外,尤其可貴的是,孔子“仁者安仁”把仁學(xué)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思想高度。“安仁”就是“樂仁”,以仁為安,就是以仁為樂。仁者安仁,意味著仁與人性有涉。仁不單純只是外在強(qiáng)加給我的人倫規(guī)范,而且也是我內(nèi)在先驗(yàn)性的天賦。徐復(fù)觀先生將孔子人性論概括為“人性仁”,恰如醍醐灌頂,使人有“電然”(梁啟超語)之感。牟宗三先生也說,孔子之“仁即是性,即是天道”(53)牟宗三:《名家與荀子》,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10年版,第135頁。。 遠(yuǎn)在孟子之前,孔子就已經(jīng)不再是就道德談道德,而是有所超越,開始從人性論高度論證仁存在正當(dāng)性,這是儒家仁學(xué)一大特點(diǎn)。董仲舒進(jìn)而從宇宙論視閾論證仁與宇宙本原的關(guān)系,“陽氣仁”,“仁,天心”。仁是氣本原之德性,道德本體論已初步建立。在周濂溪的太極圖式中,無極、太極是本體,誠是本體之德,誠是純粹至善。二程起而踵之,從本體論高度證明天理與仁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學(xué)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54)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第16-17頁。二程哲學(xué)中的“仁”,猶如周濂溪哲學(xué)思想中之“誠”。誠是太極之德,貫通天人上下。仁是“理之性”之德,遍在于人和天地萬物。朱子承二程之余緒,進(jìn)一步從天理哲學(xué)論說仁,“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shù)”(55)朱熹:《答何叔京》,《朱熹集》卷四十,第1885頁。。
通而論之,程朱為何從理本論哲學(xué)高度論說“仁”?其中一個(gè)原因就在于證明:仁是人人先天賦有的自然權(quán)利。在學(xué)術(shù)史上,無論是“性即理”、“性只是理”、“天地之心”、“仁包四德”、“自然本有之理”、仁性愛情,抑或朱子晚年弟子陳淳所言仁是“天理自然流行”,如果我們進(jìn)一步深入思考,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二程、朱子等人所力圖要表達(dá)的一個(gè)觀點(diǎn)為:“仁”屬于人的自然權(quán)利。
仁是自然權(quán)利這一觀念,包含三個(gè)相連貫的命題:
其一,仁作為自然權(quán)利,是天理“自然本有之理”(56)朱熹:《又論仁說》,《朱熹集》卷三十二,第1398頁。。仁是天理的自然規(guī)定,不假外求,內(nèi)在先驗(yàn)自足。孟子稱之為“天爵”,其具體內(nèi)涵是仁義禮智“四德”。既然仁義禮智出于天,孟子進(jìn)而認(rèn)為“人人有貴于己者”(《孟子·告子上》)。“貴”有“良貴”與“非良貴”之別,公卿大夫是“非良貴”,仁義禮智是“良貴”,“良者,本然之善也”(57)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36頁。。本然之善的仁義禮智,人人皆備,所以孟子說“飽乎仁義”(《孟子·告子上》)。仁義之“飽”,不是后天父母、師長“喂飽”的,而是人人先天自然而然“飽”。理解了“飽乎仁義”,方能讀懂“萬物皆備于我。”二程朱子先后從天理本體維度證明仁義源自天理,這是一個(gè)事實(shí)判斷。與此同時(shí),二程朱子認(rèn)為,仁義出自天理這一真理,又可以自動轉(zhuǎn)換為價(jià)值判斷。程頤、朱熹皆認(rèn)為性是天理在人的實(shí)現(xiàn),“性者,渾然天理而已”(58)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五,第2427頁。。性有“理之性”和“氣質(zhì)之性”之分,“理之性”先驗(yàn)蘊(yùn)涵“健順五常之德”。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都是性之固有內(nèi)涵。天理是仁義禮智的“總名”,仁義禮智是天理的“件數(shù)”。天理與仁義禮智信“五常”的關(guān)系不是本體與派生物之間的關(guān)系,而是本體與屬性之間的關(guān)系。在五常之中,仁的地位最高,仁是“體”或“全體”,義、禮、智是“支”:“仁者,全體;四者,四支。”(59)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第14頁。仁是集合概念,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是仁之精神在各種社會關(guān)系中的自然流行發(fā)用。“學(xué)者須先識仁。”程朱哲學(xué)中之“仁”,猶如周敦頤哲學(xué)思想中之“誠”。誠是太極之德,貫通天人上下。仁作為“天理”之德,“不是待人旋安排”(60)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六,第111頁,第111頁。,而是顯現(xiàn)為“一個(gè)渾然溫和之氣”(61)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六,第111頁,第111頁。,作為一個(gè)亙古不移的價(jià)值判斷,自然發(fā)用流行于人的經(jīng)驗(yàn)世界中。
朱子晚年弟子陳淳起而踵之,在朱子仁是天理“自然本有之理”基礎(chǔ)上,進(jìn)而提出仁是“天理自然流行”(62)陳淳:《北溪字義》卷下《嚴(yán)陵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5頁。。當(dāng)年曾子以“忠恕”概括孔子一貫之道,忠是內(nèi)在的盡己之心,是對自己的道德要求;恕是對待他人的道德態(tài)度,恕是由未發(fā)轉(zhuǎn)向已發(fā)過程中的價(jià)值判斷與選擇,既有價(jià)值之心的因素,也包含外在的禮儀節(jié)文。忠與恕相合,就是仁。陳淳撰有《一貫》一文,“一”是天理本體,“自其渾淪一理而言,萬理無不森然具備”(63)陳淳:《北溪字義》卷上《一貫》,第31頁,第31頁,第31頁。。 “貫”是體用之用,指謂“一理流出去”,貫行到天地萬事萬物。按照二程朱子的思維邏輯,天理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性中仁包四德。陳淳這里所說的“一貫”之“貫”,就是仁。仁從“一理流出去”,在父為慈,在子為孝,在夫妻為別,在朋友為信,在君臣為義。甚至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動容周旋之禮,都是仁“從這大本中流出見于用”(64)陳淳:《北溪字義》卷上《一貫》,第31頁,第31頁,第31頁。。大至參天地之化育,小到日常灑掃應(yīng)對、挑水劈柴,都是仁的體現(xiàn)與應(yīng)用,“無非此一大本流行貫串”(65)陳淳:《北溪字義》卷上《一貫》,第31頁,第31頁,第31頁。。陳淳特意提及孔子待師長之道,以論證“一貫”之理。一位名叫冕的盲人樂師曾來拜訪孔子,孔子親自出門迎接,走到階沿,孔子細(xì)心提醒他“小心臺階”。走到坐席旁,孔子又提醒他坐席的位置。待主客坐下后,孔子一一介紹:“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告辭后,弟子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問孔子這是否就是尊重盲人的禮儀,孔子回答“然,固相師之道也”,指出這就是尊敬師長之禮儀。生活禮儀的深處,可以感悟價(jià)值本體之仁的存在。韓愈嘗言“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師是道的承載者、弘揚(yáng)者,而道則是師存在的理由與精神歸宿,師與道合一。
其二,仁義禮智信作為人先驗(yàn)的自然權(quán)利,具有普遍性。人人擁有自然權(quán)利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們都是人。人的自然本質(zhì)“天生注定”人人享有基本的權(quán)利和實(shí)現(xiàn)這些自然權(quán)利的自由。無論是貴戚之冑,還是販夫走卒,人人都有仁性。猶如“月印萬川”,月光播撒每一寸山河大地。
孟子認(rèn)為“人皆有仁義之心”(66)焦循:《孟子正義·告子章句下》,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77頁。,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都有成為堯舜的心性與道德基礎(chǔ),就在于人人皆有此“心”。順心而“為”,猶如“掘井”。半途而廢,“猶為棄井”。漢代董仲舒從宇宙論高度證明:天撫育萬物、泛愛群生、謙退自讓、周而復(fù)始、誠而有信,天有“仁”之德。“仁,天心也。”(《春秋繁露·俞序》)人“受命于天”,所以“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之血?dú)馐窍忍斓拇嬗校盎熘径省?《春秋繁露·為人者天》),血?dú)饣熘荆@現(xiàn)為仁德。因此人之仁德源自天,落實(shí)于人心,具體體現(xiàn)為“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是上位概念,已可統(tǒng)攝忠、信、慈、惠、禮、義、廉、讓諸德目。程伊川從“性即理”出發(fā),進(jìn)而認(rèn)為,“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是見乎外”(67)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三,《二程集》,第309頁。。既然仁是“固已存乎其中”,仁就屬于全人類,仁對“陌生人社會”普遍適用。正因?yàn)槿示哂衅毡樾裕拍艹蔀橐环N天然而普遍的自然權(quán)利。在這一自然權(quán)利與道德基礎(chǔ)之上,圣人境界才得以可能臻至。其后朱熹進(jìn)一步推導(dǎo):既然“天下無性外之物”(68)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四,第61頁,第56頁,第60頁,第57頁,第58頁。,既然天地萬物都先在性稟具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那么,至少在邏輯上承認(rèn)天地萬物甚至禽獸也稟受了“五常”成為無法回避之事實(shí)。有人問朱子:既然“性具仁義禮智”,此處之“性”,是否涵蓋天地萬物甚至昆蟲?朱子回答:“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69)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四,第61頁,第56頁,第60頁,第57頁,第58頁。既然承認(rèn)禽獸也先在性稟具“五常”之性,虎狼也有父子之親,蜂蟻也有君臣之禮,豹獺也知道報(bào)本,睢鳩也講究雌雄之別,那么人與禽獸昆蟲的區(qū)別在何處呢?朱子答道:“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卻專。人卻事事理會得些,便卻泛泛,所以易昏。”(70)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四,第61頁,第56頁,第60頁,第57頁,第58頁。既然“人物之性一源”,當(dāng)然禽獸也具“五常”之德。人獸之別僅僅在于:人能稟受“五常”之全體,禽獸由于氣稟有別,只能得“五常”之偏:“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diǎn)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diǎn)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diǎn)子光。”(71)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四,第61頁,第56頁,第60頁,第57頁,第58頁。朱熹將“性”比喻為日光,人性得“性”之全和形氣之“正”,受日光大;物性得“性”之偏,受日光小,因而只“有一點(diǎn)子明”。“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72)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四,第61頁,第56頁,第60頁,第57頁,第58頁。當(dāng)年孟子明確指出,人與禽獸的“幾希”之別,就在于人先天賦有仁義禮智道德本質(zhì),禽獸是絕對沒有的。 朱子的天理既是人類文明共同體的道德根基,也是人類與宇宙萬物的“共同善”。既然如此,就必須承認(rèn)虎狼有“仁”,蜂蟻有“義”,盡管只“有一點(diǎn)子明”,但畢竟還“有一兩點(diǎn)子光”。
其三,仁作為自然權(quán)利,與人的本性密不可分。但是,人必須借助理性對這一自然權(quán)利進(jìn)行認(rèn)識。霍布斯說:“著作家們一般稱之為自然權(quán)利的,就是每一個(gè)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運(yùn)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這種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斷和理性認(rèn)為最適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73)[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5年版,第97頁。霍布斯于此指出自然權(quán)利有兩大特點(diǎn):一是自然權(quán)利是自由的基本內(nèi)容;二是自然權(quán)利來源于人的天性。朱子指出仁作為“愛之理”,是天理“自然本有之理”(74)朱熹:《又論仁說》,《朱熹集》卷三十二,第1398頁,第1394頁。。后生弟子首先在認(rèn)識論上需“識仁之名義”,認(rèn)識到仁為“自然本有之理”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其次,在工夫論與境界論上,后生弟子“知其用力之方”(75)朱熹:《又論仁說》,《朱熹集》卷三十二,第1398頁,第1394頁。。陳淳第一次拜見朱子時(shí),朱子就諄諄教誨陳淳做學(xué)問需從“根原”處下手。換言之,思考問題需打破就道德論道德的藩籬,應(yīng)上升到本體論層面探究事物的根原。陳淳撰有《孝根原》一文,專門探究“人為何行孝”?“為人子止于孝,夫人子于父母,其所以拳拳竭盡如此,篤切而不敢緩,極至而不敢少歉者,是果何為而如此也?”(76)陳淳:《孝根原》,曾棗莊等主編:《全宋文》卷六七二六,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頁。孝源自父母的懇切教導(dǎo)嗎?孝源自對父母責(zé)罵的畏懼嗎?人降生于世,絕不可能“天降而地出”。懷胎十月而出,不是父母的“安排計(jì)置”,而是“為天所命,自然而然”。所謂“自然而然”,意味著人的出生是天道自然而然,“人道之所不能無俯仰戴履”,人道因循天道,人稟陰陽二氣而有此身,又稟天理而有此性。人生天地間,“豈能出乎天理之外哉”(77)陳淳:《孝根原》,《全宋文》卷六七二六,第211-212頁,第212頁。,人性中的仁作為“理之性”核心,并不是后天教化所形成,而是先天的稟賦。但是,人只有從哲學(xué)高度思考,才能梳理天理與仁的關(guān)系。仁源自天理,作為普遍性、絕對性的自然權(quán)利和道德自律賦予人類。正因?yàn)槿绱耍热蝗松谑溃瑹o法一日而游離出天理之外,“決不可空負(fù)人子之名于斯世,決然在所當(dāng)孝,而決不容于不孝”(78)陳淳:《孝根原》,《全宋文》卷六七二六,第211-212頁,第212頁。。當(dāng)年程子增字解經(jīng),將孝悌訓(xùn)讀為“行仁之本”而非“仁之本”,目的就在于從天理本體層面證明:仁作為天理之性,是孝存在正當(dāng)性的形而上依據(jù)。陳淳的《孝本原》在問題意識與觀點(diǎn)上,對程朱的觀點(diǎn)作了更加詳細(xì)的闡釋。
仁是“自然本有之理”、“天理自然流行”、仁作為自然權(quán)利人人皆有、仁內(nèi)在于人性,仁作為自然權(quán)利所具有的這三大規(guī)定,陳淳用理有“能然”、“必然”、“當(dāng)然”和“自然”加以融匯貫通:
其一,“理有能然”(79)陳淳:《理有能然必然當(dāng)然自然》,《全宋文》卷六七二七,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30頁。。乍見孺子入井,觸動惻隱之心。惻隱是情感,是氣,惻隱之心何以能夠發(fā)生?是因?yàn)閻烹[情感的背后有仁性驅(qū)使,仁是人性先驗(yàn)的存有,仁不是人建構(gòu)出來的,也不是人理性的產(chǎn)物。仁是人發(fā)現(xiàn)的人性奧秘,猶如阿里巴巴喊著“芝麻開門”走進(jìn)神秘山洞發(fā)現(xiàn)了奇特寶藏。正因?yàn)槿讼忍炀哂腥市裕栽凇罢б姟鼻榫爸拢瑫匀欢灰l(fā)惻隱之心。
其二,“理有必然”。乍見孺子入井,必然會引發(fā)惻隱之心,施以援手。人不是槁木死灰,人心是活潑潑的,活潑潑的人心見孺子入井,必然觸動內(nèi)在的惻隱之心。“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80)陳淳:《理有能然必然當(dāng)然自然》,《全宋文》卷六七二七,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30頁。即使出于后天某種功利性考量忍住不上前搶救孺子,但是,基于內(nèi)在仁性之上惻隱之心“不容已”。惻隱之心猶如地下泉水,生生不息,噴涌不止。即使有人出于某種利益上的欲求強(qiáng)行壓制,但泉水一如既往“不容已”。
其三,“理有當(dāng)然”。乍見孺子入井,觸動惻隱之心,不假思索上前營救,這是天理之“當(dāng)然”。人與禽獸的區(qū)別就在于有“不容已”之天理良心,“當(dāng)然”就是人類特有的價(jià)值判斷與價(jià)值選擇,一旦違背“當(dāng)然”,就是“悖天理而非人類”(81)陳淳:《理有能然必然當(dāng)然自然》,《全宋文》卷六七二七,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30頁。。具體而論,“當(dāng)然”又可細(xì)分為兩類:一是以義裁斷,在“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82)陳淳:《理有能然必然當(dāng)然自然》,《全宋文》卷六七二七,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30頁。。譬如,孺子入井應(yīng)當(dāng)惻隱,為父應(yīng)當(dāng)慈,為子應(yīng)當(dāng)孝,為君應(yīng)當(dāng)仁,為臣應(yīng)當(dāng)義,凡是都以“義”作裁斷,“惟其義盡,所以仁至。”二是以智立身處世,事事“揀別其是是非非”(83)陳淳:《理有能然必然當(dāng)然自然》,《全宋文》卷六七二七,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30頁。。視其所當(dāng)視,聽其所當(dāng)聽。是非善惡辨別清楚,“則得其正而為理”(84)陳淳:《理有能然必然當(dāng)然自然》,《全宋文》卷六七二七,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29頁,第230頁。。
其四,“理有自然”。乍見孺子入井,觸動惻隱之心,奮勇上前營救,屬于“天理之真流行,發(fā)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偽預(yù)乎其間”(85)陳淳:《理有能然必然當(dāng)然自然》,《全宋文》卷六七二七,第230頁。。乍見孺子入井,我們可以說是“觸動”、“引發(fā)”了惻隱之心,但不可以說“滋生”了惻隱之心。見到或者沒有見到孺子入井,惻隱之心本來就存在于我心,“乍見”引發(fā)了我先天固有的惻隱而已。“乍見”不是見到孺子入井,馬上立一個(gè)“心”去盤算、計(jì)較是否去上前營救,而是“乍見”與惻隱之心同一時(shí)間閃現(xiàn)。這種閃現(xiàn),猶如大自然電閃雷鳴。“乍見”與惻隱之心,在時(shí)間上完全同步,不分先后。在學(xué)術(shù)史上,王夫之曾經(jīng)對孟子關(guān)于惻隱之心的觀點(diǎn)提出質(zhì)疑:“且如乍見孺子將入于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及到少間,聞知此孺子之父母卻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救之為逆,不救為順,即此豈不須商量?”(86)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八《孟子》,《船山全書》第六冊,長沙: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943頁,第943頁。應(yīng)該說,王夫子沒有讀懂孟子的“惻隱之心”,他的這一反駁失之偏頗。如果因不共戴天之仇而棄孺子入井于不顧,這已經(jīng)是由后天的功利性利益支配其行為。但是,孟子力圖要證明的是:人之仁義禮智“四心”,超越后天人文教化與知識。不是“乍見孺子將入于井”會“滋生”出我的惻隱之心,而是惻隱之心本來就存在于我心,孺子入井只不過是觸動、引發(fā)了我內(nèi)在的惻隱之心而已。“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87)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八《孟子》,《船山全書》第六冊,長沙: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943頁,第943頁。惻隱之心屬于“本心”、初心,不是后天“安排商量”產(chǎn)生的,而是不假思索的“天理自然流行”。
四、結(jié)語
天理本體無方所、無時(shí)間,是一無時(shí)空性的形而上存在。但是,天理從來就沒有游離人的歷史,是宇宙生命共同體的道德根基,是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共同善”。至善天理的普遍存在,在天地自然“生生之德”和有限的生命個(gè)體經(jīng)驗(yàn)世界中,皆可以得到證明與彰顯。至善的天理作為“共同善”,屬于絕對性的“命”。天理至善是一個(gè)事實(shí)判斷,而且又可以轉(zhuǎn)換為價(jià)值判斷。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程朱學(xué)派以天理說仁,還蘊(yùn)含仁是人類自然權(quán)利的內(nèi)涵。仁作為先天的人類自然權(quán)利,是天理“自然本有之理”,屬于“天理自然流行”,不假外求,內(nèi)在先驗(yàn)自足。人擁有自然權(quán)利的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們是人,人的自然本質(zhì)決定了人雖然是有限的個(gè)體,但先在性賦有這一權(quán)利與自由。由此而來,仁既然是自然權(quán)利,違反自然權(quán)利就是違背天理。人的自然權(quán)利不是社會制度與法律發(fā)明出來的,自然權(quán)利先于人世間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社會制度與法律作為人類讓渡其自然權(quán)利而產(chǎn)生的社會契約性存在,其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運(yùn)用公權(quán)力確認(rèn)與保衛(wèi)這些自然權(quán)利。在西方歷史與文明史上,自然權(quán)利的理論可以上溯至古希臘時(shí)代的哲學(xué)家們。啟蒙運(yùn)動之后,繼而從自然權(quán)利中衍生出財(cái)產(chǎn)權(quán)、法律權(quán)、選舉權(quán)等權(quán)利與自由。在中國思想史傳統(tǒng)中,對自然權(quán)利的思考與敘述,有著自身獨(dú)特的問題意識、敘事模式與發(fā)展趨向。自然權(quán)利與自由思想資源,還有待于我們繼續(xù)深入挖掘與系統(tǒng)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