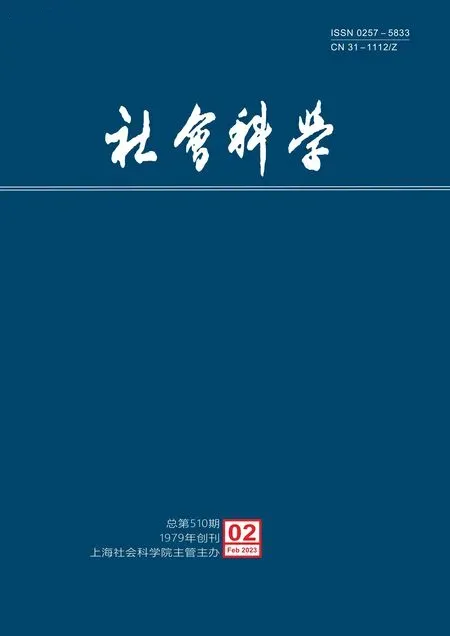古爾納的《天堂》與東非貿易圖景*
朱振武 陳 平
引 言
2021 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 1948—)對移民問題始終如一的深切關懷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高度關注,其實商貿主題也是古爾納小說中的一個重要特點。古爾納出生于東部非洲的桑給巴爾,獨立后歸屬坦桑尼亞,其母語為斯瓦西里語。由于20 世紀60 年代桑島政權交替,內部動亂,古爾納為躲避迫害便逃到了英國。此后,古爾納便一直在英國學習、工作和生活,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從事文學創作。作為研究者,古爾納的研究領域為后殖民文學,曾撰有多篇關于奈保爾、恩古吉、索因卡等作家的研究文章。作為小說家,他目前已發表了10 部長篇小說,還零散發表了一些短篇作品及隨筆。《天堂》(Paradise, 1994)是古爾納的第四部長篇小說,曾獲得布克獎提名。這部小說不僅有著引人入勝的情節,更有著豐富深刻的文化意蘊,所營構的文學空間充分體現了古爾納學者型作家的特點。小說借助斯瓦西里孩童優素福(Yusuf)的視角,展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特殊歷史。故事發生于原本是阿拉伯人貿易天堂的德屬東非海岸,但隨著歐洲殖民勢力的滲透,阿拉伯商人阿齊茲(Aziz)為開拓貿易空間,采用了一條非常規的路線進入非洲內陸。內陸的大湖地區常出現在歐洲探險者們的游記之中,而阿齊茲所從事的象牙貿易也極易讓人聯想到一些文學史上的其他經典之作。
一、進入內陸深處的三種文學方式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非洲的內陸深處便是這樣一處危險而又充滿誘惑之地。《天堂》與康拉德的經典作品《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均涉此空間,兩部作品中的故事人物也同樣是從海岸到達內陸,只不過馬洛(Marlow)駕駛的蒸汽船自西逆流而來,而阿齊茲的商隊則是從東海岸出發,翻山越嶺方至。兩部小說的發表時間相隔幾近百年,但具體的故事發生時間卻前后不過相差一二十年。康拉德和古爾納各自在小說中反映了一段歐洲人和阿拉伯人在非洲內陸不甚光彩的貿易歷史。因兩部小說所涉文學地圖有重合之處、“敘事上存在逆轉和修訂”,①J.U. Jacobs, “Trading Palaces in Abu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2, No.2, 2009, p.77.故有西方學者認為二者存在互文性關系。當然,這種關聯性是一種羅蘭·巴特或克里斯蒂娃式的,而非熱奈特式的。②在小說《天堂》的文本內部,并未出現與《黑暗的心》相關聯的直接文本,因而二者是一種廣義上的互文性,而非狹義的互文性。同樣,不止是古爾納的《天堂》,獲得2001 年諾貝爾獎的印度裔作家奈保爾的小說《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也被認為是康拉德經典文本的文學回聲或共振。但事實上,這三部小說無論是在創作動機還是文本呈現上都保持著高度的獨立性,它們各自營構的是三段分隔卻也互補的歷史場景。可以說,康拉德、奈保爾、古爾納是在三個不同的文學路徑上抵達了非洲的大陸深處。
既然三者之間缺乏比較文學法國學派所主張的那種事實影響關系,緣何眾多讀者、批評家們卻熱衷于將《天堂》與另兩部作品相比較呢?③此類研究如Fawzia Mustafa, “Gurnah and Naipaul:Intersections of Paradise and A Bend in the River”,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Vol.61, No.2, 2015。原因可能無非就是兩點:一是康拉德的文本太過經典,已深入人心;二是內陸深處過于吸引人,而所涉文學又少之又少。因而,《天堂》這類涉及到非洲內陸深處的文本一出現便被自然或不自然地納入到了《黑暗的心》所衍生出的文本宇宙中。作品一經產生,其闡發批評的權利便落到了讀者、批評家的手中。作為學者型的作家,古爾納自然深知這一點,在采訪中也大方承認互文性閱讀的愉悅性及價值和意義。④參見Tina Steiner, “A Conversation with Abudulrazak Gurnah”,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6, No.1, 2013, p.166。關聯性的閱讀不僅不會減損這位諾獎新貴的作品價值,反而可以讓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古爾納的文學地圖及文學地圖中的古爾納。
古爾納雖與康拉德和奈保爾一樣入籍了英國,但統觀他目前已發表的10 部長篇小說和零散的幾部短篇作品,便不難發現,古爾納筆下的文學地圖主要還是東非海岸及桑給巴爾島周圍的斯瓦西里文化區。而這也是古爾納與康拉德及奈保爾的根本不同之處,古爾納雖移民英國,并采用英語寫作,但從其作品文化層面來看,他仍舊是一名流散的非洲作家。作為一名后殖民文學研究專家,古爾納自然熟稔《黑暗的心》《河灣》等此類經典文本,面對康拉德、奈保爾這些文學先驅,影響焦慮固然存在,但這種影響卻在其小說《天堂》中幾乎察覺不到。從作品時空來看,古爾納的第四部小說構建的是一個與《黑暗的心》幾乎平行的歷史空間,一個屬于東非海岸阿拉伯、斯瓦西里商人的貿易空間。其次,若論文化互文性,這部小說明顯受到的是以《古蘭經》為代表的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小說主人公優素福的經歷便可看做是《古蘭經》中同名人物的斯瓦西里海岸版本。此外,該小說還同樣受到斯瓦西里語作品的影響,如游記、自傳等,目前已有國外研究者撰文論述這一影響。⑤如Fawzia Mustafa, “Swahili Histories and Texts in Abu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8, No.1, 2015, pp.14-29。但對于國內研究者來說,若想弄清這一影響關系,難度還較大,因為古爾納的作品其實是經過了文化轉譯:他將自己腦海中的斯瓦西里語作品文本自譯為英語作品。其作品中夾雜著大量的斯瓦西里語詞匯、洋涇浜拼寫,因而翻譯、研究這類作品難度較大,穿越英語文化后還要面對相對比較陌生的斯瓦西里語文化。再論《天堂》與《河灣》,雖然奈保爾筆下的印度裔主人公薩林姆(Salim)同樣來自東非海岸,也是自東向西來到內陸深處從事商業貿易,但除卻兩部小說的故事時間分屬殖民時期和后殖民時期外,二者最大的不同便是作家的文化立場不同。奈保爾更多的是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考量非洲大陸,而當奈保爾癡迷于個人主義時,古爾納卻始終棲居在破碎的集體中。
明晰了古爾納筆下的文學地圖,再跳出來看文學地圖中的古爾納。在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非洲文學研究者們都面臨一個尷尬的問題,即如何在現有的文學版圖尤其是非洲文學版圖中重新擺放古爾納的問題。畢竟,他在此前是一個相對透明的存在,確實“不常見于經傳”。中國國內也只是在古爾納獲得諾貝爾獎后才購買了他一部長篇小說的版權,此前只有兩個短篇作品得到過譯介。通常情況下,非洲往往被看做一個整體,但非洲并非鐵板一塊,其內部文化千差萬別。如果細數非洲著名的英語作家,除了同樣獲得諾貝爾獎的南非作家庫切這類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作家外,大多數非洲作家其實是部族集體的代言,如:代表伊博文化的阿契貝,代表約魯巴文化的索因卡,代表基庫尤文化的恩古吉,代表白人“殖民流散”①這一概念詳見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學的時代表征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9 年 第7 期。群體的戈迪默等。而之前被忽視的古爾納,其代表的恰是亞非融合的斯瓦西里文化。絕大多數非洲作家置身于大西洋文化圈中,關注的是殖民地與宗主國的歷史與現實等諸多問題,而古爾納試圖將讀者帶入的則是一個更加錯綜復雜的印度洋文化空間。印度洋既是一個貿易文化的空間,又是一個伊斯蘭文化的空間,從這一視閾出發,能更好地認識古爾納,更好地解讀和研究《天堂》這部小說。
二、移動性與貿易空間
幾千年來,印度洋一直是一片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競技舞臺。沖突在此上演,融合亦在此上演,而沖突與融合的背后,是圍繞著貿易空間展開的力量角逐。蒸汽時代來臨之前,在這片大洋上航行的船只還需憑借季風的力量,無論是阿拉伯商販的單桅帆船、印度商賈的三桅貨船,還是中國使臣的旗艦寶船。“使節勤勞恐遲暮,時值南風指歸路”,②引自馬歡的紀行詩,詳見馬歡:《瀛涯勝覽》,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這句詩說的就是印度洋上的東南季風。因季風每年如約而至,交替分明,故印度洋上的商業航行呈現出一種規律性和時序性。同樣,為配合貨物出航,路上的商隊之旅也具有明顯的周期性。非洲的東海岸構成了印度洋的西翼,阿拉伯商人很早就開始在這里擇優良港口來建立自己的貿易站點,而隨著19 世紀阿曼勢力在東非的恢復與進一步滲透,阿拉伯商人也極大地擴張了他們的貿易空間。當阿曼的賽義德蘇丹遷居桑給巴爾島后,海岸與非洲內陸的貿易便愈發繁榮。阿拉伯商隊幾乎主導了這一時期的貿易,他們將攫取的黃金、象牙以及奴隸等運抵海岸,進而運往印度洋各地。這種貿易模式一直持續到歐洲殖民者統治時期,后來即便歐洲人叫停了海岸的奴隸貿易,但象牙貿易還在繼續進行,《天堂》中的故事便發生在這一歷史時期。
移動性是古爾納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征,《天堂》更是如此。主人公優素福是一名“雷哈尼”(rehani),③這一詞匯為斯瓦西里語,古爾納常在其小說中保留斯瓦西里語的特定表述,并進一步用英文加以解釋。詳見Abdularazak Gurnah, Paradise, New York:The New Press, 1994, p.47。即債務奴隸。他原本與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個叫卡瓦(Kawa)的小鎮上,但因其父經營不善,十二歲的他被父親典當給了阿拉伯商人阿齊茲。隨后,他便被阿齊茲帶到了海岸的住處,并被安排在商店里工作。但店鋪盈利顯然不是阿齊茲的主要收入來源,按照小說中的描述,他是那個時代少有的能夠自行組織商隊前往內陸的阿拉伯商人,因此,稍稍長大的優素福又隨阿齊茲及其商隊前往了內陸。當然,阿齊茲之所以帶上優素福,個中另有隱情。小說到了第五章才揭示這一原因:為了使優素福遠離女主人。總之,在12 歲到18 歲這一段時間里,移動是優素福的常態,而當其在小說結尾選擇逃離并加入德國雇傭軍后,這種空間移動想必還會延續下去。
不止優素福,小說中的眾多人物都經歷了或多或少的移動,但歸根到底,都可以找到一個經濟的動因。在一個以貿易為主導的商業社會中,絕大多數商人會因貿易空間的變動而變動。以優素福的父母為例,他們之所以來到卡瓦小鎮,是因為看中了德國于此修建鐵路的紅利。但新的貿易空間很快萎縮,鐵路站點只帶來了短暫的繁榮。再比如乞力馬扎羅山腳下的哈米德· 蘇萊曼(Hamid Suleiman)夫婦,他們原本都來自海岸地區,之所以扎根山下小鎮,無非是因為那里是來往商隊的落腳歇息之地。此外,還有印度錫克教教徒哈班斯·辛格(Harbans Singh),①在小說中,眾人都叫他卡拉辛加(Kalasinga),卡拉辛加類似于哈班斯· 辛格的外號。Fawzia Mustafa 在其研究文章中指出, 卡拉辛加在歷史上確有其人。而在斯瓦西里語中,人們習慣將東非的錫克教徒稱為“卡拉辛加”。他是一名機械師,獨自生活在山下小鎮,想必無非是為途經此地的火車和商人們提供技術保障。當然,富商阿齊茲,無疑是小說中為探求新的貿易空間而移動的代表性人物。而他的行蹤路線,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阿拉伯商人的貿易軌跡。可以說,阿齊茲,不是在貿易行進中,就是在貿易籌備中,只有在齋月才盡可能地留在自己家中。綜合優素福及優素福的商店伙伴哈利勒(Khalil)的早先經歷,可以大致管窺阿齊茲的貿易活動范圍之廣。小說開頭提到,阿齊茲在優素福家的停歇是短暫且每次相隔很久的,如此規律的來訪讓年幼的優素福誤以為他就是自己的叔叔,因而才稱呼他為“阿齊茲叔叔”。但只有優素福叫他“叔叔”,在小說中,與優素福同為債務奴隸的哈利勒以及商隊領隊穆罕默德·阿卜杜拉(Mohammed Abdalla)等人,都只能畢恭畢敬地稱阿齊茲為“賽義德”(Seyyid)。②賽義德雖為阿拉伯男性的常見姓名,但在小說中,這是人們對阿齊茲的尊稱,有主人、雇主之意,古爾納也借助小說人物 哈利勒之口將其解釋為“master”。這位賽義德早年也只是一個小商人,往返于桑給巴爾島與海岸之間,從事著小商品貿易。他被桑給巴爾島的一位富孀相中后,命運得以改變,變賣了富孀的資產后,才真正有實力染指內陸貿易。
組織一次內陸貿易需要雄厚的財力支撐,并非所有人都像阿齊茲那般幸運,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其實是:當時的絕大多數阿拉伯商人、斯瓦西里商人在組織內陸商隊時都需要向印度金融家借貸。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馬克森在其著作中指出:
印度的商人和銀行家以借貸的方式向貿易者提供資金,而斯瓦西里和阿拉伯的商人則組織并率領商隊進入內陸地區。商隊由許多搬運工組成,他們搬運貿易商品如布料、銅線、玻璃珠以及槍支,以換取內陸的象牙。③羅伯特· 馬克森:《東非簡史》,王濤、暴明瑩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 年,第98 頁。
可見,一次成功的內陸貿易需要多方的合作,印度金融家為當時的內陸之行提供了資金支持。這些印度資本家多來自孟買,在東非海岸及桑給巴爾島的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甚至桑給巴爾的蘇丹有需要時都向他們借貸。
除卻資金支持外,前往內陸的貿易還需要一批職業的搬運工,畢竟這是一項充滿危險且極具挑戰性的工作,一般人難以勝任。事實上,在19 世紀時,坦噶尼喀就形成了獨特的搬運文化。早在阿拉伯人深入內陸之前,尼亞姆韋齊人(Nyamwezi)就已經開始將象牙運輸到海岸。之后,他們作為自由勞工被阿拉伯人雇傭。由于紀律性強,能力突出,尼亞姆韋齊人在商隊貿易中逐漸成了專業搬運工的代名詞。起初,這些尼亞姆韋齊人只是在旱季農閑時才參與搬運工作,后來隨著內陸與海岸間貿易的加強,他們為上一個商隊搬運完又立刻投入到下一個商隊的工作中,搬運便成為了他們的全職工作。根據斯蒂芬·勒克爾的研究,除了坦噶尼喀西部的尼亞姆韋齊人之外,在東部海岸也陸續出現了其他搬運工人:
后者通常是一些來自海岸地區、桑給巴爾島的奴隸或重獲自由的奴隸,他們部分或完全加入到了斯瓦西里社會中,盡管他們曾經可能來自東非任何其他社群。他們自稱為“紳士”(waungwana④該詞為斯瓦西里語詞匯,意為先生,但在搬運文化中,這個詞匯有著特定意義。or gentlemen),當然有時也被他們的歐洲雇主稱為“桑給巴里斯”(Zanzibaris)。⑤Stephen Rockel, “ Wage Labor and the Culture of Portera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Tanzania:The Central Caravan Routes”, SouthAsia Bulleti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15, No.2, 1995, p.14.
《天堂》中阿齊茲商隊的搬運工人就屬于后者,在當時,這些搬運工人不只為商人服務,還常為歐洲探險家們所雇傭,理查德·伯頓、約翰·斯皮克以及亨利·斯坦利等人的探險隊伍中就存在著大量的搬運工人。東非的職業搬運工人可謂海岸商業社會的標志性群體,他們代表了一種特殊的移動性文化,在貿易空間的開拓中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為何如此遠距離的貨物運輸要依靠人力而非畜力呢?事實上,由于歐洲人的到來,19 世紀的東非牛瘟盛行,可供使用的牲畜資源在當時十分稀少。況且,內陸地勢復雜,氣候濕熱,采用人力搬運更具有機動性和安全性。不過,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隨著鐵路的修建,新的交通方式改變了商隊原有的行進方式。從小說《天堂》中不難看出,阿齊茲商隊向內陸行進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商人和搬運工從海岸先坐火車前往內地,之后再下車徒步前行。古爾納雖未明確交代小說的背景時間,但從鐵路修建進度以及英德之間的關系等信息就可大致推斷該時期為一戰前夕。對于地理空間的描寫,小說中的許多地點也并非真實,古爾納采用了真實與虛構相結合的空間構建。但同理,我們依舊可以通過鐵路線大致推斷小說人物的主要活動空間,只是需要一些交通史知識。德國,早先其實是德屬東非公司,在坦噶尼喀共修建了兩條鐵路:先修建的一條是烏薩姆巴拉鐵路(Usambara Railway),之后又沿著當時最重要的商路修建了一條從海岸通內陸的中央鐵路(Central Railway)。據優素福與阿齊茲的鐵路出行路線可大致推斷出優素福父母所在的虛構小鎮就處于修建中的中央鐵路線周圍,而小說中的海岸小鎮很可能就是坦喀(Tanka)。鐵路作為東非商人的一種新的移動方式,便捷之處自不待言。但凡事都有利有弊,如此高效的交通方式自然會擠壓原有的貿易空間,搭乘鐵路前來的商人越多,貿易的難度也就變得越大。也正是基于此,阿齊茲才去尋求新的貿易空間,只不過隨著歐洲殖民勢力的不斷滲入,阿拉伯商人的貿易天堂正在消逝。
三、貿易秩序的構建與維系
20 世紀初的坦噶尼喀,雖已是德屬殖民地,但在古爾納的《天堂》中,德國人的存在感甚至還不如印度人。除了開篇與結尾,德國人只是出現在商客們閑談時的只言片語中,仿佛一個遙遠的存在。小說主要呈現的是一個由阿拉伯人、斯瓦西里人占主導的商業社會,而在這一空間內,無論是英國人,還是德國人,都只是被模糊為歐洲人并作為背景人物提及。其實,古爾納的這一處理方式既是一種有意為之,又是當時真實歷史的一種斷面呈現。當時的東非海岸,各方勢力錯綜復雜,德國雖占據了此地,但是根基還不牢,①與歐洲其他殖民國家不同,德國在東非的殖民活動早先其實是由民間殖民協會主導,卡爾· 彼得斯的殖民活動甚至一度還 曾遭到宰相俾斯麥的反對。1885 年柏林會議之后,政府層面的德屬東非才真正成立。所以其殖民統治面臨內憂外患。在外,英德之間一直暗中角力,德國強占的海岸原本是桑給巴爾蘇丹的主權地,而彼時的桑給巴爾蘇丹國又成為了英帝國的保護國。在內,各種反抗活動不斷,既有海岸阿拉伯人的抵抗活動,又有內陸土著居民此起彼伏的起義破壞。②德國控制坦噶尼喀后,在當地強行推廣棉花種植,這一行徑迅速激化了矛盾,當地民眾紛紛起義抵抗。其中,最大規模的 一次起義是馬及馬及起義(Maji Maji Rebellion)。古爾納在這種宏觀歷史背景下只呈現某一特定社群的書寫方式其實在其他非洲作品中也十分常見,如阿契貝的《瓦解》,如恩古吉的《大河兩岸》等。恩古吉在其作品中為構建基庫尤部族的民族獨立史詩,直接將英國殖民者符號化為“利文斯頓”這一背后人物。而在《天堂》中,古爾納去歐洲化的書寫其實是通過聚焦敘事視角來達成的,盡管那時阿拉伯人的貿易空間已經越來越逼仄,但在一個斯瓦西里男孩眼中,貿易仍是井然有序的。
貿易秩序的構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阿拉伯人經過幾代人幾個世紀的經營方才達成這一目標。當然,這種秩序構建的過程勢必充斥著暴力與罪惡,而在這套貿易體系之下,不止有普通的商品交易,還曾有奴隸販賣。眾所周知,歐洲人在殖民活動中一手捧著《圣經》,一手執著利劍,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阿拉伯人在東非海岸的勢力擴張,只不過他們帶去的是《古蘭經》。如果說阿拉伯人在東非海岸打造了一處貿易天堂,那么以《古蘭經》為代表的伊斯蘭文化無疑穩固并裝點了這一天堂。
古爾納筆下的穆斯林們有著很強的榮辱觀念,國外學者古德溫·希恩杜(Godwin Siundu)在自己的研究文章中就指出古爾納小說中的人物憑借榮辱觀念來構建自己的族群身份,以達到和其他族群的區分。③Godwin Siundu, “Honour and Sham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in Abudulrazak Gurnah’s Novels”,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6, No.1, 2013, pp.105-116.在小說《天堂》中,海岸社會就被商人群體視為“文明”社會,而內陸地區則被看做“野蠻人”的國度。因此,即便是一名債務奴隸,但生活在海岸的優素福也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悲慘,其周圍仍舊是井然有序的環境。盡管榮譽觀念在古爾納的多部小說中都有所體現,但在這第四部小說中有所不同的是:這種宗教榮譽觀念已與世俗貿易活動緊密結合在一起。“榮耀”(Honour)一詞,在小說中足足出現了19 次,這還不包括以此為基礎的同義詞和衍生詞。在當時社會,成功的貿易商人是被稱頌推崇的,如優素福的父親就將阿齊茲的到來視為一件蓬蓽生輝之事。如此崇商重商的社會,貿易自然也披上了某種神圣的榮光,就像商隊領隊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教育優素福時所言:
這就是我們活著要做的事情……去貿易。不論沙漠多么干燥,森林多么幽暗,我們總是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我們也絲毫不在乎貿易對象的身份,國王也好,野蠻人也罷,因為他們對于我們來說都一樣。在我們即將途經之地,你會看到這樣一番景象:貿易還未帶去生機之處,一片死氣沉沉,人們活得就像斷足的螻蟻。在這世上,沒有人比商人更聰明,也沒有任何一項事業比貿易更崇高。是貿易,給了我們想要的生活。①Abdularazak Gurnah, Paradise, p.119.
這段對貿易的詮釋幾乎可媲美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對“人”的贊美。貿易已不僅僅是一種世俗事務,它同時具有了一種文化信仰層面的意義。貿易文化被海岸的社會所信奉,貿易規則被各個社群所遵從。一支前往內陸進行貿易的商隊就像一個移動的小型社會,盡管在同一個商隊中,商人、領隊、引路者、翻譯員、搬運工們可能來自不同的社群,操著不同的語言,信仰著不同的宗教,但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便暫時舍卻了“異”,在人生地不熟之地不得不維持著一種“同”。盡管商隊像一個“衣帽間式的共同體”,②該概念援引自鮑曼,具體可參見齊格蒙特· 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年。但每次貿易出行,都至少月余,長期的相處自然也就促進了不同族群的交流。斯瓦西里語是當時使用最普遍的貿易語言,這一語言隨著貿易空間的拓展而得以推廣,并最終成為現代坦桑尼亞的官方語言之一。
任何一套秩序都不是懸浮于空中的,必有其深厚的社會經濟文化根基。古爾納筆下的海岸是一個典型的以貿易為中心的父權制社會,這一社會最典型的兩大特征就是占有與交易。換句話說,就是一切皆可作為商品,一切皆可用來交易。盡管這個社會有著文明禮貌的表層,但冷酷殘忍才是它真正的內核。關于這一點,小說中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人可以作為商品被抵押:優素福、哈利勒、阿米娜(Amina)等債務奴隸在本質上都是商品。在小說第一章中,優素福的父親前邊還在訓斥優素福,讓他玩耍時遠離當地野蠻人以防被拐賣,隨后卻直接將他給“賣”掉了,可謂諷刺至極。不僅如此,女性在他眼中也只是一件有價值的商品,五只山羊加兩袋豆子就可以買來一個女人。他曾憤怒地對自己妻子咆哮:“如果你出事了,他們會從圍欄里再挑一個賣給我。”③原文為:“If anything happens to you, they’ll sell me another one like you from their pens.”詳見Abdularazak Gurnah, Paradise, p.13。原文中“圍欄”一詞用的是英文單詞“pens”,即羊圈之意。兒子、妻子之于父親/丈夫,就像山羊之于牧民一樣,都只是一種財產。優素福的父親之所以如此冷酷無情,固然是因為他已在貿易上走投無路,但除此之外,古爾納還設置了一條隱約的暗線原因:血統。從優素福母親的敘述中可以得知,她只是優素福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在她之前,優素福的父親還曾娶過一位阿拉伯女子。盡管這樁婚事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對,但他還是憑借朋友的幫助帶走了那位女子。當時女方父母之所以阻止,是因為優素福的父親雖然有著一個榮耀的名字,但膚色卻略深了一些,也就是說,他的阿拉伯血統還不夠純正。后來,這段婚姻還是以失敗告終,他的第一任妻子跑回了基爾瓦的父母家中,同時帶走了二人的子女。優素福的父親曾因血統遭到輕視,但這并不影響他繼續輕視他的第二任妻子,因為優素福的母親來自山地部落。在海岸小鎮上,小說也多次提到富裕的阿曼家庭會把女兒關在閣樓上,并且只將她們嫁給自己親戚家的子嗣。毫無疑問,海岸的阿拉伯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血統只是其中的一個側面體現。在一定程度上,血統其實是與財富掛鉤的,血統壁壘的存在也是為了防止家族財富的外流。但在一個商業社會里,總是有人會發跡,貿易財富也可抬高一個人的社會等級。只不過優素福的父親并不屬于這一類人,而阿齊茲,卻是這類人中的佼佼者。
占有,是為了更好地交易,交易,則是為了更多地占有。在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里,交易往往是掠奪性的、不對等的,比如阿拉伯人早期的奴隸貿易。在后奴隸貿易時代,掠奪性的經濟行為也依舊是最高效的財富占有方式,而這一點,在阿齊茲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阿齊茲這一形象仿佛就是提普·提卜(TippuTip)①提普· 提卜(1832—1905),原名哈米德· 本· 穆罕默德(Hamid bin Muhammed),東非著名的象牙商人,奴隸販子。有趣 的是,在《天堂》中,阿齊茲還向優素福講述了提普· 提卜的事跡。的文學再現。在古爾納筆下,阿齊茲被描述為商人中的佼佼者,自信而穩重,處驚不亂,臉上常掛有微笑,未見其人,便已先聞其濃重的香水味。阿齊茲的外表文明體面,但其內心卻冷酷貪婪,他通過掠奪手段讓自己的貿易伙伴們對其俯首稱臣。一旦他的貿易伙伴們無法償還他,阿齊茲就會毫不留情地將他們的孩子帶走,使其作為債務奴隸為自己工作。由阿齊茲主導的商業秩序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關系之上,在這種秩序下,所有人都不得不依附于阿齊茲。很多貿易伙伴都因他而破產,在這些家庭走向地獄時,阿齊茲卻正攀向天堂。他海岸住處的花園就像天堂中的樂園,女主人、優素福、哈利勒、阿米娜與其說生活于此,不如被囚禁于此。
四、亂局之下:“優素福”們的逃逸
《天堂》可以被視為一部成長小說,因為它展現了一個斯瓦西里少年優素福的成長歷程;《天堂》也可以被視為一部冒險小說,因為深入內陸的商業之行跌宕起伏、驚險刺激;同樣,《天堂》還可以被視為一部歷史小說,因為作家還原構建了一個人們不熟悉的特殊歷史空間。當然,它也可以被看作三者的疊合:一個德屬東非斯瓦西里少年的貿易歷險記。但《天堂》又不僅僅是這些,古爾納在這部小說中真正關注并探尋的其實是特殊環境中個體(尤其是弱者)的生存境況。國外的研究者往往喜歡將這部作品與《黑暗的心》和《河灣》并置,進而開展互文性闡釋,但其實,若將這部作品放回古爾納自己的小說譜系中,反而能讓我們更容易走進它。
在《天堂》之前,古爾納于1990 年發表了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 《多蒂》(Dottie),講的是一個出生于英國的黑人女孩的成長故事。主人公多蒂面臨著身份危機,不知自己從哪里來,便試圖通過閱讀英國經典來重構自我。而《天堂》中的主人公優素福則是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卻不知自己能到哪里去。這兩部小說就像古爾納的一個成長對照實驗:一個是離開者的后代,一個是于故土被拋棄的少年。古爾納感興趣的是他們所處的文化是如何塑造他們的,以及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兩位主人公又同是弱者,一個是處于種族歧視之下的黑人女孩,邊緣中的邊緣;一個是生活在掠奪文化中的美麗男孩,人人都想“得到”優素福。古爾納的這種實驗在其最近的一部小說,也就是第十部小說—— 《今世來生》(Afterlives, 2020)中達到了極致,而這部小說,中伊利亞斯(Ilyas)的經歷又像是《天堂》結尾處優素福追上德國雇傭軍后的“故事延續”。
在小說的結尾處,優素福躲過了阿斯卡里軍隊,卻又主動去追趕這支德國雇傭軍。古爾納這一“突兀的結尾”一直讓讀者和研究者們費解,雖然有研究文章從“殖民代理”②參見Nina Berman, “ Yusuf’s Choice:East African Agency During the German Colonial Period in Abudulrazak Gurnah’s Novel Paradise”,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6, No.1, 2013, pp.51-64。的角度來解釋這一選擇的目的,但造成這一行為的原因卻罕有具體分析研究。作為歷史后來者,我們當然可以肯定這一選擇注定會帶來失敗。一戰后,德國在東非的殖民地很快被英、法等國接管,優素福在亂局中加入的是即將戰敗的一方。即使他可以一直追隨這些戰敗者回到德國,但《今世來生》中的故事也揭示了這種可能只會以悲劇收尾。但優素福畢竟是生活于當時的歷史之中,他做出選擇時并不知道歷史的走向,優素福只是做出他所認為的最利于自己的選擇,盡管這一選擇其實是對自己所屬族群的一種背叛。
這一選擇可以被視為一種沖動性的行為。在小說中,造成優素福這一選擇的最直接原因是阿齊茲返家后的興師問罪。在阿齊茲外出籌資期間,阿齊茲的夫人,即小說中的“女主人”,一直要求優素福進入內室為其祈禱療傷。這位女主人就是之前桑給巴爾島的富有孀婦,但婚后的她卻成了一個閣樓上的瘋女人。盡管優素福的好友哈利勒多番勸阻,并警告他這一行為的危險性,但優素福仍舊執意多次前往女主人房中,因為真正吸引優素福這么做的原因其實是哈利勒的妹妹阿米娜。阿米娜并不是哈利勒的親妹妹,兒時的她被哈利勒的父親從人販子手中解救出來,并作為女兒收養在家中。但后來她卻跟哈利勒一起成為了阿齊茲的債務奴隸,哈利勒負責運營墻外的商鋪,阿米娜則在墻內服侍女主人。由于哈利勒的父親無法償還債務,阿齊茲后來便按照契約娶了她,永遠將其占為己有。優素福明顯是愛上了阿米娜,他想帶她一起逃走,但是卻遭到后者拒絕。頻繁進入內室的行為最終也給優素福帶來了危險,瘋癲的女主人試圖將其擁入懷中,但優素福卻掙扎逃脫了。在逃脫中,優素福的襯衫被女主人抓破,而這也最終救了他,因為這足以向阿齊茲證明他的清白。在阿齊茲問罪時,哈利勒用阿拉伯語解釋了一番,阿齊茲便相信了優素福,顯然,哈利勒引用了《古蘭經》中優素福篇的相似情節。①在《古蘭經》第12 章《優素福》中,優素福便是因襯衣于后邊被撕破而得以自證清白。具體可參見《古蘭經》,馬堅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第116 頁。在阿齊茲的繼續追問下,優素福坦白了真正原因,這一坦誠行為其實可視為優素福向阿齊茲的挑戰,連阿齊茲也連連感嘆道:“你可真是越來越勇敢了!”②Abdularazak Gurnah, Paradise, p.241.在經歷了侮辱性的審問,另加拒絕所帶來的打擊后,一個青春期的少年難免會在亂局中做出沖動性的決定。
這一選擇其實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優素福離家時他的母親告訴他要學會勇敢,在經歷了內陸之行后,優素福確實已擁有了這一品質,已不再懼怕“叔叔阿齊茲”,擺脫控制的想法慢慢在他心中扎了根。父親在兒子的成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被自己的父親拋棄后,優素福與自己的族群文化便存有了間隙。盡管在其成長中,好友哈利勒、商人哈米德,甚至是領隊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以及阿齊茲都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父親”的角色,但這些人其實只起著將優素福束縛在族群文化之下的作用。初到海岸時,哈利勒手把手地教授優素福如何在商鋪工作,還給他講述《古蘭經》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滯留山下小鎮時,哈米德出于道德感更是將其送進專門教授《古蘭經》的學校,但清真寺里伊斯蘭文化的熏陶遠不及商隊中弱肉強食文化對他的塑造。無論是在海岸社會中,還是在行進的貿易隊伍里,一切都由強者主宰。領隊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代表的是原始野蠻的強大,阿卜杜拉揮舞著藤條,搬運工們都屈服于他的淫威,甚至愿意為他“四腳著地”。③同性性行為在商隊中較為普遍,一些歷史著作如《季風帝國》等都有所提及。另,男性之間的這種性行為在古爾納的多部小 說中都有所涉及,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詳見Kate Houlden, “It Worked in a Different Way:Male Same-Sex Desire in the Novels of Abudulrazak Gurnah”,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6, No.1, 2013, pp.91-104。小說中曾多次隱晦地提及商隊中的同性性行為,阿卜杜拉這樣的魔鬼似乎并不是同性戀者,這一行為其實與小說開頭卡瓦小鎮上男孩們掏出生殖器比大小的舉動相似,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男性強者氣質的極端展示。阿齊茲代表的則是一種更高級的強大,他可以只憑借知識、經驗及一身香氣身入險地。但即便強大如斯,他還是在查圖(Chatu)遭遇困厄,并險些賠上身家性命。是歐洲人的出現,改變了查圖小鎮的對峙,并解救了阿齊茲一伙。這些歐洲人讓優素福認識到:在阿齊茲之外,還有更強大的存在。優素福一直處于族群文化的逃逸線上,移動性的經歷讓他對他所處的社會有了更本質的認識。當他問哈利勒為什么不離開時,哈利勒稱他要為自己父親恥辱的所為負責,因而他不能拋下自己的妹妹獨自離開。但這種表層的道德觀念很快便被優素福戳穿,因為在一個依附性的社會中,哈利勒離開阿齊茲便寸步難行。事實也確實如此,哈利勒曾提到在他之前,商鋪中就已有一個叫穆罕默德的年輕人在這里工作,穆罕默德常吸食大麻,一次因賬目出錯被阿齊茲打了一巴掌,之后就不見了。巧合的是,小說第一章中優素福救濟的流浪漢也叫穆罕默德,還好心地勸告優素福要遠離大麻。這些看似是小說中的閑筆,其實卻是伏筆,離開雖然簡單,但離開之后又能如何呢?商鋪中的人生就像一個循環,當被告知自己的父親已死,被贖回的希望就徹底破滅了,優素福開始思考自己如何跳出這一循環,如何逃脫這一海岸秩序。就像德勒茲在其逃逸理論中所言,“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逃逸線是從屬性的”。④德勒茲、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75 頁。在當時的社會歷史中,能改變的只是從一種依附轉為另一種依附。德國雇傭軍的到來,無疑讓優素福找到了離開后的去處,找到了更強大的依靠。而在逃離的那一刻,優素福也實現了短暫的自我解放。
德國人雖只出現在小說的首尾兩處,但德國的勢力擴張卻通過鐵路線的延展和貿易線的改變等信息得到書寫。德國人的到來無疑改變了東非海岸原有的社會結構,也就是說,由阿拉伯人主導的貿易秩序遭到了挑戰與破壞。德國殖民者打敗了阿拉伯商人,一戰后,其在坦噶尼喀的殖民地又被英國接管。歷史總是由強者來書寫,經過德、英兩大帝國的歷史過濾,阿拉伯人的海岸貿易圖景早已黯淡蒙塵,清晰可辨的就是關于他們曾于此從事奴隸貿易的記錄。古爾納并不像大多數非洲作家那樣,對歷史存有一種懷舊之情。在作品中,他也如實反映了東非海岸商業貿易的殘忍一面。還原真實的印度洋文化歷史,關心曾在那里生存的個體生命,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爾納在《天堂》這部小說中真正的文學訴求。
結 語
天堂,不只是一個宗教詞匯,它有著更豐富的文化意蘊。古爾納以之為小說名稱,可以說是一個大膽且冒險的選擇。這意味著這部小說一方面要符合讀者對天堂的認知,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讀者的認知閾限。《古蘭經》與《圣經》具有淵源關系,前者尊后者為《天經》,因而二者關于天堂的講述是大體相同的。在一般的西方人眼中,人類的始祖早先生活在天堂中的伊甸園內,由于違背了與上帝的約定,便被驅逐出了樂園。知曉天堂的故事是理解小說的關鍵,同樣,讀懂了這部小說也可以更深一步地理解天堂的指代。天堂表層的意思就是宜居的樂園,小說中阿齊茲的花園、乞力馬扎羅山上的瀑布都像是伊甸園的人間映射,美不勝收。而這些美景所在的東非海岸對生活于此的人們來說就是真實的天堂:一個貿易的理想之境,一個世界主義者的樂園。其次,天堂還意味著遵守約定,做出承諾后,就要按照規則執行。在貿易活動中,最重要的就是誠信守約,金融家、商人、搬運工都遵守自己的承諾,一個有秩序的貿易天堂才能得以構建和維系。此外,天堂之中還有魔鬼的出沒。阿齊茲就像天堂中的魔鬼一樣,以利益引誘貿易伙伴,進而吞噬并占有他們,隨后又將他們的子女囚禁在自己的身邊。如此,天堂便有了囚籠、地獄之意。但最后,古爾納將天堂落腳為一個富含隱喻的故事,一個讓讀者追思過往及憧憬未來的跨文化故事,而這也為世界文化多樣性與文明互鑒帶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