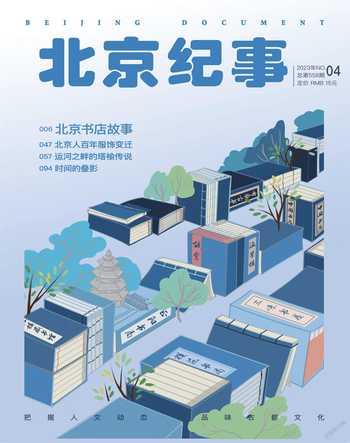古玩市場往事
林碩,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中國致公黨北京朝陽區委理論研究組組長,致力于明清史、北京史和絲綢之路史研究。文章散見在《新華文摘》《光明日報》《人民政協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文物報》《中國博物館》《世界知識》《文史知識》《國家人文歷史》等報刊。
北京這片沃土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與人文情懷,從南到北、自西徂東,大小數百座各具特色的博物館,猶如滿天繁星一般,星羅棋布地分布在京城的每個角落。它們各有各的故事,徜徉其間,細細品讀,令人流連忘返。希望做一位向導,抑或是引路人,為大家講述北京博物館的過往與展望,前世與今生,用趣聞軼事串聯起獨特的博物館之旅。
古玩市場的源流
古玩行業古已有之,但稱謂不盡相同,有古物、古董(骨董)、古器、古玩等說法。隋唐時期的藏家多用“古物”,內涵與近代的“文物”相似,到二十世紀初人們仍在沿用。比如,清帝遜位之后,北洋政府批準在紫禁城外朝成立的博物館就被稱為“古物陳列所”。又如,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文物保護條例、法則也沿用了該稱謂,即《名勝古物古跡保存條例》和《古物保存法》。兩宋以降,在文人當中開始頻繁使用“古董(骨董)”;目前已知的最早使用者是北宋江西詩派的大文豪韓駒,在《送海常化士》中有“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取江南骨董歸”之句。古董的說法影響深遠,直至明末清初仍被普遍采用,更流傳到日本等鄰國。同時,另有部分宋人使用“古器”,如徐夢莘在《三朝北盟匯編》采用此說。洎明清時期,“古玩”的說法后來居上,在乾隆朝蔚然成風。
古玩市場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彼時文人雅士、富商巨賈對古物追捧達到了新高峰,范疇也日益擴大:除了器物、字畫,金石拓片也進入了收藏圈,實現了金石學與考古學的融通。如果說宋代古玩交易人群集中在名流商賈,明代參與交易者則進一步擴大,更涌現出一批頗具規模的古玩交易市場。比如京城的城隍廟市場,售賣種類從商周匜鏡,到秦漢書畫,再到唐宋珠寶,可謂亂花漸欲迷人眼;每月“月朔、望、廿五日,東弼教壇,西逮廟墀廡,列肆三里”,雖是市井陋巷,卻令人樂而忘返。
不過,相較于清代市場的火爆程度,宋明以降的古玩市場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一方面,號稱“千古一帝”的高宗弘歷嗜好古物。上行下效,從廟堂重臣、封疆大吏,到士庶百姓,鐘情于此者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乾隆帝下旨編纂《四庫全書》產生了衍生效應,有志參與編纂、謄錄工作的飽學之士匯萃都下,客觀上推動了金石碑帖和古籍市場的蓬勃發展,也將古玩交易在清中期推向了一個新高峰。以琉璃廠為例:當時赴京趕考的各地舉子大都棲身宣南的會館、廟宇之中,與琉璃廠(海王村)相去不遠,前往購置二手舊書、筆墨紙硯,物美價廉。與此同時,琉璃廠地處宣武門,屬于內城與南城的接合部,距離皇城未遠。故官員散朝之后,也偏愛到此購買、品鑒金石拓本、古董字畫。由此產生了虹吸效應,使琉璃廠古玩市場名聲大噪,歷經二百多年長盛不衰。截至1937年,琉璃廠的古玩店鋪多達九十七家,成為文人墨客流連忘返之地。從吳昌碩、徐悲鴻,到朱自清、齊白石,概莫能外。魯迅先生在京十四年,在日記中記錄自己前往琉璃廠的次數達到四百八十次之多。透過琉璃廠的興盛,我們仿佛看到了晚清以降京城古玩市場的縮影。
晚清以來的時代烙印
時至今日,許多民間藏家還熱衷于前往古玩市場“淘寶”,但各地古玩市場都存在同質化發展的問題。不管您是逛北京的潘家園、十里河,還是在上海的豫園、沈陽的魯園,又或者廣州的清平路、天津的沈陽道,皆均趨于同質。實際上,在上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不同地區的古玩市場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北洋時期,在特殊的歷史條件影響下,京城古玩交易數量明顯增多,循環速度和頻率大幅攀升。隨著清帝,仰仗“鐵桿莊稼”的八旗子弟迅速走向沒落,衣食堪憂,就連末代克勤郡王晏森都賣光祖產,拉起了洋車。當然,這絕非晏森的個案。另一位鐵帽子王怡親王載垣之子溥斌,也把祖上幾代收藏典當、變賣,從晚清直至民初,四十年始盡。更有甚者若“小恭親王”溥偉,不但將大量古玩以四十萬銀元售與日本商人山中定次郎,更將自家王府以八萬銀元抵押給西什庫教堂。不過,這種理直氣壯地變賣祖產者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是趁著夜色,悄無聲息地兜售,半夜入市,拂曉前散去,保留祖上最后的顏面,也就是民間所謂的“鬼市(又稱曉市)。
鬼市交易的特點是某些貨物見不得光,或某些賣家本人不愿見光,故遵循“照貨不照臉”“拉手詢價(袖里乾坤)”等原則。比較成規模的市場分別是宣武門外的西曉市、德勝門外的北曉市,以及崇文門外的“東曉市”。其中,又以東曉市的鬼市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漸偃旗息鼓。改革開放后,北京的古玩市場逐步復蘇,大眾對古玩收藏的參與再度萌發。起初是依附在舊貨市場、農貿大集和花鳥魚蟲市場而存在,舊貨、文玩與花鳥魚蟲、貓狗寵物夾雜一處,極不規范。八十年代末,監管部門逐漸將原本零散的地攤勸導入市,有序管理。今天,在潘家園、大柳樹仍有“鬼市”存在,但徒具其型,算是老北京“鬼市”文化的一抹印記。

與北京不同,上海、廣州作為沿海城市,其古玩市場的形成與發展也別具特色。上海古玩市場的發軔與太平天國運動有關。咸豐年間,太平軍定鼎天京(南京),繼而占據了富庶的蘇州等地。江南的富商巨賈們紛紛避入十里洋場,為繼續維持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們當中的部分人前往城隍廟附近出售古董、字畫,形成商鋪林立的交易鬧市。不過,上海最有特色的古玩交易形式是“茶會”,即在茶樓內商洽古董、珠寶生意,有些外國人也慕名而來。茶會的火爆場面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才被古物商場取而代之。1921 年,上海清真董事會董事長馬長生等人募集資金,在公共租界五馬路(廣東路)建起了“中國古物商場”,次年正式開業,開啟了室內交易場所的新紀元。作為華南最大的經濟文化中心,廣州也有屬于自己別具特色的“墟”文化。“墟”字又寫作“圩”,在粵、閩等地的方言中是市集之意,故廣州人進行二手舊貨、古玩字畫交易的市場被稱作“天光墟”,也就是夜間出攤,天明散場的交易場所,與北京“鬼市”相似,而流動攤販則稱“走鬼”。墟市在民國時期尤為興盛,很大程度上與文物外流有關。晚清時期,香港、九龍等地被割讓給英國,使廣州成為內地與港九之間的聯系紐帶。許多投機商趁著軍閥混戰,政府無力監管文物的漏洞,以廣州為中轉站,將文玩奇珍偷運往港澳及海外。上述現象,在清末民初的沿海城市都很常見,最臭名昭著者要數盧芹齋、吳啟周的“盧吳公司”。他們罔顧法紀,從國內低價收購了大量的文物精品,盜賣至歐美,給國家和民族造成難以估量的巨大損失。

從私藏到共享的轉變
今天,在文物部門的推動和管理之下,古玩市場早已步入正軌,走上了健康有序的發展之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民辦博物館如雨后春筍一般遍地開花,是與文玩市場息息相關的另一件事物。
談起民辦博物館,許多人并不了解。其實,國人獨立創辦的首家公共博物館——南通博物苑就是由末代狀元張謇個人創立。近年來,社會資本參與民間收藏的熱情日漸高漲,越來越多的藏家通過開始民辦博物館,將私人收藏轉變為博物館法人財產,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過,老百姓對于民辦博物館的稱呼五花八門,有民間博物館、私立博物館、私人博物館等等。實際上,官方正式提法是“非國有博物館”,即按照相關規定完成所有手續,獲得主管機構認可的民辦博物館,屬于博物館行業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既完善了我國的博物館體系、填補了門類空白,又體現出民眾從“私家珍藏”走向“社會共享”的文化自覺。
目前,北京的非國有博物館數量在三十家左右。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馬未都先生的觀復博物館。該館于1996年獲批,屬于北京市文物局最早批復建立的博物館之一。觀復博物館初名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位于宣武區(今西城區)琉璃廠西街,館舍幾經輾轉,遷至朝陽金盞鄉。博物館的外墻上有巨幅的《道德經》第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即館名出處。館內庋藏有各類藏品一千六百余件,下設陶瓷館、門窗館、家具館、油畫館和工藝館,在上海陸家嘴、廈門鼓浪嶼設有分館,成為較早采取總-分館制的民辦博物館之一。
民辦博物館與古玩市場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首先,許多民辦博物館是從古玩市場中的私人收藏館發展而來。步入潘家園市場,游客可以看到諸如郵票收藏館、錢幣收藏館、連環畫收藏館等,類目繁多。店主出于興趣展示自己的藏品,滔滔不絕地為您講述每件收藏的來歷;進店之人既是顧客,又是參觀者。盡管他們并未在政府文物管理部門注冊備案,達不到民辦博物館的相關要求和準則,但在實際運營過程中,卻也具備了某些類似博物館的要素和特性;在各項條件具備之后,它們都有機會華麗轉身,成為規模和影響力更大的民辦博物館。
其次,古玩市場也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優勢所在,那就是老百姓在這里不僅可以“淘寶”,還能親手觸碰字畫、器物、文玩、擺件,貼近歷史,觸摸文化,在無形當中滿足了大家的“淘寶”心態和鑒藏需求。相對于“只能遠觀,不可褻玩”的博物館,這恰恰是古玩市場的魅力所在。被譽為“中國最大的露天博物館”的潘家園舊貨市場,更是把“可觸摸的博物館”貼到了外墻之上,加以宣傳。
最后,民辦博物館的藏品來源,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古玩市場收購而來。從這個層面上說,民辦博物館的出現,恰恰是古玩市場發展的產物。隨著民辦博物館規模的日漸擴大,甚至出現了成都建川博物館那樣的博物館集群,與國有博物館共同承擔起保護、繼承、傳播中華民族璀璨文明和文化自信的歷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