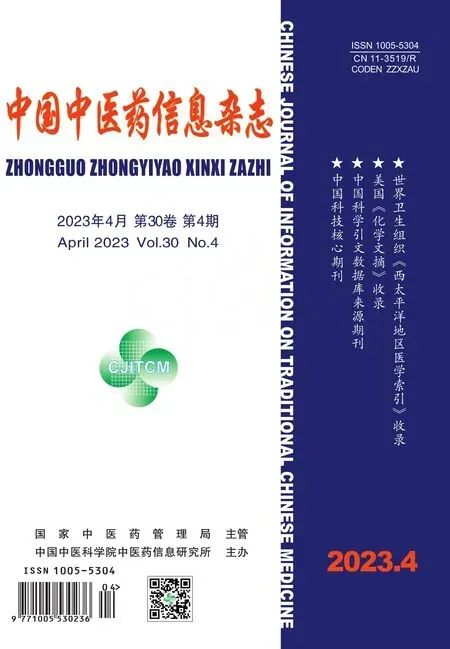基于真實世界研究類風濕關節(jié)炎患者的中醫(yī)證候與臨床特點
李琇瑩 ,金曄華 ,姜婷 ,范曉蕾 ,沈杰 ,錢奕 ,章淵源 ,古英 ,胡春蓉 ,蘇曉 ,薛鸞 ,方勇飛 ,蘇勵 ,高明利 ,薛愉 0,彭江云 ,魏強華 ,劉紅霞 ,黃清春 ,汪榮盛 ,朱琦 ,何東儀
1.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光華醫(yī)院,上海 200052; 2.上海市中醫(yī)藥研究院中西醫(yī)結合關節(jié)炎研究所,上海 200052; 3.綿陽市中醫(yī)院,四川 綿陽 621000; 4.重慶市第九人民醫(yī)院,重慶 400700;5.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市中醫(yī)醫(yī)院,上海 200071; 6.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yī)結合醫(yī)院,上海 200437;7.陸軍軍醫(yī)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重慶 400038; 8.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yī)院,上海 200032;9.遼寧中醫(y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遼寧 沈陽 110000; 10.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yī)院,上海 200040;11.云南省中醫(yī)院,云南 昆明 650021; 12.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yī)院,上海 200080;13.上海中醫(yī)藥大學藥物臨床研究中心,上海 201203; 14.廣東省中醫(yī)院,廣東 廣州 510120
類風濕關節(jié)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以多發(fā)性關節(jié)炎為特征,累及外周關節(jié)的慢性、系統(tǒng)性、炎癥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病理表現(xiàn)以滑膜炎、血管翳生成、關節(jié)軟骨及骨組織破壞為主,臨床表現(xiàn)多見關節(jié)腫脹壓痛,伴晨僵,甚者關節(jié)畸形[1-3]。真實世界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從整體出發(fā),還原真實醫(yī)療數(shù)據(jù),這與中醫(yī)藥基于整體觀念診治各類疾病趨同[4]。RA屬中醫(yī)學“痹證”范疇,為風、寒、濕三氣雜至合于人體致病。關于RA中醫(yī)證型分布的Meta分析顯示,以風濕痹阻證、肝腎不足證、寒濕痹阻證、濕熱痹阻證、瘀血痹阻證居多[5],但目前證候分布情況存在地域及年限差異,樣本量普遍較小,可能存在偏倚[6]。本研究在廣泛查閱文獻與專家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制定RA中醫(yī)四診信息收集評分表,對全國10家醫(yī)院2 650例RA患者進行前瞻性橫斷面調查,旨在為中醫(yī)藥診治RA提供依據(jù)。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來源
收集2015年9月-2020年1月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光華醫(yī)院、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市中醫(yī)醫(yī)院、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yī)院、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yī)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yī)院、重慶市第九人民醫(yī)院、陸軍軍醫(yī)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遼寧中醫(yī)藥大學附屬醫(yī)院、云南省中醫(yī)院、綿陽市中醫(yī)院10家醫(yī)院門診及病房RA患者,根據(jù)納入標準及排除標準篩選患者2 650例。本研究經上海市長寧區(qū)光華中西醫(yī)結合醫(yī)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2014-K-04)。
1.2 西醫(yī)診斷標準
RA診斷符合1987年美國風濕病學會(ACR)分類標準[7]或2010年ACR/歐洲風濕病聯(lián)盟(EULAR RA)分類標準[8]。
1.3 中醫(yī)辨證標準
參考《中醫(yī)內科病證診斷療效標準》[9]、《證候類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技術指導原則》[10]制定濕熱痹阻證、寒濕阻絡證、氣血虧虛證、肝腎虧虛證、痰瘀互結證辨證標準。通過中醫(yī)四診信息收集評分表對RA患者進行辨證,符合1條主癥計2分,符合1條次癥計1分,符合舌象計2分,符合脈象計1分,總分≥4分辨證成立。由風濕科醫(yī)生或研究生與患者面對面訪問填寫,辨證由主治及以上級別醫(yī)師根據(jù)評分表信息完成。
1.4 納入標準
①符合上述西醫(yī)診斷標準及中醫(yī)辨證標準;②年齡>18歲;③簽署知情同意書。
1.5 排除標準
①合并心血管、肺部等嚴重疾病及近1周嚴重感染疾病者;②孕婦及哺乳期女性。
1.6 觀察指標
通過問卷方式采集RA病例信息。①流行病學特征:性別、年齡、吸煙史、家族史;②臨床特征:病程、晨僵時間、紅細胞沉降率(ESR)、類風濕因子(RF)、抗環(huán)瓜氨酸肽抗體(抗CCP抗體);③疾病活動評價[11]:采用ESR進行28個關節(jié)的疾病活動度(DAS28-ESR)評分,并將患者疾病活動度分為緩解期(DAS28-ESR評分<2.6分)、低疾病活動度(2.6分≤DAS28-ESR評分≤3.2分)、中疾病活動度(3.2分
1.7 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SPSS25.0統(tǒng)計軟件對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tài)分布以xˉ±s表示,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或t檢驗;不符合正態(tài)分布以M(Q1,Q3)表示,采用Kruskal-WallisH檢驗或Wilcoxon秩和檢驗。計數(shù)資料以構成比或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檢驗。檢驗水準α=0.05,P<0.05表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多組間比較總體差異顯著時,將檢驗水準α調整為0.005,P<0.005表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中醫(yī)證型分布
2 650 例RA患者證候分型為肝腎陰虛證(1 280例,48.3%)、濕熱痹阻證(589例,22.2%)、寒濕阻絡證(432例,16.3%)、痰瘀互結證(241例,9.1%)、氣血虧虛證(108例,4.1%)。
2.2 一般資料
患者平均發(fā)病年齡(51.33±14.20)歲,多數(shù)患者發(fā)病年齡<45歲,痰瘀互結證平均發(fā)病年齡最低,與除氣血虧虛證外各證型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45歲發(fā)病患者中以痰瘀互結證居多,與濕熱痹阻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患者男女比例1∶4.4,其中濕熱痹阻證女性占比最少,與痰瘀互結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患者中位身高161(158,165)cm,中位體質量56.00(52.00,61.00)kg,中位體質量指數(shù)(BMI)21.64(20.20,23.44)kg/m2,痰瘀互結證患者身高較低,與肝腎陰虛證和濕熱痹阻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不同證型RA患者體質量及BMI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一般資料情況見表1。進一步分析發(fā)現(xiàn),男女BMI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超重或肥胖患者共337例,男女比例1∶2.7,見表2。

表1 RA患者一般資料不同證型比較

表2 RA患者BMI不同性別比較
2.3 發(fā)病特點
患者有風濕病相關家族史135例(5.1%),其中濕熱痹阻證與肝腎陰虛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有吸煙史52例(2.0%),不同證型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各證型患者均多發(fā)于春季(885例),較少發(fā)于秋季(405例),不同證型患者發(fā)病各季節(jié)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RA患者發(fā)病特點不同證型比較[例(%)]
2.4 臨床特征
患者中位病程72(28,145)月,其中濕熱痹阻證患者病程最短,與肝腎陰虛證及痰瘀互結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患者中位晨僵時間30(2,60)min,寒濕阻絡證患者晨僵時間最長,與肝腎陰虛證及濕熱痹阻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痰瘀互結證及氣血虧虛證晨僵時間較短,與肝腎陰虛證、濕熱痹阻證、寒濕阻絡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2 650例RA患者RF有效數(shù)據(jù)811例,其中RF陽性患者680例(83.8%),氣血虧虛證患者RF陽性率最高;抗CCP抗體有效數(shù)據(jù)699例,抗CCP抗體陽性患者574例(82.1%),濕熱痹阻證患者抗CCP抗體陽性率最高。各證型RF和抗CCP抗體陽性率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患者中位ESR為28.0(15.0,48.0)mm/h,其中濕熱痹阻證患者ESR最高,與肝腎陰虛證及痰瘀互結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見表4。

表4 RA患者臨床特征不同證型比較
2.5 疾病活動度評價
患者中位DAS28-ESR評分為4.10(3.17,5.08)分,緩解期379例(14.3%),低疾病活動度306例(11.5%),中疾病活動度1 318例(49.7%),高疾病活動度647例(24.4%)。入組RA患者DAS28-ESR評分達標685例(25.8%),痰瘀互結證患者達標率最高(99例,41.1%),與除氣血虧虛證外各證型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DAS28-ESR評分未達標1 965例(74.2%),濕熱痹阻證患者未達標率最高(483例,82.0%),與除寒濕阻絡證外各證型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見表5。

表5 RA患者疾病活動度不同證型比較
3 討論
焦樹德教授[12]認為,尪痹的病因病機復雜,以“虛為本,實為標”,辨證分型對RA的中醫(yī)治療起重要作用。本研究2 650例RA患者證型為肝腎陰虛證(48.3%)、濕熱痹阻證(22.2%)、寒濕阻絡證(16.3%)、痰瘀互結證(9.1%)、氣血虧虛證(4.1%),患者平均年齡超過50歲,該年齡段素體正氣較虧,且病久易傷及肝腎,致肝陰不足、肝血不充,導致氣機郁結、血脈不榮,腎中精氣陰陽俱損則筋骨失養(yǎng),故多見肝腎陰虛證。
RA可發(fā)生在任何年齡,多發(fā)于50歲左右[13]。本研究顯示,患者平均發(fā)病年齡(51.33±14.20)歲,以女性多見,男女比例1∶4.4,該結果與國內外研究相符[14-16]。有研究認為,雌激素在免疫應答中對細胞炎癥因子產生影響,絕經后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低濃度雌激素可誘導炎性細胞因子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6等分泌,產生廣泛炎性反應,促使RA發(fā)生發(fā)展[17-18]。
本研究結果提示,不同證型RA患者的體質量及BMI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進一步分析顯示,不同性別RA患者BMI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其中超重或肥胖的患者占12.7%,男女比例1∶2.7(女性245例,72.7%;男性92例,27.3%),提示女性超重/肥胖可能與RA有相關性。目前,已有研究證實超重/肥胖能夠對RA患者癥狀及結局產生重大影響,且存在性別差異[19-20]。丹麥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發(fā)現(xiàn),超重/肥胖的女性RA患病風險比正常人群增加50%,其體脂率、腰圍或BMI與發(fā)病風險呈正相關,而在男性RA患者中未見關聯(lián)[21]。
RA發(fā)病與遺傳、環(huán)境因素等相關[22]。本研究對不同證型RA患者發(fā)病特點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2.0%的患者有吸煙史,各證型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5.1%患者有家族史,其中肝腎陰虛證患者有家族史占比最高(81例,6.3%),與濕熱痹阻證(18例,3.1%)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3)。這可能由于中醫(yī)體質類型與基因多態(tài)性之間存在密切相關性,且個體中醫(yī)體質類型差異性能夠決定疾病易感性與疾病的證候分型[23-25]。RA屬多態(tài)性基因易感性疾病,有遺傳風險的基因位點以HLA、DRB1、PTPN22、ILF3、TYK2等為代表,其中與HLA-DRB1相關程度最高[26-30]。有研究顯示,RA患者體質差異與HLA-DRB1多態(tài)性對RA的發(fā)病有一定影響,陽虛質、氣郁質為RA患者發(fā)病易感體質[31],這可能是不同證型RA患者有家族史率差異的原因。RA發(fā)病還有一定季節(jié)性,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證型RA患者較多發(fā)病于春季,中醫(yī)認為春季以風主氣,風為百病之長,易夾雜其他邪氣侵襲人體。風邪為其病理因素之一,《素問·五臟生成篇》有“臥出而風吹之,血凝于膚者為痹”,這可能是尪痹多發(fā)于春季的原因。另外,本研究發(fā)現(xiàn),不同證型RA患者均較少發(fā)病于秋季,可能由于秋季主燥,氣候清爽,疾病活動度相對較低。以上結果與國內多項研究結果[32-33]一致,但不同證型間發(fā)病季節(jié)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本研究結果提示,寒濕阻絡證患者晨僵時間[30(10,60)min]在5種證型中最長,與肝腎陰虛證[20(0,32)min]及濕熱痹阻證[30(0,60)min]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痰瘀互結證[10(0,45)min]及氣血虧虛證[5(0,30)min]晨僵時間較短,與肝腎陰虛證、濕熱痹阻證、寒濕阻絡證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中醫(yī)學認為,關節(jié)冷痛僵直的表現(xiàn)是由于寒性收引,氣血阻滯于筋脈所致,而痰瘀氣虛所致“不通則痛,不榮則痛”,更易表現(xiàn)為關節(jié)局部隱隱作痛,因而晨僵時間較其他證型更短。入組患者中濕熱痹阻證病程[60(22,123)月]在各證型中最短,與肝腎陰虛證[78(32,156)月]及痰瘀互結證[78(33,151)月]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濕、熱之邪均為實邪,往往來勢急兇,濕熱燔淫日久易耗傷臟腑陰津,正如《景岳全書》所言:“陽邪之至,害必歸陰,五臟之傷,窮必及腎。”因而,以濕熱痹阻證病程較短,肝腎陰虛證病程較長,另痰瘀互結易使疾病遷延難愈,久病必虛,故痰瘀互結證亦以病程較長多見。本研究結果提示,RF陽性患者680例(83.8%),氣血虧虛證患者RF陽性率最高(32例,88.9%);抗CCP抗體陽性患者574例(82.1%),濕熱痹阻證患者抗CCP抗體陽性率最高(118例,83.1%),上述各證型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本研究結果提示,濕熱痹阻證患者ESR為31.0(17.0,53.0)mm/h,在各證型中最高(P<0.005),與肝腎陰虛證[27.0(14.0,46.0)mm/h]及痰瘀互結證[24.5(16.0,44.0)mm/h]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濕熱痹阻證患者DAS28-ESR評分[4.34(3.47,5.22)]在5種證型中最高,且與除寒濕阻絡證外各證型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痰瘀互結證患者DAS28-ESR評分[3.55(2.55,4.78)]最低,與除氣血虧虛證外各證型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5),該結果與國內多項研究[34-35]一致。這是由于濕熱蘊結,氣血留滯筋脈,此時患者往往有關節(jié)局部腫脹發(fā)熱甚至疼痛的表現(xiàn),提示疾病處于活動期,體內持續(xù)炎癥狀態(tài),ESR作為反映炎癥水平的指標而升高;而肝腎陰虛證或痰瘀互結證患者關節(jié)局部以虛證表現(xiàn)為主,疾病處于穩(wěn)定期,炎癥狀態(tài)較低,因而ESR水平較低。同時,由于DAS28-ESR評分與RA疾病活動性呈正相關[34-35],因而濕熱痹阻證患者DAS28-ESR評分較高,痰瘀互結證患者DAS28-ESR評分較低。另外,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發(fā)現(xiàn),RA患者處于緩解期379例(14.3%)、低疾病活動度306例(11.5%)、中疾病活動度1 318例(49.7%)、高疾病活動度647例(24.4%),DAS28-ESR評分達標患者共685例(25.8%),說明多數(shù)RA患者處于疾病活動期,病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該現(xiàn)象多由診斷延誤、患者依從性差等情況引起[36]。目前仍有相當比例的風濕科醫(yī)生未能嚴格貫徹達標治療,這是導致多數(shù)RA患者炎癥狀態(tài)改善不明顯及疾病活動未能良好控制的原因之一[37]。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RA多數(shù)患者處于中高疾病活動度,各種證型RA患者具有不同臨床特點,在臨床上早期診斷、辨病和辨證相結合及達標治療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