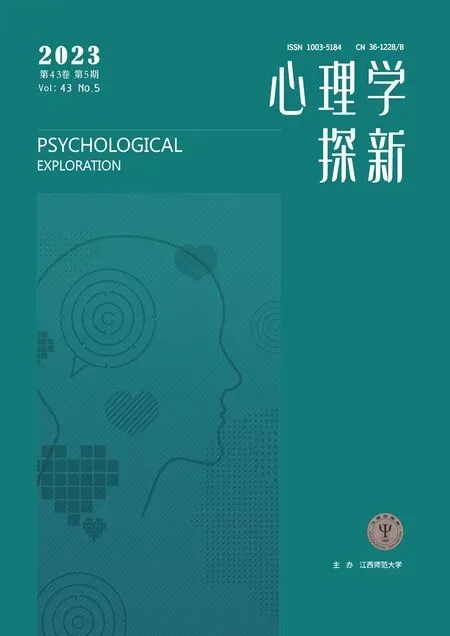覺性:中國本土高級心理機能
彭彥琴,朱曉燕
(1.蘇州大學教育學院心理研究所,蘇州 215123;2.桐鄉市崇福實驗小學,嘉興 314511)
1 引言
隨著冥想訓練的臨床研究不斷深入和拓展,越來越多的西方心理學家開始研究冥想中的特殊意識覺知狀態(Vieten et al.,2018)。心理學家關注冥想中出現的統一的、純粹的、非概念的覺知狀態,這種覺知狀態擁有諸如不涉及外部信息加工,且脫離符號、概念表征,非主客二分等特性(Shapiro,Carlson,Astin,& Freedman,2006;Josipovic,2014,2019,in press),故而也有學者將這種意識狀態稱為純粹意識(Pure consciousness)(Travis &Pearson,2000)。此類研究已然涉及到了意識的本質,認識到了沒有認知活動涉入,甚至沒有內容的意識覺知屬性的本來樣貌。
不僅如此,近期冥想研究并不滿足于所謂“神秘現象”,而是致力于通過認知神經科學范式進一步探索這種真實存在的人類意識覺知狀態的本質及其神經機制(Vieten et al.,2018),且已獲得一定成果(Lutz,Jha et al.,2015;Josipovic,Dinstein,Weber,& Heeger,2012)。因此“借助腦功能成像中核磁共振(fMRI)、事件相關電位技術(ERP)等新興技術,意識不再因其主觀性而被科學拒之門外,而是與特定的腦生物電反應、腦區密切相關”(安暉,2018,p.79),然而,這類“片段式的,著重于對局部微觀的神經生物特性的描述”(霍涌泉,段海軍,2008),僅強調神經生物特性的理論可能是一種“遺漏現象性和主觀性的心智理論”(陳巍,2018,p.66),因為它忽視了大腦生理結構與意識的主觀體驗之間的鴻溝(王曉陽,2008)。于是,受西方現象哲學與東方傳統哲學影響的強調意識主體性且具有具身化取向的神經現象學研究范式逐漸成為意識研究的新熱潮(陳巍,2018;Lutz &Thompson,2003)。但總的來說,無論是認知神經科學還是新興的神經現象學都只是提供了一種研究視角及策略,遠未能形成有關于這類高級意識覺知狀態的完整理論體系。
反觀千百年來始終建立在實證(內證)基礎上的中國本土心理學,已然形成了去玄學化、非思辨性的關于覺性的理論及實踐訓練體系。在心性、心智領域擁有豐厚且獨特的資源的中國本土心理學很早就探及意識覺知性的本質,并且突破了意識經驗層面,將之拓展至包括反身意識(reflexive consciousness)、甚至超越反身意識的覺性層面,即超越一般認知機能的高級心智機能層面(彭彥琴,2020)。
2 覺性:中國本土心理學特有的研究領域
中國本土心理學很早就關注“心”的覺性功能,并且明確地區分了“知”與“覺”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機能:“知”指由感官輸入信息加工為代表的認知功能,絕大多數人的心理過程以認知為主;“覺”指對包括認知活動在內的所有心理、精神現象及其本體的覺察、體證的功能。“覺性”即關于“覺”的機能,是一種多層級的高級心智機能。覺性是中國本土心理學特有的研究領域,它為意識本質等人類高級心智機能的探索提供了中國人自己的理論輸出。
中國本土心理學認為“知”與“覺”是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兩種心智機能,并且“覺”是更為高級的心智機能。這是基于中國人對心的總體功能的認知,“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道心、人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熹,2013b,p.15)。可知,心是精神活動的運轉與表達,它最基本的功能是“知覺”(1)此“知覺”功能并非通常意義的對外部事物進行認知的知覺,即西方認知心理學中最基礎的加工過程,而是心理學所說的“意識”(consciousness)。,即能知能覺的意識活動,但決定心的本質的是“性”,由不同的“性”所引發、趨動的心理機能系統不同,心的終端表現——知覺功能則截然不同。具體而言,如果我們的心理活動是“生于形氣之私”,即受制于生物本能,那就是人心,由人心所趨動的就是經由感官系統的一般認知活動;如果是“原于性命之正”,即由先天的心性、精神本體趨動,那就是道心,由道心所趨動的是高級覺性機能。有學者認為“知”與“覺”的差異只是認知內容上的差異(陳四光,2009),或是認為“覺”的機能與“知”相比只是多了思維的參與,且這種思維能力仍處于對事物的整體認識,尚未達到掌握事物規律的思慮階段,進而得出結論“知”、“覺”同屬于感性認識階段,大體與西方心理學的知覺相當(車文博,2009)。事實上,中國本土心理學之所以要將“覺”與“知”分開,就是要強調心的功能是由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心智機能構成的,一種是一般的包括思維在內的認知功能,這是“人心”驅動的“知”;另一種則是超出一般認知水平的更高一級的覺察功能,它是對認知過程本身甚至心性、精神本體的覺察及體證,是“道心”驅動的“覺”,這才是“覺”的意義所在。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知”。在中國本土心理學中“知”的含義與西方心理學的認知基本一致。宋代大儒張載將心的知覺功能分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兩種不同的心理機能。“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張載,1978a,p.24),“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于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張載,1978a,p.25),“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張載,1978a,p.63),“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張載,1978b,p.313),由此可以看到“知”的機能的活動過程就是主體與外部事物接觸時,主體通過耳目等器官對外部對象的刺激信息進行知覺加工,繼而產生感受、理解、認識等。雖然“見聞之知”強調“與物相合”以及“耳目”器官的作用,但“知”并不直接等同于西方心理學的“感知覺”,“見聞之知主要是屬于認知哲學的概念。它不限于‘感性認識’,凡不具有德性意義的純粹客觀知識包括今天所說的理性認識都屬于見聞之知”(周熾成,1994,p.25)。張載之所以將“知覺”分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關鍵是要將感官所輸入的外部刺激的單純信息加工(也就是狹義的信息加工過程),與更高級的心智機能(包括道德價值判斷)相區別,因此,見聞之知就不應只涉及感覺、知覺等感性認識,也應當包括思維、想象等理性認識,這才是完整的認知心理過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對“知”的理解與張載的“見聞之知”基本吻合。朱熹認為“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就是說,朱熹認為“識別痛癢”等生物對外部刺激的本能感知覺以及“了知事理”、“人際應對”等理性思維都屬于一般認知活動,屬于“知”的功能。
佛家也持同樣觀點。如唯識宗區分了“識”(2)雖然佛家與儒家所使用的稱謂不同,但“知”與“識”實質上是同種心理機能,與西方心理學的“認知”一致。與“智”兩種不同的心理機能,并以“轉識成智”為成佛的途徑(魏德東,1998)。“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楞伽經,2020-07-26),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感官系統及其機能)與色聲香味觸法六境(外部刺激)相觸和合產生對應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識(水野弘元,佛歷2528,pp.145-152)。“識謂了別”(玄奘,1995,p.3),“識以了境為自性”(玄奘,1995,p.49),“識的功能為‘了別’外境,即分析、歸類客體對象的認知功能……前五識是感官對外部物理刺激進行‘了別’的功能,第六識則加工抽象的認知對象”(彭彥琴,李清清,2018,p.1270)。可見,“識”既包含識別經由感覺神經系統輸入的外部物理刺激,也包含概念抽象,分析判斷等理性思維,這與西方心理學對“認知”機能的定義是一致的。
綜上,中國本土心理學的“知”既包含感知覺也包含更為高級的理性思維,這與西方心理學的“認知”基本一致。
其次是“覺”。所謂“覺性”即“覺”的機能,是不同于認知機能的高級心智機能,“覺性”不僅能夠覺察與反觀“知”(認知)的機能及其活動,還能夠直接體證心性、精神本體。
中國本土心理學體系中的“覺”(或“覺性”)是一種能夠覺察與反觀“知”(認知)的心理機能及其活動的高級機能。擅長心理現象分析的佛教對此早有深刻認識,比如唯識宗提出的“自證分”(3)唯識宗認為心識的功能包括三部分:(一)相分,相,即相狀,就是認知對象(客體);(二)見分,見,即見照,就是認知功能;(三)自證分,自,自體之義;證,證知之義,就是對自己之認知活動的認知。參見(玄奘,1995,p.20)。就充分展現了“覺性”反觀自證內部認知活動的能力。“相分是所緣,見分名行相,相、見所依自體名事,即自證分。此若無者,應不自憶心、心所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憶故……似境相所量,能取相自證,即能量及果”(玄奘,1995,p.20),就是說,如果沒有這種能夠覺察、反觀的機能,我們就無法監控自身的認知活動,也就無法形成任何經驗、認識。由此可知,在進行意識活動的同時必然伴隨對自身意識活動的反觀,這是心的同一個過程,而非兩個過程。正如呂澄所言“譬如點燈,燈光四射,既照明了余物,同時也照明了燈的本身。心也一樣,如眼見草青青,天蒼蒼,既見到天、草的顏色,同時也了解了自己這是‘見’了”(呂澄,1991,p.2151),他很好地解釋了佛典經常出現以“燈光”比擬心識的原由,西方心理學家亦認可“意識的照亮本質上也是一種自我照亮(self-luminosity)——意識本質上是自我顯現或自我揭示的”(Thompson,2015,p.18)。基于此,中國本土心理學尤其重視“心識中能夠親證心識活動自身的那個不可或缺的成分”(倪梁康,2008,p.20),即覺性機能。新心性心理學倡導者葛魯嘉曾指出“人的心理本性在于人的心理‘覺’的性質,‘覺’是人的心理活動的基本特征”(葛魯嘉,2005a,p.114),這個領域“應該成為心理科學關注的中心”(葛魯嘉,2005b,p.145)。儒家也同樣注重這種“覺性”機能。朱熹認為“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熹,2013a,p.242),“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朱熹,1986,p.1363),顯然,在朱熹的分類中,“知”是“識其事”,即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覺”是“悟其理”,即對“識其事”的覺察與反觀。“知”是“因事因物可以知”,就是對事物的認知加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即是對自心內在之“理”,即內在心理、精神活動及其規律的直接領悟。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說“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王陽明,2014b,p.284),可知“良知”就是覺性機能,因此“良知”不同于一般的“認知”,而是能夠對一般認知活動進行監察、反觀的高級心智機能。所謂“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于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于睿知”(王陽明,2014f,p.295),可見,“良知”絕不是感知覺、理性思維等認知功能,而是能夠覺察、反觀認知活動的高級心理機能。只有發揮監察、反觀的覺性機能,才能達到“聽之聰”、“視之明”、“思覺之睿知”,我們的認知活動才能達到更高的心智水平。
“覺”(或覺性)不僅可以反觀認知活動,還能夠直接體證心性、精神本體,這也是覺性最核心的機能。正如前文所言,儒家的“見聞之知”基本等同于認知機能,而“德性之知”是明確區別于“見聞之知”的另一種高級心智機能,能夠直接體證心性、精神本體。“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程顥,程頤,1931,p.317),“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見聞小知而已”(張載,1978a,p.20)。可見,“德性之知”的心理機能所體證的是自身本具的心性、精神本體,而非外界事物的刺激,故而“德性之知”是超越了信息加工式的認知機能的高級心智機能,是“天德良知”,具有天然的“德性”。王陽明的學說中,“良知”直接成為了心性、精神的本體,“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王陽明,2014a,p.106)”,“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王陽明,2014a,p.108),也正因為“良知”是所有人都具有的最核心的精神本體,它才能超越一般認知功能,能對認知功能進行覺察監控。佛家同樣給予了“覺性”核心地位,將其作為心性的本質屬性。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在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過程中,逐漸由“心性本凈”轉為主張“心性本覺”(喬根鎖,2009)。“心性本覺”謂心性的根本在覺性,強調由“覺”成“佛”,即通過覺性實現高級心智機能的轉化與提升。在浩如煙海的佛家典籍中,“覺性”有諸多表述,“覺性大菩提心它的同義異名有:本性、妙覺、自覺、自然智慧、大圓滿、大空明、真體、真性、法界、大我等等”(劉立千,1996,p.95)。包括唯識學“轉識成智”的“智”也是“覺性”的一種表達方式,只有突破了根境識三者要素的“識”即一般認知層面,才能到達直接體證心性、精神本體的“智”的高度。總之,覺性與佛性、法界、大圓滿、真如等均為同義詞,均指向心性或心智機能的最高形態。
綜上可知,覺性的本質是一種多層級的高級心智機能,它既是一種高級心智機能,也是一種最基本的心智機能,且可依據機能的激發程度劃分為若干層級結構。首先,作為一種基本心智機能,覺性表現為對自身感知覺的覺察,它是生命體對刺激的一種本能反應與覺知能力,例如“看見了……”、“聽見了……”等,屬于“知覺”功能“知”的層面。這一階段是初始階段,是生命體生而就有的;其次,它表現為對一系列心理活動過程及機能的反觀,包括將自我及其心理過程本身作為反觀對象。這個階段雖然還是有操作對象,但它是通往覺性最高階段的中介橋梁、必經之路;最后,覺性表現為無對象操作的純粹精神主體的自明。佛家說“心性清凈無相,猶如虛空,但又圓滿具足(元成)一切境界之相”(引自劉立千,1996,p.87),儒家諸如“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王陽明,2014a,p.84),表達的都是覺性的第三層級。借助自我反觀的持續訓練,達到對所有心理過程及機能不間斷的敏銳覺察,最終突破原有的心智水平(即通常的意識活動、認知活動),進入到無對象的操作,達到精神主體的純粹自明的高級心智水平,這是覺性激發的最高形態(4)覺性機能的第二、第三層級屬于“覺”的層級。稍加比較可知,覺性的前兩個層次則與西方心理學的認知、元認知、心靈哲學的反身意識基本相似,但代表覺性機能最高形態的無對象的純粹精神的自明則是目前心理學尚未觸及、意識與哲學研究爭議重重的領域。。
3 覺性:區別于認知加工的心理機制
中國本土心理學關于“覺性”的表述并不統一,例如“德性之知”、“良知”、“本覺”等不一而足。但凡高階的精神現象往往超出人們的慣常思維與日常概念,故而只能用有限的語匯取其眾多特質之一、二加以描繪。而大多數哲學、宗教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使得原本就難以表述的高級精神現象更添玄秘和不確定性。因此,如果從傳統的哲學、宗教視角,轉為基于實踐的心理學研究取向時,所謂的覺性本質則充分展現為一種精神領域最高存在的真實樣態,它是千百年來眾多心性實踐及證悟者的親證體驗,是基于切實心理機制及原理的心理事實,并沒有任何神秘玄妙可言。故而,作為一種真實存在的高級心智機能,覺性的心理機制及原理必然能夠為我們所把握。認知活動的基本機制是主體對輸入的客體信息進行加工的過程,而覺性的心理機制則是無分別、自明地直接體證心性本質、精神本體,且同步進行主體道德價值判斷,并伴隨強烈的愉悅感。因此,覺性具有區別于一般認知的特殊心理機制,具體表現為:
3.1 無分別性
覺性在反觀體證心理活動,甚至心性、精神本體時采用的是“無分別”的心理加工。
“分別”是佛家心理學一個重要概念,又名“毗婆阇”,“思量識別諸事理曰分別”(丁福保,1921a,p.724),“有分別作用之意……能分別所緣之境,故名之為有分別”(丁福保,1921b,p.1009),可知“分別”就是主體對外部對象的識別、分析、思維,故大多數學者認為它等同于現代心理學的認知、思維(陳兵,2015)。“無分別”是指心理活動的非對象化(即加工主體與對象之間的統一),且不以概念識別、評判為結果,所謂“若智與所取不異。平等平等起。是名無分別智。”(世親菩薩,2020-03-18)。區別于一般認知加工,覺性并非運用符號、概念等主觀經驗對某一對象進行識別、定義、評判,而是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與喚醒,以一種整體的方式直接體證心性、精神主體。
首先,從操作內容上來說,覺性是“向內”的,而一般認知是“向外”的。Newell和Simon的信息加工觀點認為認知活動的一般程序是由感受器接收外部環境刺激,接著將此轉變為符號結構(外部事物屬性的內部表征)傳入加工器,同時記憶提取與儲存符號結構并與加工器發生交互作用,最后加工器整合所有信息(符號結構)形成一定的程序傳達給效應器,由效應器對外部環境做出反應(王甦,汪安圣,2006)。可見,認知活動的機制在于加工外部環境刺激以形成某種知識、經驗,其操作內容由始至終是“向外”的,都是圍繞著外部環境或客體屬性。而覺性的操作始終指向內部心理機能、自我甚至于更高的精神主體自身,而不是處理外部環境、客體屬性。換言之,人類通過認知機能處理來自外部的信息,而覺性關注的是認知機能本身,而不是外部環境刺激及由此引發的認知結果。故而《大日經》言“云何菩提。謂如實知自心”(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2020-03-18),覺性體證的是自身的心理機能、精神主體。單就這一角度可以說,覺性是“意識”之后的“意識”,也就是胡塞爾的超驗層面的“意識本質”(5)胡塞爾自身意識的現象學基礎就是尋求意識的根源性的普遍結構。他主張“一種關于意識本質的學說,而不像后者那樣是個別的具體的事實性心理體驗。……它尋求的是要理解各種對象的呈現方式,以及其條件、結構如何等諸如此類的本質東西”。可見,意識的根源性問題是不能通過經驗層面(一般認知層面)達到的,而必須是更高一級的——現象學所謂的超驗層面才能達到。這種高級的心理機能就是中國本土心理學之謂“覺性”。(參考埃德蒙德·胡塞爾,1984/2016,pp.257-259)。
其次,從操作過程而言,一般認知是一系列以符號、概念為載體并根據主觀的知識、經驗對外部事物進行分別、定義和評判的對象化操作(王甦,汪安圣,2006)。這是一種典型的主客二分式的操作。即便是元認知、內省這類高級的認知活動也是將內部心理活動視為認知操作的對象,仍然是將主體的心理活動客體化、對象化;而覺性則是非對象化的,它以一種主客統一的整體方式直接體證心性本質、精神主體。認知神經科學家Zoran Josipovic等對這種“非二分化的心理現象(nondual awareness,NDA)”進行了fMRI的實證研究(Josipovic,2014)。實驗證明在NDA禪修狀態下內、外在大腦網絡系統之間的拮抗顯著減弱。換句話說,在NDA狀態下,原本主客二分的、相互拮抗的兩種心理系統呈現不區分主客、內(加工自我)外(加工外部刺激)的統一趨勢。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不區分自我與對象的主客統一的高級心智機能存在的可能性。
認知機能的對象化操作其實就是概念化的識別過程。“對事物進行命名的時候,你正在對它們進行分類,這個分類過程被稱為識別”(E.布魯斯·戈爾茨坦,詹姆斯·R.布洛克摩爾,2014/2018,p.16),識別、命名、分類就意味著概念及其符號的產生。與之相對,“無分別”的覺性在體證心性本質及精神主體的過程中則是非概念化的直接領悟,不會出現“這是……”的命題式結論。“諸佛如諸法如。一如無分別。”(摩訶般若波羅蜜經,2020-03-18)。“一如”就是非概念化、非對象化的直接領悟。正因此,覺性過程中沒有任何心理符號為載體,所謂“無相無名”(僧肇,2010,p.67),“舍離主客觀之相”(曹樹明,2009,p.151)。正如Zoran Josipovic提出非二分覺察的主要屬性是非表征的、非概念的自反性,即直接地知道自己是在意識的或覺察的,而不依賴于概念和符號的表征(Josipovic,2019)。故而,在一些禪修條件的實驗中,被試常常會報告他們感覺自己的意識變得非常純粹(pure),是一種沒有內容的覺察(Baars,2013),其實“無心理內容”并不是指什么也沒有的“空”,而是指覺性體證不會形成概念或者其他符號表征,其“能夠從意識內容例如想法中分離出來,更加清晰客觀地覺察、體證每時每刻的經歷”(Shapiro et al.,2006)。
綜上可知,“無分別性”描述了覺性作為一種高級心智機能的活動過程和原理,是覺性最為重要、最為典型、最能與一般認知機能相區別的代表性特征。覺性研究對于心智哲學的“未解之謎”——意識是如何被意識到的做出了回答。覺性是以一種非對象化的方式直接體證,其“自證自知”機能確保了意識活動不會落于循環論證之中——意識能被我們所直接意識到,不需要一個更高階的心智機能間接地“觀察”。就這一角度,胡塞爾的“自身意識(Selbstbewuβtsein)”與覺性有高度一致性,“自身意識是一種直接的、隱藏著的、非關系性的、非對象化的、非概念的和非命題式的前反思的意識,不同于那種反思的自身意識……前者比后者更根本,而且構成后者得以可能的隱含條件”(黃迪吉,2018,p.154)。
3.2 自明性
自明性就是自知自明,指覺性在體證過程中產生的非分析式的清晰、明確的直接領悟與自證自知。
中國本土心理學常以“明鏡”比喻覺性的自明特性,如“覺性自性(光明)如明鏡,其中具有能明現一切之現源”(引自劉立千,1996,p.86),“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王陽明,2014a,p.125),“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莊周,2010,p.116),以此表達覺性在體察過程中,如同明鏡映照萬物那般可以直接、清晰地體證領悟,無須提取已有經驗進行一系列概念化的邏輯分析,正如陽明所說“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王陽明,2014a,p.133),“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王陽明,2014a,p.10)。同時這種“明”(領悟感)是“自明”的,是覺性本身具有的,故而能夠自證自知,“明是自明,不是由造作始明,如珠寶之光亮,為珠寶所本具,非由它法而使之明亮,‘明’乃覺性本具性德,故能明分不滅”(劉立千,1996,p.86)。正因為覺性自性光明,能夠自證自知,故而相較一般認知機能更具有不謬性,“義理非它,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神明也”(戴震,1937,pp.5-6)。一般認知機制依靠理性分析,不可避免的存在主觀經驗、知識的涉入以及情緒的干擾,反而會遮蔽我們的本性良知,而覺性機能自覺自證,排除主觀干擾,從而復歸心性、精神本體,所謂“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才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王陽明,2014a,p.193)。此外,覺性的自明是常在常知的,“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王陽明.2014a,p.183),不同于認知機能是有斷續的,例如在熟睡等心理狀態下認知機能通常中斷。
布倫塔諾也發現了高級心智機能的自明性。他認為“內知覺(inner perception)”超越了一般的認知機能(即“外知覺”external perception),不需要通過概念的識別、分析、推論,只通過親證體驗便能直接地體證、領悟“真”與“善”。“內知覺……一種它所獨具的特征,這就是它具有直接性、不謬性和自明性……只有內知覺具有這種特點。所以,當我們說心理現象乃是由內知覺所把握的現象時,我們由此也就指出了對它們的知覺乃是直接自明的”(弗蘭茨·布倫塔諾,1874/2000,p.53),這種非邏輯推理的直接自明阻止了主觀的知識、經驗和錯誤的偏見等的影響,反而是更加直接和不謬的。“這些命題必須是當下得到保證的,亦即它們必須是排除了一切錯誤的可能性的——內觀。這種命題(內觀)才是惟一真正的知識的原則”(Brentano,2009,p.10)。
可見,無論是布倫塔諾的“內知覺”還是中國本土心理學的“覺性”都強調了高級心智機能的自明性——只需要直接體證就可以自知自明,獲得不謬的關于心性本質及精神主體的直接領悟。
3.3 道德性與愉悅性
覺性不同于“唯智”的純粹信息加工的常規認知機能,而是具有道德性(包括道德實踐性)的高級心智機能,且一旦經由覺性機能體證到心性本質乃至精神主體的本原之善時必然伴隨強烈的自恰與愉悅感。
覺性所具有的道德性不同于西方心理學的道德認知,覺性機能因其由心性、精神本體生發并能夠直接體證心性、精神本體而天然具有“德性”。“道德認知,又稱道德認識,是指人們對客觀存在的道德現象、行為準則及其意義的主觀反映。它是人們在與其他道德角色和社會道德生活現象接觸、交往的過程中,通過對其他道德角色或道德生活現象外部特征的知覺,判斷其他道德角色的動機、興趣、個性和心理狀態以及道德生活現象的是非、善惡、美丑等狀態,從而形成人們對于各種社會道德生活現象的認識、印象、評價和理解”(汪才明,2003,p.48),可見從機能或是心理機制來說,道德認知本質上仍然屬于認知機能,其只是純粹的“唯智”的信息加工,即通過對外部客體信息的知覺、思維、判斷最終形成某種觀念、認知,道德認知與其他認知活動的最大區別只是在于其對象、內容是道德現象,其機能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屬性。
而覺性不是一種“唯智”的、中性的“自身意識”,是一種能夠自證心性乃至精神主體之本原性道德的高級心智機能。簡言之,覺性是天然、內源地具有道德價值判斷自知自覺的高級心智機能。覺性的道德價值判斷不是以概念識別為基礎的分析式的評判或者基于個體有限感性經驗的判斷,而是一種當下的、直接自知的道德判斷,是通過覺性機能體證心性、精神本體實現的,與基于一般認知層面所做出的道德判斷有本質差異。正如張載所說的“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張載,1978a,p.24),“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見聞小知而已”(張載,1978a,p.20),可見,覺性的道德性是內生的、本原的。故而儒者才會不斷強調倫理道德不假于外的當下性、自明性,所謂“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他人者也”(王陽明,2014d,p.250),“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而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王陽明,2014a,p.156)。基于此陽明多次強調“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王陽明,2014c,p.232),故而耿寧提出“良知”是一種“道德自身意識”,以區別于西方現象學中性的 “自身意識”(耿寧,2012a)。
由上可知,但凡人的高級心智機能——覺性,必然內在地具有道德自知功能,伴隨高級心智機能發展呈現出的道德判斷是內源自生的。這一點是中國本土心理學(尤其儒家)的創見。
其次,不同于西方多為超驗層面的哲學思辨,覺性(良知)可在心理及行為層面予以操作,具有切身的道德實踐性。王陽明認為“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王陽明,2014a,p.192),“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王陽明,2014a,p.112)。可見,覺性在直接自明道德的同時伴隨著切實的道德實踐——對善的追求艷羨與對惡的厭惡戒慎的即時反應,“對王陽明來說,‘良知’這一術語說的正是直接的關于意念之道德品格的自身判斷,這一自身判斷不是一種理論上的判斷,而是‘愛’與‘惡’(wù)”(耿寧,2012b,pp.182-183)。故而要通過覺性不斷實踐體證“好惡”,以實現覺性道德機能的完全激發,這就是“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儒家所強調的“工夫論”、“知行合一”的傳統在這里得到體現。
愉悅性則是指覺性體證過程中伴隨強烈的愉悅體驗。眾所皆知的 “孔顏之樂”正是覺性體驗的典型狀態,佛家“禪悅”也極有代表性。“禪悅”指“入于禪定,快樂心神也。……同凈影疏曰:‘禪定釋神,名之為悅。’”(丁福保,1921c,p.2780)。佛家認為通過禪定訓練激發覺性,必然伴隨強烈的精神愉悅感。甚至于將愉悅感視為檢驗禪定訓練、覺性開發的一個重要指標,“謂令心不散,相續安住,故心能任運住于所緣,若時引生身心輕安之喜樂”(昻旺朗吉堪布,1995,pp.835-836)。
事實上,覺性的愉悅性與道德性總是互為一體的。相較佛家,立足于倫理道德本位的儒家更是自覺強化了覺性的愉悅性與道德性的同步性。儒家明確提出覺性機能展開道德價值判斷的同時必然伴隨主體的愉悅體驗,即體證到心性本源、精神主體與倫理之善高度一致時,愉悅感便由然而生。王陽明曾多次表達了踐行良知(即覺性呈現)的愉悅感——“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只要不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這里何等穩當快樂”(王陽明,2014a,p.156)。“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王陽明,2014a,p.181)。可知,覺性(良知)因其道德性而“必然帶有‘樂’的維度”(朱剛,2015,p.109),這種“樂”乃內源于主體覺性機能,“皆是發于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王陽明,2014e,p.287),故而“樂是心之本體……良知即是樂之本體”(王陽明,2014e,p.286)則理所當然。可見儒家準確把握了覺性機能中道德與愉悅相具互依的深層屬性,這一見解顯然不同于西方學者僅將自身意識視為一種非道德的中性心智機能。
綜上可知,胡塞爾的“自身意識”理論、布倫塔諾的“內知覺”理論與中國本土心理學的“覺性”理論均強調人類存在著超越一般認知層面的高級心智機能,并且其心理機制與原理完全能夠為我們所認識。但是現象學反對一般經驗層面、心理現象層面的研究立場,導致現象學方法囿于哲學思辨層面;布倫塔諾的“內知覺”則是建立在基督教默禱(contemplation)的個體直接經驗之上,致使其難以提供有效的操作方法。與之相反,中國本土心理學不僅從一般意識經驗入手提煉出一種普遍的機能模式,更是積累了豐富有效的實修體系與技術。中國本土心理學提供了一套貫通“身-心-性”的實踐操作系統,涵蓋了從基礎身心訓練(止定技術)到高級心智機能訓練(慧觀技術)的全過程(彭彥琴,2020)。
在此由衷感謝惟海法師對本文中佛教覺性理論與禪修技術部分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