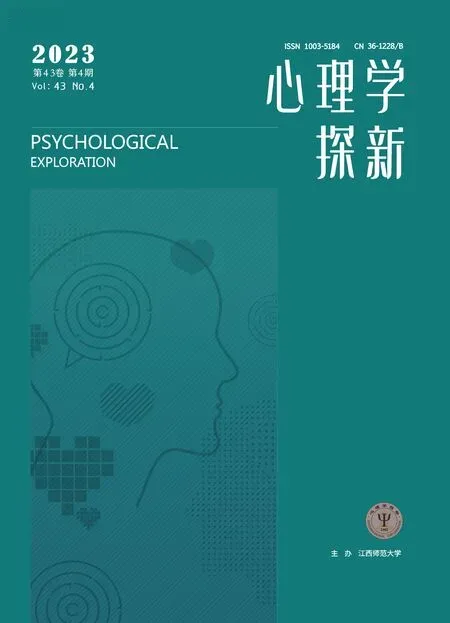“超華生”的胎動:郭任遠激進行為主義思想的歷史重估
王 勇,王佳慧,鮑晨燁,陳 巍,4
(1.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廈門 361005;2.紹興文理學院大腦、心智與教育研究中心,紹興 312000;3.密蘇里大學心理科學系,哥倫比亞 MO 65211;4.紹興文理學院心理學系,紹興 312000)
1 引言
2021年,在《比較心理學雜志》創(chuàng)刊一百周年之際,一篇題為《郭任遠與“取消心理學中的本能說”,100年之后》的文章赫然出現(xiàn)在其慶祝創(chuàng)刊百年的專欄上面,引發(fā)了學者的廣泛關注(Freeberg,2021)。“郭任遠的名字可能沒有被當下諸多研究動物行為的學生所認識。然而,他的觀點對動物行為學和比較心理學中研究動物行為的方法的發(fā)展產生了影響,也引發(fā)了爭議。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幫助人們了解郭任遠在1921年那篇文章(即《取消心理學中的本能說》)中的一些關鍵思想,并論證它們與我們今天研究的相關性”(Freeberg,2021,p.151)。歷史的鏡頭再次切回到20世紀初,將郭任遠(Zing-Yang Kuo,1898-1970)這位世界心理學史上的傳奇人物請到時代的聚光燈下。
對于心理學而言,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時間段是個“瘋狂的時期”(Boring,1929)。盡管新式心理學,即實驗心理學已經繞過歐洲傳統(tǒng)的意識心理學在美國大陸悄然出現(xiàn),但舊式的思辨的概念宛如“幽靈”般依舊縈繞在美國心理學的上空。受達爾文主義的廣泛影響,本能(Instinct)概念在動物行為上的重要性引起了心理學家的注意。美國心理學的精神領袖James(1890)在其巨著《心理學原理》中專門探討了“本能”話題。他首次將人的行為與本能相結合,并提出人的行為與動物一樣都是受到本能的支配。作為James忠實的追隨者,哈佛大學心理學系主任McDougall成為本能在心理學中的主要代言人。McDougall擴大了本能概念在個體行為領域中的解釋范疇,并將更復雜的社會行為歸因于個體的本能。由此,本能成為動物,包括人類在內的全部行為的激發(fā)因素,成為“一切思想和行動的根本來源和原動力”(McDougall,1908,p.26)。在此背景下,那些理論學家就像使用單詞魔術一樣把幾乎所有的人類行為都用本能這一神奇工具來套用,例如合作本能,性欲本能等。這嚴重阻礙了科學心理學,特別是實驗心理學的發(fā)展(Holt,1931)。
彼時,恰逢行為主義運動在美國心理學界狂飆突進。作為運動的發(fā)起人,Watson(1913)為一種全新的心理學研究姿態(tài)——行為主義發(fā)出了宣言:“在行為主義者心中,心理學是自然科學的一個純粹客觀的分支。它的目標是對行為進行預測和控制”(p.158)。然而,如果說本能理論可以描述、解釋、預測和控制人的行為,那么心理學的研究就只能回到內省式的意識分析,這是行為主義心理學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上,能否消解本能問題事關行為主義運動的成敗。事實上,Watson在1907年就和神經心理學家Lashley一起開展過許多關于動物本能的研究。例如,研究過燕鷗(terns)的遷徙本能。沒有任何訓練的燕鷗能夠從相隔1000多英里外的陌生地方重新找到回家的路(Watson &Lashley,1915)。盡管他們試圖去解釋燕鷗是如何做到的,但都徒勞無功。此后,Watson對本能的態(tài)度逐漸變得緩和。到1919年,Watson(1919)直接承認本能存在于生命早期,但強調習得的習慣很快會取代本能。盡管如此,本能問題依舊如同一座高山阻擋著行為主義者遠眺心理學殿堂的目光。
隨著問題的日益堆積,一大批圍繞本能問題闡述的論文相繼出爐,《是否存在本能?》《本能是假說抑或是事實?》……它們興起了近代心理學史上名噪一時的“本能論戰(zhàn)”。其中,來自中國的青年學者郭任遠憑借其極為激進且徹底的反本能觀點,逐漸走入一眾美國心理學家的視野。1918年,郭任遠從復旦大學肄業(yè)后,負笈至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深造,師從新行為主義的旗手——Tolman。期間,他接受了Watson的行為主義主張,成為堅定的行為主義者,并極力主張將心理學建設成一門客觀的自然科學。1920年秋,正值大三學期的郭任遠作了題為《取消心理學中的本能說》的研討報告,把批評的劍鋒直指McDougall。同年冬,他將該報告整理成論文寄給美國權威刊物《哲學雜志》。由于觀點過于犀利和出格,這篇文章直到1921年11月才被發(fā)表。旋即,McDougall(1921)回應了一篇長達48頁的文章,并將其稱為“超華生”(Out-Watson Mr.Watson)的行為主義者。
本文試圖通過梳理郭任遠在20世紀20年代發(fā)表的系列批判本能的論著及相關史料,將郭任遠的主張重新放置于國際本能論戰(zhàn)之中,進而對他的理論進行審視與定位,并闡述其對于郭任遠個人職業(yè)發(fā)展,乃至整個心理學學科的影響與價值。
2 郭任遠反本能主張的醞釀與演變
在郭任遠學術生涯的開端,“本能”問題無疑成為了他激進行為主義觀點進攻舊式心理學的最佳“靶目標”。在1924年發(fā)表的《反對本能運動的經過和我最近的主張》一文中,郭任遠仔細回憶了他關于本能思想變化的過程,并用他在那段時間發(fā)表的三篇文章作為劃分間隔(Kuo,1921,1922,1924)。
2.1 取消心理學中的本能
在《取消心理學中的本能說》中,郭任遠指出本能是一種習慣的傾向,是為了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而后天產生的習慣行為(Kuo,1921)。在他看來,新生兒降生后受到周圍環(huán)境的刺激,從而產生各種紛亂的動作。在經歷社會對于這些動作的篩選(對能夠滿足社會需求的行為進行獎勵,對不符合需求的行為進行懲罰),新生兒會重復最后能夠得到滿意結果的行為。當再次面對相同的刺激時,新生兒就會自然而然地重復這一行為。此時,該行為就轉變成為面對特定刺激的習慣性傾向。而這也恰好容易被那些沒去深究其行為發(fā)生原因的心理學家快速地判定為“本能”。在對行為發(fā)生進行深入反思后,郭任遠提出這些行為的背后本質是機能的組合。盡管看似種類繁多,其實只是幾個基本元素,即反應單位以不同方式組合得到的不同反應。研究者無法發(fā)現(xiàn)本能是機能組合的原因在于本能的命名方式。出于對最后反應的偏重,導致他們注意不到其中包含的附屬動作和機能組合。至于類似“飛本能”“性本能”這些在發(fā)育后期才表現(xiàn)出來的行為,它們是機能逐漸變化的結果。只是這個過程是內隱的,無法被外在觀察者所觀察得到。
郭任遠不僅批判了本能的理論,還對其相關的實驗結果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由普通觀察法所得的結論——凡某項反應足以表示某類動物特性者都可以稱為本能,是不可靠的。原因有兩點:(1)某類動物出現(xiàn)相同的反應是因為其處于相同的環(huán)境,且得到一種遺傳下來相同動作的方法。動物行為的產生會受到遺傳和環(huán)境的雙重影響,而非單一的遺傳影響。由此可見,“本能”不符合普遍認可的“不學而能”的條件。(2)種群中的社會性影響也是使得個體出現(xiàn)相同行為的原因。郭任遠認為,有些動物本能的實驗是不嚴謹?shù)摹R曾B飛實驗為例證,Spalding(1875)僅由從未見過飛翔的鳥在同齡鳥能夠飛的時候,它也能夠飛的現(xiàn)象就得出鳥具有飛翔本能的結論。鳥能夠飛是由于其機能組合已經成熟(如,翅膀發(fā)育完整),并且受到環(huán)境對它的要求(趕出鳥籠,強迫它飛)。鳥飛行為并非不學而能的,而是環(huán)境和遺傳共同的結果。只是有些沒有表現(xiàn)出來反被人認為是不存在。
此外,針對那些主張將本能視為行為上最重要組成部分的心理學家的動機,郭任遠進行了分類,并逐一批判。第一種是受達爾文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的影響,認為每個本能都有適應環(huán)境的作用。對此,郭任遠給出了兩條反對的理由:(1)本能無法在每個時代都適用。行為和環(huán)境緊密相連,本能和行為也密切相關。隨著新環(huán)境的變化,本能必然要發(fā)生改變。(2)個體的行為并不適應環(huán)境。新生兒對危險刺激進行積極反應,對有利環(huán)境進行消極反應的現(xiàn)象,足以說明個體剛出生是無法適應環(huán)境的。顯然,這類學者的主張是矛盾的。第二種認為本能是一種沖動。它足以形成重要動力,從而驅使個體發(fā)生各項動作。這是McDougall等人的觀點。他們深信人類各項活動的動機皆由本能的發(fā)生所致。對此,郭任遠也給了兩條理由:(1)新生兒的動作是由外界刺激而生,并非內在動力驅使。(2)個體只有與外界環(huán)境接觸,才會有社會性。以Whitman(1919)的鴿子求偶實驗為例,郭任遠認為實驗中的鴿子會向斑鳩求配是因為其生長在斑鳩的環(huán)境中,受到群落中刺激的結果。在他看來,鴿子與同類或者異類,甚至是非生命體求配是一樣的自然趨勢。這是社會刺激的結果,與鴿子的經驗有關。
面對Watson(1914)對特殊本能的保留態(tài)度,即主張?zhí)厥獗灸芤韵忍旆磻男问酱嬖?郭任遠也沒留有情面。他指出,Watson在新生兒行為的研究中,除了發(fā)現(xiàn)隨機運動外,并沒有找到任何特殊本能的跡象。由此,Watson被迫接受了本能出現(xiàn)的時間順序理論,但也沒有任何科學證據(jù)可以支持這種觀點。所謂不學而能的動作,不是先天適應的表現(xiàn),而是新環(huán)境與具有這些動作可能性的行為系統(tǒng)直接作用的結果。所以,個體的行動應用其與周邊環(huán)境間的關系來解釋。至于動作的原素,似乎不能稱為先天或遺傳的適應,除非證明細胞中有預先形成的部分(Kuo,1921)。
2.2 本能何來?
在過渡階段,郭任遠明確地提出為什么要在心理學研究中放棄本能的理由(Kuo,1922)。在郭看來,本能是一個“完結”的心理學概念。那些擁護本能的學者對本能概念的使用,如同原始人把那些行為中無法解釋的神秘性質歸因于神明的力量一般。除了冠以科學的名稱以外,它并不能在解釋行為發(fā)生方面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對本能概念的揚棄決定了心理學能否有資格成為一門自然科學。郭任遠這一系列激進的主張背后的直接目的就是“無論反對本能者同意與否,我相信我們否認的主要動機是把心理學從‘扶手椅中的玄想’解救出來;我們是要從發(fā)生的心理學里面將這塊絆腳石搬走”(Kuo,1922,p.346)。作為反本能心理學家,郭任遠提出他的研究在本能心理學家結束的地方才剛剛開始。
自James以來,幾乎很少有學者繼續(xù)深入分析和解釋個體的行為是如何獲得的。為此,盡管在實驗證據(jù)匱乏的現(xiàn)實情況下,郭任遠仍嘗試提出一些試探性的建議。首先,郭任遠再次重申反應單位假說的重要性。他認為,反應單位的最大特點是具有可塑性和整合的多樣性。這些特點能夠有效地幫助反應單位整合成系統(tǒng)化的反應。至于反應單位如何形成本能,郭任遠提出了兩種可能的方式:(1)同時整合(simultaneous integration);(2)時間順序整合(integration in temporal order)。其中,同時整合是指將反應單元直接或間接地組合成一個單一且有組織的反應。具體而言,同時整合包含三種潛在的形式:①將最初的反應單位組成統(tǒng)一的反應。例如,幼兒學習站立時產生的反應。②將先前整合的行為組合成更復雜的行為。這種整合形式通常發(fā)生在個體發(fā)展的后期。例如,兒童學習寫字的過程。兒童一只手要緊握鉛筆,另一只手還需按住書本。同時,眼睛跟隨筆尖運動、軀體姿勢(頭部、肩膀、手臂等)保持規(guī)范等活動又必須同時發(fā)生。這些活動本身又都是先前整合的行動組合。當被要求在寫字過程中一起工作時,它們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更復雜的、有組織的反應。③當新獲得的習慣與已經習得的習慣的性質不相融時,個體就需要打破敵對的習慣,逐步重建新的習慣。例如,當成年人學習一門新語言時,他總是很難發(fā)出一些在母語中沒有的音節(jié)。那么,他就必須要打破舊的發(fā)音習慣,重新組織新的發(fā)音習慣。
當然,行為并不孤立發(fā)生的,每一個行為之前或之后總是跟隨著其他行為。以一定規(guī)律,并按照一定的順序展開的行為,郭任遠把它們定義為時間順序整合。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老鼠走迷宮實驗。當老鼠學會走迷宮時,這一現(xiàn)象背后的行為暗示是它已經從先前組織起來的單一反應中選擇了某些單獨的行為,并將它們組合成一個新的序列順序。另外,郭任遠強調,為了把不同的行為歸類成為一系列連續(xù)的行為,心理學家必須采取某種客觀的標準,而最便利的方法就是把動作按所成就的效果來分類(Kuo,1922)。為此,他將每一系列的行為劃分為預備反應(preparatory reaction)和完成反應(consummator reaction)兩種類型。他認為,這樣劃分的目的是為了方便科學的描述,并不包含目的論,也不存在將某種生命沖動作為有目的的反應的驅動力。
同時,為了避免使用諸如“驅力”、“傾向”等容易給讀者產生有靈論導向的術語,郭任遠提議借用Tolman(1922)的文章中“行為集”(behavior-set)這一相對具體且客觀的術語來替代。所謂行為集,郭任遠將其定義為一種反應姿勢或預期態(tài)度,它們將引導個體以某種方式對不同的刺激或刺激群體做出有區(qū)別性和選擇性的反應。郭認為,個體在某一時刻產生的特定行為取決于許多因素。除了環(huán)境、刺激的性質和強度、個體與刺激之間的歷史關系、個體所擁有的反應系統(tǒng)的性質和類型以及頻率、近時性等因素的影響外,行為集在決定個體將產生何種行為或者對何種刺激作出反應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換言之,行為集形成了一種“反應基調”(reaction tone)。這種基調會一直持續(xù)到完成反應的達到,或者直到它被其他反應基調所取代或修改(Kuo,1922)。
2.3 心理學需要遺傳嗎?
到了第三階段,按照郭任遠(1924)的話來說,這一時期所有的作戰(zhàn)方針都變了。與前兩個階段相比,他的觀點日趨極端。郭任遠把心理學被定義為一門研究與個體適應環(huán)境有關的生理機制的科學,特別強調適應的功能方面。所謂功能方面,即一種反應的效果或適應價值——積極的、消極的或冷漠的。這種反應效果建立了個體對其環(huán)境、社會或其他方面的一種新的功能關系。此外,郭任遠站在行為主義心理學的立場上,強調所有研究都應該嚴格地執(zhí)行實驗室的客觀程序,并堅持對行為的生理學解釋。心理學中的任何爭議問題都必須能夠在實驗室中得到解決,或者至少對實驗室程序具有某種特殊的價值。否則,這些爭議在科學心理學中就沒有理由存在。正因如此,郭任遠堅定地否定本能的概念,并指出所有遺傳概念在實驗室心理學中沒有任何存在的空間和價值(Kuo,1924)。
為了厘清心理學的困境,郭任遠嘗試用生理形態(tài)學(physiomorphological)的術語來客觀地描述心理現(xiàn)象(Kuo,1924)。具體而言,郭任遠把研究客觀心理學的學者面臨的與遺傳有關的問題歸納為兩個生理形態(tài)學上的問題:(1)是否有任何神經肌肉模式與假定的遺傳行為模式相對應;(2)假設存在與遺傳行為模式相對應的明確的神經肌肉模式,它們與遺傳物質(germ-plasm)有何關系?也就是說,它們是如何與胚種組織相關聯(lián)。在回答第一個問題之前,實驗室心理學的工作者還有一個雙重任務:(1)必須確定每一種行為模式是否都有一個明確的、固定的神經肌肉模式;如果有,那么(2)必須確定、定位并證明這種神經肌肉模式。郭任遠認為,只有完成這個雙重任務之后,他們才能合理地探討心理學中的遺傳概念。
在用客觀的術語界定好這幾個前置問題之后,郭任遠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動物行為和生理的研究中存在一個非常確鑿的事實——行為模式沒有明確、固定和不變的神經肌肉模式。這一事實不僅被本能的否認者所承認,也被許多本能的捍衛(wèi)者所承認(McDougall,1921;Tolman,1922)。顯然,雙重任務的第一個問題已經被科學研究所否定。遺憾的是,許多心理學家借助諸如神經連接、突觸抵抗等概念,直接假定了遺傳反應與個體生理之間的關系,根本沒有人去費力研究這些關系的實際生理組成。即便是Watson(1919)也使用一個模糊的概念(條紋肌肉的運動)來回避整個問題。在郭看來,一般的生理學概念被那些理論工作者當成了掩蓋他們對行為起源和發(fā)展無知的“遮羞布”。這些亂象愈發(fā)讓郭任遠認識到心理生理學對行為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心理學需要的是生理事實,是可以在實驗室里驗證的,而并非一般性生理概念的肆意套用。郭任遠強調,對心理學而言,行為的最終原因是遺傳、自然、上帝還是靈魂,幾乎沒有區(qū)別。因為只要行為模式與神經機制沒有固定的一對一關系,行為的遺傳就無法得到科學的證明。
基于這一階段的深刻認識,郭任遠開始對之前的反本能觀點進行了回顧與反思。他指出,在《取消心理學中的本能說》一文中的論點——所有所謂的本能歸根到底都是后天的反應,這無疑是讓自己承認了遺傳和后天反應之間存在的區(qū)別。而主張那些復雜的反應系統(tǒng)是建立在反應單位的基礎上,但反應單位本身是遺傳的,這等于說自己又承認遺傳的存在。只要存在遺傳反應,無論多么簡單,他們都有理由使用“本能”一詞。郭任遠坦言,“不是我走得太遠,而是我對本能心理學家做出了太多讓步,給了他們攻擊的空當”(Kuo,1924,p.439)。為此,郭任遠對那些妥協(xié)的觀點進行了修正:(1)廢除先天-后天二分法;(2)所有的反應都必須看作是刺激的直接結果,是有機體與環(huán)境間的相互作用;(3)遺傳不是心理學的問題,因為心理特征的遺傳無法在實驗室中被證明。當下,科學心理學亟需發(fā)展心理生理學和發(fā)展心理學的實驗技術。在客觀的實驗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行為心理學的建設性綱領。這才是行為主義者需要去考慮、去實踐的重要議題(Kuo,1924)。
3 余音
在那個元理論“百花爭鳴”的年代,郭任遠憑借其激進的行為主義觀點屹立于本能爭論的旋渦之中,這無疑揭示了“科學研究也需要意識形態(tài)吸引(ideological appeal)。這種意識形態(tài)由環(huán)境論(environmentalism)提供——主要歸功于郭任遠與Watson——隨后緊密地與行為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Boakes,1984,p.239)。這種理論滲透的客觀實驗進路為當時停滯不前的心理學提供了新的研究領域和方法,顯示出極強的前瞻性與生命力。同時,它又深刻地影響著郭任遠的學術生涯。
3.1 倡導以“行為學”研究來替換行為主義觀點
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初Watson等人掀起的行為主義運動,其最初的目標是為了改造心理學的根本觀念和方法,建立一個相對不受扶手椅教條或方法論制約的行為研究新領域。然而,結果是不盡人意的。即便是轟動一時的本能論戰(zhàn)也在1922年以“未完成的姿態(tài)”潦草收場(Cravens,1978)。歸根到底,舊式心理學并沒有犧牲什么,以Watson為首的行為主義實踐最終選擇向傳統(tǒng)心理學妥協(xié)。慶幸的是,Watson的士兵們不顧重重困難,拒絕投降。郭任遠就是其中一員(Epstein,1987)。
在郭任遠看來,這一切都是Watson主張的柔弱性以及革命的不徹底性造成的。為此,郭任遠總結了自己的反本能主張,并提出行為科學的新構想。1937年,在題為《人類行為學導論》的文章中,郭任遠正式為自己的新科學命名為“行為學”(praxiology),并以此來替代Watson的行為主義(Kuo,1937)。行為學的設想融入了郭在反本能階段的諸多思想。具體來說,郭任遠將行為學定義為一門專門研究動物(包括人)行為,并且是多學科交叉的新科學,其主要研究領域在于關注行為的個體發(fā)生和生理研究。與行為主義相似,行為學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預測和控制個體的行為。不同的是,行為學家將徹底拋棄諸如本能、意圖、行為準備等概念,主張通過嚴格的實驗室控制來獲得關于刺激和反應的本質及其復雜關系的充分數(shù)據(jù)以及有關行為的生理和個體發(fā)生的基礎數(shù)據(jù)(例如,神經功能、內部分泌物和其他代謝變化之類),進而使用純粹的數(shù)學和物理術語對行為進行徹底的科學描述(Kuo,1937)。正是這樣一個初步構想,在二十世紀晚期卻成為讓比較心理學擺脫生存危機的一劑良方,“行為的比較研究應該是一個新的、全面的、多學科的行為科學的一部分。沿著郭任遠建議的路線,人們正在努力建立這樣一門科學”(Epstein,1987,p.249)。
3.2 推動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從“扶手椅”走向“實驗室”
如果站在心理科學發(fā)展史的角度來回顧這場爭端,郭任遠對于本能的批判包含了科學心理學勢力對舊式“扶手椅”心理學的強烈不滿。自Wundt創(chuàng)建現(xiàn)代心理學以來,心理學雖然擺脫了哲學的附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是其使用的方法,特別是所謂的實驗控制內省法,一直讓心理學飽受詬病。在經歷這本能論戰(zhàn)后,郭任遠逐漸認識到即使是自己當時的主張,也沒有擺脫哲學家扶手椅式的老把戲,只是沒有實驗證據(jù)的空想空談(郭任遠,1940)。那么,如何能夠在實驗室里追溯行為發(fā)展的起源,如何能夠拿出實驗的證據(jù)成為郭任遠繼反本能之后需要去直面的首要任務。
在郭任遠看來,一個好的科學研究方法應該滿足以下要求:(1)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科學數(shù)據(jù)都必須用定量或數(shù)學術語來表述;(2)在科學觀察中,研究人員所報告的相同現(xiàn)象必須能被再現(xiàn);(3)為了觀察的精確和精細化,科學儀器的幫助是必不可少的;(4)在可能的情況下,應使用記錄儀器代替人工觀察;(5)為確保科學上可接受的數(shù)據(jù),控制實驗總是必要的(Kuo,1937)。顯然,這些條件都在將心理學研究朝著自然科學的方向去推進。1923年,回國后的郭任遠先后創(chuàng)建了多個動物心理學實驗室。在嚴格的實驗控制條件下,他開展了一系列頗具方法論創(chuàng)新的行為實驗。這些實驗結果不僅佐證并進一步發(fā)展了郭任遠的理論觀點,也為世界反本能運動新增了科學證據(jù)(陳巍 等,2021;Wang et al.,2023)。
3.3 未完結的反本能研究與使命
作為一名激進的行為主義者,郭任遠在這場本能論戰(zhàn)中成為爭論的聚焦點,也成為了唯一一位遭受到與McDougall一樣多攻擊的反本能學者(Krantz &Allen,1967)。按照郭任遠(1924)的話說:“美國現(xiàn)在心理學家對于本能的問題的態(tài)度可分作數(shù)派:(1)極端贊成我的主張。(2)極端反對我的主張的,如E.L.Thorndike和Mm.McDougall等。(3)折衷派,如R.M.Verkes和John B.Watson等。(4)不贊成也不反對,惟隨波逐流一無所主張。在這四派中,折衷派占大多數(shù),贊成派人數(shù)最少”(p.H6)。同時,郭任遠自信地認為,這些觀點大多都是一些誤解或者沒有特別值得繼續(xù)深入討論并給予回應的必要(郭任遠,1924)。
值得注意的是,兩大陣營的代表人物Watson和McDougall都曾向郭任遠表達過自己的觀點。其中,Watson曾在1922年對郭任遠說:“我贊成你反本能的主張,但我不能如你那樣極端”(郭任遠,1929)。直到1926年,Watson才提出:“在人類反應的這個相對簡單的目錄中,找不出哪一種對應于當代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所說的‘本能’。于是,對我們來說,沒有本能——在心理學中我們不再需要這個術語”(p.1)。(1)也有觀點認為,Watson是受到郭任遠文章的影響才放棄“本能的遺傳”見解(Hothersall,2004,p.482)。McDougall(1921)作為前輩曾向郭任遠表達過委婉的妥協(xié):“我們現(xiàn)在有一個兩難論……(1)我們必須放棄機械主義而保全本能;或(2)我們贊成郭先生的主張,否認人類及動物的一切本能,而保全機械主義。至于我自己呢?我是寧舍棄機械主義而保存本能的觀念的”(p.310)。為此,郭任遠曾嘲諷道:“為了將本能從本能否認者的攻擊中解救出來,不惜將它們投入柏格森學派(Bergsonian school)的形而上學蔭庇之下”(Kuo,1929,p.190)。即便是Tolman(1922)出面斡旋,“我們應該持有心理學不該拋棄本能的信念”(p.152)。郭任遠也未對自己的導師采取任何讓步:“Tolman的物觀目的論(objective view of purpose),不比McDougall直接爽快的靈魂論(animism)好,或者甚至比它更糟糕”(Kuo,1929,p.190)。可見,“發(fā)展心理生物學家郭任遠在他職業(yè)生涯的這一階段代表了一種絕不妥協(xié)的新行為主義支持者”(Griffiths,2004,p.610)。
4 結語
回顧歷史,郭任遠畢生致力于倡導一種科學的客觀的心理學。正是在對這種理論信仰的追求之下,郭任遠每一次關于本能的思想轉變都已經在其整體的認識論圖景中被預設了特殊的位置。因此,無論是他早期對本能、遺傳、意識、目的論等概念的持續(xù)的理論批判(陳巍 等,2021),抑或是后期對貓捉老鼠(王勇 等,2023)、動物搏斗(胡燁 等,2022),以及雞胚胎發(fā)育的系統(tǒng)的實驗研究(Wang et al.,2023),其最終的目的都是在忠實地踐行行為主義的歷史使命。盡管現(xiàn)實處境如此不堪,晚年的郭任遠仍在畢生積累的實驗結果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為行為的發(fā)生發(fā)展指明了認識論上的方向——行為漸成論(behavioral epigenesist theory)。其中,行為漸成的概念被郭任遠定義為“從受精到出生到死亡的一個連續(xù)的發(fā)展過程,包括增殖、多樣化和行為模式在空間和時間上的改變,這是發(fā)育中的生物體與其環(huán)境(內源性和外源性)之間持續(xù)動態(tài)的能量交換的結果”(Kuo,1967,p.11)。在郭任遠(1967)建構的理論框架中,行為研究將成為一門包含比較解剖學、比較胚胎學、比較生理學(在生理物理和生化意義上)、實驗形態(tài)學以及對生物體與外部物理和社會環(huán)境之間動態(tài)關系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在內的真正的綜合科學(synthetic science)。同時,它也將成為協(xié)調的,多層次的,跨物種的綜合發(fā)展研究。為此,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郭任遠仍在呼吁“建立一個大型研究中心,由各科學學科的專家……可以制定一個共同的發(fā)展計劃,并集中精力,從不同的角度解決同樣的問題”(Kuo,1970,p.191)。
歷史證明,郭任遠激進的行為主義思想,只不過是他作為“超華生”的胎動而已,其分娩、成長、成熟的陣痛與堅韌,或仍湮滅于歷史的塵煙之中,但卻無損其歷史地位——“郭任遠的寫作跨越了大約50年(1921-1970),從1921年具有開辟性意義的重要論文《取消心理學中的本能說》開始,到1967年同樣重要的著作《行為發(fā)展之動力形成論》結束。他剩下的33篇論文可以被看作是直接從1921年首次提出的建議和想法出發(fā)的具體步驟,并被詳細闡述為20世紀為數(shù)不多的系統(tǒng)性普通心理學理論之一”(Greenberg &Partridge,2000,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