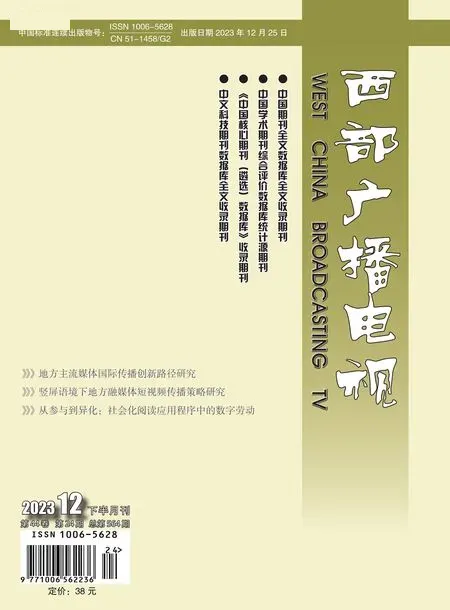數智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跨文化傳播的現實困境與優化策略
李一凡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基于對全球局勢以及中國發展現狀深刻洞察后提出的重要論述,既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生動體現。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跨文化傳播,不僅能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長遠發展規劃機制的優越性,更為當今紛繁復雜的世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從周邊國家逐步走向世界,從構想到實施,一個基于中華文明又符合世界潮流的中國聲音已經形成[1]。優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跨文化傳播策略,不僅成為新時代提升我國跨文化傳播效能的新任務,也是促進各國文化平等交流互鑒、謀求人類共同發展的新使命。
隨著智媒技術的迭代,一個區別于以往的數智時代已然來臨:一方面,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 VR)/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 AR)、5G、大數據等技術蓬勃發展,為新聞生產與傳播實踐帶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傳播渠道正逐步從傳統大眾媒體走向各種新媒體。隨著社交媒體和短視頻成為受眾獲取資訊的主要渠道,基于網絡平臺的扁平化結構特征,新聞生產過程開始了基于社交媒體邏輯的實踐和理念轉型——這是一種以“信息網絡化”理念對整個新聞的生成、分發、接受及反饋機制的改造。社交媒體、短視頻和新聞媒體結合所產生的反應對新聞生態乃至社會生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一個全新的傳媒生態已經形成。
正如學者尼爾·波茲曼所言:“每一種技術既是包袱也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2]數智時代的新傳播生態為我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跨文化傳播帶來了機遇[3]。但是,面對當今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如何見招拆招已成為急需攻克的難題。本文從數智時代的跨文化傳播特點出發,并結合當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跨文化傳播困境,提出應對策略。
1 顛覆性圖景:數智時代的跨文化傳播特點
1.1 主體邊界泛化,用戶生產內容成為新型話語模式
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在其著作《無聲的語言》中對“跨文化傳播”這一概念作出詮釋,即擁有顯著文化差異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人際交往與信息交流的抽成,也包括各種文化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遷移、擴散、變化的過程,及其對不同群體、文化,乃至國家的影響[4]。從定義不難發現,傳統的跨文化傳播主體主要集中于社會公民,即現實生活中的公眾。而數智時代的技術革新使得跨文化傳播的話語形態下放,跨文化傳播的主體邊界不斷泛化[5]。
“滇西小哥”是當今社交媒體上較受矚目的美食類自媒體博主之一,全網粉絲超過千萬。在國內視頻自媒體模式趨于同質化、商業變現存在一定困難的局面下,“滇西小哥”選擇進軍國際市場,通過發布關于中國特色美食制作的短視頻,受到國際受眾的追捧[6]。
1.2 渠道外沿擴展,新媒體晉升為重要傳播平臺
傳統的跨文化傳播由于技術的限制,其傳播渠道離不開大眾媒體,而數字技術的勃興則使得跨文化傳播的渠道從報紙、廣播、電視向新媒體轉型。現如今,各類新媒體平臺正如雨后春筍生長起來,在跨文化傳播活動中發揮愈加重要的作用。
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火遍全網的“冰墩墩之歌”在國內外短視頻平臺刮起強烈旋風,不同國家的人民都被“魔性”的旋律和“冰墩墩”可愛的形象吸引[7]。數智時代,下沉化的傳播渠道降低了人們獲取、生產及傳播信息的難度,同時也為各國文化平等交流帶來了新的可能。
1.3 內容樣式豐富,話語敘事形態向智能邁進
與過去單一的文字、圖片、音視頻等呈現形式不同,承載多種新型媒介技術的數智時代為跨文化傳播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傳播形式:H5新聞、VR/AR報道,以及數據新聞等各種新報道形態豐富了跨文化傳播的敘事形態,內容從單一走向多元,從扁平走向立體,呈現出智能化的特點。
《中國青年報》推出的融媒體作品《大象,回家了》就是一款運用新興媒介技術賦能傳統報道形態的融合產品,通過VR、交互地圖等視覺設計和編程手段,完整、立體講述亞洲象北移事件,用多元表達、沉浸式體驗向受眾展現了中國生態保護進程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故事[8]。
2 挑戰重重:數智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跨文化傳播的現實困境
2.1 數字鴻溝難消解:他塑和“數字鐵幕”下的聲音封鎖
數字鴻溝指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地區、行業、社區、民族之間,由于對信息、網絡技術的擁有程度、應用程度及創新能力的差別而造成的信息落差與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的趨勢。在數智時代更多地表現為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數字媒體接觸和使用狀況的差異[9]。
新時代以來,我國不斷夯實經濟基礎,大大縮小了與西方的數字鴻溝,但是沒有完全改變世界信息流動的不平衡狀況[10]12。這是因為經濟的增長與媒介技術的迭代不完全同頻,當今世界的信息源頭絕大部分還是從英美等少數幾個媒介技術發達的西方國家向世界各地流動,中國自身的外宣媒體近年來傳播效能已經大大提高,但與這些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11]。譬如美國的“美聯社”、英國的“路透社”,還有法國的“法新社”等,這些世界級的新聞通訊社在國際新聞流通渠道中占據優勢,卻存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理解不夠透徹的情況,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無法對其進行全面、真實的描摹,無形中建構起數字鐵幕,影響了中國聲音的有效輸出。此外,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使得跨文化傳播面臨的形勢更加錯綜復雜,在本就不完全平衡的跨文化傳播格局中,中國聲音成為他塑的對象。
2.2 高低語境難跨越:文化折扣下的低效傳播和認同離散
中西方在歷史背景、意識形態、語言體系等方面具有顯著差異,這些差異使得他者在理解我們的文化的過程中會產生曲解,跨文化交際中將這種現象稱為文化折扣[12]。愛德華·霍爾在《無聲的語言》中提出,不同的文化主體間存在高低語境之別,共通意義空間的缺乏易于導致傳播障礙與傳播隔閡的產生。
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高低語境中的文化產品置換難免會產生意義的缺損和扭曲,同時由于中西方基于各自“想象的共同體”構成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情感,對于異質文化就會趨向于對抗式解讀,從而遮蔽了符號真正的內涵。在數智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便捷,不同文化、不同地區的人民都能通過互聯網隨時與他人展開溝通。這一方面降低了溝通的難度,另一方面,文本意義的曲解、話語內涵的誤讀也在便利的交流中更加嚴重。
2.3 文化認同難搭建:“多雜散匿”傳播特點下的文化排斥加劇
在跨文化傳播中,文化認同是一個重要議題。文化認同是指來自不同文化的群體對本文化及其他文化的關系進行評估和判斷,也是個體進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慮和不確定性的主要方式[10]14。數智時代,跨文化傳播呈現出內容繁多、信息冗雜、平臺分散、主體匿名等特點,人們都能通過互聯網暢所欲言。表面上看,這種開放化、互動性的特點有助于拆除不同文化的藩籬,提升文化之間的認同感。但是,網絡空間的高自由度使得現實社會中個體的文化依存被消解,文化認同的危機反而會加劇。這是因為跨文化交流者在互聯網平臺上容易造成“圈層效應”,擁有相同意見的一批人自動聚集在一起,彼此作為支撐,不斷加深原有的觀念。因此,“多雜散匿”的傳播邏輯反而會加劇對異質文化的排斥,這恰恰不利于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3 突破重圍:數智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跨文化傳播的優化策略
3.1 以中華符號詮釋全人類共同關注
索緒爾提出結構主義符號學理論,強調了傳播活動媒介中運載的不同符號。跨文化傳播實際是不同符號之間的交流與理解、融合與發展。智媒技術為符號的可視化帶來新的可能,除此之外,在符號的選擇上避開一些政治色彩過于濃重的內容,深度挖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能夠承載全人類情感的符號,將大大提升跨文化傳播效能[13]。
例如,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中,成都市政府以大運會為媒介,利用“熊貓”元素、川劇變臉等文化符號,立體真實地還原了成都的城市形象。可愛的熊貓憨態可掬,背后隱含著中華民族珍愛動物、保護自然的發展理念。這些符號將宏大的理念具象化,用以小見大的手法向他國受眾精妙地傳遞本國價值,消除了不必要的傳播噪聲,實現了真正的民心相通。
3.2 以他者視角促進全人類共情理解
“共情”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是指個體能夠與他者平等交流,傾吐心聲,最終達到“同呼吸共命運”般心理體驗的一種能力。共情機制致力于跨文化傳播中多元文化的接觸和互動,通過主體的社會性實踐彌合因文化習俗、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因素造成的信息隔閡[14]。與傳播者自說自話相比,來自別國的“他者”現身說法,從受眾本身的角度闡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有助于促成全人類的共情理解。
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推出的大型人文地理紀錄片《極致中國》由五洲傳播中心與美國國家地理頻道聯合制作。美國探險家兼攝影師本·霍頓在節目中擔任主持人,并邀請來自中國的極限運動愛好者作為搭檔,共同前往四川、海南和陜西等地,深度探索中國人文地理和民俗特色,向世界展現一個更加豐富和立體的中國。外國主持人特別強調親身感受和情感互動,通過身體和精神的跨文化體驗感受中國少數民族的獨特歷史、風土人情和特色文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世界:中國在追求高速發展的同時,始終促進不同民族共同繁榮,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以人為本”不謀而合。
3.3 以傳播矩陣呈現全人類共同價值
在數智時代,傳統媒體作為我國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依然肩負著跨文化傳播的任務,全新的傳播生態使得多元主體都享受到了傳播媒介多元化帶來的紅利,傳統媒體也應該加快媒體融合的步伐,充分擁抱新媒體,利用新興的社交媒體,著力打造全媒體傳播矩陣,全面呈現全人類共同價值。同時以互聯網思維,用平等開放、互動交流的姿態進行跨文化傳播。在傳播矩陣的幫助下,著力打造共通的意義空間,傳遞人類共同的情感價值。
例如,新華社依托全媒體數據資源庫與區塊鏈技術,搭建“中國好故事數據庫”,圍繞中國先進的治理理念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將6萬多條中國故事分為學習、治國理政、奮斗圓夢、中華文化、合作共贏五大模塊,在國際社會中多方面、立體化地展示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海外用戶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供了新平臺[15]。
4 結語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會隨著時代的演進不斷更新,豐富的內涵會為跨文化傳播提供源源不斷的理論來源與現實依據。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此同時,數智時代日益嚴峻的數字鴻溝、文化折扣、文化排斥等現象也不容忽視。面對挑戰,必須充分利用數智時代的傳播優勢,挖掘中華符號、借助他者視角、搭建傳播矩陣,助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真正通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