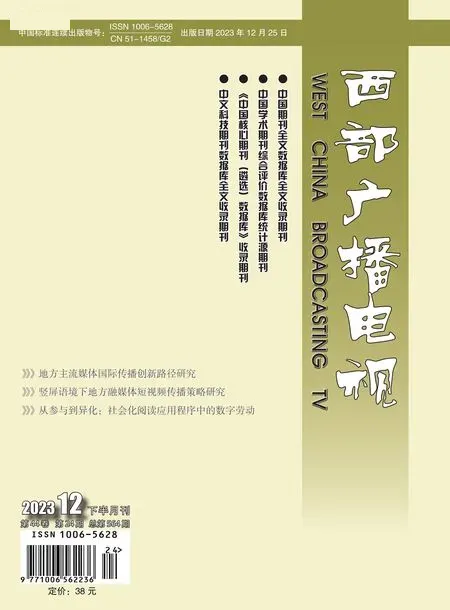從參與到異化:社會化閱讀應用程序中的數字勞動
王依晨
(作者單位:吉林師范大學)
社會化閱讀App中的“免費”閱讀助力平臺打響第一炮。當為他人“做數據”變身為自己“做數據”時,平臺賦權變為“自愿”勞動。閱讀平臺設置的規則讓參與者收獲了自我價值的實現和滿足,讓生產行為被自主意愿遮蔽。讀者用戶在社會化閱讀中的點贊、評論、分享等行為成為平臺的產品和收益。讀者用戶在為獲取“免費”閱讀特權而每天“做數據”、與好友PK(對決)、為平臺“引流”,在閱讀時長排行榜的“激勵”中不斷延長閱讀時間,繼而又產生了對于“免費”閱讀的需求,形成循環。在這個循環中,積極參與的讀者用戶的休閑閱讀行為逐步異化成一種無知無覺的數字勞動,本文將就這種異化現象進行理論闡釋,使用深度訪談法發現問題,分析現象成因,探討應對策略。
1 社會化閱讀
國內最早對“社會化閱讀”作出釋義的鐘雄認為社會化閱讀是指以讀者為核心,強調分享、互動、傳播的全新閱讀模式[1]。相對于以書為核心,強調內容本身的傳統閱讀模式,社會化閱讀更加注重讀者用戶基于閱讀的社會交往,倡導共同創造用戶生成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傳播和盈利。這種閱讀模式有多個參與主體,可在同時不同地、同地不同時等情況下共同參與到閱讀行為中。閱讀和社交是社會化閱讀App的核心功能。社會化閱讀App具備評論、關注書友、轉發、分享互贈已購圖書等功能,體現了閱讀App的社會化特性。社會化閱讀App可以實時更新共享讀者用戶的筆記、感想、二次創作等,而讀者用戶的書評、二次創作也具備再次交互的功能,優秀的長篇書評和二次創作會為平臺帶來更多流量,這種UGC模式在社會化閱讀社區中的應用豐富了在線出版的內容。書評、二次創作的共享表面屬于讀者用戶的自發行為,無償為平臺內容添磚加瓦,分享個人二次創作的智慧成果,實際上是讀者用戶商品化的體現。產消一體化的平臺規則使得社會化閱讀App成為一個數字勞動“工廠”。李林容、張靖雯對此提出,社會化閱讀App平臺的邏輯貌似將UGC的生產和消費權利交還給讀者,實則用一套話語遮蔽了分發權利的結構性不平等。從生產上看并非所有社會化閱讀中的UGC都是理想意義上集體智慧的結晶;從消費上看流量分發邏輯難以絕對保障公共權益的獲得,社會化閱讀中的讀者及其生產行為,常常陷入商品化困境之中[2]。
2 數字勞動
數字勞動的概念首先是由意大利學者泰拉諾瓦提出的,他認為數字勞動的核心規則就是免費。免費勞動最重要的、最常見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數字勞動。用戶集體智慧被規則轉化為平臺的產品,休閑娛樂行為被轉化為生產行為。這種具有生產性的勞動本質是共同體特質的聚合型的勞動,用戶集體創造,平臺集中傳播,在不同的時空持續產生著巨大的價值。而這種非物質的勞動行為被轉化為商品的過程也極易被生產者本人忽略。
同時,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斯邁茲在“受眾商品”理論中提出,大眾媒介生產的消息、思想、形象、娛樂、言論和信息并不是其最重要的產品。平臺將受眾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給廣告商。這就揭示了傳播中的真正商品是受眾群體[3]。到此為止,被商品化的不只是用戶的數字勞動,還有用戶本身。李文特將觀眾的觀看也視為一種勞動,觀看行為本身就在創造價值[4]。在社會化閱讀的平臺中,用戶所生產的評論、留言等也在被觀看,而這種被觀看也可以視作一種勞動。讀者用戶在閱讀平臺中的數字交互行為,甚至包括讀書本身都在為平臺創造價值,是一種不被勞動者所察覺的、被消遣娛樂所掩蓋的勞動。
3 社會化閱讀App中的數字勞動現象
在全民閱讀的時代背景下,社會化閱讀App的日益發展為讀者用戶提供了社交閱讀的技術便捷。讀者用戶可以依托閱讀平臺的力量獲得自身青睞的閱讀環境。基于好友通訊錄形成社交閱讀環境的微信讀書,基于連載網文愛好形成聯結的起點讀書、晉江文學城,文學發燒友聚集地的豆瓣讀書,甚至是打著“看書賺錢”旗號的番茄小說、七貓小說等,原本應當依賴自身藏書量吸引用戶的各大社會化閱讀App近年來開始頻出奇招。微信讀書推出的“換”無止境的無限體驗卡,起點讀書開辟的UGC模塊鼓勵讀者用戶進行同人創作和有聲書錄制等,這些閱讀平臺變得越來越依賴讀者用戶的“輸出”。
3.1 有意識的參與和無意識的勞動
“我在微信讀書推出初期就下載了,和幾個朋友有個小群,每天在里面完成讀書小隊PK共攢積分、周六抽組隊體驗卡的任務。一開始覺得特別劃算,感覺薅到了資本羊毛,可以免費看書。那些任務也不算太難,能省錢又能看書就是賺到了……”(受訪者3)
“我每天都會做起點福利中心的任務,看視頻、玩小游戲都能獲得免費章節卡。”(受訪者5)
受訪者們大都認為平臺推出的這類“福利”機制和規則是合理的、可行的,并付諸了實際行動去完成一些觀看、轉發的社交任務。讀者用戶認為這是合理的等價交換甚至物超所值,認為平臺制定的規則是其力所能及的,更有甚者還會從這些任務中獲得樂趣和滿足感,因而對其樂此不疲。邁克爾·布若威在研究中將勞動過程類比游戲,“玩游戲”使用戶控制自己的數字勞動行為而不是感到被控制,提高了用戶的自主選擇性,使得用戶認為參與行為是自身的獨立意志。這種自由選擇感促進了用戶對平臺的認同,用戶認為自身處于一種被賦權的自發創造環境中。
“微信讀書里那些邀請、組隊、PK、翻卡其實挺煩瑣的,特別是我的親友都不看電子書,我也知道這是平臺的一種引流手段,但也算是互利互惠吧,我拉給它流量,它讓我白看書。”(受訪者6)
平臺通過制定規則進而制造了讀者用戶同意勞動的表象。即使是意識到閱讀App通過促使其完成福利任務來增加流量、實現變現,使用者也依然形成了對平臺機制、規則的認同。這種現象說明即使讀者用戶具有實施數字行為的主觀能動性,但在與平臺博弈時依舊處于弱勢,所謂的“自由”是平臺圈地的自由。在平臺技術神話的支持下,讀者用戶通過社會化讀書App作為媒介構建的想象性關系中的平等,滿足了自身對于獲取信息、社交、游戲娛樂的要求。一些讀者用戶出于對技術的享受和樂觀,于是對于與平臺之間的一些不平等“視而不見”。
3.2 被異化的閱讀行為
各種讀書App都設有圖書排行榜,方便讀者用戶瀏覽上榜書目,了解圖書市場現狀。如今,除了圖書需要榜單的激勵,各大讀書App為讀者用戶也設置了讀書排行榜、閱讀挑戰賽、閱讀PK場等競賽機制。這些閱讀競賽的參與要素就是閱讀時長,通過時長數據來換取平臺設置的獎勵。
“一開始也沒想要在榜上卷,但是看到很多平時好像也不怎么看書的好友上榜,比賽的心就蠢蠢欲動。另外,時長兌換福利還挺實用的,比賽相當于用一元買4天會員、兩元買10天會員,也不算太貴,還可以督促自己看書,一舉兩得。”(受訪者4)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PK上段位的形式,只要達到相應的段位就有保底的積分獎勵可以兌換商城道具,和玩游戲的機制一樣,我也不去爭top,就每次卡線3 000分鐘拿星耀段位積分。”(受訪者5)
讀書的目的有很多,一直以來人們為了獲取信息閱讀,為了汲取科學知識閱讀,為了娛樂消遣閱讀。如今,人們開始為了“數據”閱讀。那些平臺設置的兌獎時長就像是等著讀者用戶去完成的“KPI”(關鍵績效指標),許多讀者用戶也確實變成了像完成工作績效一般而進行著任務性的閱讀行為。讀者用戶被平臺所設置的“游戲”規則所深深影響,在設置的競賽中獲得利益和滿足感,再次印證了布若威所說的“趕工游戲”。在這種競賽模式的“游戲氛圍”中,讀書行為被異化,讀者變得不光是單純地獲取信息、知識,還開始對社會交往方面產生需求,產生在讀書好友、同好中排名獲得第一的欲望。自此閱讀被量化,讀者用戶也默認了平臺“多多益善”的理念,以“量”為王。許多讀者用戶參與比賽的初衷是借競賽機制督促自身進行閱讀行為,但應當意識到時長的領先并不是真正在閱讀能力上的領先,最終還是應該回歸對于獲取知識為本質的閱讀。
3.3 UGC模式或成情感勞動
社會化閱讀的特點是過程中無處不在的社交行為,而社交行為也總是伴隨著情感互動、情感展示。讀書平臺通過技術將讀者有感而發的評論、書評、二次創作互聯共享,使平臺用戶可以實時共享大眾的智慧成果。
“我會在閱讀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書籍時寫一些批注和評論,其他的讀者看到我的思考可以和我進行交流。我很喜歡自己的觀點被其他讀者肯定的感覺,很有成就感。同時我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感悟,有時會給我帶來意外的靈感。”(受訪者1)
“書友圈的功能我特別喜歡,有點類似同好超話,同人創作欄目里面有很多大佬讀者的二次創作。我偶爾也會寫一下人物小段子上傳,會有很多讀者和我互動,交到了一些趣味相投的新朋友。”(受訪者2)
以提供內容為主要營業模式的讀書App開通了UGC模塊,通過閱讀書籍產生的情感聯結鼓勵讀者成為“作者”,寫評論、發書帖和進行同人創作。起點讀書更是在有聲書的板塊也開通了用戶創作的模塊,讀者用戶可以自己進行書籍演播、配音,成為業余“CV”(配音演員)。這些活動提高了讀者用戶的參與度,將無法捕捉的閱讀行為進行了變現。讀者用戶自發的情感互動、“為愛發電”(指某個團隊或者個人在收益較低或者沒有收益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做某事)都成了平臺渴望的數據。讀者用戶進行生產是社會化閱讀產生社交行為的核心環節,平臺不斷提出“協議”鼓勵讀者用戶生產內容,但其本意是獲得這些內容所代表的數據和利用自身渠道傳播所產生的流量。這些數據不僅為平臺注入活力,還可以成為吸引日活量的源頭,使數據“再生”數據,流量“再引”流量。讀者用戶的情感抒發變成了情感勞動,“為愛發電”更是平臺中一種強大的生產力,并且不求回報。不知不覺間讀者用戶吸引了更多用戶,創造了更多內容,更新了更多服務。
4 社會化閱讀App的使用反思
技術變革下的社會化閱讀環境中,數字行為所產生的數字勞動在所難免,從積極的角度看,數字勞動也促進了社會化閱讀App的發展,為讀者用戶帶來了技術福利和便利。因此,打造一個健康良好的數字讀書環境,保障社會化閱讀App中“數字勞工”的權益也成為當務之急,重中之重。
首先,切勿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去定義讀者用戶的數字行為,究竟是賦權還是勞動不能“一刀切”。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無論是享受權利還是付出勞動,讀者用戶都在讀書平臺上創造了社會價值。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的角度看,讀者的數字勞動需要更詳細具體的法律法規進行權利與義務層面的規范。UGC的創作產出涉及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書帖、長書評、同人創作的智慧成果的版權究竟歸屬平臺還是讀者用戶個人需要明確地界定。平臺中的部分內容來自集體智慧勞動的成果,如何構建合理的數字勞動成果共享機制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合理的共享機制或在一定程度上規避平臺壟斷公共勞動成果所造成的不公[5]。
其次,社會化閱讀App要培養穩定的、有黏性的讀者用戶群體需要更加注重用戶的體驗和權益。平臺長期過于明目張膽地“利用”用戶也會造成活力的流失,殺雞取卵的運營模式不可取。讀書平臺最終應是回歸閱讀本身,使前來獲取信息、知識的讀者們能夠獲得精神上的休閑和解放,而不只是利用設置規則、游戲來“督促”讀者進行閱讀。讀書平臺應當致力于給讀者用戶提供更具有排他性的價值,打造平臺自身的亮點,推出平臺差異化的產品線,策劃更多具有平臺風格特色的活動,形成平臺品牌效應,提供用戶通過免費方式無法獲得的使用價值。
最后,隨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被互聯網包圍、滲透,同時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用戶應當有意識地拯救自身于各種數字勞動的陷阱,避免成為“打白工”的“數字勞工”。讀者用戶在進行社會交往和產生情感聯結的過程中要警惕平臺規則中的不公和陷阱,盡量防止數字行為異化成為給平臺“做數據”。勞動是積極的,充滿創造性的,用戶在進行正常的數字勞動行為時,應當時刻本著創造價值、娛樂消遣或享受生活的初衷,切勿使自身陷入內耗的消極境地。
5 結語
閱讀的社會化和數字化是技術神話帶來的新圖景,閱讀App中的數字行為既是勞動也是賦權。數字經濟發展飛速、繁榮,但不規范、不平衡。我們需要回望閱讀中的社會化給讀者閱讀體驗帶來的改變和影響。數字App中的社會化閱讀究竟是參與還是勞動,需要我們更具體、更審慎地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