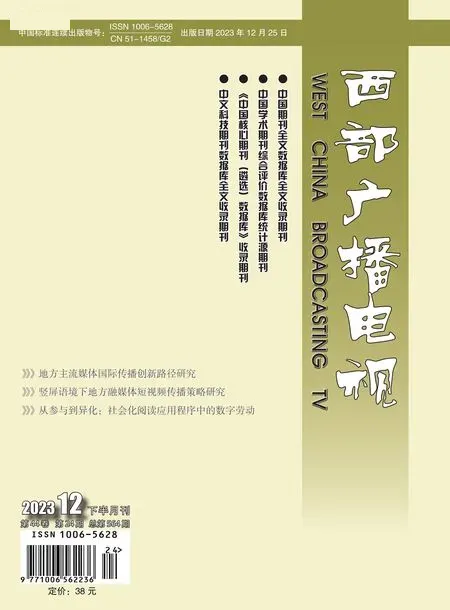《流浪地球》系列電影的聲音呈現研究
楊璐瑤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自《流浪地球》第一部上映以來,好評如潮,一躍成為當時影院中的佼佼者,獲得了口碑和票房雙豐收的優異成績,令中國電影業煥發出新生機。這部影片也被認為是中國科幻電影長期停滯發展后的一次跨越式的進步,成功開創了中國電影新篇章,成為公認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擁有了如此光環后,導演乘勝追擊,在2023年春節檔上映了《流浪地球2》,在觀眾已經提高了審美水平的基礎上仍然收獲了不錯的成績。這一系列電影,斬獲了金雞最佳故事獎、華鼎最佳影片獎等諸多大獎。除了故事和攝影受認可外,其電影聲音制作也十分出色,連續兩屆獲得了金雞最佳錄音獎,提名了多個電影節的最佳錄音、音樂、最佳音響效果等獎項。這樣的成就得益于當今數字化時代先進技術的支撐,同時離不開創作者對聲音特質、細節等的把控。本文將分析《流浪地球》系列電影中聲音的運用與呈現,探尋其可學之道,以期為之后的電影創作提供參考。
1 對聲音技術的得心運用
繼聲音和色彩之后,數字技術已成為第三大電影技術,它的發展更新了電影制作方式和理念。數字技術在聲音制作上的成熟,可以說為電影行業拓展了新的藝術創作空間。通過數字音頻技術,創作者可以創造出更具真實感和藝術性的聲音。例如,《流浪地球》系列電影中對聲音技術的運用使得聲音實現了數字化,增強了聲音的方位感、臨場感,真實地突出了原本聲音的質感,從而大大提升了影片聲音的質量,放大了聲音的魅力。
1.1 保證真實:同期錄音
同期聲(ADR)是指畫面拍攝和錄音同時進行,包括在同一時間中的對白聲及現場環境聲等[1]。隨著同期錄音技術的發展,電影創作者能夠更好地采集到清晰且充滿細節的聲音。
正如《流浪地球》的同期錄音師劉旭所說:“同期錄音的魅力在于能夠給觀眾帶來真實感和臨場感,達到視聽一致的藝術效果。”[2]22影片因頭盔這一特殊道具的使用增加了錄制難度,但導演仍堅持采用同期聲,原因有三:一是導演需要通過實時對白來評估演員的表現并提出指導意見;二是同期聲能成為后期配音的參考,確保聲音和畫面的同步性;三是能進一步增強觀眾真實聽覺體驗,使其更好地感受到演員的情緒和角色之間的互動。因此,《流浪地球》創建了智能系統來采集同期聲。錄音組采用COOPER 208D調音臺,配合主母線、輔助母線和監聽母線混合錄制,大大提高了拾音能力。除此之外,應用兩臺多軌噪聲門,提高了返送耳機中語音的清晰度,保證了演員、劇組之間的正常溝通交流,獲得了優質的同期錄音素材。正是由于創作團隊對先進設備的創新運用,才提高了同期錄音的質量,獲得了聲畫同步的影視原音,保證了聽覺上的真實感。
1.2 體驗沉浸:杜比全景聲
傳統環繞聲系統只能在固定的位置播放聲音,而杜比全景聲突破了傳統意義上5.1和7.1聲道的定義,其能結合影片的內容,呈現出動態的聲音效果,更真實地營造出空間感音效;再配合環境硬件設施,實現聲場上的包圍,呈現更多聲音細節,從而優化觀眾的視聽感受。
《流浪地球》系列電影的聲音呈現,在新技術的推動下展現出了更多的創新,如其第一次采用直接混錄全景聲。在以往的制作中,由于技術限制,需要先將音頻混錄成傳統的5.1環繞聲版本,完成后再重新進行杜比全景聲版本的混錄[2]21。這個過程耗時、耗力,還可能導致音色的損失。而隨著技術的改進,現今能夠直接混錄全景聲,一次性實現影片聲音的杜比全景聲效。杜比全景聲的引入使得電影聲音的制作變得更加靈活多樣,并且能給予觀眾身臨其境的聽覺體驗。比如《流浪地球》中韓朵朵在學校上課時突然停電被劉啟帶走時制造出的教室混亂的一段,聲音豐富多元且層次分明,極具真實感,同時有利于觀眾更好地進入敘事空間,沉浸式觀看影片。
1.3 精益求精:聲音AI修復技術
近年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術越來越發達,出現了眾多運用AI技術的事物,比如爆火的“AI修復老照片”,在勾起人們回憶的同時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AI修復圖像是指通過智能處理手段,憑借對于圖像的記憶和想象,將缺失的、模糊的或者噪聲嚴重的圖像恢復原貌的一項高級技術。但隨著行業的需要,AI修復的不僅僅是圖像,也逐漸應用于聲音方面。
《流浪地球2》的預告片中就率先使用了聲音AI修復技術。2022年,《流浪地球2》官博播出了第一版的預告,一經發布便引發了眾多網友的討論,其原因是第一版預告片中的李雪健老師聲帶受損,使得預告片中的原音非常不清晰。因此,導演借助先進音頻處理技術,即運用AI修復技術將第一版預告片中的聲音修正后重新發布,通過對比可以明顯發現在新的預告片中李雪健老師的咬字更加清晰,增強了影片宣傳效果。
2 對聲音風格的獨特打造
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出發,影片中恰當地運用聲音不僅會讓影片的藝術性增強,也會讓觀眾內心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因此,聲音設計團隊為《流浪地球》系列電影確定了不同于其他科幻題材電影的聲音表現方式,經過多次打磨最終決定打造一種樸素、自然、真實又溫暖的有東方特色的聲音風格。在聲音表現上,《流浪地球》強調聲感、知覺、想象、情感等元素,力圖讓觀眾從細節中感受到真實;同時,抓取到了情緒飽滿的“聲音焦點”;注重過渡流暢的空間轉換。
2.1 借助細節營造真實感
美國學者斯科特·布科特曼說:“在大多數科幻電影中,場景提供給觀眾的特權是能在某個敘事時刻去感受神奇華麗的未來世界,用令人眼花繚亂卻又熟悉的感受來表現出這座城市的獨一無二。”[3]145《流浪地球》作為中國具有代表性的硬科幻電影,它是建立在真實世界基礎上的虛構的未來世界,導演希望通過聲音營造更真實的觀影時空并增強科幻色彩。比如:聲效組通過選擇厚重感較強的聲音以突出行星發動機的機械感;設計組還通過多層次疊加聲音元素,在強調行星發動機聲音真實性的基礎上使聲音質感飽滿又充滿科幻感,也符合觀眾的心理邏輯和情感接受[4]。再如,在展現風雪交加的場景時,電影借助了立體聲拾取技術,創作出物體擊打玻璃的聲音,讓觀眾通過聲音能更直觀地感受當時的環境。這些對聲音的細節處理,都旨在給予觀眾更真實的觀影體驗。
2.2 情緒飽滿的聲音焦點
影視作品中的聲音都是經過選擇、提煉后被安排在合適的位置配合畫面表現的,因此影視聲音也有表情達意的功能。該影片的聲音設計總負責人王丹戎提出:“聲音是感官的同步,是導演對這個未來世界的聲音表達,聲音設計要融入電影的風格與故事,不能讓觀眾‘出戲’,更不能‘搶戲’。”[2]19因此,《流浪地球》在聲音創作方面要求既要有所表達,又要相對克制。影片遵循著“聲音焦點”的原則,將所有想要的聲音有層次地呈現出來。
早在創作《集結號》時,王丹戎就提出“聲音焦點”的理念,它指的是一種情感聚焦,體現在電影的許多聲音元素中。“聲音焦點”是流動的,這就需要對畫面中所有的聲音“做減法”,將最想讓觀眾感知到的聲音凸顯出來。比如:在《流浪地球》中劉培強撞擊木星的一場戲中,聲音設計團隊便對人物說完臺詞后的聲音做了減法處理,影片中沒有爆炸撞擊的音響,只有幾個鋼琴音;《流浪地球2》中核爆炸一段,影片去除了所有音樂和大部分音響,只留下人聲。用適當的“減法”將“聲音聚焦”的同時也能將情感聚焦,從而激發觀眾更多的想象。
2.3 過渡流暢的空間轉換
瑞典導演伯格曼曾經說過:“電影主要是節奏,它在段落的連接中呼吸。”節奏是電影藝術形式美的重要內容[3]147。要制造節奏,除了在構圖、場面調度等畫面上的設計下功夫外,聲音在電影中也能夠配合畫面營造出具有張力的節奏感,協助完成兩個場景之間的轉換,以實現過渡流暢的空間轉換,增強視聽觀感,同時能符合觀眾的接受心理,以此讓觀眾獲得更沉浸的觀影感受。
在《流浪地球》中韓朵朵向劉啟借衣服一段,動效聲與音樂融合,臺詞與鼓點相連,整體畫面與聲音的連接無縫自然。再比如《流浪地球2》中圖丫丫的數字生命卡上傳一段,影片中聲音與畫面的完美配合創造了一個數字世界的奇觀。此部分畫面快速更迭,在數據成功上傳后,小女孩的哼唱聲從短音轉為長音,象征圖丫丫的數字生命由2分鐘延長到了70年[5]。影片中這段聲音的運用不僅完成了空間的流暢過渡,也暗示了時間的變化,形成了鮮明的節奏張力。
3 對聲音價值的充分挖掘
電影符號學中電影的畫面和聲音都屬于影片表達的重要符號。但從之前的影片來看,聲音這一符號元素在電影中還處于從屬地位,聲音的功能和價值還未得到充分重視和運用[6]12。但《流浪地球》系列電影的聲音創作者不但注重打造極具風格的視聽效果,而且聲音中往往蘊含著特別的哲學思考和深刻寓意。他們利用聲音表意,將影片中人物的內心感受通過聲音傳達給觀眾,給觀眾帶來視覺和心靈的雙重影響。
3.1 用話語傳達希望主題
影片中的人聲可以體現發聲者的相關信息。人聲本身具有識別功能,話語和語氣都能凸顯影片人物的身份;而說話的腔調、力度、節奏等特征的變化也會折射出發聲者的心理活動。同時,人聲作為情緒的載體,會將片中的人物情緒傳達給觀眾,觀眾通過“移情效應”沉浸其中,領悟影片傳達的意義[6]13。
《流浪地球》中韓朵朵有一段關于“希望”的臺詞。她說:“昨天老師還問我們希望是什么?我不相信,但現在我相信希望是我們這個年代像鉆石一樣珍貴的東西,是我們回家唯一的方向。”她的話深深地了觸動了觀眾。韓朵朵的聲音逐漸從帶著哭腔的“我很害怕”,變成堅定地喊出“回來吧,救回我們的地球”,這一變化意味著韓朵朵成長了,影片也借此成功將“希望”的主題傳達給觀眾。
3.2 用音響構成聲音儀式
基于聲音理論,除人聲和音樂的一切聲音,都被稱作是音響。在電影文本中,音響除用作像似符號外,也能作為指示符號發揮其特定功能[6]13。音響與畫面搭配被觀眾理解后,當這個音響再次出現時就會成為一種具有指示性的“儀式感”聲音。影片中往往會突出這種“儀式感”聲音,以強化它的深層含義。
《流浪地球》中有一個象征著死亡的音響設計,即用救援隊成員所戴手表中發出的單頻率聲音象征生命跡象的殆盡。影片中有多個段落出現了這個設計,第一次出現在電梯井剛子、韓子昂救援一段后,第二次是組織里一個同事死亡時,第三次出現在王磊隊長犧牲之后。一聲聲單頻率長音減弱再慢慢消失,這一聲音在有人犧牲的時候便出現,成為電影塑造的一個特殊符號——象征犧牲的聲音符號,從而成為某種“儀式感”聲音。它的設計目的是當生命的痕跡消失時,在觀眾的腦海中能夠留下一個回憶點。
4 結語
“技術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藝術創作。”[3]149從《流浪地球》中可以看到,數字媒體與影視創作的融合實現了雙贏。《流浪地球》系列電影在聲音上的運用不僅為后續創作者提供了參考,也為其拓展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比如,從觀眾接受方面來考慮,首先要認識到視聽效果傳播差異性問題。在“多屏時代”,通常來說“小屏”是觀眾的第一觀影設備。在之后的聲音制作過程中,也應該考慮到有些觀眾不會進入影院觀影,因此如何通過小屏進行聲音的理想化傳播是一個挑戰。其次,隨著觀眾的主體性增強,電影聲音設計團隊應能夠根據觀眾喜好和需求進行個性化定制,給予觀眾更符合其喜好的音頻體驗;也可以借助人機交互等技術,讓觀眾通過語音指令、手勢控制等方式就可以與電影互動,給予其更豐富、良好的觀影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