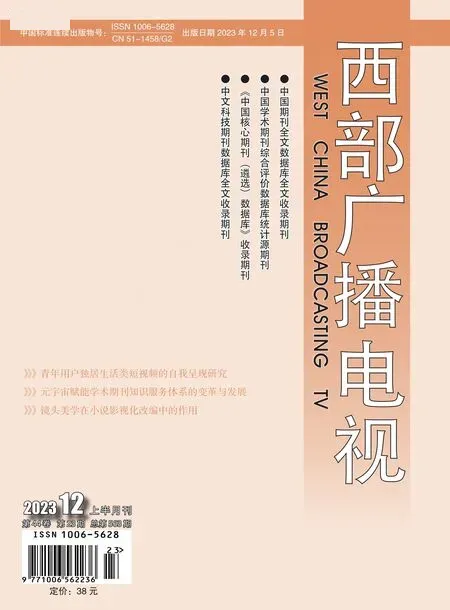電影《四海》的視聽語言與符號建構
何言知 巨傳友
(作者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藝術學院)
影片《四海》講述了南澳島上的青年吳仁耀與其心愛的女孩周歡頌在經歷了朋友的離世、追債人的緊逼與警察的抓捕后,不得不騎著摩托車奔赴廣州打拼,并遭遇一連串意外事件的故事。截至2023年11月,《四海》在豆瓣上的評分僅有5.3分,但這真的意味該片是韓寒的失敗之作嗎?本文從視聽語言與符號意象的建構兩方面解析該影片,并最終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1 視聽語言的精妙運用
電影藝術是利用視覺元素與聽覺元素兩方面交融配合來進行敘事的。為了恰當渲染出喜劇與悲劇色彩,以及表現出賽車場面的激烈,導演韓寒在視聽語言的運用上可謂精益求精,最終呈現出恰如其分的視聽風格。
1.1 大景別展示故事發生環境
“遠取其勢,近取其神”,這句話在電影藝術中同樣適用。韓寒在《四海》中酷愛使用大景別鏡頭,即全景、遠景、大遠景一類的景別鏡頭。大景別側重于“造勢”和“交代環境”兩種功能。在影片的前半段,南澳島的生活舒適愜意、風景秀麗,與廣州的快節奏生活、高樓林立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在大景別的襯托下不言而喻。
1.1.1 大全景呈現兩種人物狀態
影片開頭伴隨著吳仁耀的自我介紹,畫面是他騎著摩托車在表演,導演用固定機位的大全景拍攝他的側面,表現主人公在所處環境中的悠然自得,向觀眾展現了一個熱愛摩托車、充滿活力的少年形象。這與他離開家鄉去往廣州時導演所給到的一系列鏡頭,如大全景的航拍跟隨鏡頭(內容是男女主人公穿梭于各種路面時的背影),完全形成對比與反差,后者無處不突出二人的失意與顛沛流離。
1.1.2 遠景奠定積極與消極兩種情緒基調
在南澳島時,影片會采用遠景來表現積極的關系,無論是影片第6分鐘左右的吳仁耀與父親吳仁騰走在海邊時展現的父子關系,還是第25分鐘左右的男女主二人漫步海邊的戀人關系,影片呈現出的終究是祥和靜謐的情緒基調。然而鏡頭一轉來到廣州,大量的遠景鏡頭表現城市是座鋼鐵叢林,反映出現實世界的冰冷復雜,情緒基調是消極絕望的,似乎導演在暗示主人公在面對問題時的無力。
由此可見,大景別在片中所起作用舉足輕重,導演韓寒恰到好處地運用大景別為該片增色不少。
1.2 特殊攝影技法表現人物情緒
影片中使用到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拍攝手法,如升格鏡頭、航拍等。鏡頭語言的使用不是胡亂選擇,而是要為敘事服務,《四海》的每一種拍攝手法都是在韓寒慎重考慮之后所得的結果。
1.2.1 升格鏡頭突出賽車情結
片中多處用到升格鏡頭,也就是所謂的慢鏡頭。現實中曾經以賽車手為職業的韓寒熱衷于在影片中加入賽車元素,這種元素曾在導演韓寒的《飛馳人生》中以汽車拉力賽的形式得以體現,而在《四海》中則體現為摩托車,更符合吳仁耀小鎮青年的形象。但由于摩托車行駛時風馳電掣,正常幀率拍攝畫面通常會一閃而過,難以看清細節,此時就要用到升格鏡頭。在吳仁耀與秋哥的雙人競速中,秋哥在某個彎道完成對吳仁耀的反超,此時導演利用成段的升格鏡頭,向觀眾詳細地展現了這一過程,充分調動了觀眾緊張的心理。這里導演利用升格鏡頭特別強調了兩個細節:秋哥騎行時用手彈開飛來的蜜蜂;秋哥頭盔與路邊的墻體摩擦出火花。這些足以將該對手的強大刻畫得淋漓盡致,觀眾只能在吳仁耀詫異的表情中,共鳴那份絕望。
1.2.2 滑動變焦展現人物焦慮內心
滑動變焦又稱為希區柯克式變焦,其原理是機位前推時縮短鏡頭焦距,或機位后拉時增長鏡頭焦距。創作者往往使用滑動變焦鏡頭以具象的畫面來體現抽象的環境氛圍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劇中角色的一種心理認知,也是導演對觀眾的影像明示[1]。當摩托車在廣州塔下被拉走后,男女主二人呆站在原地,且在畫面中景別不發生改變,而身后的高樓大廈卻像逐漸蘇醒的龐然怪物,在畫面中的占比呈線性變大,向他們逼近,仿佛要將二人吞沒。導演就是運用了滑動變焦,展現了他們在大城市壓迫中的焦慮與無力之感,表達了對男女主二人的憐憫之情,可謂深刻而又含蓄。
1.2.3 航拍長鏡頭凸顯主人公孤立無援
片中充斥著航拍鏡頭,但最值得思索的當屬男主離開父親家門口后的那一個航拍長鏡頭。男主滿懷期待來到父親的住所,然而意外發現父親早已成家,不知何去何從的他來到一片四面都被老居民樓包圍的露天場地。他在航拍畫面中活像漢字“囚”中的“人”,之后鏡頭螺旋上升,模擬人物此時暈眩迷離的狀態。隨著鏡頭的持續后拉,男主消失在畫面中,鏡頭轉向大片的破敗居民樓,似乎在暗示像男主這樣支離破碎、艱難生存的家庭只是不計其數的案例中的一個。導演僅用這一個鏡頭,就強化了男主的孤立無援與手足無措,在敘事上也進一步將他逼向絕境,進而引出飛躍珠江的影片高潮。
上述的攝影技法逐步加深主人公的困境,對于塑造人物和推動劇情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韓寒利用自己對于視覺語言的獨到理解完成了抽象的文字語言到具象的電影語言的轉化。
1.3 環境音響塑造人物內心活動
在影視作品中,環境音響除了再現畫面空間的真實性,還能表現超現實的心理感受。在表現超現實的心理感受時,可通過環境音響設計來模仿出人的主觀聽覺感受[2]。影片《四海》運用諸多手段表現人物內心活動,其中環境音響功不可沒。
1.3.1 消失的車鳴與浮現的海浪聲表達愛意
男女主與車隊一行人夜間騎車穿梭隧道時,周歡歌發起話題,讓大家依次許愿。“我想帶歡頌去一個地方抓螃蟹……”,吳仁耀緩緩道出自己的心愿。原本回蕩在隧道中的摩托車聲淡出直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陣陣海浪聲,吳仁耀的真情流露之聲也被導演刻意放大,這里的音響設計渾然天成,且具有強烈的抒情意味。消失的摩托車聲與增強的人聲模擬了在場其他人集中精神傾聽他講話的狀態,對于無關緊要的聲音自然會忽略,而浮現的海浪聲則是他腦海中的聲音,是他渴望帶歡頌去抓螃蟹的心理刻畫,凸顯了吳仁耀的深情與專一。
1.3.2 火車的嘈雜聲響打破和諧音律
在廣州,男女主共有三次離別情節。前兩次的離別在火車的嘈雜行駛聲中落幕,第一次的相互打氣和第二次的送項鏈作為禮物,讓二人暫時從壓力與苦悶中抽離,短暫停留在夢幻般的甜蜜愛情中。然而是夢終究要被打破,兩次離別中,火車駛過的聲響都被導演刻意放大,壓倒性地蓋過了人聲,將原本和諧的氛圍摧毀。火車聲可以理解為二人心理活動的外化,這種心理既是對于分別的恐懼,又是對不得不離開彼此,繼續面對冰冷現實的焦慮與不安。而第三次在餐廳的離別作為影片高潮——飛躍珠江的序幕,男主眼看勝利近在咫尺,女主也與竊賊約定好,盜取摩托車作為男主的禮物,整體情緒氛圍是積極向上的,因此導演選擇平淡收場,觀眾也在音響設計的潛移默化中相信電影的結局是美好的。然而,這就是韓寒的高明之處,出乎意料的悲劇性結局令人不勝唏噓,更能謳歌二人相互付出的偉大愛情。
環境音響的設計在影視創作或評論中往往易被忽視,導演韓寒恰好抓住了這些細節,完善了《四海》聽覺語言的豐富度,人物內心活動在這些巧妙的設計中具象化地流露出來。
2 符號的建構及意義生成
電影符號學的概念由克里斯蒂安·麥茨提出,該理論認為電影是一種以語言、文字、音符、色彩、實物、場景、畫面、人物及其服飾、表情和舉止等基本構件來傳遞更深層次的信息,它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是一種綜合符號系統[3]。
電影的制作與賞析就是導演對符號進行編碼與觀眾對符號進行解碼的過程。《四海》中建構的意象符號有很多,這些符號暗含了韓寒對影片人物命運的悲憫同情以及對“成長”這一主題的深刻探討。
2.1 人物符號
韓寒執迷于刻畫小鎮青年群體,因為小鎮青年在現代化進程中,自身的故步自封與新時代的日新月異形成了激烈的矛盾沖突,在《四海》中,這種矛盾體現在任何一個角色上。
2.1.1 吳仁耀
吳仁耀具有兩重符號意義——“留守兒童”與“理想主義者”。一方面,他年幼喪母,父親常年在外,只有奶奶與他相依為命,吳仁耀代表著典型的“留守兒童”形象。現實中,由于家庭勞動力缺少或在當地缺乏就業機會,有些父母會選擇去大城市打拼,缺乏對孩子基本的關懷與交流,孩子的心理問題就愈發明顯。片中的吳仁耀也因此不善言辭與不解風情,當周歡頌多次向他拋出諸如“我為什么會陷進去呢?”“小時候學過電子琴”等話題時,吳仁耀卻一次次潑冷水,使話題瞬間終結,之后到廣州尋求Showta哥的幫助,也被無情嘲諷。影片塑造的問題少年吳仁耀,既是滿足敘事方面的需求,也是表達導演對于無數小鎮里的“留守兒童”的關注與同情。另一方面,他又象征著每一個“理想主義者”,正如李銀河的影評,“盡管生活的真相是黯淡的、艱辛的、泥土般混沌的,但是電影中人物依然熱愛生活……”。吳仁耀竭盡所能為女友和兄弟還債,他的執著與永不言棄的精神,或許正是影片想要呼吁與宣揚的。
2.1.2 周歡頌
女主周歡頌代表著“理想”與“獨立”。首先是“理想”,在情感線索的布局上,相對于中途斷掉的父子親情線與兄弟情誼線,吳仁耀對周歡頌示愛與追求的愛情線貫穿影片始終,并且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核心動力。周歡頌是“理想”的象征,相當于《羅拉快跑》中的10萬馬克,是主人公傾盡所有想要得到的。然而當她意外死亡,吳仁耀形單影只回到家鄉時,一個特寫鏡頭展現了摩托車上的“頌”字,證明她始終活在吳仁耀的心中,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滅的追求,身雖死,但卻化作精神與信念在吳仁耀的腦海中流淌。其次是“獨立”,許多傳統影視作品習慣于將女性角色塑造成工具人,供男性角色進行爭奪與凝視,遇到危機也只是充當被英雄解救的形象。周歡頌卻是獨立自強的女性形象,她不愿始終與吳仁耀捆綁在一起,而是主動提出各自工作,她的身影奔波于規模各異的用人單位,屢屢面對面試官的刁難與失敗的結果,但這些都沒能動搖她心中對獨立的堅持,即便最終選擇做回小小的服務生,也始終沒向任何人吐過苦水,正映射了現實中女性的覺醒與獨立意識。
2.2 物件符號
片中有大量的物件,這些物件承載著暗示人物命運與折射人生哲理的功能。
2.2.1 船錨
船錨這個意象符號在影片中出現頻繁,指代著“命運”。這里的船錨特指男主車隊所在廢棄船(原本作為車隊基地,后改為夜店)船頭懸掛的船錨。船錨與周歡歌有著密切聯系,首先從“車隊命運”角度看,最開始男主來到車隊基地,導演特地給了一個特寫鏡頭展示船錨在廢棄船頭搖搖晃晃,船錨是鏡頭中唯一的運動元素,似乎充滿了活力,這是船錨第一次出現,與吳仁耀初入車隊形成一種關聯,象征著車隊的壯大。然而當最終吳仁耀被秋哥超車,車隊的生命力被終結,導演毫無征兆地在敘事中插入看似無關的船錨落地的鏡頭,這實際上是表明車隊在不言中自行解散,代表的是信仰的崩塌。而從“人物命運”角度看,這更多代表著船錨所有者——周歡歌的生命進程。從起初的活力四射、充滿野心到殞命海洋,導演使用船錨這一意象符號的從隨風晃蕩到砰的一聲落到地上,含蓄地暗示著人物生命的轉瞬即逝與命運的難以預料。
2.2.2 巨輪
巨輪象征著那些“不可抗拒的意外”。無論電影還是現實,總有人抱怨命運的不公,因為當意外來臨,往往會傷及無辜。這些意外既是《三塊廣告牌》中威洛比警長的突然自殺,也是《調音師》中的阿卡什被意外卷入兇殺案。當那艘濃霧中的巨輪難以阻擋地沖向周歡歌時,意味著兄弟吳仁耀的還債之旅即將開啟,連同妹妹周歡頌也受到牽連。一切都是毫無預兆卻又合乎情理,畢竟目睹生命的猝然消失與各類飛來橫禍都是人生旋律中的變化的節奏。導演借用巨輪這一意象,闡明了該道理,背后蘊含著的是珍惜生命、活在當下的深刻哲思。巨輪在敘事結構方面又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影片前半段營造的喜劇色彩在巨輪出現時畫上了句號,片中人物命運都因該意外而發生改變,悲劇底色逐漸浮現。
2.3 場景符號
2.3.1 故鄉“南澳島”
設定一個回不去的家鄉是電影的常用敘事手段,家鄉代表著的是“夢想”。主人公強烈的回家欲望與現實中重重的困難形成激烈沖突,主人公需要歷經挫折才能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就如同魯濱遜一樣無奈與掙扎并存。就像影片宣傳海報中提及的“向前是遠方,身后是故鄉”,家鄉與遠方不能兼得。吳仁耀想要幫心愛的女孩擺脫困境驅車去往遠方的廣州,離開家鄉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帶歡頌回到家鄉一起抓螃蟹的夢想,正如結局表現的那樣。《四海》里有了周歡頌,有了這個很多地方都很像“泥巴”的女孩,韓寒電影的故鄉才變得可以被描述、被傾聽,變得真實可信起來[4]。
2.3.2 夢碎“廣州塔”
廣州塔代表著“錯誤的方向”,現實中我們勞勞碌碌,相信朝著堅定的目標前進就能獲得成功,當面對問題,我們擁有諸多選擇,但難免走錯路、走遠路,直至頭撞南墻才知回頭。吳仁耀為了尋求Showta哥的幫助,根據其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廣州塔,然而現實卻讓他們大跌眼鏡,在南澳島包裝為成功人士的Showta哥僅僅是個修塔工人,這是男女主二人到廣州遭受的第一個打擊,也是更多不幸的開端,就像蝴蝶效應一般,緊接著的是摩托車被扣押、工作難尋等。錯誤的方向在所難免,重要的是及時調整方向,把握好人生的船舵,男女主迅速意識到這一點,并開啟了自我救贖之路。
2.3.3 拼搏“廣州”
《四海》以周歡歌的死亡為界,將南澳島與廣州編碼為表征“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的二元對立空間[5]。廣州代表“舒適圈之外的未知”,南澳島對于片中人物而言是個再熟悉不過的地方,那里的文化、習俗等對他們而言了如指掌,相對于這樣的舒適圈,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廣州顯得那樣冰冷。跳出舒適圈,前方充斥著迷霧與未知,如同剛到新城市上大學的學生,難免時刻牽掛著家鄉,想要逃離陌生的處境。片中男女主獨立、堅毅的品質最終綻放出光芒,支撐著他們完成了還債的愿望,雖然女主意外離世,但吳仁耀帶著她的精神和禮物(摩托車)回到了家鄉,這樣的結局設定未必是遺憾的,至少影片認可了男女主這股與命運抗爭、與未知較量的勇氣。
3 結語
《四海》延續了韓寒一貫的個人化風格,深刻洞見人性的同時還能詮釋生命的崇高、理想的追求等議題,尤其在拍攝手法、聲音設計、意象符號建構等方面表現出色。從這些角度來看,《四海》絕對是不折不扣的合格之作。只可惜在部分劇情設計上脫離實際,有些臺詞編寫上較為書面化,外加宣發策略上的偏差,導致電影口碑、票房雙失利,倘若導演韓寒賡續視聽語言、意象符號運用等特色,劇本打磨更加細致,相信他的第五部影片一定能成為市場寵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