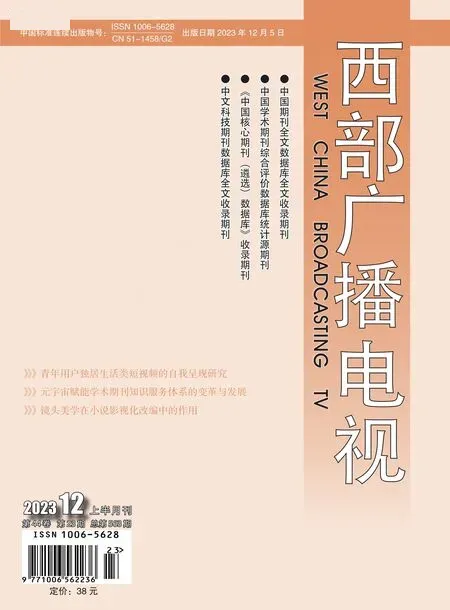再讀巴贊
——關于紀實主義電影美學的再思考
胡芷語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2022年9月13日,“法國新浪潮運動中影響力最大、生涯變化最大也最特立獨行的怪杰”[1]——戈達爾逝世。他的離世不僅引發世人對其電影作品的集體緬懷,還掀起了世界范圍內對以戈達爾、特呂弗等人為代表的新浪潮旗手們的再關注與再思考。其中,作為法國新浪潮電影人的精神導師的巴贊,雖未能親歷新浪潮運動,但他所提倡的電影紀實美學理論,以及傳揚這套理論的主要媒介陣地《電影手冊》,已構筑成新浪潮運動的精神堡壘。
據巴贊的觀點,1940年至1950年間電影史上具有辯證意義的發展在于三個意義重大的新起點:一是找到了無聲電影與有聲電影在寫實主義傳統上的聯系;二是找到了復雜的小說形式與電影的互動關系;三是出現了一種新的電影流派——意大利新現實主義[2]。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的巴贊的《電影是什么?》從四卷本中選出主要的文章,縮編成一冊[3]16。誠如譯者崔君衍所言,巴贊考察了電影語言逐漸向真實性發展的美學歷程,確立了電影現實主義理論的三大支柱:攝影影像的本體論、電影起源的心理學和電影語言的進化觀[3]5。因而巴贊的電影史論與批評并非單一的、碎片化的觀點拼貼,它包含縱向的電影發展史和橫向的(電影與小說、戲劇、繪畫的比較)電影本體論,在時空縱橫之間,立體地建構起紀實主義的電影美學體系。
本文亦將以無聲電影與有聲電影、小說與電影、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與巴贊的紀實主義電影美學這三組關系為基點,對巴贊的紀實主義美學理論體系進行再解讀與再思考。
1 默片與聲片的紀實主義承續
在討論巴贊關于默片與聲片的紀實主義承續關系問題之前,需要特別探討一下巴贊對電影與現實關系問題的認識,這兩大問題也是《電影是什么?》的關注重點之一。
在諸多有關電影與現實的關系的論述中,愛因漢姆與巴贊之間針鋒相對的觀點最為鮮明而迥異。愛因漢姆強調現實與影像之間的差異性,并將此作為藝術的必要條件,他在《電影作為藝術》(修正稿)一書中所摘錄的“完整的電影”一節中提到,黑白攝影把一切東西都變成深淺不一的灰色,因而構成了一種藝術手段,它同自然有著足夠的差別和獨立性[4]。在愛因漢姆看來,由于技術的發展,電影對自然的機械化模仿發展到了一種極端狀態,聲音的出現就是朝著這個極端的方向邁出的明顯一步。顯然他對無聲電影的評判較為偏執,并且在判別電影藝術手段的特點時,他將現實作為電影藝術的比較對象,因而無法闡明電影的特性。而巴贊在《“完整電影”的神話》一文中表示,那種認為無聲電影原本完美無缺而聲音與色彩的真實使其愈益退化的看法顯然是荒謬的[3]17。但不可否認的是,愛因漢姆認識到了藝術作品中的表現物與其現實中的原型在物理性質上是無法同一的。這就與巴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巴贊在《攝影影像的本體論》一文中堅稱,影像與被攝物本身是同一的,唯有攝影機鏡頭拍下的客體影像能夠滿足我們的潛意識提出的再現原物的需要,但已擺脫了時間流逝的影響,然而它畢竟產生于被攝物的本體,影像就是這件被攝物[3]6-8。
愛因漢姆對影像與現實具有物理性質的差異有著清醒的認識,而對藝術形象的內容與現實事件的內容之間的矛盾關系存在認識上的不足。巴贊相反,他將影像與被攝物在物理性質上混為一談,卻又清醒地認識到電影技術的發展(比如聲音的出現)所帶來的是一種風格的成熟,而并非一種風格的退化。二人的理論交匯點集中體現在對無聲電影和有聲電影的相關論述中。
形式主義與現實主義這兩種潮流皆以進步的技術目的論作為它們的識別標志[5]。愛因漢姆堅持形式主義美學原則,因而他對有聲電影和電影技術的進步持否定態度。反觀巴贊,在《電影語言的演進》一文中,他運用地理學上的“河流平衡線狀態”[3]65,形象地闡明了有聲電影所帶來的電影技術的革新并未毀掉電影藝術,反而使電影語言完成了自我進化,使電影在形式與內容上進入一種完美平衡的新狀態。
除此以外,巴贊在堅持景深鏡頭深刻影響電影語言演進的基礎之上,并未全然否定蒙太奇,而是辯證地分出二者之間的主次關系,認為蒙太奇可以作為敘事的功能性輔助,但絕非電影的主要敘事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巴贊特意提及觀眾與影像之間的知性關系,尤其強調蒙太奇會加深觀眾的思維惰性,從而不利于觀影互動。而景深鏡頭要求觀眾更積極思考,甚至要求他們積極參與場景調度。倘若采用分析性蒙太奇,觀眾則只需跟著向導,隨著導演注意力的轉移而轉移自己的注意力[3]70。觀眾需要自己從長鏡頭和景深鏡頭中找尋潛在的意義,而不是依賴蒙太奇所產生的關聯性暗示,接受早已選定的意義灌輸。這樣一來,觀眾的觀影獨立性便會被蒙太奇剝奪,從而喪失雙向互動所必要的完整知情權。
通過一系列詳細論述,巴贊循序漸進地闡明了紀實主義美學的特征,以及無聲電影與有聲電影在紀實主義美學傳統上的承續關系。
2 小說與電影的紀實主義式互動
除了探討小說與電影的互動關系,巴贊也關注到了戲劇、繪畫與電影之間的關系。巴贊似乎對于“平衡”二字情有獨鐘,他不僅強調技術帶來的形式更新與電影的內容、主題之間的平衡,也強調小說原著與電影化改編之間的平衡。而統領平衡關系的前提,便是遵循紀實主義的美學原則。既然電影與戲劇、小說的聯結不可避免,不如借電影發現新的戲劇真實和新的文學真實。巴贊曾對電影改編做過如下辯護:舞臺戲劇片的成功對戲劇有利,小說搬上銀幕對文學有利,根本談不上什么競爭和替代,只是增添了自文藝復興以來各門藝術漸漸丟失的一個新方面[3]100。
因此,對于電影改編戲劇,以《哈姆雷特》為例,巴贊僅強調電影在保持自信(自如運用特有的表現手段)的同時忠實于原著即可,因為戲劇真實不僅可以通過舞臺真實得以體現,換一種介質,電影也可以體現戲劇真實。舞臺是戲劇的載體,電影也可以是戲劇的載體,舞臺服務于戲劇,這是傳統的形式,而一旦通過電影化改編,電影也能成為服務于戲劇的新形式。
而對于電影改編小說,以《鄉村牧師日記》為例,巴贊認為電影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時,既尊重了小說原有的文學結構(不僅是故事,也是文本),又完成了跨媒介的形式合成的——畫面的寫實性與小說的文學性相結合。巴贊高度評價導演布萊松的改編,認為在整個法國電影的所有經典場景中,能比《鄉村牧師日記》中牧師還給伯爵夫人頸飾那一場景給人以更強烈的美感的時刻恐怕不多[3]114。因為這種無法用文字呈現的多義性與美感,甚至根本不是靠演員的表演,也不靠對話。如果想要呈現牧師與一個絕望靈魂的內在交鋒,單靠對話是無法言盡的。對話在此處的特殊功能是引出沉默,而沉默才是真正的對話。這里的沉默恰好充當了靈魂交鋒的無形載體,達到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美學境界。因此,巴贊所說的保留真實性,可能并不僅僅是指保留對原著文本所謂的忠實,更多是一種意義真實和風格真實,因為這種沉默往往是多義性的,不易被定義的,而這種多義性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個角落,任何一種對這段沉默的解讀都是被允許的。而這種開放的多義性,本身就是小說原著與電影改編雙重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性的體現。
在展開對小說與電影互動關系的延伸性探討時,巴贊通過對美國經典西部片和非典型的西部片在類型問題上的分析,建立起了新的討論維度。誠然,對于經典西部片的歷史真實性,巴贊給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時也指出西部片的深層現實就是神話,它由這一類型的某些固定符號和模式共同搭建,如極端的戰斗情境、夸張的情節、被英雄化了的主人公等,這些往往都是稚拙和失真的代名詞。非典型的西部片和經典西部片的差異在于:非典型西部片對經典西部片的一些既定范式采取一定程度的改良。例如:《關山飛渡》的范式改良就體現在,在特定人物形象塑造上,一定程度弱化了其特定身份所自帶的刻板印象。《關山飛渡》和小說《羊脂球》中都有類似風塵女子救眾人于水火的橋段,二者最大的不同是《關山飛渡》中妓女的英勇反抗換來了同行人的尊重,這里有雙重意義的范式革新:一是這些同行人并未因其妓女的身份而一直對其抱有刻板印象,相反,同行人對妓女的態度是隨著妓女的實際行為而發生著實際改變的;二是在傳統文藝作品中,妓女的悲慘宿命是屢見不鮮的(無論電影還是小說,抑或是以小說為藍本所改編的電影,如《羊脂球》《茶花女》等)。而在《關山飛渡》中,這位妓女的命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既定敘事范式對妓女悲苦命運的固化設置。
3 新現實主義電影與紀實主義美學的聯結
巴贊也相當關注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與紀實主義電影美學。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電影中寫實主義傳統最具代表性的繼承與發展。二戰后技術主義電影在歐洲逐漸衰落,影片的制作成本普遍降低,于是新現實主義創作理念應運而生。實景拍攝和啟用非專業演員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成本問題的考慮,因而巴贊所譽的這種類似紀錄片風格的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并非全然出自創作者的藝術自覺,應是主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
能夠體現新現實主義電影與巴贊的紀實主義美學之間的關聯的,應該是其道德主張。巴贊在《電影現實主義和解放時期的意大利流派》一文中明確指出,在這個世界中,唯有意大利電影在它所描寫的時代中拯救著一種革命的人道主義。就內容而言,我愿意把當代意大利影片中的人道主義視為影片最重要的價值[3]253-254,其次是本體論立場,而后才是美學立場。因為巴贊始終認為,像照方配藥那樣照抄新現實主義的技巧特征,未必就是新現實主義。
然而,如果拋棄了新現實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而照貓畫虎,在形式上保留其自然照明、嚴格的時間順序敘事法、非職業演員的日常化表演、實景拍攝等表征,就是拙劣的模仿。反之,如果僅將新現實主義看作一種精神,又未免限于空泛。
誠然,新現實主義的電影美學集人道主義的道德主張、生活的日常性、瑣碎性高于戲劇性的本體論立場和紀實主義的影像風格于一體。然而,如果我們將《偷自行車的人》與《溫別爾托·D》這兩部象征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始與終的電影并置相較,那么在同樣都滿足了人道主義關懷的精神特質(一個聚焦于家庭重擔巨大的失業者,一個聚焦于老無所依的退休者)、紀實主義的影像風格的條件基礎上,《溫別爾托·D》弱化了戲劇性,強化了日常性。真正將溫別爾托·D這個人物的困境嵌入更接近真實生活的日常碎片中。從溫別爾托·D為了完整支付房租而變賣財產,到生病住院時小狗不見,再到小狗出現而自己又無家可歸,最后只能為小狗另謀他主,這一系列內容并沒有明顯的主次之分(尤其是在影片開頭,溫別爾托·D作為主角,并沒有在一眾退休抗議人群中獲得畫面與鏡頭的特別凸顯),也沒有明顯的急緩之分(敘事節奏平緩似流水),這種有情節而情節弱、有戲劇性而戲劇性淡的敘事方式似乎顛覆了觀眾的傳統口味和觀影興致。
如果說《溫別爾托·D》與《偷自行車的人》在紀實性風格的情感表達上有什么不同,那也許是一種在紀實性敘事過程中,由情感傳遞介質的變化而引起的情感強度和類型的變化。《偷自行車的人》高濃度傳遞情感的片段就是兒子布魯諾目睹父親安東偷車而受辱的時刻,而負責把這種高強度痛苦情緒傳遞給觀眾的載體就是布魯諾復雜的眼神。這里的情感傳遞介質是人。《溫別爾托·D》則主要通過小狗的可憐來呼應老人的可憐。例如,在小狗弗里科銜著主人溫別爾托·D的禮帽行揖乞討的片段中,是小狗充當情感傳遞的介質,來牽動觀眾的觀影情緒。從布魯諾的眼神到小狗弗里科的肢體動作,情感所依附的介質不同,觀眾感受的情感類型和強度也就不同:布魯諾的眼神所傳遞出的情感是高濃度的痛苦,而小狗的肢體表演片段所傳遞出的情感是無止境的哀愁。由痛苦所引起的刺激性情緒更為強烈,而由哀愁所引起的刺激性情緒則更為綿密,痛苦和哀愁在觀眾的觀影過程中所傳遞的直觀情緒和與之相對應的敘事鏡頭所顯現出的美學風格是不同的。
正如美國學者彼得·邦達內拉所言,如果電影史學家能從更為寬泛的視角看待這個主題,那么也許就可以避免對戰后電影的現實主義進行過度強調了;任何關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討論都必須足夠寬泛,能夠容納各種各樣的電影風格、主題和態度[6]。這也不失為一種對巴贊理論研究的補充性觀點。
4 結語
巴贊的紀實主義電影美學理論關乎復雜的美學觀念、史學觀念、本體論信念,在這套理論體系中,他詳盡探討了電影與現實、電影與其他藝術形式、電影理論與電影史之間的關系,建立了自己的電影哲學坐標。他的理論思想在法國新浪潮運動中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在法國新浪潮之后,德國新電影運動又接過西方電影中寫實主義傳統的大旗,其整體的創作風貌與新浪潮所具有的知性傾向如出一轍。新浪潮巨匠戈達爾的離世,仿佛提醒我們在重新關注曾掀起滔天巨浪的新浪潮運動的同時,還應該回溯新浪潮發端的精神源泉,對巴贊及其相關理論進行新時代語境下的再解讀與再思考,因為巴贊不僅對他所在的時代產生了影響,也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