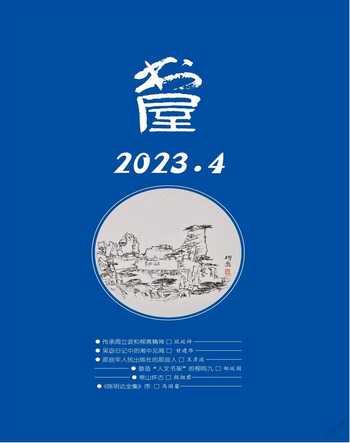最早譯介康德哲學的王國維
胡月梅
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前所長陳樂民研究西方哲學,喜歡康德,他說:“中國最早知道康德的是誰?有人說是梁啟超。我想王國維也可以算一個。”此語確然,王國維不僅是晚清最早知道康德的學者之一,也是非常景仰康德的一位學者。
王國維,浙江海寧人,早年研究哲學與美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后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他平生學無專師,自辟戶牖,成就卓越,貢獻突出,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古文字學等方面均有深詣和創新,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了廣博精深的學術遺產,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1927年6月2日,王國維于頤和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
王國維是從什么時候對康德哲學產生興趣的?據劉克蘇《失行孤雁:王國維別傳》記載,王國維在1898年進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之后,結識該社日文教師藤田豐八和田岡,“此二人原是搞哲學的,王國維曾經見過田岡君文集,其中引用了康德、叔本華的哲學,這使他非常感興趣,不過苦于不懂西文,自認為終生沒法讀康德和叔本華的原著了,于是決定學習英文”。又記,1901年夏天,王國維翻譯十九世紀德國物理學家赫爾姆霍茨的《勢力不滅論》(今通稱《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英文本,“由于《勢力不滅論》涉及牛頓古典力學、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學說’,這就成為青年王國維攻讀從康德開始的德國古典哲學的先導”。
1906年3月,王國維為十八世紀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康德專門立傳——《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王譯“康德”為“汗德”),其言:“然自汗德建設批判學派以來,使歐洲十九世紀之思潮為之震蕩奔騰,邪說卮言一時盡熄……故汗德之于他哲學家,譬之于水則海,而他人河也;譬之于木則干,而他人枝也。”從中可見王國維對康德評價之高。
至于為何要給康德立傳,王國維言:“夫人于偉人杰士,景仰之情殷,則于一言一行之微,以知之為快,不憚征引而表彰之。汗德傳之作,烏可以已乎?”然則康德其人身世形貌在人群中實在不起眼,可謂一生平淡且乏味。
康德于1724年出生于德國小鎮哥尼斯堡,出身貧寒,童年母親去世,二十二歲父親去世,兄弟姐妹多,家庭經濟狀況使他在大學期間就教授私人以獲取學費,大學畢業后做了九年的家庭老師,三十二歲重返大學做講師。生活古板克制,井井有條,一生除了一次短暫的旅游,沒有離開過家鄉。他身高只有一米五七,沒有結婚生子。他為自己制定了一套嚴格的生活作息表,以致小鎮上的市民將康德出門散步時間作為鐘點看待。王國維《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記:“方其為大學教授之時,天未明而興,以二小時讀書,二小時著講義,既畢仍讀書,午則食于肆。不論晴雨,食后必運動一小時,然后以二小時準備次日講義,以余時雜讀各書。入夜九時而寢。三十年間,無日不如是。”又記:“終其身,足未越凱尼格斯堡(今譯哥尼斯堡)一步,受普通教育于是,受高等教育亦于是,為大學教授于是。自幼至老死,與書籍共起居,未嘗一馳心于學問之外,宜其無甚事跡授后世史家以紀載之便也。”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不起眼的人物,卻有著驚人的頭腦和強大的生命力量。他大器晚成,五十七歲完成《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一鳴驚人,給當時的哲學界帶來一場革命。隨后的十多年又相繼發表《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引領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批判哲學時代。
康德的“三大批判”超越了以往哲學家以純粹的邏輯推理和論證方法,而以人的終極關懷為哲學的追問,把哲學當作一項道德事業,回答了人可以知道什么、應該做什么、可以期望什么的問題,開啟了哲學探索更高的維度,也體現了哲學家溫暖的道德情懷。王國維在《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中評述:“而《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等,則今世海內哲學家所相與奉為寶典也。”
康德哲學博大精深,論證極其晦澀,王國維對康德哲學下了苦功,他從二十二歲到三十歲,曾經四次讀康德。他第一次讀《純粹理性批判》,啃不動,幾讀幾輟,后來發現叔本華的知識可以通向康德,于是便讀了整整兩年叔本華,之后再返回康德,才覺比較順了。他讀《純粹理性批判》后,寫了一篇撮述要義的長文《汗德知識論》,分為十點加以釋義,對《純粹理性批判》作了提綱式的梳理,是經過苦讀后消化了的“讀書筆記”。1907年,王國維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一”中寫道:“次年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志與表象之世界》一書。叔氏之書,思精而筆銳。是歲前后讀二過,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則論》《自然中之意志論》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與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學之批評》一篇,為通汗德哲學關鍵。至二十九歲,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窒礙矣。嗣是,于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1907)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
事實上,自1904年王國維主編《教育世界》以后,康德便成為該刊出現頻率最高的西方學人,關于他的生平、思想、學說曾被反復譯介。而尤為王國維推崇的,更在康德之“德”。他說:“古今學者,其行為不檢,往往而有。伯庚(今譯培根)以得賂見罪。盧騷(今譯盧梭)幼竊物,中年有‘浪人’之名。論者重其言,未嘗不心非其人也,若夫言與人并足重,為百世之下所敬慕稱道者,于汗德見之矣。”
王國維對康德敬佩不已,又作《汗德像贊》四言詩以禮贊表彰,儼然呈現了一位峨冠大袍的中國化圣人。詩云:
人之最靈,厥維天官;外以接物,內用反觀。
小知閑閑,敝帚是享;群言淆亂,孰正其枉。
大疑潭潭,是糞是除;中道而返,喪其故居。
篤生哲人,凱尼之堡;息彼眾喙,示我大道。
觀外于空,觀內于時;諸果粲然,厥因之隨。
凡此數者,知物之式;存于能知,不存于物。
匪言之艱,證之維艱;云霾解駁,秋山巉巉。
赤日中天,燭彼窮陰;丹鳳在霄,百鳥皆瘖。
谷可如陵,山可為藪;萬歲千秋,公名不朽。
這首《汗德像贊》用中國古奧的頌贊詩體,運用不少“古典”和“洋典”闡述晦澀艱深的康德哲學,顯得深奧難懂。但我們從“群言淆亂,孰正其枉”“息彼眾喙,示我大道”“萬歲千秋,公名不朽”等語句中,仍可看出王國維對康德的推崇。
可惜,正如蔡元培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中說:“王氏那時候熱心哲學到這個地步。但是他不久就轉到古物學、美術史的研究;在《自序》中所說‘研究汗德’的結果,嗣后竟沒有報告,也沒有發表關于哲學的文辭了。”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王國維在青年時期對康德等西方哲學家的攻讀,是這位后來成為學貫中西的學者學術生命中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