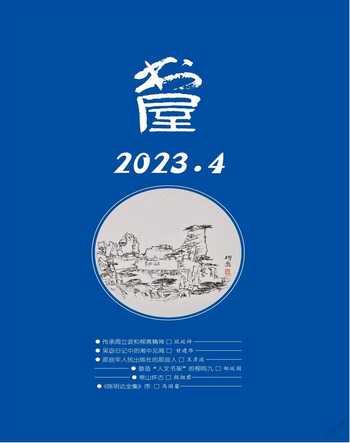徐旭生、蘇秉琦考古手記中的陳寶祠與陳倉城
王俊錚
一
十年前的那個午后,當我騎著單車穿過橫跨渭河之上的蟠龍大橋,戴家灣便在橋北的蟠龍塬下。
有關民國時期戴家灣一帶的情形,因時年僅二十五歲的蘇秉琦先生曾參與北平研究院與陜西省政府合組的陜西考古會在斗雞臺一帶的大規模考古發掘,故而留下了些許珍貴的記錄。蘇先生在《斗雞臺考古見聞錄》一文中曾對戴家灣的經濟與生活狀況有如下記述:“本地人民的經濟狀況,都非常困窘……自然的原因:第一是耕地不足。例如陳寶祠所在的戴家灣,全村約六十戶,耕地共不過四百畝。所以每戶占地最多的不滿五十畝,普通只三五畝。鬧災的時候,餓斃逃亡的,大約不下十分之三四,可以想見原來人口的稠密了。”
蘇先生對關中一帶因“鴉片繁榮”而帶來的“陜西的黑化”深為慨嘆和憂慮。他首先概述了當時這一情狀的基本情形:“陜西的社會既如同煙鬼,所以當他犯了癮以后的狼狽無力的情形,正好和我們前邊所見的畸形的繁榮,是一個對比。”而后以戴家灣村為例,陳述了吸食鴉片所帶來的兩大“嚴重的惡果”:
第一是耗費的驚人。例如代家灣種煙二十六畝,一畝平均按收割五十兩計算,共合一千三百兩,可是代家灣的青年男子吸煙有癮的就有三十多個,如果每人每天吃一錢,全年就需要一千多兩。固然實際種的不只二十六畝,可是吸煙的更不只青年男子……
第二是勞動的不足。現在舉幾個實例,我們在斗雞臺所用的工人四五十名,是從附近的幾十個村選拔出來的。因為凡有煙癮的一概不用。所以代家灣雖然有五六十戶,壯丁也當不下五六十人。可是淘汰的結果,只有二十多個是沒煙癮的,僅占總數的小半。
足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陜西關中一帶鴉片泛濫及其所引發的種種社會亂象是多么令人觸目驚心。
絕然不同于民國時期那滿目瘡痍的民生慘象,現如今氣勢恢宏的行政中心綜合體已經拔地而起,城市建設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戴家灣新建高層住宅間混合著村落中尚未拆遷完畢的老舊房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那個還沒有高鐵的年代,緊挨著戴家灣村半塬穿行而過的老隴海鐵路顯得異常繁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營建隴海鐵路時,出于對古跡陳寶祠的保護,在楊虎城將軍和邵力子先生的主持下,鐵路從陳寶祠下方、由其二人親自題寫碑額的“斗雞臺隧道”中穿行而過。斗雞臺即位于戴家灣村以北、戴家溝與劉家溝之間的一塊臺地。
蘇秉琦先生在其撰寫的著名考古學報告《斗雞臺溝東區墓葬》開篇便有如下記述:“乘隴海鐵路火車,由西安至寶雞,在未抵達目的地之前,經過最后一個小站,不遠便看到一個隧道。在隧道洞口的上方,有一橫額,曰‘斗雞臺’,即北平研究院曾經發掘過的遺址所在。因本院的發掘,事在鐵路未通之前,據說,該隧道的穿鑿,乃出于路局主管人保護古跡的美意,而非工程上的必需。因此,此一橫額刻石,亦可說是本院在此發掘的一個紀念。”
1983年對隴海鐵路進行電氣化改造后,斗雞臺隧道便廢棄了。現遺跡已全然湮沒無聞,唯楊、邵所題寫之兩方“斗雞臺隧道”碑額至今仍保管于寶雞市金臺區文化館內。
二
“陳寶”及“陳寶祠”史事,最早見于《史記》。所謂“陳寶”,一般或釋義為“陳倉之寶”。東漢應劭曰:“時以寶瑞,作陳寶祠,在陳倉,故曰陳寶。”《史記集解》引漢魏時人蘇林曰:“(若石)質似石,似肝。”《水經注》亦有“得若石焉,其色如肝”之語,從年代上看,陳寶“似肝”至少在蘇林所處的漢魏之際已有流傳,《水經注》著文史源或肇端于此。至于陳寶為何物?蘇秉琦先生即提出其“原不過為‘流星’‘隕石’,特神乎其說而已”。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若”之語境常與上天或神祇有關,“陳寶”應為一枚天外隕石。有關“陳寶”的記述后世不絕于史,特別是常以“陳寶鳴雞”以為祥瑞氣象,逐漸為后人所尊崇。晉人干寶所著《搜神記》所記尤為傳奇,最是稱著。后來又演繹出了美麗賢惠、法力非凡的陳寶夫人形象。
有意思的是,今陳寶祠所在之臺地依然以斗雞臺名之,舊稱祀雞臺。明清至民國地方志對陳寶祠與祀雞臺的著錄大致相同,可見系著者因襲傳抄。蘇秉琦先生在《斗雞臺溝東區墓葬》中對斗雞臺、祀雞臺、寶雞、陳寶及陳寶夫人等地名與神祇關聯已作考究。寶雞之得名源于自秦文公以來歷代不斷“層累”之“陳寶鳴雞”的典故,已幾為地方學界之通說。蘇先生對陳寶祠歷史地位的肯定則奠定了后世論述之基石,茲錄文如下:“以現存的祠廟規模而論,可謂平平無奇,一無可取。但如就祠廟的歷史而論,則又極不尋常,值得大書特書。第一,此祠在我國古代的神祇祀典中,恐為最富于浪漫色彩的一個。第二,此祠在海內古神祇中,除天、地、龍王之類,似建立最早。第三,此祠自秦文公初建至現在,雖史料殘缺,不盡可考,然其間存續之跡,大半可辨,享祀之久,海內無二。”
2012年探訪時,由于當時基建有限,半塬臺地上的陳寶祠幾無任何遮擋,沿著并不難走的土道即可輕松抵達。親吻故都深處的那一刻,心情無疑是激動而暢快的。此刻不禁又想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秉琦先生一行抵達陳寶祠時的情形。根據他在《斗雞臺考古見聞錄》中的記述,可知他們抵達陳寶祠的時間為民國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二十日傍晚:“二十日早晨比昨日更冷。約一二小時便到汧水(即今千河,筆者注)岸。正當秋泛之后,水勢還大,汽車過不去。于是把行李箱子用具等都卸下來,改裝騾車和驢馱。因為雇車和裝卸,費時很久,等我們步行到斗雞臺陳寶祠的時候,已經太陽平西了。”
關于秦文公時至漢代陳寶祠的方位,唐代《括地志》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之東。”徐旭生、蘇秉琦等先生入住之陳寶祠系清乾隆四年(1739)由寶雞縣令喬光烈主持重建于陳倉城之南。蘇秉琦先生述其所在“是一座土堡。土堡內,一片麥田,已無人居”。1995年《重建陳寶夫人祠銘》云:“寶殿三楹,依崖而立。卷棚獻堂,宇敞軒明。崖辟仙洞,深邃幽奇。陳寶仙像,端坐神龕,婉約慈祥。此一莊嚴古建,直立存至西寶鐵路復線修通之時。”陳寶祠在當時尚有廟管會,有公地十畝,以地養廟。廟內有方丈和僧人駐祠。
鑒于民國時期戴家灣村一帶的艱苦條件,考古發掘辦公和居住地點便選在了尚可勉強居住的陳寶祠內。據1934年4月19日《徐旭生陜西考古日記》記述:“十九日,與仲侶縣長(即時任寶雞縣縣長全祖謀,筆者注)偕往斗雞臺。至村西頭,大道北有一廟,內有第二學區區立第二十七小學。據言臨時辦公處可設于此,乃下車入觀。未幾,正區長田君,副區長韓君,前任區長□君,村長張君,排長楊君均至。校中教員符君。問此何廟,符君言系娘娘廟。廟大門三間,無神像,畫壁剝落。正殿三間,有畫壁神像。陪殿三,各一間,內有神像畫壁,無門窗。教員住室一間,門窗全。后面有洞二。”
該年5月18日,徐旭生致李書華之信函中有云:“此七村中,廟雖不少,而成社之廟,則指古陳寶廟。此廟名亦吾輩據舊書名之,土人則僅曰‘娘娘廟’。”另據該年4月20日《徐旭生陜西考古日記》,云陳寶祠“廟固無額,而神龕前顏曰‘陳倉福神’,當非無故”。廟門兩側有聯,聯曰“神降陳倉,瑞映岐陽鳴鳳;廟臨渭水,祥開鄜野飛熊”。日記中所載之“娘娘廟”實為陳倉時人對“陳寶(夫人)祠”的俗稱,從對聯中亦可見當時這一地區對陳寶典故的來龍去脈依然有著清晰的認識。
蘇秉琦先生對其有此描述:“光景動人的陳寶,也式微的不堪了。現在只有不大的三間正殿,三間門洞,和四小間東西廂房。陜西考古會的臨時辦公處,就設在此地。各屋都門窗洞開,我們立刻找來些高粱稈做窗楞,用麻紙糊起來,然后把行李鋪在旅行床上就睡了。夜間涼風陣陣,真有說不出來的凄清滋味!”
又據當代碑記可知,清代陳寶祠與斗雞臺隧道大抵同時消逝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隴海鐵路電氣化改造。
1995年,由寶雞市炎帝研究會、寶雞市政協、寶雞市陳倉鎮戴家灣村委會等籌資,再度選址興修了新的陳寶夫人祠,后有所增葺,與陳寶奉祀合二為一,遂一般以陳寶祠稱之。主殿“陳寶祠”匾額由陜西著名書法家任步武先生題寫。據1998年、1999年兩通《重建陳寶祠記》碑文,陳寶祠新址“北依文公城(即陳倉城,筆者注),東望臥龍寺,南臨祀雞臺,西接長樂原”。2013年,因修建公路,陳寶祠所在大半院落被占。2015年底,僅剩的唯一一座大殿毀于火患。
三
陳寶祠所在之戴家灣一帶古代遺存極為豐富,在歷史上不僅是西周高等級貴族墓葬區,也是秦文公至隋代陳倉縣徙治于北周留谷城(今寶雞市北崖中學一帶)前,歷代陳倉城故址之所在。
自1901年以來,戴家灣地區屢有盜挖古墓的事件發生,常有珍貴文物流出,其中著名者如收錄于《陶齋吉金錄》中的端方舊藏“柉禁十三器”。1928年,盤踞于鳳翔一帶的軍閥黨玉琨(又名“黨跛子”)大肆盜掘墓葬,致使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其中有相當數量是西周青銅重器,如周公東征銅方鼎、魯侯熙銅鬲、毛伯鼎等。這一當世慘劇給徐旭生等考古先賢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促成后來斗雞臺考古發掘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著名商周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雷興山教授曾在一次以周原遺址考古為主題的講座中說到,以往每每攜學生自周原遺址赴寶雞市區參觀訪問,當車輛行經寶雞行政中心所在之戴家灣一帶時,他都會要求車上的學生向斗雞臺方向“行使注目禮”,因為在那里,對于中國考古學而言,坐落著一處堪與安陽殷墟齊名的圣地。1934年4月,由北平研究院等聯合組建成立的陜西考古會主持了對寶雞斗雞臺的發掘,正式揭開了陜西科學考古發掘的序幕。在斗雞臺考古發掘中,以溝東區的發掘成果最為顯著,共發現墓葬一百零四座,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徐旭生、蘇秉琦等前輩先賢都在這里對溝東區先周瓦鬲墓進行了系統研究,開創了周秦考古之先河,成為中國考古類型學理論一次深刻的實踐。
徐旭生先生初來斗雞臺遺址時在陳寶祠后身土堡區域內發現“漢錢多件”。據其1934年5月4日記述:“上午見向東又有一墓洞,下午在此墓洞下層,發現一溝,且見瓦片破痕極新,知墓已為人盜過。盜自北方來。察破陶片,知墓大約屬漢代。”溝東坑內亦曾發現五銖錢多枚。蘇秉琦先生在《斗雞臺溝東區墓葬》報告中亦有認定:“今祠之前后左右,均屬漢式陶瓦片。……土堡露頭大都為漢式磚、瓦、陶片。由此推測,祠堡所在,或即周、秦、漢諸朝古祠遺址之一部分,抑或即古陳倉城遺址之一部分。”位于戴家灣的陳倉城遺址歷經兩千年風霜洗禮,遺跡幾已湮沒無聞。民國時期隴海鐵路的修建、新中國成立后引渭渠及近年通向蟠龍新區之上塬公路的興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隴海鐵路的電氣化改造,以及駕校、陂塘、工廠等現代建筑工程,已將遺址切割得支離破碎。陳倉城遺址現僅殘存土墻一段,年代不詳,但大抵與陳倉上城之北墻相合。
2014年4月,陜西考古學會、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部門在寶雞舉辦了“紀念寶雞斗雞臺考古八十周年座談會”,徐旭生之子徐桂綸、蘇秉琦之子蘇愷之以及張忠培等先生悉數到場,并在戴家灣遺址保護碑旁共同植下一株白皮松,以示追思之念。近年每逢夏日,我常與父親單車拉練,沿著引渭渠公路騎行穿過戴家灣遺址,歲歲年年,眼見著那棵稚幼的白皮松樹已愈加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