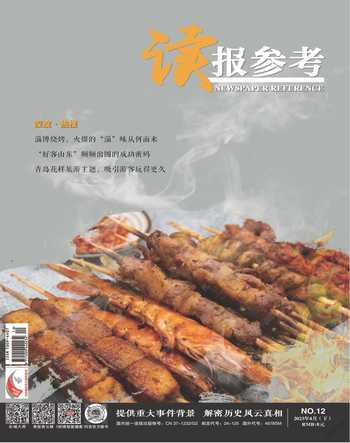“00后”開始立遺囑:送給自己一份成年禮
《2022中華遺囑庫白皮書》數據顯示,2020年以來,來中華遺囑庫立遺囑的“00后”共有357人,他們大多為大學在讀學生和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在中華遺囑庫“微信遺囑”小程序留言的人群中,超六成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
18歲立遺囑,“沒什么好避諱的”
2023年3月,剛滿18歲的李紅,在中華遺囑庫鄭重地立下自己的遺囑:如果遭遇了不幸,打算將財產全部捐給公益機構,包括存了多年的壓歲錢和一個游戲賬號。“沒什么好避諱的。”她說,這是一種未雨綢繆的行為,還覺得“很酷”。 “我覺得想到就要去做,不要等,等著等著可能最后什么都沒有留下。”今年20歲的廣東男生王皓,在自己17歲那年立下了遺囑。“網絡小說的分成是我的收入,我平時靠自己賺的錢生活。”王皓是家里的獨生子,14歲那年,他萌生了寫小說的想法。當時還在上學的他,已完成了多部作品,獲得了穩定的收入。
“平時我寫作壓力比較大,也經常看到一些年輕人猝死的新聞,為自己立一份遺囑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王皓說,“如果還來不及交代,人就走了,這是很不負責任的。我平時是一個比較有規劃的人,把自己的事情都安排好,也是對父母的一個交代,相當于留下自己的愛。”
在遺囑里,王皓將遺產同時贈予朋友一部分,“父母不缺錢,朋友對我很好,很照顧和支持我,所以,我也想留給朋友一些”。
“立遺囑不是終點,而是新起點,以后會更加認真地活著。”21歲的林雨,也是在18歲那年立下了遺囑。當時,她還是一名大一新生。“我輔修了法律,懂得一些法律知識。”一個偶然的機會,林雨了解到立遺囑的程序,如果發生了什么意外,她希望把存在銀行卡里的兩萬多元留給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在她最傷心難過、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予了支持幫助和關愛,“雖然錢不多,就當是一種回報吧”。
林雨的父母并不知道她立下了遺囑,“這純屬我的個人意愿”。她認為,每個年齡段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一旦說了怕父母不了解,反而造成誤解。眼下,她考慮更多的是未來,以后有了賺錢能力,掙的錢會繼續存入這張銀行卡,如果資產增多,她可能會重新訂立遺囑,增加遺囑繼承人。
“父母在他們眼里很重要,他們同時也會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而對物質的關注則顯著降低。”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告訴記者,很多“00后”把立遺囑視作一種新生事物,認為是對生命的尊重和自我認知價值的體現,并將其作為人生里程中的一個重要儀式。
“來不及作準備就走了,這是最難過的”
“我害怕來不及作準備(就走了),這是最難過的。”3月23日,“90后”王蕭來到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二登記中心,咨詢遺囑登記的相關手續。
此前,王蕭完全沒想過遺囑登記這事,“我剛成家幾年,孩子還小,沒什么好寫遺囑的”。不過,作為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在工作和生活中,她見了太多“來不及”的例子。之前,她的舅舅和姥爺相繼離世,但他們對于自己的財產沒有任何安排,除了房子外,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們有哪些財產,該如何處理,“大家都蒙了,不知道該怎么辦”。
害怕這種“來不及”的時刻,她決心要提前對自己的資產拉好清單、作好安排,“這是防患于未然”。
“財產清單是遺囑重要的功能之一。”中華遺囑庫江浙滬區域負責人黃海波告訴記者,“實際上,對許多財產,家人之間是不知道的。”被繼承人通過遺囑可以將自己擁有的比較值錢的財產進行整理,并分別傳承。在家庭關系比較復雜的情況下,財產不明可能會導致繼承人之間相互猜忌,繼而產生家庭矛盾和糾紛。“而遺囑能夠幫助定紛止爭,挽救家庭關系。”黃海波說。
今年23歲的陳瑞,出于保護自我財產的需要,在18歲生日第二天就來到中華遺囑庫立下了遺囑。
在陳瑞兩歲的時候,他父親有了外遇,父母離婚。他的母親沒有再婚,而是努力打拼事業,積蓄起一定的財產,許多都在他名下。
2018年,陳瑞打算去美國讀書。臨走前,他的母親來到中華遺囑庫,想在遺囑中將所有財產都指定給他。經過詳細咨詢,母親得知,如果他發生意外,他的生父也有一半財產繼承權。在陳瑞的遺囑中,他指定財產全部給母親或其他指定繼承人,力求最大限度地保護母子兩人的財產。立下遺囑后,他母親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
黃海波介紹,通過登記遺囑,年輕人可以避免在遭遇意外等情況后,把財產留給不符合意愿的繼承人。“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來,風險無處不在。”陳凱說,越來越多人考慮的不僅僅是怎么避開風險,更會考慮如果這個風險避不開,他們該做些什么,“在這種意識、觀念下,對遺囑的思考就提上了日程”。
“許多人認為,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我什么都沒有做、沒有說就走了,太遺憾了。”陳凱認為,當今社會,人們觀念不斷改變、更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把立遺囑看成是人生終點要做的事情,而是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定期思考和盤點。
“錄像時不要哭泣,立遺囑是開心的事情。”這句話,寫在中華遺囑庫電子屏幕上,正成為越來越多人立遺囑時的心中所想。
(摘自《中國青年報》劉胤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