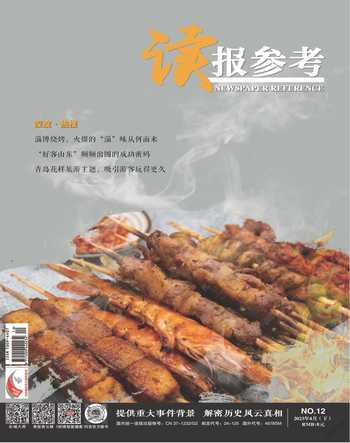“最美醫(yī)者”馬玙:為病人作一輩子功課
從風(fēng)華正茂到銀發(fā)滿頭,在中國結(jié)核病防治歷史上,馬玙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她卻謙遜地說:“我沒什么多么遠(yuǎn)大的理想,一個(gè)人這一輩子,總要給國家、給人民作點(diǎn)貢獻(xiàn)。”
“逼出來”的醫(yī)者
馬玙成長于動(dòng)蕩的年代。1932年,她在江蘇如皋出生,父親是生意人,家境富裕,生活無憂,但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一家人不得不融入逃難的洪流,一路輾轉(zhuǎn)來到上海。
1950年,馬玙高中畢業(yè),同時(shí)被清華大學(xué)外語系和江蘇省立醫(yī)政學(xué)院(今南京醫(yī)科大學(xué))錄取,她選擇了學(xué)醫(yī)。大學(xué)畢業(yè)后,馬玙被分配到剛剛成立的中央直屬結(jié)核病研究所(今首都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北京胸科醫(yī)院)當(dāng)專科醫(yī)生。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每100人中就有1.75位結(jié)核病患者,人人談“癆”色變。出于恐懼,一同分配來的同學(xué)想打退堂鼓,馬玙卻沒有絲毫顧忌。
然而,現(xiàn)實(shí)的殘酷超出她的想象。有的病人大咯血時(shí)需要用臉盆去接血,令人膽戰(zhàn)心驚;有的人病情長期沒有好轉(zhuǎn),醫(yī)生束手無策;還有不少患者,被結(jié)核性胸膜炎、腦膜炎無情地奪去了生命。
馬玙白天忙于臨床工作,晚上就去聽著名結(jié)核病學(xué)家裘祖源的課。后來,裘祖源專門給她布置了一個(gè)作業(yè),讓她以“糖尿病對肺結(jié)核的影響”為選題寫一篇文章。對剛剛畢業(yè)的馬玙來說,這無疑是困難的。為了寫好這篇文章,她在圖書館廢寢忘食地查找資料。她忐忑著交了作業(yè)后,裘祖源看了半晌說:“這篇文章寫得不錯(cuò),你以后就用這種態(tài)度學(xué)習(xí)吧。”
受到鼓勵(lì)后,馬玙決心要像裘祖源一樣獻(xiàn)身結(jié)核病防治事業(yè)。那時(shí),空洞型肺結(jié)核傳染性強(qiáng)、病死率高,可是口服藥物的治療效果并不理想。針對這一難題。馬玙和同事們大膽創(chuàng)新,發(fā)明了“定向肺導(dǎo)管治療術(shù)”。 起初,這個(gè)救命的“土辦法”,用的都是“自制器械”——“肺導(dǎo)管”,其實(shí)就是別的醫(yī)院用剩的心導(dǎo)管,做彈簧的高級不銹鋼鋼絲是一位搞飛機(jī)維修的患者提供的,而乳膠管和尼龍絲,則來自一位修自行車的患者。正是這個(gè)簡易裝置,使得超過60%的空洞不需手術(shù)就能愈合,不但提高了療效,還大大縮短了療程。每次看到空洞縮小了、閉合了,馬玙就萬分欣慰。“研究成果都是逼出來的。”多年后回憶起來,她依然難掩自豪,“做結(jié)核病科大夫什么時(shí)候最幸福?看見這個(gè)最幸福!”
永不停歇的“帶頭人”
1980年,教育部選派人員出國進(jìn)修,馬玙名列其中。到美國后,她從臨床轉(zhuǎn)向科研,幾乎每天都在實(shí)驗(yàn)室里工作到深夜。兩年時(shí)間里,從剛開始動(dòng)作生疏地作實(shí)驗(yàn),到后來跟著教授參加醫(yī)學(xué)討論會(huì),發(fā)表論文,馬玙進(jìn)步得很快。她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生活:“我從來沒有無名煩惱,我連嘆氣的時(shí)間都沒有。”
1982年,馬玙進(jìn)修歸來,牽頭創(chuàng)立了內(nèi)科實(shí)驗(yàn)室,并首開先河,進(jìn)行結(jié)核病免疫學(xué)研究。實(shí)驗(yàn)室設(shè)備簡單,研究方向卻緊跟國際前沿。有位美國教授來參觀時(shí)被觸動(dòng)了,當(dāng)他拿起相機(jī)拍照時(shí),馬玙很不好意思地阻止:“教授,你們的條件比我們好,我們這個(gè)小小實(shí)驗(yàn)室,你就別照相了。”美國教授卻感慨地說:“我要帶回去給我的年輕學(xué)生看看,中國在這么簡單的條件下,都在開展耐藥基因檢測,他們還有什么可埋怨的。” 正是在這個(gè)小小的實(shí)驗(yàn)室里,馬玙帶著學(xué)生們在結(jié)核病分子生物學(xu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十余年時(shí)間里,先后完成了多個(gè)項(xiàng)目,獲得北京市科委、北京市衛(wèi)生局科技進(jìn)步獎(jiǎng)共九項(xiàng)。
既懂臨床,又懂科研,馬玙被同事笑稱為“兩棲動(dòng)物”。研究成果應(yīng)用到臨床后,很多結(jié)核病患者能在第一時(shí)間得到準(zhǔn)確診斷、有效治療,結(jié)核病死亡率下降了90%以上。談起這驕人成就時(shí),馬玙卻把功勞記在了學(xué)生們身上:“這些成就主要來源于眾多研究生的辛勞和努力,我們亦師亦友、教學(xué)相長,誰是老師,誰是學(xué)生,這是說不清的。”
在馬玙的引領(lǐng)下,團(tuán)隊(duì)碩果累累,全國范圍內(nèi)最大的結(jié)核病生物樣本資源庫建立了,全國首個(gè)“結(jié)核病臨床研究智能一體化平臺(tái)”搭建完成了。諸多的“全國第一”,為結(jié)核病的快速診治提供了新方法、新技術(shù)。
從醫(yī)近70年,當(dāng)年那個(gè)陪著病人家屬哭鼻子的小姑娘,已經(jīng)成長為結(jié)核病領(lǐng)域的頂級專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dān)當(dāng)。我年輕的時(shí)候,我國結(jié)核病防治還在‘追著外國人跑,現(xiàn)在我們的結(jié)核病防治水平已經(jīng)領(lǐng)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希望新的一代能夠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新,實(shí)現(xiàn)更大的飛躍,成為國際賽道上的‘領(lǐng)跑者。”為著這個(gè)心愿,馬玙甘當(dāng)階梯,耄耋之年,她依然堅(jiān)持爬六層樓給研究生上課。如今,她培養(yǎng)的博士生、碩士生已成為全國各大醫(yī)院結(jié)核病研究方向的骨干和學(xué)科帶頭人。
繼“最美防癆人”“結(jié)核病防治時(shí)代楷模”等榮譽(yù)之后,2021年,馬玙又獲得了“最美科技工作者”稱號(hào)。一頭銀發(fā),慢聲細(xì)語,在患者心目中,馬玙是當(dāng)之無愧的最美醫(yī)者。
“玙”,即“美玉”,馬玙人如其名!
(摘自《時(shí)代郵刊》潘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