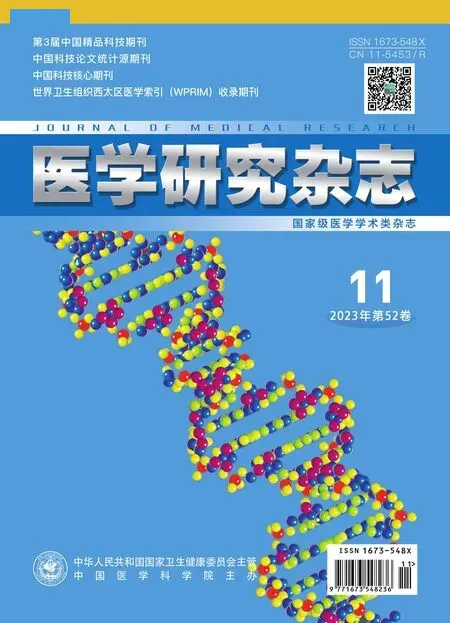糖尿病腎臟病生物學標志物的研究進展
楊其文 韓思宇 王莉華 李 元 周靜威
我國糖尿病腎臟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的發病人數隨著糖尿病患病率的升高而迅速增加,在住院患者和普通人群中,糖尿病相關的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病率均高于腎小球腎炎相關的CKD,成為我國CKD的首要病因[1]。同時在全球范圍內,DKD是終末期腎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最常見病因[2]。基于DKD在國內外嚴峻的流行病學現狀及其不良預后,可以認為DKD的防治是一項艱巨任務,而可靠的診斷和預測是減少DKD危害的基礎策略。隨著研究證據的增多,傳統生物學標志物對DKD的預測能力暴露出了特異性和敏感度不足的問題,因此迫切需要尋找更好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來預測DKD的發生、發展。近年來的研究已發現多種頗具前景的預測DKD進展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包括細胞因子和氧化應激標志物等,在此分別介紹傳統和新型生物學標志物并評估它們預測DKD進展的可能性。
一、傳統生物學標志物
1.腎小球濾過率:腎小球濾過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是反映腎臟排泄功能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臨床預測ESRD的重要指標[3]。由于通過外源性物質直接測定血漿清除率的過程繁瑣,且價格昂貴,目前臨床多用基于血清肌酐的CKD-EPI公式或MDRD公式間接得出估算腎小球濾過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4]。
基線eGFR是常用的預測DKD進展的生物學標志物之一[5]。一項為期10年的觀察性隊列研究發現,基線eGFR是ESRD的重要預測因子[6]。另一項前瞻性研究發現,eGFR重度下降的2型糖尿病患者在10.2年內發生ESRD的風險比eGFR正常的患者增加了81.9倍[7]。eGFR的變化率同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ADVANCE-ON研究納入了8879例2型糖尿病患者,經7.6年的隨訪后發現,eGFR的下降速率與發生ESRD的風險呈顯著正相關[8]。基線eGFR水平和eGFR的變化率可以預測DKD的進展,但是對于eGFR水平正常且沒有明顯下降的DKD(尤其是DKD早期),eGFR難以獨立預測其進展。
2.白蛋白尿:白蛋白尿是診斷DKD的重要依據之一,《中國糖尿病腎臟病防治指南(2021年版)》定義尿白蛋白/肌酐(urinary albumin-to-creatinine ratio,UACR)≥30mg/g或24h尿白蛋白排泄率(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rate,UAER)≥30mg/24h為尿白蛋白增高[9]。UAER與UACR對DKD的診斷價值相當,但是因為UAER操作繁瑣,臨床上常用UACR判斷DKD尿白蛋白水平[9]。
UACR是DKD腎功能進展的獨立危險因素,當前被廣泛地應用于預測DKD患者的ESRD風險[5,10]。UACR同時也是DKD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率的獨立危險因素[11,12]。
但隨著研究證據的增加,UACR預測DKD進展的能力逐漸受到質疑。正常UACR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出現腎功能進行性下降,UACR中度升高(UACR為30~300mg/g)的糖尿病患者也可以表現出穩定的腎功能。此外,糖尿病患者從UACR中度升高消退至正常水平是常見的現象[13]。34例UACR中度升高的2型糖尿病患者接受了腎活檢,結果顯示,1/3患者有典型的糖尿病腎小球硬化,1/3患者有更符合高血壓腎硬化的非典型表現,其余1/3患者的腎臟組織學則表現為正常,說明UACR升高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腎損傷情況[14]。UACR是目前臨床廣泛接受、相對可靠的預測指標,但是無論是其基線水平還是變化的趨勢,均難以充分預測DKD進展,尤其是在UACR水平正常的患者中。腎臟組織學檢查也證實了UACR和腎損傷之間欠佳的相關性。
二、新型生物學標志物
DKD涉及多個發病機制,包括血流動力學異常、炎性反應、氧化應激、纖維化等。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圍繞上述機制展開,致力于尋找能更好地預測DKD進展風險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基于近年的研究結果和進展,筆者列舉了多種頗具代表性和潛在臨床應用價值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包括細胞因子和氧化應激標志物等。
1.炎性細胞因子及其受體:DKD曾被認為是為非炎性腎小球疾病,大量研究表明,低度炎癥參與了DKD的發病。DKD的炎性反應是由多種機制誘導的,包括高血糖介導的細胞死亡、巨噬細胞的激活以及其他免疫細胞的參與等,進而引起基膜增生以及腎小管纖維化增加,最終加速腎小球硬化。
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是炎癥的關鍵介質,并在細胞凋亡中起著重要作用。來自Joslin糖尿病中心的兩項研究表明,TNF-α及其受體的血清水平可能是預測1型和2型糖尿病腎臟病進展的理想生物學標志物[15]。在這兩項研究中,sTNFR水平是eGFR下降的有力預測因素,sTNFR2水平處于前1/4的1型糖尿病患者達到CKD3期的累積發生率為60%,相比之下,sTNFR2水平處于后3/4的患者的累積發生率低于20%;在存在蛋白尿且sTNFR1水平在前1/4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12年內進展為ESRD的風險接近80%,而sTNFR1水平處于后3/4的患者的風險小于20%,并且sTNFR1較UAER對GFR的預測能力更強。波士頓腎活檢隊列(BKBC)研究經65個月隨訪后發現,受試者基線sTNFR1、sTNFR2水平與eGFR水平呈較強的相關性,且隨著sTNFR1、sTNFR2水平升高,腎功能進展的風險隨之增加。慢性腎功能不全隊列(CRIC)研究對894例糖尿病伴CKD的患者進行了隨訪,分析了多種與腎小管損傷、炎癥和纖維化相關的生物學標志物,在調整了其他的危險因素后,發現較高水平的sTNFR1和sTNFR2與更快的DKD進展有關,且sTNFR2的風險比最高[16]。上述研究均證明,TNF-α和sTNFR是預測DKD腎功能進展的較為理想的生物學標志物,值得重視。
2. 轉化生長因子β: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是一種參與血管生成、免疫調節和細胞外基質形成等生理過程的多效細胞因子。TGF-β家族被分為TGF-β1~TGF-β5 5個亞型,哺乳動物體內主要存在TGF-β1~TGF-β3 3個亞型,其中以TGF-β1占大多數。TGF-β1被認為是介導腎小球硬化和腎間質纖維化關鍵的細胞因子,其作用包括趨化和活化炎性細胞、介導腎小管上皮細胞向間充質細胞轉變分化、刺激細胞外基質蛋白的合成、降低基質金屬蛋白酶的活性和(或)增加蛋白酶抑制劑的合成以促進細胞外基質的沉積等。過度活躍的TGF-β1信號通路被認為是DKD慢性腎病進展中的關鍵促纖維化因子。陸靜爾等[17]測定了127例糖尿病患者的血清TGF-β1水平。結果顯示,糖尿病患者血清TGF-β1表達水平高于健康對照組,且糖尿病伴腎功能下降的患者血清TGF-β1表達高于腎功能正常的糖尿病患者,并計算出血清TGF-β1單獨診斷糖尿病伴腎功能下降的敏感度、特異性及準確率分別為75.00%、72.26%和73.10%。該研究中TGF-β1的敏感度、特異性及準確率均高于臨床常用的胱抑素C和尿素氮,說明其可能具有較好的預測DKD進展的能力。一項Meta分析納入了48篇關于中國人群TGF-β1和DKD風險的臨床研究,結果顯示,高水平的血清TGF-β1與DKD的易感性以及DKD的進展相關[18]。目前關于TGF-β1預測DKD進展的前瞻性臨床研究相對較少,其預測能力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3.氧化應激標志物:氧化應激是DKD發病和進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過量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被認為是高糖環境下產生的有毒中間體,它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加重DKD進展。在生理狀態下,腎臟會產生少量ROS,當腎臟固有細胞因高糖環境不能有效降低葡萄糖轉運率以維持細胞內葡萄糖穩態時,這些細胞的線粒體產生過量ROS誘導氧化應激,進而導致DKD的發生和進展。
8-羥基脫氧鳥苷(8-oxo-7,8-dihydro-2′-deoxyguanosine,8-OHdG)是ROS誘導核和線粒體DNA中鳥嘌呤堿8-羥基化后由特異性酶切的產物,被視為DNA氧化應激的生物學標志物。Sanchez等[19]測量并隨訪了兩個隊列共計704例1型糖尿病患者的基線血清8-OHdG水平,并分析了8-OHdG與隨訪期間eGFR、DKD和死亡風險等的關聯,結果發現,較高的8-OHdG血漿水平與1型糖尿病患者DKD風險增加獨立相關。王丹陽等[20]的橫斷面研究發現,尿液8-OHdG水平與2型糖尿病所致的DKD有較高的相關性,并認為尿液8-OHdG是反映DKD進展的生物學標志物。
4.晚期糖基化終產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AGE):AGE是體內蛋白質、脂質或核酸類大分子暴露于還原糖中生成的一組復雜的異質性物質,大量研究表明,AGE與代謝性疾病高度相關。AGE可通過改變蛋白質的生理功能、觸發細胞級聯反應,導致濾過屏障解體、引發氧化應激和腎臟纖維化進而加重CKD的進展。吳怡琪等[21]通過熒光檢測糖尿病患者的皮膚AGE含量,發現DKD患者的皮膚AGE含量高于單純糖尿病患者,且皮膚AGE含量隨DKD進展而升高。
5.足細胞標志物:足細胞在維持腎功能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許多腎臟疾病的研究焦點。足細胞損傷導致足細胞衍生的細胞碎片和特定的分子目標脫落到尿液中,這可以作為潛在的生物學標志物。尿足細胞標志物已應用于多種腎臟疾病的診斷和監測。
nephrin蛋白是對維持足細胞裂孔隔膜功能有重要作用的蛋白。既往研究表明,在1型糖尿病患者中,有30%的患者在出現微量白蛋白尿之前,可在尿液中檢測到nephrin蛋白。Kostovska等[22]研究發現,大部分UACR正常或升高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均能檢測到相比健康對照組顯著升高的尿nephrin蛋白,且尿nephrin蛋白水平與eGFR水平呈負相關。這表明尿nephrin蛋白可能先于尿微量白蛋白出現,是潛在的反映腎功能進展的早期DKD生物學標志物。
podocalyxin蛋白分布于足細胞表面,主要參與腎小球電荷屏障的形成。一項橫斷面研究發現,53.8%的2型糖尿病患者在出現微量白蛋白尿之前,尿podocalyxin蛋白水平就已經升高,因此對于DKD的早期檢測,podocalyxin蛋白可能比UACR更加敏感。而在確診的DKD患者中,podocalyxin蛋白水平與糖化血紅蛋白和UACR均呈正相關[23]。Zeng等[24]研究認為,尿podocalyxin蛋白是足細胞標志物中最具潛力的DKD早期標志物。
6.急性腎損傷標志物:已有多種生物學標志物被發現可用于急性腎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診斷及預測,而近年來的研究提示其中部分標志物對DKD也具有潛在的預測價值,包括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脂質運載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和腎損傷因子-1(kidney injury molecule-1,KIM-1),兩者均是腎小管損傷標志物。
在DKD患者中,血清和尿液NGAL水平均高于健康人群,且與尿白蛋白水平呈正相關。一項前瞻性研究發現,尿液NGAL水平的升高與ESRD風險增加有關[25]。另一項前瞻性研究發現,尿液KIM-1水平的升高可能是eGFR早期下降的危險因素[26]。上述研究均提示,腎小管損傷很可能緊隨DKD而發生,監測NGAL和KIM-1水平的變化對評估DKD的進展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7.基于組學技術的標志物:組學是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技術,它通常將各類生物分子的集合所進行的系統性研究,主要包括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和基因組學等。組學可以在無假設的前提下進行分析,有助于減少研究的選擇性偏倚。近年來,組學在DKD生物學標志物研究中的應用日益增多。
(1)蛋白質組學:Good等[27]對CKD患者和健康人群進行隊列研究,使用毛細管電泳-質譜分析首次鑒定出273種潛在的生物學標志物組,稱為CKD273。Zürbig等[28]檢測了1014例無微量白蛋白尿的1型和2型糖尿病患者的尿液樣本,發現CKD273的陽性預測值在總隊列中是34%,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可達到47%。研究結果表明,CKD273能夠一定程度地預測尿白蛋白排泄正常的糖尿病患者進展為DKD的可能。另一項前瞻性研究發現,在COX回歸模型中校正其他危險因素后,CKD273可以獨立預測DKD患者的遠期死亡風險。CKD273在DKD的早期診斷和預測遠期預后方面均具有較強的前景,但目前存在費用昂貴和依賴特殊檢測設備的問題,加之其敏感度和特異性有待于進一步驗證,因此尚未在臨床中推廣應用。
(2)代謝組學:Niewczas等[29]分析了進展為ESRD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漿代謝組學特征,發現部分血漿代謝物包括對甲酚硫酸鹽、假尿苷和肌醇等被認為與ESKD終點密切相關;該團隊還分析了伴CKD的1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清代謝組學特征,包括C-糖基色氨酸、假尿苷、O-磺基酪氨酸、N-乙酰蘇氨酸、N-乙酰絲氨酸、N6-氨基甲酰蘇酰腺苷和N6-乙酰賴氨酸共7種代謝物的血清水平與腎功能下降及ESKD終點密切相關。Tang等[30]對102例伴微量白蛋白尿的2型糖尿病患者進行了5~6年的隨訪,發現5-羥基己酸可用于識別有早期進行性腎功能下降風險的2型糖尿病患者。
(3)基因組學:DKD有較強的遺傳易感性,但仍然很難確定其遺傳病因。多項大型全基因組關聯分析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確定了1型和2型糖尿病中對應各種DKD表型的基因和基因區域,關鍵基因包括RND3/RBM43、SLITRK3、ENPP7、GNG7、APOL1、GRAMD3、MGAT4C和GABRR1等,但是這些基因預測DKD進展的價值尚不明確[31~33]。總之,目前基因組學的研究結果很難用于DKD的臨床預測。
三、展 望
DKD是ESRD的最常見病因,有研究者認為越來越多的ESRD由DKD進展而來,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難以準確地識別高風險的糖尿病患者[34]。eGFR和UACR雖然并不完美,但仍然是目前最常用的、診療指南推薦的預測DKD進展的生物學標志物[4,9]。上述在研的部分新型生物學標志物因其顯著的結果被研究者寄予厚望,遺憾的是它們目前均沒有被用于臨床一線。
有關DKD新型生物學標志物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受限于研究方法:部分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作為觀察性研究的一種,無論其結果好壞,它只能提示暴露因素和結局的相關性而非因果關系。例如Kostovska等[22]的橫斷面研究認為,尿nephrin蛋白是比UACR更敏感的早期DKD生物學標志物,但是并不清楚尿中出現nephrin蛋白是否是因果機制的一部分,亦不能說明早期出現的尿nephrin蛋白總是能預測2型糖尿病在未來會進展為DKD。因此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以解決上述問題。(2)缺乏橫向比較:多數臨床研究僅關注于某一個或某幾個相同類型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忽略了將新型和傳統生物學標志物的預測能力進行橫向比較;同時很少有前瞻性研究將多個不同類型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的預測能力進行橫向比較。在如此多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中,尚不明確最具有預測潛力的、最可能成為未來研究重點的生物學標志物。
要有效防治DKD進展為ESRD,關鍵是尋找可靠的預測DKD進展風險的生物學標志物。DKD是一種復雜的異質性疾病,發病機制復雜,提示了其進展是多因素的[18]。雖然上述研究提示部分單一的生物學標志物具有較大的潛力,但是很可能只反映了DKD病理過程的一部分生物途徑,換言之,單一的生物學標志物可能難以充分評估DKD的進展。多個生物學標志物聯合評價DKD很可能是未來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