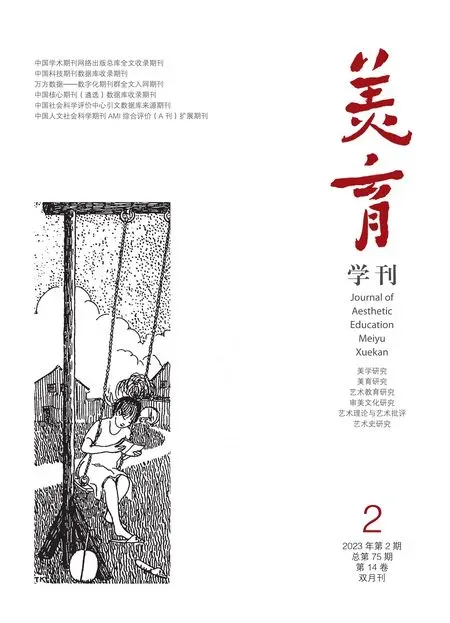洋畫再造:20世紀早期廣州西畫教育的重建與推廣
郭林林
(廣州美術學院 科研創作處,廣東 廣州 510261)
一、西洋畫在近代中國的傳播
西洋畫在中國的傳播可以追溯至明代萬歷年間來華傳教的西方傳教士。萬歷七年(1579)耶穌會士羅明堅來到廣州,兩年后(1581)利瑪竇在廣州開始傳教,同時也帶來了圣母和救世主的畫像等油畫作品。早在萬歷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入京覲見神宗皇帝并呈獻圣像油畫,在給神宗的上表中云:“謹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兩架,萬國圖志一冊,雅琴一張,奉獻于御前。物雖不腆,然從極西貢來,差足異耳。”(1)韓琦等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卷二·貢獻與方物疏,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0頁。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美術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也是西洋畫最早傳入中國的官方文獻記載。而澳門被葡萄牙租借后,西洋畫亦隨之傳播至澳門,至今在新會博物館仍保存有一幅清代之前的油畫《木美人》(圖1)。入清之后,傳教士郎世寧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被召入宮充任宮廷畫師,使用中國畫具、顏料和紙張,以西洋畫技法來繪制寫實逼真的繪畫作品,被稱為海西畫法。延至18世紀中葉,廣州作為中國唯一通商口岸,以西洋畫法描繪中國風景的外銷畫興起,畫師努力學習模仿西洋畫技法和風格,其中較著名者有林呱等廣州畫家,他們都曾于國外學習過西洋畫技法。據《續南海縣志》載:“關作霖,字蒼松,江浦司竹徑鄉人。少家貧,思托業以謀生,又不欲執藝居人下,因附海舶遍游歐美各國,喜其油畫傳神,從而學習。學成而歸,設肆羊城,為人寫真,栩栩欲活,見者無不詫嘆。時在嘉慶中葉,此技初入中國,西人亦驚以為奇,得未曾有云。”(2)《續南海縣志》,卷二十一,列傳。也因為此,西洋畫開始在廣州地區傳播,廣州各級官員、行商熱衷于邀請畫師用西洋畫技法為他們繪制肖像以留存。

圖1 油畫《木美人》,明末時期創作,廣東新會博物館收藏
二、舊式西畫教育的落后與洋畫運動的興起
雖西洋畫早在清代中期就已經傳入廣州,但直至20世紀20年代廣州真正的西洋畫教育依然是一片空白,西洋畫教育主要是教授以放大尺來描繪臨摹擦炭肖像畫和臨摹風景畫。據藝術家吳婉描述廣州當時的西洋畫教育狀況:“作為西洋畫的形式而出現的,在市上就有所謂西法寫相之流,什么美術寫真館等,就是除了舊有的‘大座裝真’之外,兼寫擦炭粉的肖像,那是以放大尺——即如現在自稱寫真的畫家所用的放大尺,從照片上把人的尊容放在紙上,然后拿蘸著碳粉的毛筆,慢慢對準照相上的光暗擦成的……擦肖像之外,還擦一些風景,也是從風景的照片上搬過來的。”[1]當時廣州的西洋畫教育即是如此,然放眼全國也是一樣,留學日本學習西洋畫歸來的胡根天對當時的西畫教育狀況了如指掌,他在民國晚期所作的《西洋繪畫在中國的發展》一文中回顧了當時全國西畫教育的發展情況:“說起國內的藝術教育,民國初年間,國人還不曉西洋繪畫應該怎樣學習,在上海、廣州等大都市,醉心西方藝術的青年,他們所謂學習西洋繪畫,最得意的玩意,便是找尋外國來的印刷畫片開始臨摹,或將攝影像片放大用炭粉照樣擦寫……上海方面,也和廣州幼稚到同樣可憐。現在上海美專的前身,就是民國二年由劉季芳(海粟)、烏始光(已故)、張聿光幾位先生創辦的上海圖畫美術院也一樣教學生臨摹稿本或寫些照像用的背景。民國四年的春季,陳抱一短期留學日本白馬會第一次歸國(翌年再東渡,才入東京美術學校,民國十年畢業后第二次歸國)。他在上海辦了一間東方畫會教學生寫畫,據說開始用木炭條寫石膏模型了,這算是得風氣之先。”(3)胡根天:《西洋繪畫在中國的發展》,原載于1947年11月1日《中山日報·藝術周》,轉引自廣州市文史研究館編《胡根天文集》,2002年,第103頁。
雖則當時西畫教育不是甚為普及,且依舊巢襲于往昔的舊規,遠遠落后于歐美西畫的發展趨勢。20世紀以來在新文化運動的號召下,發展現代主義西畫教育的呼聲漸趨強烈,并且隨著一批藝術家的留學歸來并參與到現代西洋畫的教育與推廣,鼎盛一時的洋畫運動得以在20世紀20年代率先在上海興起,標志之一就是裸體畫已漸次被社會接受,美術家陳抱一在《洋畫運動過程略記》(續)中說:“民國十年前后的期間,上海的洋畫研究風氣,似乎已經通過了相當長久的摸索時期,而開始呈現開拓時期的癥候來了。大概民國九、十年以前的洋畫展覽會中裸體人物畫之陳列還不輕易實行,往往受到無常識無理解的干涉。但民國十年以后,對于裸體畫之陳列,已漸次不致有人太過神經過敏了。”[2]與此同時,胡根天、馮鋼百等一批留學日美學習西洋畫的學生得以學成歸國,他們在上海見到這一西洋畫發展盛況,內心產生觸動,將這一洋畫風氣帶回廣州,并開啟廣州的西畫再造運動。
三、廣州西畫展覽與現代主義啟蒙
20世紀20年代之前偏處于華南地區的廣東處于軍閥混戰的亂局之中,廣東軍政局面事變紛呈、人心不靖,無力發展教育。直至1920年孫中山領導的粵軍驅逐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閥,廣州政局趨于穩定,隨即成立了廣州新的市政府,任命教育家許崇清擔任廣州教育局長(圖2)。許崇清熱衷于教育,并對美育抱有極大興趣,早在1920年就撰文《美之普遍性與靜觀性》與蔡元培進行辯論,指出美育代宗教之說的二大誤繆:“論者因此二大謬誤,遂至混淆美之意識與宗教意識,又復混淆美之意識與道德意識,既主以藝術代道德之論,復以美育代宗教之說,論者視人性則太簡,視道德又太輕矣。”[3]另外熱衷美育的許崇清早在1915年日本留學期間就與胡根天等一批粵籍藝術家相識,胡根天對此曾追憶道:“1915年我在日本東京開始和許老認識,是朋友中接觸比較多的一個……許老不是研究美術的,但對美術深感興趣,并且深刻地認識到美術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4]

圖2 胡根天(左一)與許崇清(左二)在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合影,1922年
許崇清在擔任廣州教育局長之后即著手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籌建工作,他先委托廣州畫家陳丘山信邀此時已經回國的胡根天返粵,并在廣州與胡根天面談廣州美術教育事業籌建事宜。胡根天對當時場景回憶道,“我回到廣州之后,走訪許老于大北直街西化二巷勞園,談話當中,他提出兩件事要我考慮怎樣做:一、創辦一間公立美術學校;二、首先成立一個群眾性美術團體,兩件事我都表示贊成”[4]。根據許胡兩人商議規劃,胡根天先要成立一個群眾性美術團體,進行民眾美術啟蒙,然后再著手成立美術學校。于是胡根天就聯系了陳丘山、梁鑾、馮鋼百、梅雨天等畫家成立了“赤社美術研究會”(圖3),之所以取名為赤社,據說是“因為赤色在色彩心理學上表示熱烈、誠摯、積極和剛強,而我國古代五行陰陽學說認為南方屬火,火色赤,故名”[5]。赤社成立之后接著就于1921年10月1日在廣州永漢北路(今北京路)廣州市立師范學校禮堂和操場舉辦了廣州首次西洋畫展覽會,又稱赤社第一回美術展覽會,展出了油畫、水彩畫、木炭素描、粉彩畫和鉛筆速寫等共160多幅作品。當時論者認為“能夠稱為純粹的西洋畫展覽會,在廣州的,這算第一次了”[1]。這次展覽因為是廣東首次西洋畫展覽會,吸引了大批觀眾參觀,獲得了成功。胡根天在20世紀80年代回憶文章《赤社美術研究會的始末》中對當時的狀況做了介紹:“永漢路是人來人往最繁鬧的地方,我們用白布寫上紅字的一面橫額‘赤社第一次西洋畫展覽會’掛在市立師范學校的街口。當時有些觀眾出于好奇心,有些則是抱著研究和學習態度而來的,所以每天參觀的人相當多,作為西洋畫啟蒙運動,可以說是開始起了作用的。”[6]美術史研究學者陳瀅對赤社第一次西洋畫展覽給予了高度評價,特別是胡根天、陳丘山、梁鑾、馮鋼百等人從日美等國留學歸來所展示的寫實主義和印象主義油畫、水彩畫作品給廣州人呈現了西洋畫正確的姿容,并認為“作為廣東出現最早的西洋畫展,它是作為純粹的藝術品供觀眾欣賞的,具有自主的美學目的。它開啟了廣東社會欣賞西畫的風氣,作為廣東西畫啟蒙的先聲,影響是深遠的”[7]826。

圖3 赤社成員合影,1922年
與此同時,廣東美術界另一件大事也在緊張籌備之中,這就是廣東省第一回美術展覽會(圖4)。這次展覽會籌劃者為當時國民黨粵籍實力派大員、廣東省省長陳炯明,陳氏在1920年驅趕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后倡導“保境安民、聯省自治”,致力于將廣東建設成為模范省,加之陳氏頗有文人氣息,熱衷于地方文化建設事業。陳氏素與嶺南畫家高劍父相熟,高氏留日學習過繪畫,對展覽一事頗為熟悉,之前二人于漳州合作舉辦過美術展覽且取得了不俗效果,故決定在廣州舉辦廣東全省美術展覽會。具體個中緣由在當時報刊中已有評述:“本會(廣東全省美術展覽會)發起之遠因,陳省長平日對于美育,最為注重。嘗謂一國之文明程度,視美術之消長以為衡。故從前在漳州時,亦曾開美術展覽會一次,蓋深知美術為工業之母,非振興美術,不足以促工業之改良也。”(4)見《廣東全省美術展覽會會場日刊》第2號。此次展覽會依照西方展覽制度設有作品審查組,成員囊括了廣東當時畫壇各方,對送展的近千件作品進行嚴格甄選,據時任審查委員會西洋畫審查委員的胡根天回憶:“我們首先就把千幅以上——其中包括孫中山肖像三百多幅,陳炯明像二百多幅的炭粉相以及炭粉風景畫全部淘汰;其次不論油畫、水彩、粉彩、鉛筆等的臨摹品以及廣告月份牌畫也給他落選了。結果入選作品只有一百五六十幅。另外加上審查員作品合共差不多二百幅。”[8]156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展覽于1921年12月20日在廣州文德路廣東畫業館(今省立中山圖書館)開展,并大獲成功。據當時報紙報道僅開幕兩天,就賣出五千多張門票,盛況空前:“此次美術展覽會……頃查一二日共售券五千余張,足征粵人心理,崇尚美術,而會內美術之多且精亦可見矣。”(5)見《廣東全省美術展覽會會場日刊》“游覽券銷額日增”條。而此次展覽會的許多作品以新穎的面目出現,特別是許多留學日本與歐美回國畫家的西洋畫的展出,打破了以往人們對西洋畫的傳統認知,也促進了西洋畫在廣州觀眾中的藝術影響。胡根天曾高度評價此次展覽,認為“對于廣東美術多方面的發展,作用是顯著的。特別是對于西洋畫方面的理解,在觀眾中逐步踏上了正確的方向,給予那些以擦炭相為號召引誘青年或以臨摹抄襲為本領的不正之風一次無情的打擊”[8]159。

圖4 廣東省第一回美術展覽會全體職員合影,前排左三為高劍父、左四為陳炯明,中排左一為胡根天
四、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建立與現代西洋畫規范教育
經過赤社第一回西洋畫展覽會和廣東省第一次美術展覽會之后,廣東美術發展迎來了一個大好形勢,群眾對美術的熱情被激發出來,全面地欣賞了真正的西洋畫。社會對美術尤其是西洋畫的觀感得到了新的認識,促進了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創建。用胡根天的話來說,就是“志愿學習美術的青年逐漸多起來,這就是廣州市立美術學校設立的時代背景”[9]76。就這樣經過近一年的籌辦,廣州市立美術學校于1922年4月24日在廣州中央公園成立,成立之初因為校舍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胡根天等最終決定在廣州中央公園東北角空地搭建臨時校舍招生開課(圖5)。

圖5 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全體員工合影,1922年12月,前排左八為胡根天
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成立后由廣州教育局長許崇清兼任校長,胡根天、馮鋼百分別擔任教務主任和總務主任。據當時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學生趙世銘的回憶:“胡根天為教務主任,兼任西畫、藝術史、藝術理論老師;馮鋼百為總務主任,兼任西畫老師;趙雅庭任西畫老師;陳丘山任水彩畫老師;梁鑾任圖案構成法老師;沈光燾任國文老師;何拙任法文老師。”[10]57在系科專業上鑒于當時情況只設立了西洋畫科,于1922年當年即開始招生。據資料記載,第一屆學生共80人,其中女生12人,學生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分作兩班教學,西洋畫系的學制為四年,于1922年4月26日開學。[7]826之所以只設立西洋畫科,據筆者分析應該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是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師資班底是以胡根天為主的赤社美術研究會成員,成員大部分為西洋畫專業人員,在《尺社小史》中關于赤社(6)赤社1921年成立,至1929年改名尺社。具體改名原因可見《尺社小史》,大致因1927年夏間中國國民黨實行分共后,“社會上無智者流,見了‘赤’字就有點恐怖”,為避免誤會,改名尺社。早期的創建過程對此就有說明:“民國十年(1921)的秋間,同人中陳丘山、胡根天、容有璣、徐守義、梅與天等七八人相聚于廣州,當時大約一則有點慨乎社會上對于西洋美術太不了解,二則自己一伙人也該有一種結合,不論自渡和渡人都有賴乎群策群力,于是赤社便組織起來了,并非自吹,這是中國南方破天荒的一個研究西洋美術的團體。”[11]由此可知以赤社成員為教員班底的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早期的專業構成主要限于西洋畫方面。其二是廣州當時的畫壇狀況,畫壇主要為兩派所把握,一派是以高劍父及其門徒為主提倡在國畫中引入西方寫實畫法具有日本畫風味的折衷派,一派是以趙浩公、黃般若等人為主的主張延續傳統畫法的中國畫畫家,兩派早在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成立之前就互相論爭,以至于形成一種相互攻訐的局面。對此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實際創辦者胡根天亦熟知于胸,他曾在對廣東第一次美展的回憶文中特別提到這一情況:“這一次省展的評選,中國畫方面,由于以高劍父、高奇峰為首由日本引進的比較傾向于形似的畫法(當時叫做‘折衷派’),和我國傳統——主要是宋、元以來已經形成的各家畫法之間,在過去幾年間首先由高劍父挑起爭論,人為地造成較大矛盾和對立,互不相讓,甚至互相攻擊。因此,在這一次美展評選一開始又出現了爭論。”[8]154而且依據胡根天的觀點,他對折衷畫派的做法亦非常不認同,甚至屢次撰文進行譏評,并在《新國畫與折衷》一文中表明他的態度,“我對于新國畫的建立,否決了折衷這一個辦法”,并且認為,“假使有人徒然以‘折衷’為標榜,認為這是百年的大計,而忘記了自身應當還有更遠大,更健全的前途,這在政治上必然陷國家于附庸而失去其獨立性,使藝術和文化也必然造成卑陋的風格而難有堅強偉大的發展。那是應當警惕的!”(7)胡根天:《新國畫與折衷》,原載于《中山日報》1948年2月26日,見《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研究文選》(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第340頁。雖然胡根天不認同折衷派,但是折衷派主將高劍父卻與時任廣東省省長陳炯明有著非凡的關系,是當時廣東文化界的精英人物,并于1920年11月被任命為工藝局長兼工業學校校長,然而又因“甲工學潮”而被迫離職,旋由陳炯明委托組織廣東省第一次美術展覽會。如果市立美術學校成立中國畫科,時任省長陳炯明極有可能讓自己的好友高劍父前來主持。有鑒于此,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在成立之初僅設立了西洋畫科,而中國畫科的設立則是在四年后的1926年,此時的陳炯明已因為發動“六一六兵變”反叛孫中山革命事業而被視為國民黨的叛徒,并于兵敗之后避居香港。與此同時,高劍父指派學生方人定發表論文,拉開了與國畫研究會的筆戰序幕,在這時候成立中國畫科,并將折衷派反對方廣東國畫研究會成員聘為教授,使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成為國畫研究會的陣營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五、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洋畫教學成果
根據現存的校史資料來看,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西洋畫系的學制為四年,采用新式的課程式教育方式來培養人才,一改過去單一依靠師承關系傳授繪畫的狀況。學生入學之后,第一年和第二年以畫木炭素描為主,對象是石膏模型和景物,然后是人物,素描有了一定基礎后,就學習水彩、粉彩,第三年才開始畫油畫。1925年廣州市立美術學校開設人體模特寫生課程,以供三年級學生作畫訓練,這一舉動在20世紀20年代是非同尋常的。[7]826除了木炭素描、水彩畫和油畫的技法課程之外,根據當時形勢還開設有美術史、美學、藝術概論、色彩學、透視學、解剖學等理論課,以及國文、外國文和體育等普通科目,外國文以法文為主修科,日文和英文為選修科,共計有17門課程。在課程編制上,廣州市立美術學校采用按照課時授課的方式:“市美各種科目依照規章分別編配,以實習時間為主體,各班實習時間多編在上午,理論課多編在下午。每日八時至十時五十分、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二十分為授課時間,平均每班每周授課時長至多四十小時至少三十七小時。各畫系各班之理論功課,由教師自編講義,或用課本教授。”(8)劉石心:《廣州市市立美術學校一覽》,廣州:廣州市市立美術學校,1937年,第2-3頁。據對西洋畫科課程表中各科目課時的安排統計來看,課程設置強調實習課(即繪畫實踐),注重基礎技法的訓練。以課程來看,設置與胡根天在日本留學的東京美術學校類似。劉海粟曾于1919年9月赴日本考察美術,并將此次赴日見聞撰寫成《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一書,書中對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的各科課程設置進行了專門記載,其中關于西洋畫科的課程記載如下:“西洋畫科第一學年專門習木炭畫,寫石膏像,并授以油繪靜物和郊外寫生……第二學年,用模特兒作木炭人體寫生……第三四學年,教授油繪寫生,人體以外還練習靜物和野外寫生。”[12]由此可見,胡根天在設置西洋畫系教學課程安排時,是參照了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的課程安排,而東京美術學校的課程安排據劉海粟觀察又是和法國巴黎學院一樣(9)劉海粟在《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中寫道,“(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所有的制度和辦法差不多和法國巴黎學院一樣”,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第84頁。,可見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西洋畫科課程安排是和當時世界美術教育相接軌的西畫教學方式。
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教師的選聘以留學歸國的西畫教師為主,雖則教師中早期以留學日本的居多,但同時兼顧聘任有留學歐美背景的西洋畫教師。胡根天十分了解當時中國人在海外留學學習西洋畫的情況,他在《西洋繪畫在中國的發展》一文中就對這一情況進行了說明:“民國成立之后,到外國留學的風氣,近則日本,遠則歐美,一時真有風起云涌之概,學習西洋繪畫的也不乏其人。最初十余年間,由日本歸國的西洋畫家……華南有陳丘山、許敦谷、譚華牧、何三峰、陳士潔、關良、丁衍庸諸先生……由美洲歸國的華南有梁鑾、馮鋼百、劉博文、趙雅庭、黃潮寬、朱炳光、梅侖昆、余本、李秉諸先生。由歐洲歸國的,華南有李超士、林風眠、陳宏、關金鰲諸先生。他們學成陸續歸來之后,一面各以其自己的作品公開展覽,作為新繪畫的介紹;一面又多數從事于藝術教育,以栽培國內有志于西洋繪畫的青年。”(10)胡根天:《西洋繪畫在中國的發展》,見廣州市文史研究館編《胡根天文集》,2002年,第103頁。所以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在教師中既有留日的譚華牧、何三峰、陳士潔、關良等,也有留學歐美的馮鋼百、趙雅庭等人。這些教師深受現代西洋畫的影響,如馮鋼百畫風具有扎實的學院派古典風格,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廣東畫壇,曾被視為油畫藝術的“正宗”。胡根天與何三峰畫風絢爛,近于印象派;譚華牧則更進一步,畫風凌厲接近野獸派;關良畫風則傾向于稚拙單純,充滿現代意味。對這些現代主義的西洋畫畫風,校長胡根天也是了如指掌,他曾追述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初期西洋畫畫風的發展軌跡:“大概由民國初年至十五六年,寫實主義和印象主義,差不多完全支配了西洋繪畫整個畫壇,十五六年以后,則后期印象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或先或后,增加了不少活動。這大概跟西洋方面的藝術潮流相一致的,不過還未達到充分發展的境地而已。”(11)胡根天:《西洋繪畫在中國的發展》,見廣州市文史研究館編《胡根天文集》,2002年,第104頁。這說明活躍在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教師的繪畫風格是和當時世界西洋畫發展潮流相呼應的。這些教師以所學新洋畫帶領學生進行寫生、構圖等洋畫教學活動,更新了西洋畫在民眾心目中的認識,使廣州地區的西洋畫面貌煥然一新。這正如胡根天所說的:“這樣,西洋美術的啟蒙運動使社會上漸次普遍地開展了一個新局面,過去只懂得臨摹抄襲的錯誤認識被扭轉過來了。”[9]78
這些在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并存的風格各異的畫風也對學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廣州市立美術學校首屆西洋畫科畢業生趙世銘這樣回憶當時各位教師的繪畫教育內容:“何三峰的作風傾向當時風靡世界的法國印象派,譚華牧更跨進一步,接近后期印象派與野獸派之間簡練清麗的風格,陳士潔較為保守,技巧亦遜一籌,不若何、譚兩人之純熟多變化,但他們都是科班出身,受過嚴格訓練。令我們觀感一新,和馮鋼百老師的穩厚華滋、千錘百煉、大家典范的寫實作風大異其趣。換一句話說,馮老師的大作,仿佛高不可攀,只許仰止,難以繼蹤。反之,后者清新可喜,平易近人。比較之下,使我們進一步認識藝術風格的衍變,與藝術流派的多彩多姿。這個展覽會在同學間播下革命性的種子,茁發了傾向自由奔放的嫩芽,吳琬(子復)對之尤為傾倒,影響一生,至死不渝。”[10]571922年考入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學習西洋畫,畢業后留校任教的吳琬也回憶說:“以印象派的作風,在畫面上運用著絢爛的閃耀的色彩的何三峰現實的風景;以后期印象派作風,表現物體的內在的真實的譚華牧先生的人物,卻給市立美術學校的學生以很深的影響……他們對于自己的老師馮鋼百先生也懷疑起來。”[1]這就使廣州洋畫界的藝術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現代主義成為洋畫的主流藝術傾向。美術史學者陳跡曾對此做了至為恰當的評論:“20世紀中后期,留學日本的何三峰、譚華牧、丁衍庸、關良、許敦谷等,以及留學法國的陳宏、留學墨西哥的趙雅庭等,亦都先后受聘為廣州市立美術學校西洋畫教授;該校還聘請了陳之佛以及‘決瀾社’的龐薰琹、倪貽德等來校任教;本校第一屆畢業生吳琬、李樺等也相繼成為該校青年教師。至此及稍后一段時期,在廣州的洋畫界,現代主義繪畫——尤其是帶有東方情調的類野獸主義風格的‘新派繪畫’,幾欲壓倒原來的‘官學派或保守主義’,而成主流。”[13]
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學生受益于兼容并包、多元開放的學習風氣,繪畫水平得以不斷提升,而且對西洋畫的追求也趨向于現代性。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學生很快在當時全國性的美術展覽中取得佳績,據趙世銘回憶:“一九二九年四月在上海舉行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辦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中,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師生獲選展出者多人,作品在特刊揭載者共六人,都是西洋畫,計丁衍庸《女士讀書圖》、馮鋼百《肖像》(圖6)、梅雨天《隆冬》(圖7)、許敦谷《肖像》、陳宏《歐婦》、何三峰《畫室之中》。第二次全國美展,則于八年后(1937)四月一日起在首都(南京)新建之美術陳列館揭幕……市美師生,西畫入選者九人,圖案四人,雕刻二人。”[10]97-103廣州市立美術學校還培養了如趙獸、梁錫鴻、李樺、吳琬等一批在全國都具有影響力的美術人才。1927年,廣州市立美術學校西洋畫系首屆畢業生李俊英(李樺)、吳琬(吳子復)、趙世銘組成青年藝術社,宗旨是要“為藝術而努力,用方剛的血氣去開拓新藝術領域,反對守舊因循的態度”,力圖推動現代藝術發展。20世紀30年代中期成立的先鋒美術團體“中華獨立美術協會”,骨干成員如趙獸、梁錫鴻、李仲生等,也曾經就讀于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受該校青年教師藝術思想和新派繪畫的影響,走上了比師輩更新潮的藝術風格追求道路。

圖6 馮鋼百《肖像》(12)見《上海漫畫》1929年第52期。

圖7 梅雨天《隆冬》(13)見《美展》1929年第6期。
六、結語
這樣,通過現代主義西畫的展覽和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創辦,廣州的西洋畫教育和藝術創作面貌得以改觀,真正的西畫教育得以普及和提倡,現代主義西畫創作大行其道,洋畫實現了再造,對華南乃至中國的西畫教育都產生了重要影響。1928年的《青年藝術》就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市美的出世,是應時代的要求的。她不特是南方美術界的中樞,同時也是畫壇的燈塔。她的降生,便是真藝術和假藝術的分野時期。她一方面訓練出一班藝術界的新殿軍,同時更給人們以認識藝術的標的。所以她在廣東的藝術運動,以至在南方的藝術運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無可懷疑了。”[14]同時,廣州市立美術學校還帶動了廣州畫壇的現代轉變,可謂是廣州現代藝術發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嶺,不僅在廣州確立了純粹藝術的西畫標準,還以培養的學生為根基催生了華南乃至全國現代美術社團的建立,其中以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畢業學生李樺、吳琬、趙世銘于1927年創辦的青年藝術社以及李樺、賴少其等于1934年創辦的現代創作版畫研究會最具影響力。
如果將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放置于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美術教育的版圖及洋畫運動的發展格局上來看,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則更是與上海一樣為中國現代藝術教育的一極。如當代美術史家評價所言:“胡根天主持下的市美格局,實際上是當年在東亞地區已初具規模的現代美術活動網絡的一個成功實踐,自20年代初開始,廣州、東京、上海三個東亞都市開始將引進西方現代美術體制的實踐活動逐步推向高潮,三個城市間出現頻為活躍的聯動現象。20世紀初在東京等地學成歸來的留學生紛紛謀職于上海和廣州的美術院校,他們開始制度化、規模化地介紹西方美術觀念和藝術生產方式。由此,滬穗兩地率先發展成為推動中國現代藝術發展的兩個最重要基地。”[15]當我們回顧百年前中國美術教育的發展和洋畫運動時,廣州的美術先驅者的西畫展覽和再造洋畫的教育活動至今仍值得我們去再度探索,尋求先輩們那種篳路藍縷推廣現代美術精神、立中研西探索時代美育路線,而這樣的時常回望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百年歷程也能帶給我們對當下美術教育的思索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