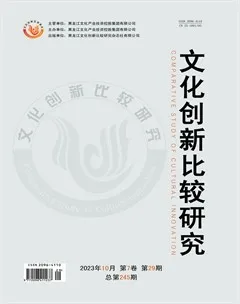鄂豫皖蘇區(qū)紅色歌謠的教育功能探析
王婧宇,宋南南
(鄭州工業(yè)應(yīng)用技術(shù)學(xué)院,河南鄭州 451100)
紅色歌謠是紅色基因的一部分,并且在鄂豫皖蘇區(qū)革命根據(jù)地創(chuàng)建之初,革命領(lǐng)導(dǎo)人運(yùn)用其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取得了顯著效果。本文全面分析了鄂豫皖蘇區(qū)紅色歌謠的產(chǎn)生、興起及發(fā)展,對現(xiàn)代紅色教育的開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 興起:紅色歌謠產(chǎn)生原因
紅色歌謠是語言的藝術(shù)。“每種藝術(shù)作品都屬于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環(huán)境,依存于特殊的歷史和其他的觀念和目的。”[1]紅色歌謠產(chǎn)生并興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是傳統(tǒng)歌謠是當(dāng)?shù)厝嗣駣蕵飞畹囊徊糠郑踉ネ畹貐^(qū)的人民普遍喜歡唱山歌;二是當(dāng)時人民革命意識比較薄弱,通過紅色歌謠可以對人民進(jìn)行思想教育。鄂豫皖蘇區(qū)早期革命領(lǐng)導(dǎo)人有成仿吾、沈澤民等,他們多是知識分子出身,學(xué)習(xí)了蘇維埃俄國利用文藝進(jìn)行思想宣傳的方法,為此深入民間進(jìn)行文藝挖掘成了他們的主要活動。為了尋找到合適的方式進(jìn)行宣傳,他們主動融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找到了當(dāng)?shù)孛耖g文藝形式——歌謠。
將革命意識形態(tài)融入歌謠中是出于現(xiàn)實(shí)考量。鄂豫皖邊區(qū)長期受封建統(tǒng)治體制機(jī)制的影響,加之地處偏遠(yuǎn),當(dāng)時90%的群眾都沒有接受教育的機(jī)會,文盲占據(jù)總?cè)丝诘慕^大多數(shù),如果想實(shí)施“農(nóng)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quán)”的策略,就需要取得廣大工農(nóng)群眾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支持。“鄂豫皖地處大別山系,交通閉塞,文化落后,群眾文化活動僅限于當(dāng)?shù)貏谧鲿r唱唱山歌、田歌,參與較為簡單的民間舞蹈及花鼓、咳子和花籃等地方小戲。”[2]由此可以看出,對于鄂豫皖蘇區(qū)人民群眾來說,歌謠是為數(shù)不多且深受人民喜愛的娛樂活動之一,民歌滲透在大別山區(qū)人民群眾的生活中,以山歌、茶歌、秧歌、排歌、小調(diào)、勞動號子為主。原始歌謠是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反映,有著屬于自己的優(yōu)勢,比如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因此,即便當(dāng)時大部分的群眾是文盲,大家也能夠比較快地聽懂、學(xué)會歌謠。在表達(dá)方式上,歌謠不僅不受時間、地點(diǎn)的限制,更不需要借助外在的樂器。對于地處大別山區(qū)鄂豫皖蘇區(qū)的人民群眾來說,歌謠已經(jīng)成為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中抒發(fā)情感、娛樂身心的一種重要方式。革命領(lǐng)導(dǎo)人尋找到了可以用來進(jìn)行思想教育的藝術(shù)形式,如何運(yùn)用歌謠對人民群眾進(jìn)行革命思想教育是需要進(jìn)一步思考的問題。
2 嵌入:教育組織對歌謠的規(guī)約
傳統(tǒng)歌謠在革命意識表達(dá)方面相對比較薄弱。一方面,為了更好且有效地傳播革命思想,鄂豫皖蘇區(qū)革命領(lǐng)導(dǎo)人通過“舊瓶裝新酒”方式,衍生出富有革命思想的歌謠。革命歌謠保留著原有藝術(shù)風(fēng)格,并且革命話語的轉(zhuǎn)換符合當(dāng)?shù)卣蝿訂T的需要,用一種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進(jìn)行群眾教育。例如在鄂豫皖蘇區(qū)廣泛傳唱的紅色歌謠 《八月桂花遍地開》。“《八月桂花遍地開》脫胎于傳統(tǒng)民歌《八段錦》,但卻超越了原歌中的男歡女愛,原歌詞中的‘小小鯉魚壓紅腮,上游游到下呀下江來’在新歌中被改造成‘八月桂花遍地開,鮮紅的旗幟豎呀豎起來’”[3]。通過《八月桂花遍地開》這首歌謠可以看到,歌謠主題已經(jīng)發(fā)生明顯變化,原歌描寫男女之間的兩情相悅,但是通過融入革命思想,革命歌謠主題由兩情相悅“小我”升級為現(xiàn)身革命事業(yè)的“大我”。
另一方面,蘇區(qū)政權(quán)建設(shè)是我黨高度重視的問題,蘇區(qū)順利的建立與發(fā)展,前提是革命思想能夠得到人民群眾認(rèn)可。為此早期革命領(lǐng)導(dǎo)人收集傳統(tǒng)歌謠,并運(yùn)用行政手段推動傳統(tǒng)歌謠接受革命理念的規(guī)約,后通過報刊、課本,以及宣傳手冊等進(jìn)行傳播。鄂豫皖蘇區(qū)革命根據(jù)地前后創(chuàng)辦了《紅安青年》《群眾》《戰(zhàn)斗報》《蘇維埃三日刊》等,這些報刊上刊載了大量的歌謠之類的文藝作品,對革命思想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群眾、紅軍戰(zhàn)士和黨的領(lǐng)導(dǎo)人創(chuàng)編的革命歌謠,對宣傳革命思想、教育群眾起到了重要作用。“分田又分地,自種又自吃,讀讀文化課,唱唱革命歌,看看革命報,大家真快樂”真實(shí)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群眾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開展土地革命、傳唱革命歌、讀取革命報的喜悅心情。眾多革命報刊的發(fā)行無疑對革命歌謠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4]。革命領(lǐng)導(dǎo)人為了最大范圍地進(jìn)行思想教育,通過革命思想對歌謠進(jìn)行規(guī)約,在不改變原有的曲調(diào)的前提下將革命思想與歌謠相融合,人民也在傳唱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滌。
3 探析:紅色歌謠所具有的功能
語言的講述過程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一定的思想觀念為導(dǎo)向,因此紅色歌謠在其傳播過程中也總是以一定的功能為導(dǎo)向。
3.1 辨析真假——鄂豫皖蘇區(qū)紅色歌謠中的評價功能
評價功能主要涉及兩方面: 一是解釋我黨的方針、政策; 二是敵對方會通過言語對我黨進(jìn)行“抹黑”,為此可以通過歌謠來進(jìn)行辯護(hù)。
革命戰(zhàn)爭時期,被農(nóng)民運(yùn)動嚇跑的豪紳地主紛紛返鄉(xiāng),與反動派進(jìn)行勾結(jié),對革命人民進(jìn)行了反撲。國民黨反動派不僅傳播反革命思想,還進(jìn)行欺騙宣傳。革命領(lǐng)導(dǎo)人通過歌謠拆穿反動階級的虛假政策,并同時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一切為了人民大眾的思想。曾任黃安縣委員會、赤衛(wèi)隊(duì)黨代表的吳煥先,經(jīng)常領(lǐng)導(dǎo)游擊隊(duì)夜襲敵人的駐地,機(jī)智勇敢地同敵人展開斗爭。
3.2 激發(fā)斗志——鄂豫皖蘇區(qū)紅色歌謠中的激勵功能
革命領(lǐng)導(dǎo)人進(jìn)一步通過紅色歌謠動員人民群眾參與革命斗爭。如1927 年11 月13 日,黃麻兩縣的農(nóng)民武裝匯集了兩萬余人的起義大軍正式?jīng)Q定武裝奪取黃安縣城:“暴動暴動! 工農(nóng)打先鋒,拿起刀和槍,一同去進(jìn)攻! 暴動暴動! 哪怕白匪兇,拼出一條命,勇敢向前沖! ”50 年后,許世友將軍在回憶黃麻起義時說道:“在慷慨激昂的銅鑼聲中,浩浩蕩蕩的起義大軍唱著暴動戰(zhàn)歌出發(fā)了。”[5]人民在這首紅色歌謠的指導(dǎo)下,順利奪取了黃安城。
紅色歌謠的動員功能更為突出的一點(diǎn)是能夠成功地瓦解敵人,如《槍會革命歌》:“槍會學(xué)友們,窮苦的工農(nóng),這世界少不得要推翻。要我做苦工,逼我把崗站,人人長吁又短嘆。可憐我,窮人們,缺油又?jǐn)帑},肚子癟連連那來力氣干? 槍會學(xué)友們,窮苦的工農(nóng),要想出頭除非是共產(chǎn)。”[6]用于瓦解敵人、反動派的歌謠還有《槍會革命歌》《兵士歌》《十一連嘩變》《兵嘆歌》《勸告白軍士兵歌》等歌謠。
3.3 堅定信仰——鄂豫皖蘇區(qū)紅色歌謠中的導(dǎo)向功能
鄂豫皖蘇區(qū)紅色歌謠中的導(dǎo)向功能就是為所有成員指出前進(jìn)的目標(biāo)和方向。如歌謠:“蘇區(qū)好呀好風(fēng)光,革命紅旗到處揚(yáng),農(nóng)民協(xié)會建起來,(伙計兒)窮苦人民把家當(dāng)。蘇區(qū)好呀好風(fēng)光,工友農(nóng)友齊武裝,男的參加赤衛(wèi)隊(duì),(伙計兒)女的扛槍去站崗。蘇區(qū)好呀好風(fēng)光,勞動歌聲震天響,金谷銀花鋪滿畈,(伙計兒)豐收增產(chǎn)支前方。蘇區(qū)好呀好風(fēng)光,男男女女斗志昂,為了創(chuàng)造新世界,(伙計兒)永遠(yuǎn)跟著共產(chǎn)黨。”[7]這首歌謠描繪的場景反映出鄂豫皖蘇區(qū)革命根據(jù)地創(chuàng)建前后人民群眾對未來生活抱有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在根據(jù)地成立之前,他們對未來多生活是恐懼之感,創(chuàng)建之后,他們對未來生活多是憧憬之情。
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組織的不斷發(fā)展,革命趨勢一路向好,人民群眾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物質(zhì)上都得到保障,為此人民發(fā)自內(nèi)心地唱出:“工農(nóng)兵士都是一家人,一條戰(zhàn)線要抱緊,帝國要打倒,軍閥一掃清,土劣貪官,無處逃生。殺盡敵人駐地革命成,社會一切皆平等,各有房屋住,各有田地耕,飽食暖衣,人人翻身。共產(chǎn)主義一定要實(shí)行,社會步步向前進(jìn),人人生產(chǎn)好,處處建設(shè)新。階級消滅,世界和平。那個時節(jié)不分工農(nóng)兵,整個都是自由民,黃金的世界,神仙的光景,快樂逍遙,一言難盡。”[8]從這首歌謠中我們可以看出,通過革命思想教育人民群眾已經(jīng)從心底里,將思想內(nèi)化于心、外化于行。
4 鄂豫皖蘇區(qū)紅色歌謠的當(dāng)代啟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xí)近平總書記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要用好紅色資源,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9]。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探析紅色歌謠在傳播過程中的功能,具有增強(qiáng)文化自信、推動宣傳工作等多重意義。
4.1 增強(qiáng)文化自信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紅色歌謠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時代精神的融合體。一方面,紅色歌謠是傳統(tǒng)歌謠與革命思想的“衍生物”,它之所以生動是因?yàn)樗哂懈锩枷搿A硪环矫妫t色歌謠的曲調(diào)、用詞等依舊保持著民間文化傳統(tǒng),是一種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藝。文藝作為上層建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精神。經(jīng)典文藝作品是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的凝練、是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寫照,是時代的烙印與特征。紅色歌謠是時代的文藝,傳唱紅色歌謠有助于人民了解革命歷史、弘揚(yáng)紅色精神、傳承紅色精神,更好地傳承和創(chuàng)新革命文化。例如,當(dāng)時鄂豫皖蘇區(qū)流行一首紅色歌謠《黃安謠》,這首歌短小精悍,反映了黃麻戰(zhàn)役中,人民踴躍參加革命、支持革命的盛況,體現(xiàn)出萬眾一心的團(tuán)結(jié)精神和舍生忘死、不怕犧牲的紅安精神。還有《八月桂花遍地開》折射出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精神,反觀當(dāng)今,我們同樣可以沿用文化與思想教育相結(jié)合的方式,充分發(fā)揮文化育人實(shí)效。
4.2 助力宣傳工作
首先,紅色歌謠所蘊(yùn)含的傳統(tǒng)文化及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豐富的內(nèi)容和資源借鑒。其次,紅色歌謠之所以能夠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與革命,主要原因在于通俗易懂。2016年歌曲《馬克思是個九零后》以短視頻的方式在社交網(wǎng)站上被點(diǎn)贊和轉(zhuǎn)發(fā),該歌曲同紅色歌謠的產(chǎn)生有異曲同工之處。在傳播方式上,它的曲調(diào)朗朗上口,歌詞通俗易懂。在傳播內(nèi)容方面,它把馬克思的生平事跡、一生功績通過搖滾和說唱的方式講述出來。對于馬克思及其理論思想,部分人會有先入之見,但是通過傳唱《馬克思是個九零后》,其他群體和90 后群體的距離在無形之中被拉進(jìn),人們了解馬克思生平、學(xué)習(x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愿望被激發(fā)。在華東理工大學(xué)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將《馬克思是個九零后》作為案例用于課堂導(dǎo)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如一位同學(xué)所說,“這種歌曲的傳播形式既能被年輕人接受,又能使年輕人產(chǎn)生共鳴”。
4.3 促進(jìn)紅色文化轉(zhuǎn)型
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傳承紅色基因,實(shí)現(xiàn)紅色文化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一是要傳承,二是要創(chuàng)新。
一方面,以傳統(tǒng)文化為精神力量供給,助力革命斗爭。在鄂豫皖蘇區(qū)革命根據(jù)地,歌謠是民間傳統(tǒng)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革命領(lǐng)導(dǎo)人的號召和動員之下,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地搜集、整改、傳播紅色歌曲,在潛移默化之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革命領(lǐng)導(dǎo)人通過紅色歌謠助力革命斗爭,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我們要通過汲取鄂豫皖蘇區(qū)紅色歌謠的產(chǎn)生、傳播等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增強(qiáng)紅色文化的吸引力,通過文化凝聚人心。另一方面,鄂豫皖蘇區(qū)開發(fā)了以報刊歌本、宣傳隊(duì)、課堂教學(xué)等為代表的多樣化的紅色歌謠宣傳載體。在新時代背景下,紅色文化應(yīng)努力通過報刊、期刊等載體的大眾媒體傳播,以大中小課堂為載體的課堂傳播,以短視頻等為載體的新媒體傳播,以宣傳部門為載體的組織傳播等多種形式的、全面立體的傳播方式,使廣大人民群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紅色文化的熏陶[10]。
5 結(jié)束語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是紅色歌謠得到人民喜愛,且在傳播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關(guān)鍵點(diǎn)。首先,從形式上,紅色歌謠保留了傳統(tǒng)歌謠的藝術(shù)特征,所以它能夠獲得群眾的喜愛;其次,從內(nèi)容上,蘇區(qū)領(lǐng)導(dǎo)人對革命歌謠的革命話語進(jìn)行了重建,內(nèi)容既有理性的認(rèn)識,同時滿足情感的需要;再次,從效果上,歌謠成功動員和教育了群眾,建立了代表最廣大工農(nóng)群眾利益的蘇維埃政權(quán)。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jìn)入新時代,紅色歌謠所具有的傳播經(jīng)驗(yàn)依舊對當(dāng)代文化傳播與創(chuàng)新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