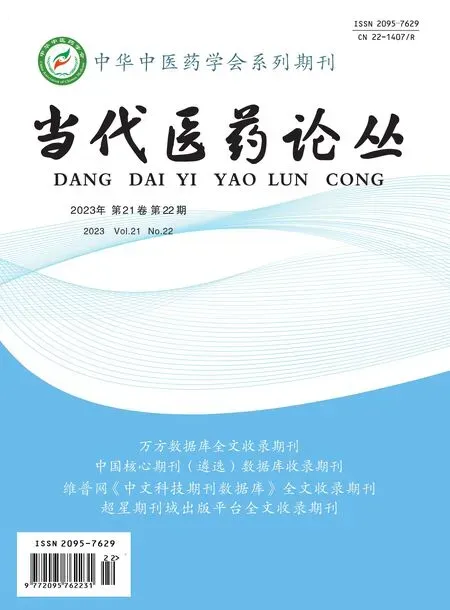早期胃癌診斷的研究進展
張文麗,黃明海,羅雪梅
(1.吉首大學,湖南 吉首 416000 ;2.吉首大學第四臨床學院,湖南 懷化 418000)
胃癌(Gastric cancer,GC)是一種消化系統惡性腫瘤,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細胞的惡性增生。本病具有高患病率和高致死率。統計數據顯示,2020 年GC的發病率排名第五,致死率排名第四,亞洲報告的GC 發病率和致死率在全球最高[1]。EGC 定義為GC病變僅發生在黏膜或黏膜下層,未侵犯固有肌層,無論病變的大小或是否發生淋巴結轉移。大量研究表明,GC 患者的預后與臨床分期有關,EGC 患者的5年生存率高達90%,而晚期GC 患者的5 年生存率大約只有10%[2]。研究顯示,在我國GC 中,EGC 僅占約10%,大多數發現時已處于進展期,相較于GC 同樣高發的日本,我國GC 患者的總體5 年生存率僅有20%(日本5 年生存率達60%)[3-4]。早期篩查及內鏡下切除病灶是日本GC 患者存活率高的重要原因。GC的篩查方法包括血清腫瘤標志物檢查、內鏡檢查等。本文對EGC 的診斷方法進行了總結,以期為臨床診治GC 提供參考。
1 血清學檢查
血清學檢查在早期發現和診斷GC 方面具有操作簡單、安全性高、非侵入性等特點,因此,在GC 的早期篩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就GC 早期診斷的血清學檢查方法進行總結。
1.1 傳統的血清腫瘤標志物
癌胚抗原和傳統的血清腫瘤標志物,包括糖類抗原72-4(CA72-4)、糖類抗原19-9(CA19-9)、糖類抗原15-3(CA15-3)和糖類抗原12-5(CA12-5),主要在GC 的治療監測和預后評估中發揮作用,而不是早期發現或篩查[5]。雖然在GC 中可以發現CA72-4、CA19-9 等血清腫瘤標志物水平升高,但它們既不敏感,也無特異性,并且通常是在晚期GC 中升高[5]。
1.2 血清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PG)
PG 包括兩種同工酶原, 即胃蛋白酶原Ⅰ(Pepsinogen Ⅰ,PG Ⅰ)、胃蛋白酶原Ⅱ(PepsinogenⅡ,PG Ⅱ),二者分別在胃的不同部位產生[6]。PG Ⅰ僅由胃底的主細胞分泌,而PG Ⅱ可由胃的各類腺體以及十二指腸布氏腺產生。血清PG 升高是胃萎縮的標志,而不是GC 的標志,但考慮到胃腺癌主要是在GC 癌前病變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可以認為PG是GC 風險的間接標志。在日本,GC 篩查的標準廣泛認同為PG Ⅰ≤70 μg/L 且PG Ⅰ/PG Ⅱ比值(PGR)≤3.0,其診斷萎縮性胃炎的敏感性達80%、特異性達70%[7]。我國關于PG Ⅰ、PGR 用于EGC 篩查的最佳臨界值仍未統一,主要在于血清PG 水平受研究對象的生活方式、生活環境、年齡、性別及幽門螺桿菌感染等因素影響有關[8]。但與國外研究一致的是,血清PG Ⅰ和PGR 水平下降提示患者有較高的GC 患病風險。
1.3 血清胃泌素(Gastrin,GAS)
GAS 主要由胃竇的G 細胞和十二指腸近端黏膜細胞產生,其中絕大部分為胃泌素17(Gastrin-17,G-17),因此可以通過檢測血清G-17 水平推測GAS水平[9]。G-17 通過刺激胃酸分泌(主要是對低胃酸水平的反應)和維持胃黏膜穩態在胃生理中發揮重要作用[10]。有研究表明,慢性萎縮性胃炎引起的胃內pH 值升高可能來自胃竇的G-17 分泌過多[11]。有報道稱,GC 患者的血清G-17 水平高于非GC 患者[12]。因此,血清G-17 水平升高通常被用于識別GC 高危人群。
1.4 新ABC 法
聯合檢測血清PG、G-17 被稱為“新ABC 法”。新ABC 法對比單項指標檢測在GC 的診斷中敏感性、特異性和準確率均更高[13]。陳卿奇等[14]研究表明,血清中PG Ⅰ、PG Ⅱ、PGR 和G-17 聯合檢測診斷GC 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達到了83.7% 和76.8%。因此,聯合檢測這些指標可以提高GC 的陽性診斷率,從而提升GC 患者的治療效果和預后。
2 內鏡診斷
目前,臨床診斷GC 的金標準為內鏡及內鏡下組織病理活檢。近年來隨著內鏡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EGC 的檢出率有了顯著提高。這些技術可使胃黏膜成像更加清晰,幫助醫生檢測和診斷EGC,從而及早發現潛在的病變并采取相應的治療手段。
2.1 白光內鏡(Whitelightendoscopy,WLE)
WLE 是臨床診斷EGC 的主要方法之一。WLE可以觀察EGC 病灶表面的色調、邊界、形態、顏色、腸上皮化生和(或)萎縮、自發性出血、潰瘍、白色不透明物質等特征,輔助EGC 的診斷[15]。研究表明,WLE 診斷EGC 的敏感性、特異性和準確性分別為57.33% ~71.2%、50.00% ~99.1% 和25.58% ~97.1%[16]。盡管WLE 的分辨率有限,但其操作簡便,適用于快速篩查可疑病變,能夠為發現EGC 提供線索,并且臨床上可以結合染色內鏡等檢查進一步明確病變性質,避免資源浪費[16]。
2.2 色素內鏡
色素內鏡是指內鏡檢查時將染色劑或染料配置成一定濃度的溶液對消化道黏膜進行染色,以提高組織的可視化、表征和診斷可靠性的一種內鏡檢查方法。染色劑或染料溶液分為可吸收性的、造影劑的和活性的。吸收性的染色劑被胃腸道的特定上皮細胞吸收。造影劑染色不被吸收,而是聚集在黏膜縫隙中,突出組織的形態和黏膜的不規則性。活性染色劑能夠根據組織內的化學環境作出反應,并依據酸性或堿性發生顏色變化。常用內鏡染料有亞甲藍、靛胭脂、剛果紅、酚紅、醋酸等[17]。在日本,主要使用亞甲基藍的色素內鏡技術用于早期發現胃部病變[18]。大量研究顯示,在診斷EGC 和GC 癌前病變方面,色素內鏡比標準WLE 具有更高的準確率、特異性及敏感性[17]。
2.3 電子染色內鏡
2.3.1 窄帶成像技術(Narrow band imaging,NBI)NBI 利于黏膜表面的檢查,在胃鏡檢查特別是EGC 的診斷中應用廣泛。其原理是:光的穿透深度與波長有關,波長越短,穿透越淺,形成了胃黏膜表面的對比度,有利于胃黏膜細節的可視化[19]。有研究表明,NBI 對GC、胃腺瘤、腸化生等局灶性胃部病變有很好的鑒別價值,特別是在結合光學放大的情況下[19]。有研究報道,放大內鏡結合窄帶成像(ME-NBI)診斷EGC 的敏感性在60% ~97% 之間[20]。
2.3.2 富士能智能電子分光技術(Fuji intelligent chromoendoscopy,FICE) FICE 是新開發的計算虛擬色素內窺鏡系統,可按波長分解圖像,然后直接生成具有增強黏膜表面對比度的重建圖像。FICE 可以識別胃部病變,精確測量病變的大小,獲得高質量的形態學診斷依據。FICE 通過可改變入射光的波長范圍來控制光線的穿透程度,將接收到的光譜信息進行圖像合成,觀察胃黏膜表面的細微結構,不需要使用染色劑,且操作簡單,可見黏膜下血管[18]。研究表明,FICE 可清晰觀察胃黏膜病變與正常組織的界限,結合放大內鏡(ME)可提高EGC 的診斷準確性[21]。
2.4 超聲內鏡(Endoscopicultrasonography,EUS)
EUS 是一種將內鏡與超聲結合在一起的診斷技術,能夠借助高頻超聲探頭直接觀察胃黏膜的形態結構,并具有放大功能,可以發現微小病灶[22]。EUS 可以在圖像上顯示整個胃壁層,是預測GC 浸潤深度最準確的工具。與常規內鏡相比,EUS 具有更高的診斷敏感性、特異性和總體準確性。特別是在特異性方面,EUS 比傳統內鏡具有更顯著的診斷優勢(83.3% 比59.8%)[23]。研究表明,EUS 有助于GC 的檢出和分期,為患者治療方案的制定和預后評估提供依據。
2.5 共聚焦激光顯微內鏡(Confocallaserendomicroscopy,CLE)
CLE 是一種全新的顯微內窺成像技術,可在內鏡檢查的同時進行組織學診斷,因此也被稱為“光學活檢”[24]。CLE 對GC 的早期診斷起著重要作用。但CLE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探測深度僅能掃描至黏膜層,不利于診斷EGC 的浸潤深度[21]。一項系統回顧和薈萃分析結果表明,CLE 診斷EGC 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達到了91% 和99%。
2.6 自體熒光內鏡
自體熒光內鏡是利用特定波長的光照射組織,使腫瘤細胞組織和周圍正常細胞組織發射出不同光譜,從而得到成像結果。自體熒光內鏡分為外源性和內源性兩種熒光內鏡[25]。內源性熒光內鏡利用人體的熒光基團,在特定波段的照射下自發產生熒光的原理使癌變組織在成像結果中呈現紅色,而正常組織則呈現綠色。這是基于癌變組織與正常組織在熒光特性上的差異[25]。戈之錚等[26]研究指出,使用自體熒光內鏡技術可將消化道早期癌的檢出率提高至86.7%。自體熒光內鏡技術在指導臨床活檢方面也具有較高的精準性,對于提高EGC 的檢出率至關重要。
3 小結
GC 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和致死率,是一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早期治療是降低GC 患者死亡率的關鍵。然而,目前我國的EGC 診斷水平相比一些發達國家仍有明顯差距。積極發展與提高GC 的早期診斷技術對于提升我國GC 患者的生存率至關重要。臨床對于EGC 的篩查需要進一步探索,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準確識別EGC 并及時予以治療,最大限度地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