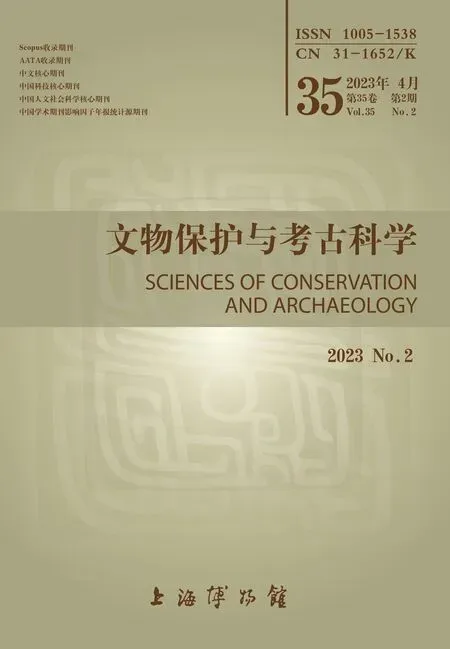旬邑上廟遺址出土馬具附著有機殘留物的科學研究
李昱珩,楊 璐,葛若晨,豆海鋒
[1.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陜西西安 710127; 2. 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西北大學),陜西西安 710127]
0 引 言
旬邑西頭上廟遺址位于陜西省咸陽市旬邑縣張洪鎮原底社區以西[1],2020年,該遺址發掘出一座墓葬,編號2020XXSM39,經14C測年,約為南北朝至初唐時期。墓室棺木西側出土了銜鑣、鞍橋、雙鐙等多件鎏金青銅質地馬具配件,是陜西地區首次發現的較為完整的南北朝至初唐馬具遺存,對研究我國古代馬具的工藝及形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騎馬之風自魏晉南北朝起在民間傳播開來,隋唐時期逐漸興盛[2],馬具的發展與完善是這一社會現象的基礎。我國古代馬具中的轡頭構件目前最早發現于殷商時期,至東周已較為成熟,而鞍具的出現與改進則與騎兵的發展息息相關。馬鞍最早出現于戰國末年,至西漢末年漸漸演化出高鞍橋形式的馬鞍[3],而同一時期,作為輔助上馬工具的早期馬鐙也以單件的形式開始使用。東晉時期,鞍具進一步發展,雙鐙出現并被推廣使用,為之后鮮卑式、突厥式等不同式樣馬具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因此,南北朝至唐初出土的鎏金青銅馬具是我國古代馬具從發展至完善這一過渡歷程的重要實物資料,對其工藝的分析是探究我國古代馬具與馬飾發展的關鍵內容。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包括:劉斌對北朝時期甲騎具裝的演變進行了梳理,總結了甲騎具裝的發展脈絡[4];張寧總結了馬鞍的起源與構造,分析了陜甘地區所出土馬鞍的時代特點[5];王浩天等對洛陽漢墓出土的鐵質馬具進行了修復保護,并使用離子色譜儀、掃描電子顯微鏡、X射線衍射儀等對馬具的金屬銹蝕進行了科學檢測[6];張曉嵐等對出土于內蒙古的遼代馬具皮條進行研究,使用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了樣品的顯微形貌[7]。然而,由于出土時較為完整的馬具罕見,且文物有機殘留物樣品珍貴,我國在馬具有機質構件工藝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本工作以旬邑出土的青銅馬具表面附著的有機殘留物為研究對象,運用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儀、掃描電子顯微鏡、超景深三維視頻顯微系統等進行科學研究,以期探明其工藝及特征,為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中原地區馬具的研究提供線索,并為該類文物的保護修復提供參考。
1 實驗部分
1.1 樣品描述
如圖1所示,馬具部分銅質構件如卡帶、帶扣、金花等表面附著有紡織物與黑色殘留物。實驗樣品取自編號B-C1-2的青銅卡帶內表面(圖1a),其中黑色殘留物H1糟朽嚴重,無法辨認其特征,而紡織物F1層則保存相對完整,可通過肉眼辨識編織痕跡。樣品情況詳見圖2。圖2a為50×倍率下紡織物樣品及黑色殘留物樣品的表面形態,可見H1邊緣干燥略卷曲,表面無光澤,而F1呈棕黃色,附著于皮革內側。圖2b為50×倍率下紡織物樣品及黑色殘留物樣品截面結構,可見織物與皮革結合較為緊密,并通過測量得到紡織殘留物厚度約為0.58~0.71 mm,黑色殘留物厚度則約為0.40~0.51 mm。在考古發掘過程中,使用手術刀和鑷子于第一時間對出土馬具上的黑色殘留物及紡織物提取采樣,并將H1與F1剝離。

圖1 出土青銅文物及其附著有機殘留物Fig.1 Unearthed bronze cultural relics and their attached organic matters

圖2 實驗樣品Fig.2 Experimental samples
1.2 分析方法
1.2.1紅外光譜法 使用棉簽蘸取超純水對紡織物F1表面進行簡單的清理后將其置于烘箱中干燥,按照質量比1∶150加入干燥的KBr(光譜純),并在瑪瑙研缽中混合研磨至均勻。所得粉末取100 mg在20 MPa壓力下壓制樣片,并使用德國Bruker公司生產的LUMOS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儀進行檢測。樣品與背景掃描次數:64次。波數范圍:4 000~500 cm-1。分辨率:4 cm-1。
使用超純水清洗黑色殘留物H1并低溫干燥,在ATR模式下進行檢測。樣品與背景掃描次數:32次。波數范圍:4 000~500 cm-1。分辨率:4 cm-1。
1.2.2掃描電子顯微鏡分析 提取單束紡織物樣品F1,使用環氧樹脂制作鑲嵌樣塊,拋光后噴金100 s。提取片狀殘留織物F1與黑色殘留物H1,剝離后低溫干燥。對以上樣品使用捷克Tescan公司生產的VEGA-3 XMU型鎢燈絲掃描電子顯微鏡以及FEI公司生產的Quanta FEG 450型場發射環境掃描電子顯微鏡進行觀察。模式:SE模式。電壓:10 kV、20 kV。束斑直徑:4.0 μm。
2 結果與討論
2.1 紡織品殘留物分析
2.1.1纖維種類研究 紡織物F1的紅外吸收光譜圖如圖3所示。F1的特征峰集中在1 000~2 500 cm-1,主要吸收峰位于1 045 cm-1、1 383 cm-1、1 455 cm-1以及1 626 cm-1。882 cm-1處為β-D-葡萄糖苷鍵特征吸收振動峰,1 045 cm-1為纖維素中醚鍵的伸縮振動峰,1 455 cm-1處為纖維素與木質素中—CH2—彎曲振動,1 626 cm-1處為木質素中共軛羰基和碳碳雙鍵伸縮振動重疊吸收峰[8]。麻類纖維主要由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等成分構成[9],對比標準譜庫可知,該樣品的紅外光譜圖與麻類纖維相吻合[10]。為進一步了解織物纖維信息,采用掃描電子顯微鏡對鑲嵌樣塊進行纖維橫截面的觀察。圖4b為放大倍率8000×下纖維徑向形貌,可見其表面較粗糙,有橫節豎紋,呈扁平帶狀[11]。圖4c為放大倍率4000×下樣品的截面結構,可見該束樣品由多根纖維加捻而成,纖維截面呈鈍角多邊形,空腔呈細長狀。以上特征均與大麻纖維相吻合[12]。

圖3 紡織物F1紅外光譜圖Fig.3 Infrared spectrum of Sample F1
2.1.2編織工藝研究 為探究樣品F1編織工藝,使用掃描電子顯微鏡對樣品進行觀察,圖4a為放大倍率35×下樣品形貌,可見纖維束縱橫交疊,排列較為均勻,為一經一緯的平紋編織,無圖案變化。分別測量經緯線各38組,發現緯線平均直徑略大于經線,在95%的置信度下:緯線平均直徑為(0.647±0.014)mm,標準偏差為0.043 mm;經線平均直徑為(0.468±0.011)mm,標準偏差為0.035 mm。為判斷二者差異是否顯著,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對數據進行分析[13],得到t=-19.901,P=0.000<0.05,因此在95%的置信度下拒絕H0,經緯線直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由此可見,編織F1所使用的經線與緯線存在極大可能并非同批次生產,而是分批加捻制作而成。另外,根據以上數據,計算得到紡織品經緯線密度為11根×9根/cm2。由于目前罕見漢晉時期麻類紡織物的相關研究,因此對比臺西村商代遺址出土兩塊麻布的經緯密度分別為14根×9根/cm2、18根×6根/cm2[14],吐魯番出土唐代兩幅麻布被單的經緯密度分別為25根×25根/cm2、15根×11根/cm2[15],可知樣品F1編織密度較低,與日常生活使用的紡織品存在差異。
大麻纖維由于細度低、摩擦系數小,且纖維兩端鈍圓,因此兼具良好的強度與手感[16],而較高的回潮率又使其保有極佳的吸濕性與透氣性,因此大麻纖維被認為是天然纖維中性能最優的種類之一。使用紡織物包裹皮革的形式較為少見,而F1編織密度低,使用普通的平紋編織工藝且無紋樣變化,可見制作并不精細,因此推測并非用于裝飾。考慮到大麻纖維的強度與手感,以及取樣位置位于馬具青銅卡帶內側,初步推斷該紡織物是用于構成固定銜鑣或鞍韉的帶子,在馬具的各部件之間起到連接加固或襯墊的作用。
2.2 黑色塊狀殘留物分析
使用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儀測試皮革樣品,保存譜圖后使用氣氛補償﹑最大最小值歸一化、點平滑、基線校正等方式進行處理,得到黑色殘留物H1的紅外吸收光譜圖(圖5)。H1的特征峰集中在1 000~3 000 cm-1,主要吸收峰位于2 921 cm-1、2 853 cm-1、1 648 cm-1以及1 594 cm-1。對比標準譜庫可知:波數2 921 cm-1處為—CH2—的不對稱伸縮振動;2 853 cm-1處為—CH2—對稱伸縮振動的特征吸收峰;1 648 cm-1附近為羧基中—C=O—的伸縮振動,該活性基團形成特征吸收譜帶酰胺Ⅰ帶;1 594 cm-1與1 246 cm-1處為—NH2剪式振動與C—N伸縮振動峰,并形成特征吸收帶酰胺Ⅱ帶與酰胺Ⅲ帶[17]。α-氨基酸是構成天然皮革中膠原蛋白的基本單位,其主要側鏈基團包括羧基、亞甲基以及胺基等[18],與樣品檢測結果相吻合。根據紅外光譜可知H1中含有膠原蛋白,而膠原蛋白是動物皮的重要成份。結合樣品形貌推斷馬具上附著的黑色殘留物可能為動物皮革制品,但由于樣品老化嚴重,無法進一步得出鞣制工藝等相關信息。另外,使用掃描電子顯微鏡對H1進行觀察,可見樣品呈團絮狀(圖6),動物皮原本應呈現的纖維網狀結構已被破壞[7],在掃描電子顯微鏡下無法觀察到皮革毛孔的形狀、粗細度,無法判斷其種屬信息。

圖5 黑色殘留物H1紅外光譜圖Fig.5 Infrared spectrum of Sample H1

圖6 黑色殘留物樣品的掃描電子顯微鏡圖像Fig.6 SEM images of the black substance sample
我國古代對于動物皮毛的使用及加工可追溯到史前時期,經過不斷發展,漢代的皮革制造業已經相當興盛[19]。鞣制加工后的動物皮雖然具有了更高的韌性以及更加柔軟、舒適的特性,但由于真皮為膠原纖維束經交錯穿插所形成的立體網狀主體架構[20],因此皮革依舊容易受潮變形、長霉,并且在機械摩擦過程中受到損傷。馬具可大致分為絡頭與鞍具兩部分。絡頭的系帶分為項帶、額帶、頰帶等,與銜、鑣組合使用,在秦代已大致定型。鞍具一般包括鞍、韉、障泥等,為固定鞍韉需用系帶繞過馬尻、馬腹、馬胸,即分別稱為鞦、韅以及攀胸,其在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的陶戰馬上已有體現[2]。通常來說,馬具之系為革帶,其經由帶卡扣連接,且部分飾有銅泡等物[3],根據文物出土時疊壓關系及青銅卡帶形貌,可認為本實驗樣品即為系帶之鞦,屬于從馬尻處固定鞍韉的結構。有機殘留物樣品分別為皮革及紡織品,經過千余年埋藏的皮革已嚴重糟朽,但襯墊于皮革及青銅卡帶之間的紡織物則因為銅離子具有抑菌性能而得以保存。
綜上所述,皮革及紡織品共同組成馬具的鞦帶,推測皮革上層本應同樣襯墊有紡織物,并與下層織物連成一體,將皮革包裹在內,然而由于土壤中水、鹽及微生物等因素的侵蝕,上層織物已消失殆盡。使用紡織物包裹皮革共同形成革帶的形式在目前的考古發現中并不多見,而由于多處青銅構件上存在相似痕跡,故推斷該件鎏金青銅馬具上所使用皮帶均為紡織物包裹皮革的工藝制作。使用大麻纖維包裹皮革可減輕皮革磨損,同時,麻類纖維強度高,且吸濕性、透氣性良好,包裹后也能起到固定皮革、防止皮革霉變的作用。因此,這種紡織品包裹皮革的組合皮帶便得以在馬具上使用。
3 結 論
旬邑上廟遺址出土的鎏金青銅馬具上所附著的有機殘留物為皮革與紡織品的結合物,其中皮革已老化糟朽,位于上層,而紡織物則呈較完整片狀襯墊于皮革下方,與青銅構件緊密貼合。經檢測,該紡織物為大麻纖維平紋編織而成,編織密度較低。紡織物與皮革通過包裹的形式構成馬具的鞦帶,繼而通過青銅卡帶的連接,將馬鞍等部件固定在馬背之上。自馬具出現以來,皮革已被普遍運用于固定馬具,本工作通過研究首次認識到皮革外包裹一層紡織物使二者共同組成馬具系帶的制作工藝,佐證了該時期我國馬具發展已經較為成熟的觀點,對研究中國古代輿服以及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北方地區馬具工藝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