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創(chuàng)新企業(yè)100強(qiáng)
尋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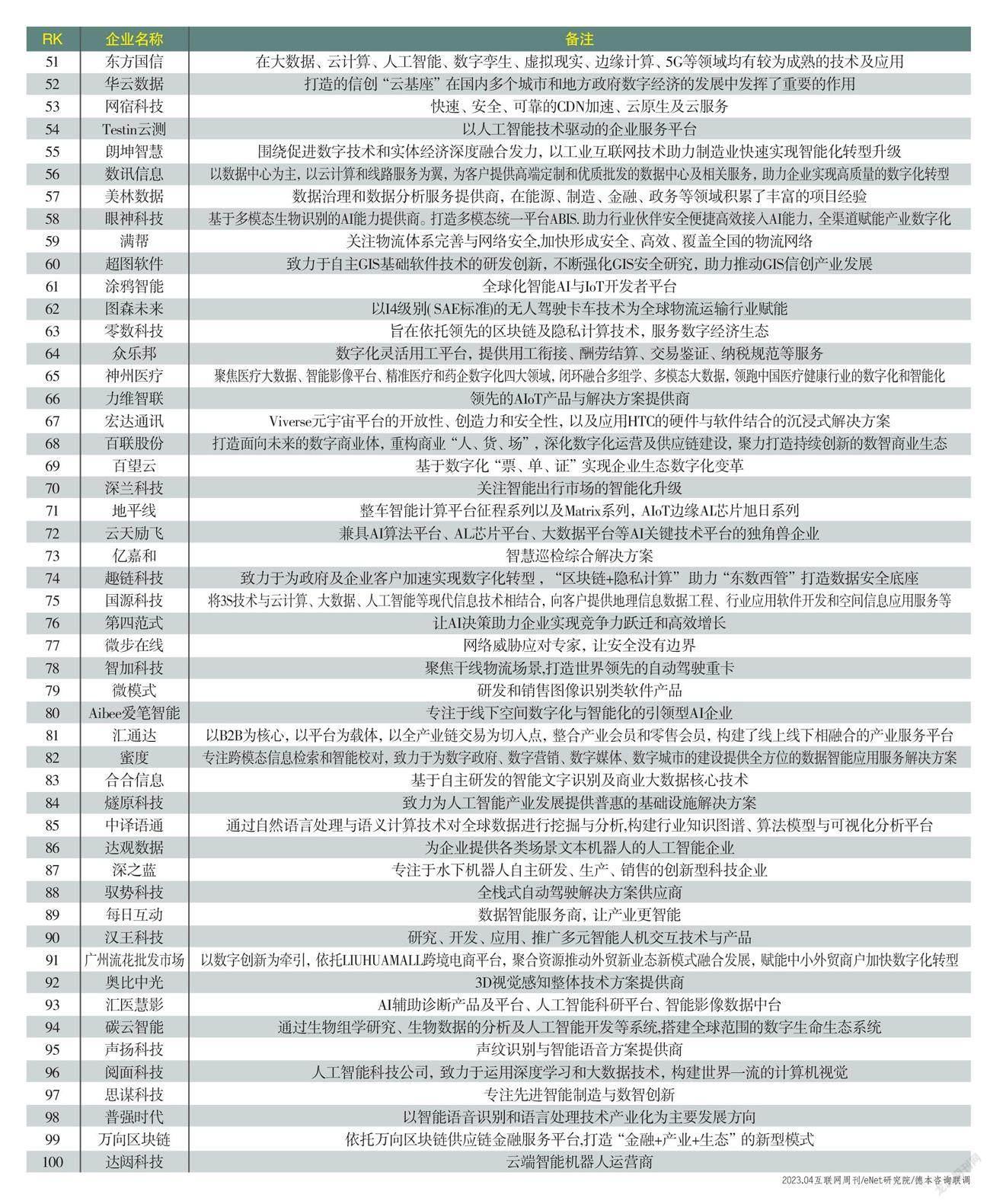
創(chuàng)新是經(jīng)濟(jì)增長的第一動(dòng)力。在數(shù)字經(jīng)濟(jì)這樣一個(gè)多元化的經(jīng)濟(jì)形態(tài)中,創(chuàng)新的范疇甚廣。諸如華為等在網(wǎng)絡(luò)基礎(chǔ)設(shè)施領(lǐng)域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海爾智家以用戶為主線進(jìn)行數(shù)字化全面運(yùn)營體系的搭建與升級的組織管理創(chuàng)新;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與電商相結(jié)合而開辟出的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
數(shù)字經(jīng)濟(jì)企業(yè)通過以數(shù)據(jù)資源為要素的數(shù)字產(chǎn)業(yè)鏈和產(chǎn)業(yè)集群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壯大,也通過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脫胎換骨”,在穿越經(jīng)濟(jì)周期途中,展現(xiàn)出韌性,實(shí)現(xiàn)蝶變。
站在新高度
正如吳軍在《數(shù)學(xué)之美》中向讀者生動(dòng)地解答了幾個(gè)問題——“如何化繁為簡,如何用數(shù)學(xué)去解決工程問題,如何跳出固有思維不斷去思考創(chuàng)新”。數(shù)字化應(yīng)該首先轉(zhuǎn)化為一種理性且具有邏輯性的、有新意和高度的思維方式。那么如何去衡量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成果又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
通常來說,人們考量企業(yè)創(chuàng)新行為通過專利數(shù)或是研發(fā)投入。根據(jù)國家發(fā)改委今年發(fā)布的《關(guān)于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發(fā)展情況的報(bào)告》,我國數(shù)字技術(shù)研發(fā)投入逐年上升;2021年我國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核心產(chǎn)業(yè)發(fā)明專利授權(quán)量達(dá)27.6萬件,占同期全社會發(fā)明專利授權(quán)量的39.6%,關(guān)鍵數(shù)字技術(shù)中人工智能、物聯(lián)網(wǎng)、量子信息領(lǐng)域發(fā)明專利授權(quán)量居世界首位。
這對于還在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道路上摸索中的我國而言,是令人欣喜的成績,但“為學(xué)患無疑,疑則有進(jìn)”,抱有懷疑的態(tài)度才能不斷精進(jìn)。
早在2015年,美國戰(zhàn)略研究機(jī)構(gòu)蘭德公司便發(fā)布報(bào)告稱,盡管中國的專利數(shù)量迅猛增加,但代表創(chuàng)新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TFP)增長并未跟上步伐。拋開中美專利制度、市場環(huán)境差異帶來的研究噪聲,其反映出我國創(chuàng)新原創(chuàng)性、質(zhì)量、績效不高仍然值得警惕。
蘭德報(bào)告中提到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計(jì)量方式一方面指向了數(shù)字化創(chuàng)新的根本目的——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來源于知識進(jìn)展、教育普及、人力資本增加、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化等廣義的技術(shù)進(jìn)步的促進(jìn)作用。
但是,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環(huán)境動(dòng)蕩的背景下,單一組織很難擁有創(chuàng)新所需的全部資源來實(shí)現(xiàn)這種“廣義的技術(shù)進(jìn)步”,于是企業(yè)與企業(yè)、企業(yè)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xié)同共生成為了研究與實(shí)踐的新趨勢。
1993年,Moore第一次提出“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即企業(yè)和與之有利益關(guān)系的利益相關(guān)方共同形成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這些主體之間通過協(xié)同合作或者競爭的方法達(dá)到創(chuàng)新的目的。相關(guān)理論經(jīng)過多年的沿革,其關(guān)鍵詞從可持續(xù)發(fā)展、開放創(chuàng)新、價(jià)值創(chuàng)造與協(xié)同創(chuàng)新演變?yōu)槿缃竦膬r(jià)值共創(chuàng)。
由于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大潮迭起,國內(nèi)聚焦這方面的研究也日漸火熱。孫永磊等學(xué)者認(rèn)為,數(shù)字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有三個(gè)演化方向:關(guān)系互動(dòng)、知識能力和行為規(guī)范;儲節(jié)等提出,數(shù)智賦能的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運(yùn)行機(jī)制包括資源編排機(jī)制、知識增值機(jī)制、開放性機(jī)制、共生演化機(jī)制、技術(shù)驅(qū)動(dòng)機(jī)制、柔性機(jī)制、績效反饋機(jī)制和支撐保障機(jī)制。
從單純關(guān)注表面的創(chuàng)新行為到分析深層次的創(chuàng)新形成機(jī)制,讓我們改變“試圖通過對‘果施加影響來改變‘果”的習(xí)慣,專注和耕耘“因”。根本的問題,也即“因”是完善創(chuàng)新體系,實(shí)現(xiàn)這一輪體系重構(gòu),應(yīng)強(qiáng)化自下而上的、市場導(dǎo)向的、包容的以及更多基于需求的創(chuàng)新支持方式和項(xiàng)目,引導(dǎo)公共研發(fā)資金更多地投向基礎(chǔ)研究,并加強(qiáng)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提高專利質(zhì)量。如此,才能朝著“數(shù)字中國”的偉大藍(lán)圖前進(jìn)、再前進(jìn)!
看向新天地
“創(chuàng)新就是創(chuàng)造性的破壞”“需要有新的或另一種意識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領(lǐng)域、范圍和時(shí)間內(nèi)的工作或牽掛中,去為設(shè)想和擬定出新的組合而搏斗”……創(chuàng)新理論之父熊彼特深刻的洞見仿佛山谷間亢長的回音,直到今天都盤旋在人們頭頂,激勵(lì)重新思索創(chuàng)新的意義。
按照他的觀點(diǎn),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將新的生產(chǎn)要素——數(shù)據(jù)引進(jìn)生產(chǎn)體系中去,產(chǎn)生與生產(chǎn)條件的“新組合”,從而“建立一種新的生產(chǎn)函數(shù)”,它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見。因此每當(dāng)我們眺望“數(shù)字中國”的光景,目之所及雖有崇山峻嶺、低洼溝壑,但仍感嘆天地廣闊、大有可為,不免心潮澎湃。
中國信通院發(fā)布的《中國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發(fā)展白皮書(2022年)》顯示,2021年,數(shù)字經(jīng)濟(jì)規(guī)模達(dá)到45.5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6.2%。其中,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化基礎(chǔ)實(shí)力持續(xù)穩(wěn)固,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占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比重超過八成,已經(jīng)是增長的主引擎,這說明,“數(shù)字中國”的建設(shè)已經(jīng)容納了越來越多的創(chuàng)新主體。
如果說熊彼特理論的靈魂在于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那么管理學(xué)大師德魯克則認(rèn)為創(chuàng)新的最終目標(biāo)應(yīng)該是取得市場領(lǐng)導(dǎo)地位,并在微觀層面為企業(yè)家、創(chuàng)新主體系統(tǒng)化地管理創(chuàng)新、尋找創(chuàng)新機(jī)遇指出了可行的道路。
從行業(yè)市場地位角度而言,大型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投入和創(chuàng)新能力往往更突出,且能通過規(guī)模效應(yīng)在產(chǎn)業(yè)鏈有更多話語權(quán),但也常常給人以機(jī)構(gòu)臃腫、企業(yè)文化封閉而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創(chuàng)新變革途中步履蹣跚的刻板印象。
轉(zhuǎn)型維艱,但結(jié)果卻令人振奮。面對急劇下滑的電腦主機(jī)市場影響下奄奄一息的IBM,時(shí)任CEO郭士納曾放出豪言:“如果大象能夠跳舞,那么螞蟻就必須離開舞臺。”最終在他功成身退之時(shí),留下了一個(gè)持續(xù)盈利、股價(jià)上漲10倍的IBM,堪稱商業(yè)神話,以及記錄著個(gè)中秘辛的自傳《誰說大象不能跳舞?》。
誰說大象不能跳舞?郭士納用行動(dòng)證明了IBM大象能夠跳舞的同時(shí),也巧妙地回避了后半句話的隱喻——“螞蟻就必須離開舞臺嗎?”
不一定。因?yàn)槠髽I(yè)經(jīng)營活動(dòng)是可以實(shí)現(xiàn)雙贏的非零和博弈。
促進(jìn)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化、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企業(yè)共同發(fā)展,一方面,打好數(shù)字基建基礎(chǔ),尤其要加快制造業(yè)數(shù)字化發(fā)展,帶動(dòng)中小企業(yè)數(shù)字化改造。考慮到數(shù)字化成本,由于大企業(yè)在創(chuàng)新條件上的先發(fā)優(yōu)勢,需要進(jìn)一步激發(fā)其創(chuàng)新潛力,為降低行業(yè)數(shù)字化門檻、加速中小微企業(y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進(jìn)程提供更多更豐富便捷的數(shù)字化工具。
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小企業(yè)破除轉(zhuǎn)型過程中“不愿轉(zhuǎn)”“不敢轉(zhuǎn)”的畏難心理,循序漸進(jìn)地運(yùn)用好公關(guān)服務(wù)平臺等一切有利條件,從信息化到數(shù)字化再到智能化,以務(wù)實(shí)的態(tài)度,推動(dòng)達(dá)到企業(yè)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
從企業(yè)戰(zhàn)略角度而言,發(fā)展的過程也是創(chuàng)新的過程。總結(jié)今年Q3各大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的財(cái)報(bào),除了老生常談的“降本增效”外,與消費(fèi)者價(jià)值共創(chuàng),開辟新的用戶群、市場、盈利點(diǎn)讓近年來普遍承壓的龍頭們實(shí)現(xiàn)了逆勢生長。
抓住了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機(jī)遇的阿里云,其來自非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的客戶收入在Q3實(shí)現(xiàn)同比增長28%,主要由金融服務(wù)、電訊及公共服務(wù)行業(yè)驅(qū)動(dòng),非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的客戶收入已經(jīng)占阿里云總收入的58%;無獨(dú)有偶,在騰訊其他各大業(yè)務(wù)板塊營利收窄的情況下,金融科技與企業(yè)服務(wù)業(yè)務(wù)同比增長4%至448億元,再度超越游戲板塊,成為騰訊營收最大支柱業(yè)務(wù)。
創(chuàng)新的影響力絕不僅僅體現(xiàn)在財(cái)報(bào)上的只言片語。熊彼特把創(chuàng)新定義為企業(yè)家的職能,而德魯克把創(chuàng)新從企業(yè)的層面擴(kuò)大到非營利機(jī)構(gòu)和政府,提出了“企業(yè)家社會”。企業(yè)家社會不但是企業(yè)家的社會,而且是任何具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組織的社會。德魯克以其獨(dú)特、博大和睿智的社會視角告訴我們:所有人類思想、理論、機(jī)構(gòu)、制度以及技術(shù)的產(chǎn)物都會陳腐、僵化和過時(shí),創(chuàng)新則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xù)和自我更新的特殊工具。
或許,“螞蟻”不會輕易離開舞臺,當(dāng)它們在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卻無法自我更新或是不能完成目標(biāo)之后,才會退出歷史舞臺。
結(jié)語
無論熊彼特高喊著經(jīng)濟(jì)增長的激昂陳詞,還是德魯克務(wù)實(shí)且具有原則性的金玉良言,都將創(chuàng)新的主動(dòng)力拔高到新的高度——企業(yè)家精神。“企業(yè)家”不是投機(jī)商,也不是只知道賺錢、存錢的守財(cái)奴,“企業(yè)家”可以是你,是我,是千千萬萬大膽創(chuàng)新敢于冒險(xiǎn),善于開拓的創(chuàng)造型人才。時(shí)也,勢也。在“數(shù)字中國”的建設(shè)中,他們有著遠(yuǎn)大的理想——產(chǎn)業(yè)現(xiàn)代化大發(fā)展、生態(tài)共榮;以及更遠(yuǎn)大的理想——用高效、便捷、普惠的數(shù)字化治理和應(yīng)用,為消費(fèi)者價(jià)值共創(chuàng),為人民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