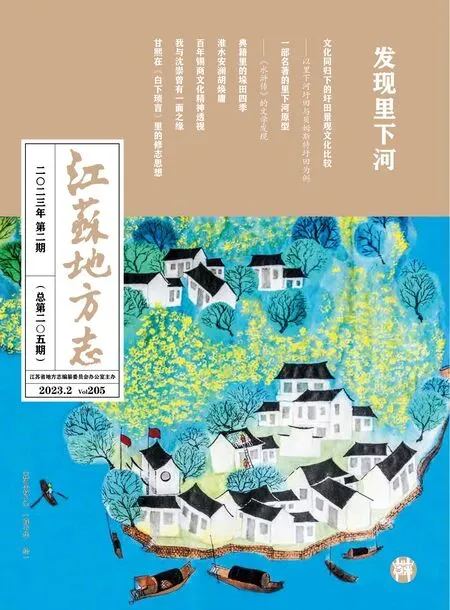伊婁河名稱的由來
◎黃繼林
(江蘇揚州225000)

中國大運河世界遺產點瓜洲運河碑(黃繼林 提供)
京杭大運河揚州段的南端、從高旻寺三汊河口向南至瓜洲長江邊,有一條以“伊婁”為專名的人工水道——伊婁河,亦稱新河、瓜河,今稱瓜洲運河。唐代中期,因江中沙磧形成的瓜洲與北岸相連,堵塞了揚子津渡口,有礙漕運,潤州刺史齊澣于開元二十六年(738)主持開鑿這條水道,初長25 里。光緒十年(1884)瓜洲全城坍入長江,古鎮移至城北的四里鋪,形成今瓜洲,伊婁河也隨之縮短。唐代的伊婁河是南漕北運的咽喉,雖只有25 里,但江南的漕糧經此轉輸長安,在當時支撐了唐王朝,宋、元、明、清的江南漕糧也經此北上。運河對歷代王朝政權的穩固、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文化的交流均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和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人們在談及開鑿這段咽喉要道的功績時,多引用李白《題瓜洲新河餞族叔舍人賁》中的詩句來評說:“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2014年,這條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水道作為大運河的一個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伊婁河開鑿的歷史背景、緣由,史料記載甚詳,今人也多有述及,而為何以“伊婁”作為這條水道的專名則未見記載。地名的命名有多種方式:有以地理實體的特征、形態、方位命名的;也有出于對做出利國利民重要業績人物的熱愛,用他們的姓名命名的;還有以地理實體形成的時間先后來命名的。這條水道以“新河”稱,是相對于原來的水道;名以“瓜河”是因河道所在地理位置瓜洲;若以開鑿者的姓名稱,似應以李白所稱“齊公”為專名。今人有說因傍“伊婁山”而名。瓜洲因“江中沙磧淤漲”而成,“山”從何來?〔乾隆〕《江都縣志》、〔嘉慶〕《重修揚州府志》的記載都只是說有“汀”,且文字相同:“伊婁河,在城南十五里。《輿地紀勝》云:伊婁河即揚子鎮以南至江之運河也,隋以前揚子鎮尚臨江,至唐江濱積沙二十五里。開元間潤州刺史齊澣奏開此河,以通運道。又有伊汀即在伊婁河。”“汀”為“水邊平地”或“水邊平灘”,言“傍山”者,蓋誤以為“汀”為“山”也。再者,即便有山。那“伊婁”又是何意?本文探討何以用“伊婁”作為這條水道的專名。
一、齊澣其人其事
《舊唐書》與《新唐書》皆有《齊澣傳》,內容基本一致,只是有些細節、措辭的表述略有差異。齊澣(675——746),定州義豐(今河北安國)人。少開敏,有才華。圣歷初,登進士第。開元初,遷給事中、中書舍人,佐中書令姚崇,“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任汴州刺史時,“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頗有政績,“吏民頌美”,得玄宗賞識,拜尚書右丞,轉吏部侍郎,玄宗常召其入宮密議,成為“天子近臣”。時龍興四大功臣之一、掌控羽林軍的王毛仲居功自傲,在朝中拉幫,玄宗很是不悅。齊澣進言,說王毛仲“寵極則奸生,若不預圖,恐后為患,惟陛下思之。況腹心之委,何必毛仲”。力舉高力士,說“高力士小心謹慎,又是閹官,便于禁中驅使”。這次所議之事,關系重大,齊澣請求玄宗保密:“‘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惟圣慮密之。’玄宗嘉其誠,諭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義,我徐俟其宜。’”然而齊澣在與朋友麻察飲酒時“語禁中諫語”,又被麻察告發。玄宗怒,“令中書門下鞫問。又召澣于內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而疑朕不密,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訓斥一番后,將其“貶高州良德(廣東西南部近南海)丞”。(《舊唐書·齊澣傳》)
齊澣在粵多年,直到王毛仲被流放賜死后,才得高力士相助,“徙索盧(今廣東中部新興縣南部)丞、郴州長史,濠州、常州刺史”(《新唐書·齊澣傳》)。而《舊唐書·齊澣傳》則略去遷常州前所任,記為“澣數年量移常州刺史”。開元二十五年(737)從常州任上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采訪處置使,開元二十六年(738),“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完工后,“復徙汴州刺史,充河南道采訪處置使”。
揚子津運口被淤漲的沙洲堵塞,非一日而成。玄宗始設專司漕運的官員。《新唐書·李杰傳》記載:“李杰……后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先天中,進陜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杰始……江、淮漕運不通。杰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浚之。”說明此時運道已經出現了問題,盡管設了專司整理運道的官員,漕糧的轉運依舊時時受阻,每每漕糧不能及時到達,皇室、官員都要到東都洛陽就食。
《資治通鑒·唐紀》記載,開元二十一年(733),關中大災,玄宗去東都就食前,召京兆尹裴耀卿商議漕運之法,確保運道的暢通必定是商議的內容之一。齊澣整治過淮、徐運道,深得玄宗贊許。高力士適時進言,蓋已有召回齊澣之動議。雖未見明確記載,但《新唐書·地理志》透出了信息:“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州北隔江……開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立埭。”〔嘉慶〕《瓜洲志》卷8也說:“昔時瓜洲沙尾與潤州隔六十余里,舟多敗溺,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埭以達揚子。”當是從開元二十二年后,逐步回遷,至“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舊唐書·齊澣傳》)。經實地考察制定方案上奏,二十六年玄宗準奏。《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于揚州南瓜洲浦。”《資治通鑒·唐紀》的記載較為完整:“開元二十六年,戊寅,潤州刺史齊澣奏:‘舊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立伊婁埭。’從之。”此說為后世史家所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李廷先《唐代揚州史考》皆從此說。今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中國大運河遺產點——瓜洲運河的標志牌的標注也是“始于唐代開元二十六年(738)開鑿的伊婁河”。至于〔嘉慶〕《丹徒縣志·卷二·山水》所說:“伊婁河,唐地理志開元二十七年潤州刺史齊澣所開。”蓋是開元二十六年動工,二十七年完工通運。而〔乾隆〕《江都縣志》、〔嘉慶〕《重修揚州府志》說“開元間潤州刺史齊澣奏開此河,以通運道”。
齊澣復官后的工作,就是疏通運道的“苦差”。《舊唐書·齊澣傳》載“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為兩道采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史書未明確記載其在常州任上所做,但可推知,蓋是考察“常州府運河”,擬改運道從孟瀆河過江(明宣德六年,陳瑄也曾一度改漕船由孟瀆河過江);而“復徙汴州刺史”,《舊唐書》已明確記述“興開漕之利”,盡管開鑿、整治運道,使天子滿意,然終未能回京任職。失意而惱恨,操行漸行敗壞,為賄賂權貴而斂財,遭李林甫參劾,“遂廢歸田里”。天寶初,召回任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天寶五年(746)又出京主政平陽(今為浙江溫州下轄縣),旋卒于任上。
二、伊婁氏是皇室大姓
筆者所見相關辭書及文獻,“伊婁”僅有“鮮卑姓”一解,別無他說。《辭海》《辭源》皆未收錄。明廖用賢《尚友錄·伊婁》說:“伊婁,后魏(北魏)獻帝第六弟為伊婁氏,為十姓。見《官氏志》。”《中國姓氏大全·伊婁》:“歷史上鮮卑族姓氏,北周有伊婁穆,隋代有伊婁謙。后改為伊氏或婁氏。”《中國古今姓氏辭典·伊婁》:“鮮卑姓。后魏獻帝六弟為伊婁氏。后改為伊氏。或曰改婁氏。”《魏書·官氏志》載:“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為內姓焉……獻帝以兄為紇骨氏,后改為胡氏;次兄為普氏,后改為周氏;次兄為拓跋氏,后改為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后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后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后改為丘氏;次弟為侯氏,后改為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為叔孫氏。又命疏屬曰車焜氏,后改為車氏。凡與帝室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國之喪葬祠禮,非十族不得與也。高祖革之,各以職司從事。”
鮮卑原是一個部眾頗盛、占地極廣、遠居塞外,且與中原接觸極少的北方游牧民族。《三國志》上說鮮卑“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魏書·官氏志》也說到“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北方游牧民族進入中原所立政權中,鮮卑族為數最多。范圍從遼西一直到甘肅、青海。北朝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都是鮮卑族所立。
中原地區,以漢族為主,有較鮮卑族發達的科技和文化。太和十八年(494),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頒布一系列推進漢化改革的政令,其中有改鮮卑姓為漢姓;不說鮮卑語而說漢語;不穿鮮卑服而穿漢裝;提倡鮮卑人與漢人通婚等。語言、姓氏等是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傳統文化,鮮卑人長期居住中原漢地,和漢人及其他各族人民間形成自然融合。孝文帝的改革,促進并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但語言、姓氏等文化傳統的變更,不是令行即改的事,需要一定時間,鮮卑復姓也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全部改為漢族單性。

今日瓜洲運河(金鑫 攝)
從北魏到李唐王朝的皇室不僅有鮮卑血統,還有特殊的親緣關系。伊婁氏是獻帝六弟,北魏帝室十姓之一。其地位雖不如皇室顯赫,在朝中也有一席之地,前文提到的“北周伊婁穆,隋代伊婁謙”皆為朝廷重臣,《周書》 《隋書》分別有傳。李唐王朝的官員中,前朝官員的后裔也不在少數,前文提及的首任專司漕運的水陸發運使,就是后魏并州刺史李寶之裔孫。
玄宗時機構龐大,刺史其下還有別駕、長史、司馬、錄事等數十位佐官,長史、司馬通常是優待宗室或安置閑散官員,無具體職任。齊澣佐官的長史、司馬中或有“伊婁氏”,或負責具體施工者為“伊婁氏”(可惜未見史書記載)。“伊婁河”這個名稱,一開始就見于官方文獻,后來逐漸在民間傳開(新河、瓜河一開始是民間所稱,如前文提及的李白詩句,此后漸有文字記載)。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人們習慣于“用人的后半生,來推定前半生;用人最后的行為,來審度一生所有行為。若某人先前不良不善,后來改過自新,那叫浪子回頭金不換,知名人物有晉朝的周處;若某人先前德高望重,后來惡貫滿盈。那叫大奸大詐、包藏禍心,知名人物有王莽”(趙劍敏《細說隋唐》)。齊澣雖說于開河有大功,并得天子贊賞,然中年泄密受貶,晚年斂財遭劾,官家不以齊公名此水道,而以“伊婁”名之,蓋是此理。史家公正客觀記述齊澣一生,使人們從中悟出許多道理。
文字是記錄語音的符號,鮮卑人無文字。“伊婁”是用漢字音記錄的鮮卑姓氏,這兩個音節在鮮卑語中所表示的意思(也即以此為姓的緣由)已無從查考,鮮卑人在和漢人融合過程中使用漢語,鮮卑語逐漸弱化,至隋末唐初失傳。“伊婁”之姓,唐代以后融入漢姓。
“伊婁河”雖因通漕而開,而且也只有25 里,但對后世的作用和影響遠遠超出了漕運。這水道雖沒有以“齊公”命名,卻透露出民族融合的信息,所揭示的民族大融合的文化內涵也是“天地同朽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