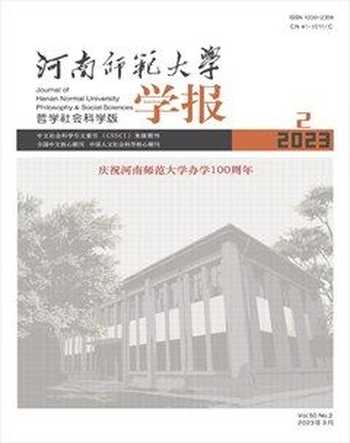論竟陵派“性情”說與“真詩精神”觀
李永賢 周道河
摘 要:明代詩人對“真詩”的追求多強調主體“性情”之真,他們因對于“性情”的理解不同而產生出相異的詩學主張。鐘惺、譚元春論“真詩精神”,分別從德性與才性兩個方面對主體“性情”提出要求:一、主體德性之正,強調詩歌所表現的情感不能違反儒家倫理之道,是對“風雅”精神的繼承;二、主體才性之奇,強調詩歌應展現出文采之奇秀與語言之簡練,是對道家自然觀的闡發。為了獲取“真詩精神”,他們認為需要用“養氣”的方式涵養主體“性情”,進而通過虛靜內心和飽讀詩書的路徑加以修煉。“養氣”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主體之“性情”與古人相合,德性與才性相融并呈現出“厚”的狀態,便構成了“真詩精神”的外在特征。
關鍵詞:竟陵派;性情;真詩精神;養氣
作者簡介:李永賢(1967—),男,河南新鄉人,文學博士,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文學與文論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7BZW119)
中圖分類號:I206.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359(2023)02-0091-09
收稿日期:2022-11-16
鐘惺在《詩歸序》中提出:“真詩者,精神所為也。”[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0頁。]對于“真詩精神”的理解,鄔國平將其指向“幽情單緒”,認為鐘惺、譚元春“向往幽事寂境的清思孤懷,缺乏闊大雄壯的氣概和向未來進發的意氣”[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0頁。]。戴紅賢認為:“‘真詩精神決非詩人的自然個性,而是主體對其自然個性進行錘煉、陶冶的藝術個性。”[戴紅賢:《從“獨抒性靈”到“真詩精神”:袁宏道、鐘惺“性靈說”離合關系探析》,《貴州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鄭凱歌認為:“鐘惺所謂的真詩‘精神指的是詩人、時代的核心風格及主要成就,即身份與本色。”[鄭凱歌:《鐘惺“真詩精神”說及其詩學史意義》,《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陳廣宏認為:“‘精神是一種真正能夠共享而又統攝發用之變化的本源性存在。”[陳廣宏:《竟陵派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41頁。]李瑄認為:“‘精神指向超越物質層面的意志范疇。”具有“超卓”“遍在”“永恒”的特點[李瑄:《〈楞嚴經〉與竟陵派文學思想的指歸》,《文藝研究》,2019年第8期。]。本文從“性情”入手,分析鐘、譚所謂的“真詩精神”。自臺閣體以降,明代文學發生的“場域”由宮廷逐漸走向社會,其內容也從政治教化緩緩轉向主體抒情,就其本質而言,復古、公安、竟陵諸派都是主情、尚真的,只是由于具體的社會背景、個人才情,以及經歷不同,詩人們對于“性情”的理解存在差異,才有了在“真詩”探尋道路上的不同思考。
復古派所言之“性情”,是為了“批判古典詩歌創作中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傾向,力圖保持和恢復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的審美特征”[廖可斌:《明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57頁。]。李東陽“將詩的自然抒情與詩的聲律聯系起來,提出了格調說”[羅宗強:《明代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2013年,第3頁。],前、后七子沿著李東陽的道路走向了文學復古。隨著明代中后期陽明心學的發展,詩人關于“性情”的觀念從板滯走向圓融,“詩學的發展也從單一走向多元,出現了‘人自有詩的詩學繁榮局面”[李永賢,孫達時:《儒學轉向與詩學變革:明末清初詩學發展之一面觀》,《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在王學左派的光芒之下強調“獨抒性靈”[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7頁。],開始越過詩歌“格調”說的藩籬,使自我俗世的性情率然表現于詩歌之中。在晚明思想收束[黃卓越認為,晚明思想上的轉折大致發生于萬歷二十七年/萬歷二十八年。參見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60頁。],以及士人心態轉變[左東嶺認為,從公安派到竟陵派,其心態由開放走向保守,就“性情”而言,則表現為對于德性的再度關注。參見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552-573頁。]的背景下,鐘、譚主張“真詩精神”,對于“性情”又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內容分四部分,第一、二部分從“性情”(德性與才性)分析“真詩精神”的內涵:一方面,鐘、譚強調詩歌在情感上不能違反儒家倫理,比公安派更加重視主體德性;另一方面,鐘、譚積極探尋詩歌的語言及文采,又沿用了公安派對主體才性關注的一些做法。第三部分論述鐘、譚對如何獲取“真詩精神”的理解。最后一部分則論述“真詩精神”的外在特征。
一
鐘惺、譚元春二人對于德性的強調,一方面是對詩歌因王學左派“無善無惡”說帶來的空疏無物之風的矯正;另一方面是對詩歌在公安派末流自然率性影響下過于強調俚俗之風的反撥。曹淑娟曾指出:“性靈論者因同時主張新奇乃真人性情的自然流露,故能自行發展出兼含正、奇的觀念,避免過度強調奇的流弊。”在具體的論述當中,該文將公安派和竟陵派統之以“性靈派”,與復古派所標榜的性情之“正”相對立[曹淑娟:《孤光自照:晚明文士的言說與實踐》,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0頁。],此一觀點似過于絕對。因為就詩歌內容而言,竟陵派已從德性的角度對“性情”進行了正邪善惡的區分。雖然公安派與竟陵派都注意到了民歌的“性情”之真,但是他們對于性情的理解截然不同。鐘惺《秣陵桃葉歌并序》云:“予(伯敬)初適金陵,游止不過兩三月,采俗觀風十不得五。就聞見記憶,雜錄成歌。此地故有桃葉渡,借以命名,取夫俚而真,質而諧,猶云《柳枝》《竹枝》之類,聊資鼓掌云爾。”[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57頁。]袁宏道《敘小修詩》云:“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8頁。]比較兩人關于民歌之“真”的觀點,袁宏道認為民歌“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而為“真聲”;鐘惺則以“俚而真,質而諧”為擇取標準,認為語言上的俚俗本色與內容上的質樸相協調才是“真詩”。就內容而言,鐘惺所言的“真詩”對詩中所表現的“情欲”設定了一個范圍,即在德性的范圍內表現個人之情性,以便詩歌在內容上不違反儒家的倫理道德。譚元春認為詩歌“了然于心,猶不敢了然于口,了然于口,猶不敢了然于手”[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8頁。]。作詩雖強調“心手相習”“志氣相隨”[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4頁。],但是,若“茍為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只能算是“橫議”而已,“胸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謂中倫之言,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與手者是也”[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17頁。],可見,詩人唯有做到胸中有“中倫之言”,才能做到心手相應。再如,鐘惺認為戰國之文有“雄博高逸之氣,迂回峭拔之情”,雖能見其才情,但內容上“于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4頁。],因而舍之。可見,竟陵派對詩文的內容有格外的注意,即不能違反儒家的倫理道德,個人的才情不能逾越德性的范圍。
鐘、譚二人編撰《詩歸》也反映了此一觀點。民歌多有兒女之情的描寫,但是,民歌自然而發的情感也有正邪善惡之分,鐘、譚對詩歌內容的性情之“正”給予鼓勵:“媚而正,不傷性情。”[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頁。]“性情極邪之言,裝裹得極正便妙。”[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2頁。]“不負心之言,性情亦正,歌中最難得。”[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0頁。]對針砭時弊的詩歌,主張“周旋”的妙用。如《詩歸》評沈佺期與崔湜關于金城公主與西蕃和親所作的應制詩:“如此丑事,何勞群臣作詩應制?唐時君臣廉恥意氣盡矣!每讀之氣塞。沈佺期、崔湜二詩,粗能回護。中寓傷諷,得詩人之意,然終不如勿作耳。”[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頁。]“周旋可謂極得體矣,然多此一番周旋,益覺損威中國,舉動何可不慎。”[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頁。]因“天威在上”[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3頁。]而不得不作應制詩,然和親之“丑事”有損“君臣廉恥”,更“損威中國”,若直接說破則不能“回護”,若敷衍了事則不能得“詩人之意”,處于兩者之間,只能運用“周旋”與謹慎的修辭,以便讓詩歌達到既“得體”又不違反道德倫理的審美效果。此外,詩歌在抒發個人情志的時候,亦需“擇地而出”[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8頁。],追求“風雅”。如,評論孟郊之詩:“仁孝之言,自然風雅。”[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7頁。]“苦調自深厚中出,去風雅不遠。”[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8頁。]總的來說,無論是民歌中的兒女之情,還是對時事的諷諫規勸,抑或是個人的幽怨感激,竟陵派均主張“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30頁。]。這是對“德性”之正的堅守,也是對于“風雅”精神的繼承。
二
鐘、譚二人對于才性的關注,一方面源于他們早年受公安派的影響,另一方面來自他們性格的孤僻狷介、落然寡合。此外,竟陵派所交之人,也多以奇士稱之,如鐘惺稱周伯孔“慧性俊才,奇情孤習”[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7頁。],稱唐君平“落落然奇士也,生有絕才高志”[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0頁。];再如,稱與譚友夏有交的楊修齡,性格“落落然”[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05頁。],稱程子“風趣落落,然俊爽不可羈紲,而天機敏妙”[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10頁。],等等。竟陵派對于才性的獨特追求,在詩歌創作上集中體現在文采的奇秀與簡練兩個方面。《詩歸》選虞舜時期《卿云歌》《八伯歌》《帝載歌》,認為“三歌與《明良》同為虞歌,然《明良》和雅有典謨氣,三歌奇秀有騷些氣。予(伯敬)選古詩雖意在存古,然去時太遠,而昭然六經者,姑舍之,亦文士之習也”。[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頁。]“《明良》和雅”,就內容而言屬德性之正,其“典謨氣”更接近典謨訓詁的“六經”,由于它只注重內容的雅正,而缺少文采,所以不能入選;“三歌”文采“奇秀”,有“騷些氣”,所以“三歌”可以入選。《詩歸》選詩多注重詩歌語言的“字奇”“字奧”“語奇”[據統計,《詩歸》中共有20處評語中提到“字奇”,5處評語中提到“字奧”,30處評語中提到“奇語”,6處評語中提到“語奇”。]等,也關注詩歌的對法、葉法、章法之奇等。譚元春《詩歸序》云:“古人進退焉,雖一字之耀目,一言之從心,必審其輕重深淺而安置之。”[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6頁。]古人對于字句的審視是為了表現其內心之才情,竟陵派對語言之奇奧的追求,正是他們“奇情孤習”[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7頁。]性格在詩歌觀念中的體現。
鐘、譚二人亦追求語言上的簡練,這主要體現在他們的詩評中。譬如,“唐人神妙,全在五言古,而太白似多冗易,非痛加削除不可,蓋亦才敞筆縱所至”[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7頁。]。“斬截有力在一‘即字,每文字簡妙處,似有脫文,而解人讀之了然”[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7頁。]。“尚簡”的詩語如何體現才性的奇崛?《詩歸》云:“古人數字,便如一篇大文章;今人一篇大文章,不當數字。古人不全說出,無所不有;今人說了又說,反覺索然。則以古人簡而深,今人繁而淺。”[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頁。]相對“今人”文章的“繁而淺”與“索然”無味,“古人”文章則“簡而深”,人們往往在“古人”文章淺易的表達中,領略到深邃的情思內涵,進而讓自我的“靈心”在領悟之際得以展現。正如譚元春所說:“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一其思,以達于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6頁。]“自出眼光之人”的自我才性唯有在體悟到古人“性靈”的時候,方能得以顯現。
在談及為何追求詩歌語言“尚簡”的原因時,鐘惺《文天瑞詩義序》指出:“《詩》之為教,和平沖淡,使人有一唱三嘆,深永不盡之趣。……然秦詩《駟驖》《小戎》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校獵》諸賦所不能贊一辭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奧工博之致。”[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39頁。]在鐘惺看來,《詩經》風格上的“和平沖淡”可“使人有一唱三嘆,深永不盡之趣”,簡練的語言可以達到豐富的表達效果;《詩經》風格上的“奇奧工博”,則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校獵》諸賦所不能贊一辭者”。他在《詩歸》中也多稱賞詩歌語言所產生的意外妙處,如“其語言之妙,往往累言說不出處,數字回翔略盡”[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2頁。]“妙在一篇中,語意有落落不屬處”[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7頁。],等等。
語言“尚簡”是對詩歌言約義豐的追求。所謂“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也”[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33頁。],同時也是對比興手法的繼承。鐘惺《簡遠堂詩近序》曰,作詩需“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4頁。],其中的“比興”便是就語言的表達方式而說的。總的來說,鐘、譚二人對詩歌語言“奇秀”“尚簡”的追求,既是表現個人才情的需要,也是繼承比興傳統的需要。至于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文心雕龍》曾云:“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第352頁。]語言“尚簡”近乎“隱”,意在追求“文外之重旨”;辭采“奇秀”近乎“秀”,意在追求“篇中之獨拔”。“隱”與“秀”當然不能刻意為之,只能“自然會妙”[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第356頁。]。可見,在才性的表現上,竟陵派還是受道家自然觀的影響較大。
三
鐘、譚二人認為詩人必須憑借“養氣”的功夫來涵養主體“性情”,方能獲取“真詩精神”。有論者指出:“‘養氣關涉創作主體主觀修養和精神狀態的培養,它凝為情,發為志,散而為文。”[汪涌豪:《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體系》,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56頁。]鐘惺告誡周伯孔要“多讀書,厚養氣”[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8頁。],告誡王永啟要“讀書、觀理、養氣”[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6頁。]。譚元春稱賞蔡敬夫是“懼以養氣,氣以養智”[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06頁。],等等。按照鐘、譚二人的理解,“養氣”的過程,可分為“辨氣”“積氣”“行氣”三個部分。
(一)“辨氣”。鐘、譚二人認為每一篇詩作中都有不同的“氣象”,對這些“氣象”進行分析的過程就叫做“辨氣”,它是人們獲取“真詩精神”的主要條件之一。古人“性情”以“氣”的方式寓于詩歌之中,“辨氣”的過程就是感受詩歌氣象的過程。鐘、譚二人在《古詩歸》中認為左思的詩歌“氣和語厚”[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4頁。],陶淵明的詩歌有“一段淵永淹潤之氣”[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頁。],謝靈運的詩歌“氣清而厚”[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5頁。],等等。詩人所稟之氣不同,詩中所寓之“氣”也就自然有別,鐘惺曰:“陳正字律中有古,卻深重;李太白以古為律,卻輕淺。身分氣運所關,不可不知。”[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頁。]“身分氣運”不同,詩歌氣象就不同,“真詩精神”的具體表現更會隨之相異。鐘惺《韻詩序》曰:“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不失為彭舉。夫風雅后,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諸體詩,輕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孟之致。”[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5頁。]時代已經發生變化,詩歌作者也并非一人,故《詩經》之后的四言詩便會呈現出和此前不一樣的“氣象”,所謂漢郊祀為“事鬼之道也。幽感玄通,志氣與鬼神接”[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頁。];韋孟四言詩“肅肅雍雍,有雅頌之音”[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頁。]而氣“和”;曹公“直寫其胸中、眼中一段籠蓋吞吐氣象”[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3頁。]而氣“壯”;彭舉“有王、孟之致”而氣“幽”,等等。
“辨氣”的目的是說明詩人才性之于“真詩精神”的重要性。詩人寫詩應循著自我靈心,去找尋與之相應的表達方式,正如漢郊祀“不學雅頌,自為幻奧之音”[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頁。];韋孟將諷諫寄于家世的敘述之中;魏武帝之詩不失“魏武身份”[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4頁。],等等。如果詩人一味恪守單一的法度、靠定某一派別,而不求作詩的變化,最終往往會與“真詩”失之交臂。鐘惺認為:“詩文有創有修,不可靠定此一派,不復求變也。”[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頁。]此外,“辨氣”的本身還要有“不膈靈之眼”[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6頁。],這一過程也是對主體靈心的發現與修持。
(二)“積氣”是對“氣”的涵養,也是一個悟道的過程。主體唯有在長時間的“積氣”中涵養性情,才有獲得“真詩精神”的可能。“積氣”的途徑,一方面依靠主體內心的虛靜,另一方面則需要主體博覽群書以厚植學養。
第一,依靠主體內心的虛靜。首先,詩心的“觸發”源于現世中的人事變遷,鐘惺曾說:“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23頁。]其次,詩人在俗世的紛擾之外構建了一個詩意空間,正如鐘惺《詩歸序》所說:“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0頁。]然而,如何調適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呢?鐘惺認為:“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為二。”[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35頁。]這本是贊賞蔡敬夫的語言,對于伯敬來說,此種境界是達不到的,因而他在《蔡敬夫自澧州以詩見寄和之》中感嘆道:“何以塵務中,穆如清風詠。乃知寄托殊,形神本淵凈。以茲暇整情,何紛不可定!”[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頁。]如果內在性情“淵凈”,即使有俗世的紛爭又能怎樣呢。
然而,晚明黨爭激烈,詩人主體的性情很容易被損傷。鐘惺《湯祭酒五十序》指出:“諸凡摧抑人才,破壞元氣,滋議論而傷國體之事,即不以先生(湯賓尹)一人終,實以一人始。”[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1頁。]《告雷何思先生文》亦云:“方今景象,底滯痿蹶,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復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勢必用一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33頁。]為了使主體自我的精神和元氣不受損傷,詩人必須從中將自己抽離出來,鐘惺在晚明黨爭之中秉持“一無依傍的立場”[陳廣宏:《竟陵派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9頁。],即是典型的表現。
此外,明代科舉出現了“士商互動”的現象。與鐘惺同鄉的李維楨,曾為商人撰寫碑銘之類的文章達百篇之多[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8-543頁。];明代中后期商業的發展、城市的繁榮,則又為文人結社提供了新的活動空間[邱仲麟:《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年,第267-316頁。]。在與文人或者商人往來的過程中,詩人往往會寫一些應酬性的詩歌或者程式化的墓志銘,這種“為文造情”的書寫往往會給自我性情帶來負面影響,譚元春就指出:“今人慣喜作壽詩,予謂性情所乘,萬不可以此損傷。”[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4頁。]那么,詩人應該秉持一種怎樣的處世態度呢?鐘惺《簡遠堂近詩序》云:“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4頁。]顯然,在鐘惺看來,個人應該和世俗保持一段距離,保護自我的真性情不被社會所浸染。他在《詩歸》中也指出內心之“靜”的重要性,如評《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蕩滌放情志”句所言:“未有居心不凈,而能放者。”[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頁。]詩人只有在掃除外在的喧雜和內心的雜念之后,才能由靜其心,進而達致抒發情志的目的。
第二,依靠主體的博覽群書。《文心雕龍》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第14頁。]圣人的文章中蘊含著倫理之“道”,人們可以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涵養德性。當然,“真詩精神”追求的是德性與才性的融洽,而非一方對另一方的“占有”,個人的才性不能被束縛在古文之中。晚明“正文體”的出現是知識界重建思想秩序,恢復儒學正統地位的一種象征[張德建:《正文體與明代的思想秩序重建》,《文學遺產》,2019年第1期。],鐘惺認為,“正文體”的根本在于“平日博于讀書,深于觀理,厚于養氣”之后“得其才情神志”[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5-366頁。],“讀書”與“觀理”不應止于圣賢所述之文,也可兼及佛道之學,如此才能達到且“博”且“深”的境地,才能厚養其氣。除了閱讀古人之文以外,編撰古人之詩文,也可達到浸潤主體性情的目的。《詩歸》的編撰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9頁。]。繆鉞曾指出:“詩之質有三,一曰深遠之思,一曰溫厚之情,一曰靈銳之感。”而“人固有生而具溫柔敦厚之情者,然其情真矣,未必能深;深矣,未必能廣。……欲情之深而且廣,必多讀古詩人之作,以古人濃摯之情引己之情,浸潤激蕩,日大以長,如雨露之潤草木,肥甘之養肌理。至于有深遠之思,則必識通今古,學貫天人,胸襟超曠,閱歷深宏,所謂真本領也。”[繆鉞,繆元朗:《古典文學論叢》,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06-409頁。]詩人因現實的遭遇而觸發情感,但由此所產生的現實之“情”與古人“性情”并非完全符合,況且詩人的當下之“情”只不過是一念之感而已,并非濃厚之情,所以,要想達致浸潤主體性情的目的,就必須借助古人詩歌中深厚情思的移情作用。鐘惺曰:“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能無斷缺補湊。”只有具有一定的“識”“詣”的詩人,才能將自己的“氣”培育深厚,他的“才”“情”才不會受到體制的束縛。鐘惺告誡伯孔要“劌心于唐以上之所至”,要“多讀書,厚養氣”,作詩要達到自然無痕,才能避免走向“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7-308頁。]的錯誤之路。
無論是上述哪一種養氣的方法,“積氣”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都需要主體用內心的“誠”去堅守。鐘惺《贈唐仲言序》云:“(唐仲言)五歲以后所出為詩文及注古之為詩文者,皆其心所授于其口,其口所授于人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類既多,其體既備,其立意又皆以該且核為主。……然能使人之為仲言誦多且久于其自為誦,數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為也。”[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7-368頁。]唐仲言因為心“誠”,且常年積累,最終才達到了“自為誦”的境界。再如,鐘惺《送錢先生歸婁東序》說他自己與錢先生之事,“精神往來,合為一身。中心達于面目,意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仍是眾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6頁。]。錢先生之所以被稱為“醫王”,主要在于其內心的極“誠”,用醫者的誠心感之于患者,所以,他的用藥雖然和別人沒有多大區別,但是由于能與患者取得精神上的相通,因此常常能取得藥到病除的效果。喻之于詩,雖然面對同樣的古詩文,抑或是同樣的自然風光,只有以心感之的心誠者才能和它們取得精神上的共鳴。
(三)“行氣”。“行氣”是“真詩精神”的呈現環節,譚元春曰:“氣之所為,不可使復泄也。誠以蘊之,懼以守之。其誠彌積,其懼彌深。懼日以深,而氣日以達。一旦不得已而用于世也,則非我欲其然也,氣自然也。”[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06頁。]創作主體的內心之“氣”經過“誠以蘊之,懼以守之”的積累之后,便會“自然”地流露于詩歌的創作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行氣”需要以“積氣”為基礎,“氣”唯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自然地傾瀉出來,不可強而為之。《古詩歸》評《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云:“此古今第一首長詩,當于亂處看其整,纖處看其厚,碎處看其完,忙處看其閑。此隆古人氣脈力量所至,不可強也。”[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頁。]因詩人所積累的“氣”比較隆厚,他才能將“亂”與“整”、“纖”與“厚”、“碎”與“完”、“忙”與“閑”和諧地統一起來。鐘惺《詩論》云:“趣以境生,情由日徙。……以予(伯敬)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強同矣。”[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59頁。]對于《詩經》的體悟,他會因前后所積之“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不可強求其同。其次,若強而為之便“有痕”,創作主體唯有在涵養之氣達到一定狀態的時候才能做到無“痕”。鐘惺認為:“‘我輩詩文到極無煙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50頁。]最后,詩人所稟之氣行于詩的過程是自然而然的,不能刻意為之。鐘惺認為:“極奇莫如造化,妙在皆由自然。”[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2頁。]當然,“自然”之中也有“偶然”之意,所謂“偶然妙想,偶然妙舌,深求則失之”[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9頁。],元氣“偶然吐出”[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8頁。],常常會造成詩歌“偶然真境”[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頁。]的出現。
可見,“行氣”是一個觸物起興的過程。當主體所涵之“氣”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詩人經常會觸物起興,因外在事物的觸發而激起靈感的閃現,進而將所體悟的“真詩精神”呈現出來。觸物起興發生于自我與外物相融的時刻,一如伯牙學琴:
伯牙學琴于成連,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連曰:“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赍糧從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汩沒,山林窅冥,群鳥悲號。仰天嘆曰:“先生將移我情!”及援琴而作此歌。[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0頁。]
伯牙師從成連三年,學的是作琴技巧,此時的物與我、人與琴是分開,而非融合的,“不能移人之情”而多刻意為之。援琴作歌則需要在“精神寂寞”處,譚元春評“精神寂寞”四字云:“大道妙藝,無精神不可,然精神有用不著處。‘寂寞二字,微矣,覺‘專心致志四字至此說不得。”[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頁。]“精神”如同摩詰詩中處于“有無中”的山色,不再以全然的理性看待外物,主體的主體性似乎在慢慢消失,詩便于此時發生。相較于“精神寂寞”,“專心致志”在這里顯出了太多的目的性和主體性。喻之于詩,詩歌發生于“精神寂寞”處,主體之情與外在之景相融,詩歌與詩人相融。在詩人與外在事物的接觸之際,其內心的感情油然而生,就像伯牙因成連“旬時不返”,其悲切之情從胸中油然而生一樣,并與“海水”“山林”“群鳥”相融合,這便是“移人之情”,然后援琴作歌,則自然就能做到詩與樂相融、主與客渾融。
情與理相融的極致不是用理性的語言表現,而是用外在的物象呈現的,所以,“行氣”需要落實在具體的物象之上,即“真詩精神”需要通過詩歌意象呈現出來,這就涉及一個“取象”的過程。對于“象”的選取,鐘惺《蜀中名勝記序》云:“要以吾(伯敬)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7頁。]所謂“出乎述作之外”,在于通過山水寄托“吾(伯敬)與古人之精神”。再如,鐘惺《寄吳康虞》云:“舊識南中半,公還自古人。意于林壑近,詩取性情真。”[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2頁。]可見,竟陵派詩人的“取象”范圍應以“山水”“林壑”為主。
竟陵派詩人所選取的物象多為細小之物。《唐詩歸》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云:“少陵不用于世,救援悲憫之意甚切,遇一小景、小物,說得極悲憤、極經濟,只為胸中有此等事郁結,讀其諸長篇自見。”[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5頁。]評《苦竹》云:“每一小物,皆以全副精神,全副性情入之,使讀者不得不入。”[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1頁。]杜甫詠物詩“生其性情,出其途轍”[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5頁。],其詠物詩雖然都出自“性情”,但是由于所詠之物不同,所以寄托的情感也就不同。至于選取“小物”“細物”的原因,一方面,“就小物說大道理,古人往往如此”[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頁。];另一方面,“豪則泛,細則真”[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頁。],將感情寄托到細小的事物中,才能顯得真切具體。
總之,“行氣”的過程與“真詩精神”的呈現相關,詩人通過這一程序將自我的涵養之情“外化為作品的氣脈和節律”[汪涌豪:《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體系》,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56頁。],外化為詩歌中的“一片真氣浮動,無一毫境事碎瑣參錯”[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2頁。]。所謂“活則深,板則淺”[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2頁。],寫詩不是材料的堆積,如果詩人不懂得“行氣”之法,他的詩作便了無生氣,正如《古詩歸》評張華曰:“古今極博人,下筆出口多不能快。人謂司馬遷高才,恨其不博,予(友夏)謂使其極博,恐胸中腕中反不能如此。試觀張茂先詩,有何首高妙動人處?《答何劭詩》《雜詩》已被選而復汰之,味不足也。”[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6-147頁。]
四
詩人通過“養氣”的功夫涵養性情,但是需要達到什么樣的程度才能獲取“真詩精神”,這就不得不說一下“厚”與“真詩精神”之間的關系了。從主體“性情”的角度來看,鐘、譚二人所謂的“真詩精神”是對德性之正與才性之奇的追求。那么,才性與德性之間,一奇一正,如何才能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呢?鐘惺《東坡文選序》云:“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即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5頁。]在德性與才性之間,他更重視德性的有無,即魏武帝“殺惡性者”之意。但是詩文創作離不開主體的才性,正如魏武帝欲殺“妙于音而性惡者”卻“難其才”,所以,他對才性也很珍視。那么,如何在這一兩難之境中做出取舍呢?一方面,就德性而言,應對有才而“性惡者”,修養其德性,使之存善去惡而又保有其才。另一方面,從才性的角度來說,則需修持主體的“靈心”,使其與德性相諧,并達到“厚”的狀態。如鐘惺《與高孩之觀察》曰:“詩至于厚而無余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即能厚。第(伯敬)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峻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51頁。]“詩至于厚”則“無余事”,追求的是主體德性與才性的相諧,“妙合無痕”[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頁。]而達到的“厚”的狀態。就作詩的門檻來說,有“靈心”才能作詩,強調的是個人之才性;而個人才性需要與德性融合并達到“厚”的狀態,才能獲得“真詩精神”。進一步來說,“厚”的取得是以古人精神作為導向的。鐘惺認為作詩需“盡其才以達于古人”[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21頁。],譚元春《汪子戊己詩序》認為,“汪子以抑塞之奇才,閉門十余年,與古人精神相屬”[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87頁。]。他們均強調主體性情要符合古人之精神[李永賢《論清初詩歌選本中的詩學反思》指出:“明末竟陵派以提倡性靈為號召,反對復古派的喪失性情”,其追求的性靈以古人性情為歸。參見李永賢:《論清初詩歌選本中的詩學反思》,《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而“真詩精神”的核心便是德性與才性的相融與相諧。
由于時代不同,主體的才性與德性會各有偏向,所以,主體通過“養氣”功夫所獲取的“真詩精神”便存在差異。由此而創作的詩歌或偏于德性呈現出“平而厚”的風貌,《詩歸》多以“平”“和”[《詩歸》與“平”有關的評語,如“平調不膚”“壯語平調”“平平淺淺”“平遠”;與“和”有關的評語,如“氣和”“清和”。]等字評價詩歌風貌上的平和。當然,偏于德性并非忽視才性,譬如,評宋之問《途中寒食》云:“此詩可謂平極矣,何嘗不動奇眼。”[鐘惺,譚元春:《唐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頁。]評語說的是詩歌應在風貌平和之中擁有奇思奇想。或偏于才性而呈現出“奇而厚”的風貌,《詩歸》多用“奇”“奧”[《詩歸》中與“奇”有關的評語,如“雄奇博厚”“幽奇深秀”“正理奇調”“奇險”;與“奧”有關的評語,如“清奧”“奇奧鮮秾”。]等字來評價詩歌風貌的奇奧。同樣,所謂“奇”也離不開性情的樸厚,其原因在于“刻生于樸,奇生于厚”[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頁。]“妙在奇奧處從樸野出”[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頁。]。
竟陵派詩人所強調的“厚”不只是文學風格論的范疇,在更大的程度上屬于心性本體論的范疇。在他們看來,“厚”是對心性本源之完整不可分割性的描述,是德性與才性的完美融洽,李瑄認為:“‘厚不是審美的中正深婉,而是本體遍照萬物時的涵容狀態,是虛靜感通與浩然充滿的統一。”[李瑄:《〈楞嚴經〉與竟陵派文學思想的指歸》,《文藝研究》,2019年第8期。]可見“真詩精神”是創作主體主客未分、物我相冥狀態的詩性展現,所謂“才不由天,以念所冥為才”[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6頁。]“未有不幽恬淵凈,而可謂真揮霍弘才者”[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35頁。],“冥”與“幽恬淵凈”正是對主體性情達到“厚”時的準確描述。當主體經過“養氣”功夫而使得性情達到“厚”的程度時,便接近于“道”了,譚元春《王先生詩序》云:“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王先生欲以古人之道,安于性情而行于詩。”[譚元春:《譚元春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80頁。]言性情為“近道之物”,接近“性”之本體。正是在此基礎上,陳廣宏認為公安派與竟陵派論詩有表現理論與形上理論之分[陳廣宏:《竟陵派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24-326頁。],以突出竟陵派“真詩精神”的超越性質,此一觀點有其合理性。然而,詩歌必然是涉文字的,若全然涉“道”,如何用語言文字去表現詩人“與道交融的無言境界”[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年,第82頁。]?顯然,竟陵派詩論中的“性情”概念是包含有“情”之發用的,所謂“古人所以寄其委婉之思”“以古人之道,安于性情而行于詩”,實則包含了性情之“性”與“情”兩個方面,只是“性”與“情”兩者之中以“性”之本體為主,因而其詩論以形上理論為主而兼有表現理論,其性情可近“道”而不等同于“道”。而“性情”涉“道”的部分就是對“真詩精神”的一種闡釋:就德性而言是儒家之倫理,此為本;就才性而言是道家之自然,即主體之“靈心”。
也斯曾說:“我抬頭看見一朵云無言遠去,而我仍走在人來人往的灰塵的路上。”[也斯:《山光水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13頁。]或許這也是鐘、譚二人所面對的境況吧!在一個逐漸世俗化的社會中,主體之“性情”難免不被周遭的喧囂所侵擾,詩人漸漸失卻了作詩所需要的那份純粹與天真,擁有的只是處理世俗瑣事所需要的世故與理性,如此作詩便如黃茅白葦般毫無生機。如若仍有“真詩”存在,則需暫時抽離于世俗之當下,滌清內心之雜念,或平心讀書與古人之精神相合,或虛靜其心在山光水影中體悟自然。在不斷的讀書、觀理之中厚養其氣,等待某一刻靈感的出現,從而完成一首詩的寫作,如此方能獲取“真詩”,正如鐘惺所云:“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后發而為言,有物有則。”[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17頁。]主體之性情不為外在之喧雜所困擾,不為傳統之詩法所束縛,以自我之靈心與古人精神相溝通,等候偶然的一刻,將領悟到的“精神”通過詩歌傳遞下去,以此抵擋時間的虛擲與浪費,或許這就是鐘、譚二人期望的“真詩精神”吧!然而,期望落到實處時,由于鐘、譚二人受性格、遭遇以及社會思想等因素的影響,所謂的“真詩精神”在其實際創作中則偏向“幽深孤峭”的一面。
The Theory of “Temperament” and “True Poetry Spirit” by Jingling School
Li Yongxian,Zhou Daoh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
The poets in Ming Dynasty mostly emphasized that “true poetry” is the truth of the subjects “temperament”,and they had different views about poetic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emperament”.Zhong Xing and Tan Yuanchun comprehend the “true poetry spirit” through the pursuit of the subjects virtue and talent.First, the integrity of the subjects virtue emphasizes that the emotion expressed in poetry should not violate the Confucian ethics, which 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of “elegance”. Second, the subject of remarkable talent, emphasizing that poetry should show the beauty of literary talent and language concise, which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oist view of natur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true poetry spirit”, they believ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subjects “temperament” in a way of “nourishing qi”, and then cultivate it through the inner peace and full reading of poetry.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nourishing qi” is to make the “temperament” of the subject conform to that of the ancients. Virtue and talent are integrated and present a “thick” state, which constitutes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ue poetry spirit”.
Key words:Jingling school;temperament;true poetry spirit;nourishing qi
[責任編校 海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