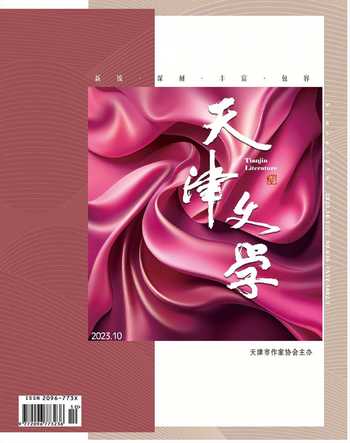呈現戰爭傳奇的另一種較量
穆繼文的寫作,何時由詩轉為小說,尚是個謎。十多年前,他攜著兩部厚厚詩集《午夜的風》《走進紅土地》走向詩壇,亮相伊始,即贏得一陣碰頭彩。此后一段時間,他陷入了寫詩的癡迷狀態,每日動筆,手癢難耐,不吐不快。那時我就發現,他的詩中含有某些值得注意的敘事元素,因而日后他的“華麗轉身”,改寫小說,并不意外。
埋首小說創作的穆繼文,充分享受著敘事虛構帶來的融融快意,筆墨間以往讀者所熟悉的穆氏詩性語境悄然隱去,仿佛有面目皆非的感覺——布局嚴謹,題材奇異,人物多面,深入其間卻可以發現,其創作主體的美學傾向并無根本改變。小說《任務》,作家致力于打造戰爭傳奇,還原隱秘的歷史現場,延續的仍是穆繼文很看重的紅色革命歲月書寫,依然是氣正血熱,筆意酣暢,只不過換了一種敘事虛構的話語方式。
《任務》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抗戰時期的中國北方。盤踞于津門市的日軍預感末日來臨,密謀了一個驚天的殺戮計劃——“櫻花行動”,企圖在退出戰場之前殊死一搏,加害千千萬萬的中國無辜百姓。這個“計劃”極其殘忍、陰毒,卻取了一個異常美麗、妖嬈的名稱,使人想起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的《菊與刀》。這部著名的文化人類學著作,從明治維新講到日本發動戰爭,分析了日本人獨特的風俗習慣和島國文化、民族性格,以及自我“道德”訓練的由來。所謂“菊”與“刀”,前者寓意日本皇室形象,后者表征武士道精神,兩種對比鮮明、截然不同的意象,正是黷武而尚美的日本軍國主義的面目拼圖,而“櫻花行動”的設計,在骨子里確與其有異曲同工的意味。
櫻花起源于中國的秦漢時代,日本只有千余年的栽種歷史,由于日本曾培育出觀賞性更強的櫻花品種而冠絕世界,便成為舉世聞名的日本國花。小說中,代號為“櫻花行動”,就是日軍在津門市秘密研制出生化武器“櫻花菌”,以感染者做標本,在津門市形成無可救藥的大范圍“霍亂”,迅速傳播、蔓延至華北地區,乃至全國,一旦成功,必將天下大亂,無數中國人將命喪于沒有硝煙的戰場。我方抗日力量最急迫的任務,就是利用抗戰諜戰人員的特殊作用,以“飛蛾撲火”特別行動,千方百計,不計代價,力阻日軍“櫻花行動”的實施與得逞。
《任務》以其戰爭傳奇的敘事文本出現,對于同類紅色革命題材的書寫是個挑戰,以至于此類“資深”讀者的以往閱讀經驗基本失效。小說中,各類相關人物擺脫了戰爭機器的符號設計,我方承擔此一重大“任務”的執行者,不再是宏大敘事中被標簽化、臉譜化的正面群像,敵我雙方的殊死角逐,也不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關系,他們明里暗里、此長彼消,你來我往、斗志斗狠,共同演繹出驚險酷烈的一幕傳奇大劇,為當代新歷史主義戰爭小說注入新的質素。
小說圍繞“櫻花”行動的驚險較量展示了一系列的多線頭纏繞處理能力,卻又不失某種紀實質感。纏繞寫法是豐富小說內涵的有效手段,秦五哥與日軍軍官野澤寧子及其父親野澤熊浩一家的纏繞,與日本姑娘野澤英子異國戀的纏繞,與抗日游擊大隊政委劉魚兒的“娃娃親”的纏繞,與蔣大川、“飛蛾”皮科恩等戰友的纏繞,涉及日本留學、中日提親、潛伏臥底、指腹為婚、佯裝叛變、背負罵名與默默付出、“飛蛾撲火”舍身赴死,如此種種,枝枝蔓蔓,方方面面,以此支起結構、串聯故事、推動情節、引爆結局,將“起承轉合”的中國傳統敘事模式翻新再造。閱讀過程中稍有滑脫,很容易被置于迷宮境地,需要不斷地重溫曾被層層鋪墊過的情節和人物,確認故事的脈絡與走向。
主人公秦五哥在日偽控制的郵電局電報室當副主任,作為秘密打入日本特務機關的臥底,頂著“漢奸”的罵名,冒著隨時掉腦袋的風險在特殊領域同日軍周旋。他曾經留學日本,與后來成為日本軍官的野澤寧子是同學,同時得到野澤一家格外照顧,他懵懂初戀的單純少女英子,還是殘忍如魔鬼的野澤寧子的妹妹。這一切,為秦五哥執行任務提供了便利,同時在國仇與私情之間也不免會有內心掙扎。五哥正是在種種取舍和堅持中,經受住嚴峻考驗。
野澤寧子作為嗜血成性的“惡魔”,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民粹灌輸和戰爭洗腦,年輕學生野澤很快就完成了靈魂扭曲的畸變。“經過半年的戰爭,他身上留下了多處傷疤,在肉搏中,他的左眼和下巴被抗日敢死隊戰士用大刀砍傷。現在一塊重重的疤痕貼補在左眼皮上,阻擋了他的白眼球和視力,造成他的左眼只露出一個黑眼球,像是一只怪獸的眼”“他笑起來更是讓人發瘆,他只要一笑,就要死人,只要是抗日義士他殺無赦”,這已經超出一般的肖像描寫,而成為人性變形的寫真。
圍繞“任務”的完成,我方人員以犧牲自己全力配合五哥的工作,許多橋段和細節感人至深。秦五哥背負著“漢奸”的罵名,一直過著忍辱負重的“雙面”生活。“女俠”劉魚兒,曾以自己“娃娃親”的“漢奸”對象五哥為恥,后來知道真相,生出愛慕,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甘愿為五哥完成“任務”而獻出生命。她與忍受“苦肉計”的“叛徒”蔣大川,重要領導人“飛蛾”皮科恩等等,在種植有櫻花的磐山“洞穴”同歸于盡,為國殉身。五哥潸然淚下,“為了支持我的潛伏,把鬼子的‘櫻花行動情報搞到手?他們這是‘飛蛾撲火,舍生取義!”這其實也道出了《任務》的主旨與價值。
書寫這部具有傳奇意味的抗戰小說,作家揪住故事主脈,絕不偏航,層層鋪墊,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引而不發,收控自如。雙方較量中并不急于抖出“包袱”,一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即戛然而止,絕不拖泥帶水,體現了作家的敘事自信和駕馭能力,也為作品添加了一定的閱讀魅力。
黃桂元,文學創作一級,天津市作家協會原副主席,第八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在百余家海內外報刊發表文學作品與批評文章約三百萬字,作品被多家選刊轉載。曾獲第十八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等。
責任編輯: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