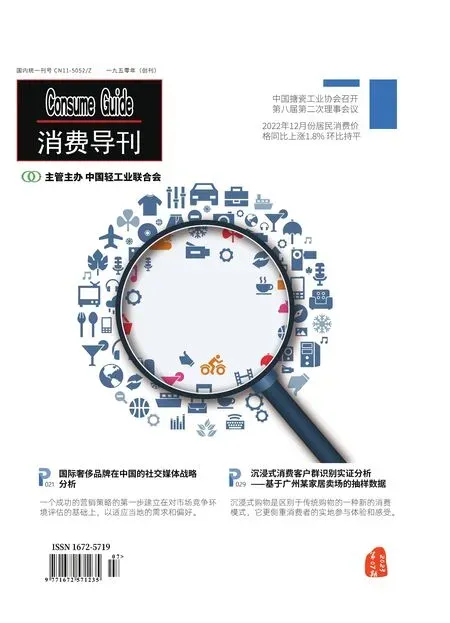大學生群體的人情消費異化研究
丘彩珍 福州大學
自古以來,“禮尚往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人與人之間的來往講究“禮”,講究“人情”。一定的人情交往能夠促進人們的互動,增進人們之間的情感,還能夠鞏固彼此之間的關系,對于形成一個和諧的社會有著莫大的作用。但近幾年來,隨著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上升,人們的消費觀念也隨著發生轉變,人情消費成為生活中一項必要的花銷。而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大學生群體盡管身處校園但也逐漸受到影響,其人際交往關系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們傾向于人情消費。
人們進行人情消費無非是想通過這種方式構建或者鞏固雙方的關系,從而獲得情感上、物質上的東西。同樣的道理,大學生進行人情消費是因為他們想要通過這種交往方式去交流情感,交換彼此間的資源。大學生的人情消費其實是在搭建屬于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這是獲取社會資本的一種方式,這種行為正是在自己的社會網絡中與他人互通人情,履行收禮回禮的義務。[1]正如梁漱溟指出,每個中國人都是地道的依存者,中國人要成功地生活于人世間,不能僅僅顧及自身,而應該在一種對應關系中盡一份責任與義務。大學生遠赴陌生之地走上了求學路,為盡快“扎根”于此而構筑一個穩定的人情網絡,那么人情交往便逐漸成了大學生群體消費的重要內容。在中國,人情往來是一項由來已久的行為,是被身處于社會網絡中人們所需要的。但是,當今社會盛行“凡事需人情,有禮才能行”的觀念,人情已經變成一種受利益驅動而運轉的畸形情感,并且這種畸變的現象也在校園中蔓延,眾多的大學生被裹挾著不知不覺地陷入了人情消費這個漩渦當中。
一、人情消費相關研究
儒家經典《禮記》記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這便是人們常用來描述人情的“禮尚往來”。以往學者對人情消費的研究大體集中為以下幾種:
第一,學者講述人情、面子是中國情理社會中的社會交換方式。[2]黃光國把“面子”“人情”整合在一起,認為這是理解中國人行為的關鍵,同時,“面子功夫”和尋求私人網絡是中國社會中最為基本的權力游戲。[3]翟學偉提出,人情與面子是嵌入于地方社會網絡之中的,而在社會網絡的形成中最重要因素是關系和權力。
第二,學者對農村當中的人情消費進行研究。[4]朱曉瑩提出,人情消費是農戶用于人情往來的禮儀性消費,也就是有關系的雙方進行交換的貨幣、物品或勞務。[5]之后劉軍對人情消費提出了他的定義,“人情消費指的是在自愿情況下因為人際關系而非自身的直接消費支付給他人的支出,有時也成為隨禮”。簡單說,人情消費就是人們在行人情時所花費的金錢或物質。
第三,有關城鎮中的人情消費。[6]何琳霞指出,人情消費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維系情感的重要社會行為,曾經起著積極的社會作用,但隨著我國城市消費水平的提高,異化的人情消費扭曲了人際關系、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經濟負擔。對此問題,應引起充分的重視。[7]杭斌(2015)通過研究發現人情支出對城鎮居民的消費既有促進效應又有擠出效應,且后者明顯大于前者。
總之,學界對人情消費研究的方面和類型眾多,但是關于大學生群體人情消費研究并不多。
二、研究設計
筆者以福建F大學為調研點,選擇F大學中的全日制本科生(大一到大四)為調查對象,調查的方法以問卷調查為主,本次調查研究采用自填問卷式,問卷的編制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用開放式問卷了解當前大學生人情消費的主要行為表現,然后篩選,將有研究價值的問卷定為初始問卷。接下來在大學生中發放這個初步的問卷進行試測,對試測結果進行問題總結,并結合已有的研究確定問卷的結構和框架,形成大學生人情消費行為項目分析和因素分析,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抽取大學生人情消費行為中存在的共同因素的問題,以此來分析當代大學生人情消費行為。共發放200份問卷,在回收的196份問卷中得到189份有效問卷。筆者使用SPSS軟件對搜集來的數據進行量化分析,以直觀的方式展示調查的結果。同時,為了更加深入了解大學生人情消費的特征、原因等方面,筆者也對一些調查對象進行了個案訪談,將所收集到的定性資料與定量資料相結合,深入探討F大學大學生人情消費行為,發現當前高校大學生的人情消費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得出本研究的結論。
三、大學生人情消費異化表現
(一)人情類別異化:人情名目繁多
經過調查發現,盡管身處校園,但是大學生人情方面的花銷并不少,多為“寢室班級聚餐”“過生日”“找人辦事請客吃飯”等等(見表1)。朋友同學生日、一些重要的如圣誕節、平安夜、中秋節請客送禮是不可避免的;麻煩其他人幫自己辦事不好意思欠別人人情,那就需要送他禮物、請他吃飯;談戀愛、交朋友過程中相互贈送禮物也是必不可少等等。如今,大學生非常明白社交場合中如何交朋友,“朋友多了好辦事”。

表1 大學生的人情消費類別
同學C:“上大學之前沒想過會花七七八八的錢在這些活動上,有時候月底算算生活費,就發現一個月下來聚餐、送禮物就得花好幾百,如果月底聽到要聚餐了,心里想又是一筆錢,有點抗拒,但是你又沒辦法不去參加。”像這樣的回答并不少見,多數同學的情況大同小異。由調查數據及訪談結果可知,大學生被卷入諸多人情名目中不堪其擾,也十分無奈。
(二)人情邊界異化:人情范圍擴大,頻次加快
人情邊界異化指的是人情往來從以往關系親近者跨至有點關系者。在傳統社會,人情往來限于關系親近或較好的親戚朋友。而現在,由于人們的流動性加強,人際關系不只限于血緣和地緣,還增加了業緣,大家不再過多考慮關系遠近,而是稍微有點關系的都要參與人情往來,這也就導致了人情范圍擴大,頻次加快。在校園內,由于大學校園活動的多樣性,大學生的人情往來不僅僅局限于舍友、同學,還可能涉及不同專業、不同學院,甚至是外校。有些受訪者表示偶爾會因為某些原因要去陌生的社交場合:“有時候同學會拉我去參加外校的活動,是他高中朋友的聚會,我想著就多認識認識別的人,但是你去參加別人聚會、生日會,不能白吃或者空手去,是吧!有一次,舍友的學長畢業典禮,我被拉過去了,后面我就送了束花。”
除此之外,人情來往邊界擴大后,同學們就慢慢感受到人情消費的頻次變得更加頻繁。在大學校園,人情范圍不斷擴大,頻次不斷增加必然給大學生心理和經濟上帶來較大負擔。對于經濟條件略低的大學生們,人情消費次數增多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較大的經濟負擔和精神壓力。一位受訪同學表示:“每次挑禮物回贈別人的時候,我都感到壓力,挑選禮物很頭疼,需要花錢也很頭疼。每年都要經歷好幾次這種抓耳撓腮的情況,次數還可能一年比一年多”。
(三)人情儀式異化:面子、攀比、從眾等觀念盛行
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出于面子、攀比和從眾心理進行人情消費的占一半以上。在傳統社會中,人情活動圍繞儀式來喚起人們之間的共同情感,拉近彼此之間的關系。但人情活動中聯結情感的儀式逐漸被面子、攀比、從眾等觀念所支配。在大學中,同學們對節日的氛圍極其看重,需要過的節日種類逐年增加,并且隨著互聯網的傳播,大學生們的跟風模仿現象進一步的發酵。
同學Z:“大家可以從網上看到其他人在過什么節日,秀禮物曬朋友圈。去年女生節,隔壁專業的班長給他們班上女生買了女生節禮物,他們同學曬出來了,壓力給到我們班長,后面他下午就去準備了。”互聯網的傳播讓大家看到其他人生活的不一樣,但是這樣由于面子、攀比、從眾等觀念異化了人情活動中原本聯結情感的儀式,變得不切合自身實際,人情活動的內涵變了,正如同學F的妥協:“上次班級聚會,我不想去,但是舍友們都去,后面想了很久還是和他們一起去”。學生群體中,由于部分同學不愿意因特立獨行、與眾不同而感到孤立,不少人選擇跟隨大眾進行人情消費。為了維持好自己和集體之間穩定的關系,這部分大學生會盡可能參與到集體當中,不希望自己成為那個“特別的人”。
四、大學生人情消費異化分析
(一)大學生人情消費的動機
一種社會行為產生的原因是人的社會性動機,而動機又來源于社會需求。以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為依據,我們可以了解到人情消費是一種需求,尤其是在中國社會,這種需求極為明顯。從交往的目的來看,大學生之間的人情往來可以分為兩種:情感型交往和功利型交往,既有盲目性也有理性。

表2 大學生人情消費的動機
通過對調查數據進行歸納整理,可以將大學生身份分為兩類:一般學生和學生干部,并就這兩類身份和人情消費的原因進行分析。學生干部比一般學生多了一個身份,也就意味著他們需要再“盡一份責任與義務”。而從一般學生競選成為學生干部是也就可能提前進行相關的人情消費:“想當學生干部就要和同學關系融洽,平時和一些同學拉近關系,給自己一些表現的機會,比方說平時買奶茶或者小零食去其他宿舍串門。寒暑假從家里返回學校,可能要買一些家里的土特產帶給同學,同學多了,這也是一筆不小的花銷。”同學在班級內成為班干部,服務的對象是自己的同班同學,但是在彼此交往時也可能需要進行一些人情消費,這是對關系的一種維系,也會對自身良好口碑的建設,同學A表示“當了班干部,像班長、團支書,到過節的時候需要自掏腰包或者拉上其他班干部一起買過節小禮物送給班上的同學。平安夜要送蘋果、圣誕節送零食等等,節日很多的,現在學校還流行過男生節、女生節。”同樣,學生會的部門內部也需要進行相應的社交網絡的建構:“我是社長,我們今年中秋節就有送社員月餅,等后面平安夜還有蘋果。因為這個是之前的傳統,我在當社員的時候上一任學長學姐就有送這些禮物,就是一些心意”。
通過調查訪談發現,一般學生以情感交流、娛樂消遣為主要動機,出于從眾心理進行人情消費的人數,一般學生要多于學生干部:“部門聚餐和班級聚餐是每一年基本上都有的,剛加入部門就要新人一起聚一下,如果一個人同時參加好幾個部門,聚餐時間又差不多,那就夠嗆的。我去年班級、部門都安排差不多的時間,連著聚了兩天的飯。沒辦法,大家都去。”而相較于一般學生,學生干部需要在建立人脈、獲取資源、鍛煉社交能力等方面進行必要的消費,由此可見,學生干部進行人情消費的目的性稍微更強。
(二)人情消費異化原因
1.個人層面:社會支持網絡的支配
社會支持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它既包括家庭內部和外部的支持和維系,還包括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和幫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至今被人們奉為經典。在這種文化影響下,個人或家庭努力建構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以應對各種風險。他們都傾向于使用人情消費的方式來搭建自己的人際網絡,從而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情感滿足和社會資源等。我們付出報酬,也能夠獲得一定報酬,按照這種循環的方式,以資源交換為動機的人情消費可以說是一個社會交換過程。一般而言,學校里面學生干部的積極性比較高,具有一定的能力,他們作為學生代表被選出來,就是為了搭建一座溝通老師和學生的橋梁,因此,這就意味著了他們需要花更多的精力與時間去獲取資源、建立人脈、傳遞信息進而協調好學校和學生之間的關系。[8]
2.心理層面:互惠原則與人情倫理
人情往來依靠互惠機制,通過“饋贈—回報—饋贈……”的互惠機制,人們始終處于人情互相虧欠的關系中。“互欠”關系在“互惠”機制下形成一種封閉的循環模式,使人們一旦進入此種關系就基本不能退出。[9]正如費孝通所說:“在親密的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在很多方面和很長一段時間內相互依賴。因此,在給予和接受之間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地解決債務,所以親密社區的團結就依賴于彼此拖欠的未償人情”。
互惠機制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機制,也是一種心理機制。對于處在“互相虧欠”關系中的學生來說,他們脫離當前人際關系,會面對心理上的愧疚感。校園是一個圈子,大家都彼此熟悉且緊密聯系,“如果我不送禮物,就會丟面子,感到尷尬”,所以,即使在人情往來上有經濟負擔,他們也會咬牙堅持。但是,如果一個人的禮物不能得到預期的回報,那么交換就會中斷,這就使人們被迫承擔來回交換禮物的義務。正如一受訪者提及“因為之前有吃別的同學家里帶的土特產,就感覺每次都吃別人的東西,自己沒有帶過會不好意思,所以后面也會特別考慮到下一次自己也會買點東西回禮”。[10]
3.思想層面:面子觀念與利益博弈
在之前的社會中,人情消費是一種互利的人際活動。學生是否進行人情的往來,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目前社會的人情消費中,人情儀式和目的已出現異化,一些學生因為盲目的跟風和模仿,造成其他學生受面子上的影響,進一步促使人情消費異化。并且,隨著學生對于人情儀式中利益的看重,慢慢地人情儀式的情感性意義漸為衰弱,而功利性日益突顯。如果有人總是處于行人情的狀態,那么他不僅經濟利益會受到損害,面子上也過不去。因此,為了平衡面子和經濟利益就會竭力要求舉辦儀式,比如為了他人的回禮而舉辦生日會,最終在面子與利益的博弈中,人情消費走向異化。
結語
大學生群體進行人情消費,其實是想通過這一方式,在校園內與其他人交換物質資源或非物質資源,進而滿足自身物質和精神上的各種需要。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學生的人際交往動機出現了異化,他們交往的出發點不單單注重情感上的交流,而是逐漸看重自身的發展,換句話說,大學生們可能會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礎之上,這種情感慢慢地變質,就會成了一種相互利用的工具,所以,大學生人際交往展現出兩種形式:情感型、功利型。并且復雜的社會環境或多或少影響到校園內的大學生們,同時大學生自身的辨別能力相對薄弱,大學生在人際交往中也不得不以人情消費作為建立情感交往的重要手段。同時,一些大學生有著強烈的自尊心與虛榮心,他們渴望得到別人的關心、重視,以實現他人對自己的尊重。于是,在人際交往中通過沉重的人情消費來博得他人的“羨慕”和“贊賞”使他們得到了自尊與虛榮的滿足。因此,社會要多加關注大學生群體人情消費狀況,培養他們樹立合理的人際交往和消費觀,讓大學生意識到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如果能做到彼此坦誠相待,用心交流,一定可以使雙方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上建立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是經得起考驗的,不管在現在還是在以后的生活學習工作中,都能夠做到相互幫助,相互支持。人情消費并不意味著壞處,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社會是有正向作用的,所以大學生一定要正確看待自己的人際交往,并且養成正確的消費觀,不要走入人際交往的誤區,也不要一味地跟從大眾隨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