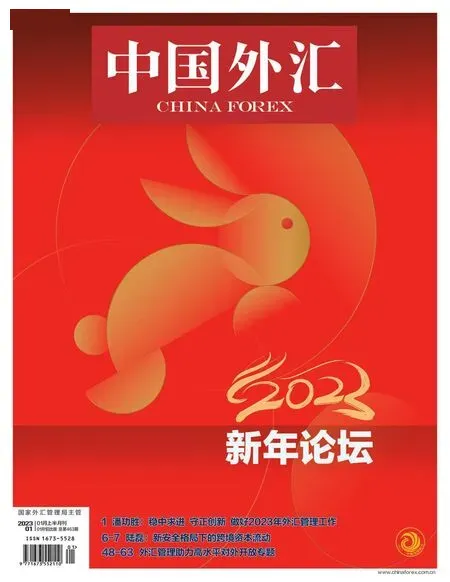美國的財政和公共債務穩健性分析
文/陸曉明 編輯/張美思
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問題由來已久,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這些問題更加惡化,并且預計未來仍難逆轉。本文分析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的歷史及現狀,探討財政政策貨幣化在其中的作用,預測其未來10年的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采用美國及國際常用的基準評估美國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的穩健性,并研究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持續上升對美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危害。
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的歷史及現狀
特朗普政府的順周期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和債務在疫情前大幅上升。美國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的70年基本上采取逆周期財政政策,即在擴張期緊縮財政降低赤字和債務,為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衰退做準備。但特朗普政府采取了順周期財政政策,在經濟擴張期繼續增加財政支出,導致財政赤字及聯邦公共債務(不含政府間債務,以下主要采用這一指標)在2017—2019年持續上升。
疫情及衰退發生后美國實施的財政政策比以往任何一次危機期間都更激進。在美國歷史上除了二戰和2008年大衰退外,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值很少超過5%;而疫情期間的衰退程度、赤字總量及其與GDP比值均已超過2008年衰退期間。大規模失業和企業倒閉使政府必須向家庭發放現金支票,向陷入困境的企業及地方政府提供緊急貸款和撥款。國會于2020—2021年先后通過的《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美國救援計劃》等政策使得財政赤字與GDP比值在2020和2021財年迅速上升到14.87%和11.9%,觸及二戰以來最高點。
美國的聯邦公共債務與GDP比值在二戰期間曾超過100%;此后大幅持續下降到60%以下;2008年衰退期間再次持續大幅上升;其后隨著經濟復蘇及政府去杠桿化增幅相對穩定;在特朗普政府的再杠桿化期間升幅也很有限。然而隨著疫情和衰退發生,公共債務從2020年一季度的17萬億美元大幅上升并在2022年二季度達到23.9萬億美元,其升幅遠超過歷史上的衰退及復蘇期間;同期公共債務與GDP比值在2020年二季度上升到104.6%的歷史峰值,隨后隨著經濟復蘇在2022年二季度下降到94.79%,仍然處于歷史高位。
財政政策貨幣化成為赤字和債務上升的新驅動因素。疫情發生后,美聯儲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通過兩個渠道影響著聯邦預算。一是寬松貨幣政策大幅降低了各期限市場利率。其路徑包括以下兩種:其一,通過降低聯邦基金利率降低中短期利率。從過去60年的年均值看,聯邦債務的凈利息支出在全部財政支出的占比與聯邦基金利率之間有0.43的相關關系,和10年期國債則有0.53的相關關系。這意味著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是維系低債務成本的重要因素(見圖1)。其二,通過大額資產購買(QE)降低中長期利率。疫情后美國財政部大幅增加了債券發行,美聯儲在新增債券中持有的份額高達62.6%,遠高于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6.5%。數據顯示,QE確實能夠有效降低中長期利率。例如美聯儲持有的國債金額和10年期國債利率之間在長期具有-0.68的相關關系(見圖2),這又進一步支持了美聯儲采用QE降低中長期利率的行為。美國財政部也因此在疫情期間以更低的利率增發了各期限定息債券,從而減少了未來若干年內的凈利息成本。

圖1 美國聯邦利息支出與全部支出比值及聯邦基金利率、10年期國債利率(年平均值)

圖2 美聯儲持有的國債額和聯邦基金利率、10年期國債利率(季度平均值)
二是寬松貨幣政策通過促進總體經濟活動增加了財政收入。其路徑為,首先,降低資本成本和信貸成本,鼓勵商業和消費支出;推高股票和房屋等長期資產價格,增加消費者財富效應;增加市場流動性,支持經濟活動。其次,美聯儲QE投資國債的收入轉付財政部增加了財政收入。特別是當短期利率包括美聯儲的主要負債——銀行準備金利率處于有效下限時,美聯儲通過QE提升中長期利率,擴大利差,進一步增加了國債投資收入,也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收入。2022年二季度美國聯邦財政收入從2020年一季度的3.78萬億美元增加到5.07萬億美元,增幅達35%;季度同比增幅平均達17.36%,遠高于歷史水平6.6%。
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未來10年的發展趨勢及其穩健性分析
美國國會預算署(CBO)基于現行稅收和支出法律總體上保持不變的假定,對2022—2032年的聯邦預算做了基線預測(CBO,2022/5),以下采用其中的預測值,參考財政及債務可持續性或穩健性評估的一般閾值和基準,并綜合考慮美國的國情,對未來美國財政及公共債務的穩健性進行分析評估和預測。
財政赤字
關于赤字穩健性的一般閾值是其與GDP比值不超過3%。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該比值曾從3%以下上升到9.7%;隨后開始下降,其年均值在2014—2016財年下降到2.77%;其后由于特朗普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再次回升,年均值在2017—2019財年上升到3.9%,并在疫情前的2019年達到4.6%。這意味著在疫情暴發前,美國的財政擴張空間已非常有限。疫情發生后,美國財政支出大幅增加,經濟產出減少,該比值在2020財年達到峰值14.87%,觸及二戰以來最高點。此后隨著GDP快速增長,新冠疫情相關的支出減少,收入增加,赤字從2020財年的3.13萬億美元到2021和2022年分別降至2.77萬億美元和1.37萬億美元,赤字與GDP比值在2021年下降到12.4%,預計在2022年下降到3.9%,在2023年進一步下降到3.7%,并觸及周期低點。未來隨著人口老齡化和人均醫療保健與社會保障支出增長,以及利息成本上升,預計財政支出將會再次顯著增加。預計2024—2032財年赤字年均值將達到1.648萬億美元,其與GDP比值的年均值將達到5.14%(見圖3),再次回落到3%以下的機會很小。

圖3 美國聯邦財政赤字與GDP比值(財年平均值,2022年以及后為預測值)
債務水平
關于公共債務水平穩健性閾值的確定更復雜。美國經濟學家萊因哈特和羅格夫在其“債務時期的增長(2010)”中將該閾值定為90%;而大多數關于債務與增長關系研究的共識都認為該閾值在75%到100%之間。美國公共債務與GDP比值曾在內戰、一戰、大蕭條和二戰等巨大危機事件時期大幅上升,并且隨后都曾大幅回落。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該比值再次持續大幅上升,但其與GDP比值仍在90%以下。疫情發生后,隨著公共債務再次上升,該比值也出現了跳躍式增長,并在2021年達到99.6%高點。根據CBO預測,該比值在2022和2023年可能分別下降至97.9%和96%;此后將再次回升;到2032年將達109.6%,不僅將超過其歷史高點107%(見圖4),而且可能在此后繼續上升。而如果美國立法者修改現行法律以維持疫情期間的某些政策,該比值則可能更高。

圖4 美國聯邦公共債務及聯邦公共債務與GDP比值(財年平均值,2022年以及后為預測值)
利息支出
財政及債務穩健性的一個主要指標是凈利息支出與財政收入及GDP比值。從凈利息支出與GDP比值看,美國的歷史水平是1.7%,最高點是3.1%,而2.5%是利息負擔嚴重超標的警戒線。從凈利息支出與財政收入比值看,穆迪將主權債務評級從Aaa下降到Aa的閾值大約是10%,這一水平和美國的歷史水平大致相等,持續高于10%則預示債務穩健性受損。
疫情發生前,由于特朗普政府增加公共債務,導致利息支出大幅增加,2016—2019財年凈利息支出與GDP比值從1.28%上升到1.75%的近二十年高點;凈利息支出與財政收入比值則從7.9%上升到接近11%的近二十年高點。疫情發生后,雖然利息支出隨著債務水平大幅上升,但由于美聯儲降息導致各期限利率水平大幅下降,2021財年利息支出與GDP比值降到1.6%,利息支出與財政收入比值降到8.7%。疫情以來,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同時發力,使得總需求快速增長直到超過總供給能力,導致美國出現了40年來最大幅度的通脹,美聯儲不得不加速提升利率和退出量化寬松,并導致各期限利率均大幅上升。未來美聯儲利率即使回歸2.5%中性水平,短期利率也會維持在2.5%以上,而10年期國債利率則可能維持在3%—4%之間。在債務水平已經很高并且持續增長的條件下,利率輕微上升也會直接推高各期限新發行及展期國債的利息支付并影響其穩健性。
據CBO預測,2021—2032財年,美國凈利息支出增幅將達240%,遠高于同期全部財政支出的增幅31%。相應地,利息支出與GDP比值將在2027財年再次達到警戒線2.5%;利息支出與財政收入比值則將在2024財年再次超過10%,并在未來若干年內持續上升,預計在2032財年再次達到18%的歷史高點,這將遠高于通常認定的穩健性閾值。
政府的政策利率
QE的實施使美國政府及美聯儲的利息成本對利率波動更敏感。美聯儲購買的大部分資產采用固定利率,但其主要負債——銀行準備金卻采用浮動利率,并隨美聯儲加息上升。在美聯儲加息又開始量化緊縮(QT)后,由于短期利率包括準備金利率升幅超過中長期利率,使收益率曲線變得平坦并且部分倒掛,導致美聯儲國債資產和銀行準備金的利差縮小,并減少了國債投資收入。2022年3—6月美聯儲凈利息收入僅增長了12%,遠低于同期總利息收入的增幅46%,原因正是利差縮小,而隨著利率進一步倒掛未來甚至可能發生利息凈損失。
債務期限結構
在利率持續上升的環境下,中短期債務占比過大可能進一步增加未來再融資的利息成本。目前國債平均成熟期為6年。根據美國政府問責署(GAO)的分析, 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償公共債務的64%將在2024年內到期,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按到期時的利率再融資。在各期限利率上升的環境下,這意味著未來的債務展期風險(以更高的利率為債務再融資的風險)也會大幅上升。
在不需大幅提高成本的條件下籌集大量債務的能力
其一,國債需求。國債在美國國內投資者組合中仍將占重要地位,在世界各國政府和企業的投資組合中也仍將占重要地位,因為全球尚未形成能夠替代美元的國際貨幣,未來也不太可能出現在深度、流動性方面能夠替代美國國債的債券市場。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國及國際投資者自2014年以來一直在減少對美國國債的持有,其在全部國債中占比從高點48%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1%左右。疊加美聯儲也開始減少國債持有,其在國債存量中的占比可能從目前約26%在3年左右下降到約10%。未來在國債持續增加的條件下,美國需要尋求新的投資者補缺,并且需要維持相似的價格,這將是很大的挑戰。
其二,國債流動性。美國國債市場對全球投資者最大的吸引力是無信用風險和極高的流動性。目前看來國債的信用風險基本不變,但隨著美聯儲大幅加息、QT,以及國債市場波動性指數(MOVE)持續上升并在2022年10月達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高位150,國債的流動性風險也在上升。而未來隨著美聯儲繼續QT,情況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流動性下降又會降低投資者意愿,并進一步提升融資成本。
是否存在削減財政赤字及債務的長期計劃,以及是否存在債務可逆性
雖然2022財年美國財政赤字比上一年減少了一半,達1.4萬億美元,但這主要是因為疫情相關的支出終止或減少。拜登政府并未制定削減赤字和債務的長期計劃,反而通過立法和行政令已經或將要實施大量可能增加赤字的項目,而唯一能夠減少赤字的項目是“降低通脹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因此預計美國財政赤字在2032年之前將再次回升到2萬億美元以上。進一步看,美國的赤字有許多長期、結構性因素,主要是人口老齡化和退休潮導致法定支出部分(老年醫保、退休社保等)持續上升。預計未來幾十年,這部分支出加上法定的利息支出可能占全部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這也將使削減財政赤字的難度更大、時間更長。而公共債務和赤字是孿生兄弟,這意味著公共債務的持續上升也難以逆轉。特別是成為常態的財政政策貨幣化行為也進一步弱化了美國改善財政及債務狀態的緊迫性,并將影響其長期穩健性。
債務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債務效率比
公共債務的成本支出需要靠財政收入償還,而最終支持財政收入的是經濟產出,因此債務效率比(單位債務能夠帶來的產出增長率)是衡量財政和債務穩健性的重要的長期指標。從歷史數據看,美國的債務效率比在20世紀70年代曾高達4以上。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著美國債務增幅大幅領先于GDP,該比值從2.8左右下降到1.4左右,隨后雖繼續下降但幅度有限。疫情發生前,該比值隨著美國債務增長在2020年已經下降到1。基于CBO預測值,未來10年美國潛在實際GDP年增長率可能維持在1.8%左右,而實際GDP則可能下降到潛在水平以下,同時債務持續上升,債務效率比也因此將進一步下降。預計在2028財年及以后,當美國公共債務超過名義GDP值,該比值也將倒掛(下降到1以下)。這意味著一單位債務支持的產出低于債務本身,同時美國的債務效率比不再具有合理性,美國將進入經濟赤字時期。
美國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持續上升對長期經濟的影響
各國實踐及學者研究均發現,當財政赤字和債務與GDP的比值上升特別是超過一定水平的條件下,繼續增加財政支出和債務不僅無法拉動經濟增長,反而會帶來一系列長短期負面作用。對美國過去50多年的數據作回歸分析發現,公共債務與GDP比值和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擬合優度R2為0.28的負相關關系。公共債務與GDP比值上升通過以下路徑影響產出的長期增長。
第一,擠出效應。一是通過擠出公共投資影響長期增長。不斷增長的利息支出會越來越多地消耗財政收入,從而可能擠占研發、基礎設施和教育等公共投資。特別是當債務與GDP比值達到一定高度時這種現象更明顯。過去60多年來,美國財政預算中的投資支出增幅滯后于全部財政支出,其在全部財政支出中占比從24%趨勢性下降,在疫情前達到10%;而在疫情發生后的2020—2021年進一步下降到8.67%和8.4%的歷史低點。二是通過擠出私人投資影響長期增長。在資金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公共債務大幅增加,并且成為許多金融機構必須持有的安全資產,其結果勢必擠壓私人投資這類生產性、高效率和具有競爭力的資源。CBO分析發現,公共債務每新增1美元,私人總投資將減少33美分,另有24美分投資可能從美國轉移到外國。私人投資減少將影響長期增長。首先,對增長率造成影響。對美國過去65年的數據作回歸分析發現,私人投資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擬合優度R2為0.59的正相關關系,高于政府支出與GDP增長之間的R2為0.027的正相關關系;同期私人投資與失業率增長率之間則具有R2為0.588的負相關關系,高于政府支出與失業率之間R2為0.0139的負相關關系。這提示私人部門支出增長在促進GDP和降低失業率方面的作用均大于政府支出。其次,對勞動生產率造成影響。對同期數據的回歸分析也發現,私人投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之間具有R2為0.256的正相關關系,高于政府支出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的R2為0.012的正相關關系。此外,政府債務增加會導致各期限利率上升,疊加美聯儲加息,會導致企業利潤及其預期下降,又會進一步擠壓私人投資及生產率增長。
第二,政府支出和債務償還的主要來源是稅收,財政支出和債務持續上升會使企業和個人形成關于未來稅收增加、退休年齡延遲、退休福利縮減的預期,并會影響企業信心及投資意愿,同時導致個人縮減支出增加儲蓄。
第三,政府在危機中的強行干預可能直接造成資源錯配,維持低效率甚至僵尸企業持續生存,影響長期生產率、債務效率比及潛在經濟增長率。
第四,難以應對新的衰退。美國在2008年進入衰退時,其債務與GDP比值僅為35%,大致為歷史平均水平,應對衰退的財政支持空間寬松;而在疫情發生前美國的財政空間已更狹小;疫情發生后及未來該空間將進一步縮減,不僅應對危機將會更加困難,而且無暇顧及長遠發展和創新,從而可能影響其長期國力和競爭力。
綜上所述,美國具有的特殊條件使其發生財政和債務危機的閾值更高,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赤字和債務可無限擴張,只是目前這個臨界點難以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