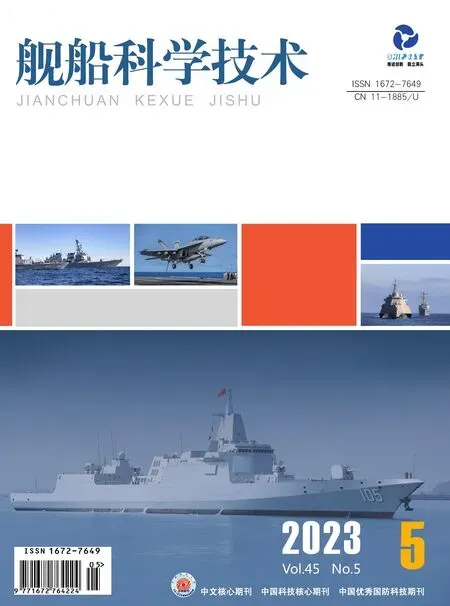進(jìn)江船型半懸掛舵升力性能優(yōu)化
黎 峰,王亞磊,顧 峰,丁 超
(上海船舶研究設(shè)計院,上海 201203)
0 引 言
相比常規(guī)全懸掛舵,半懸掛舵的結(jié)構(gòu)形式由于在展向(舵高方向)中部附近通過掛舵臂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支撐點,使得舵系梁的受力更加合理,可有效降低下舵桿處的剪力和彎矩,有利于控制舵桿直徑,因而在大中型船舶的舵系設(shè)計上得到廣泛應(yīng)用。但是,由于掛舵臂固定于船體中線,對上半部分舵葉的來流起到整流作用,減小了來流攻角,使舵葉整體的升力系數(shù)曲線斜率下降,升力性能明顯低于等展弦比的全懸掛舵[1-3],對船舶操縱性的影響是負(fù)面的。對于部分需要進(jìn)江航行的船舶而言,因內(nèi)河水域航道狹窄、交通繁忙,為了確保航行安全,必須具備良好的操縱性,如配備半懸掛舵,則易與操縱性需求形成矛盾。
在船型尺度確定的前提下,提高舵的升力是提升船舶操縱性的有效措施。本文對半懸掛舵的升力性能進(jìn)行優(yōu)化,改善配備半懸掛舵的進(jìn)江船型的操縱性。
1 設(shè)計條件
1.1 方案設(shè)計
以一型“曼谷型”集裝箱船為優(yōu)化設(shè)計目標(biāo)船型。該船型服務(wù)于中國至東南亞航線,因需頻繁進(jìn)出長江、珠江和湄南河等內(nèi)河狹窄航道,對操縱性有較高的要求。選取該船型已交付的同型船作為對標(biāo)船型(以下簡稱“原船型”),原船型的舵系采用半懸掛舵(以下簡稱“原舵系”),舵葉翼型為NACA0021,厚度比為0.21,可動部分舵葉面積為26.88 m2,舵葉展弦比(含掛舵臂)為1.835。優(yōu)化設(shè)計目標(biāo)船型(以下簡稱“目標(biāo)船型”)仍采用半懸掛舵(以下簡稱“優(yōu)化舵系”),經(jīng)過對外形的細(xì)微調(diào)整得到可動部分舵葉面積為26.99 m2,舵葉展弦比(含掛舵臂)為1.834,二者的側(cè)投影幾何特征可視為基本相同。舵系側(cè)視圖如圖1 所示。

圖1 舵系側(cè)視圖Fig.1 Side view of the rudder
原船型和目標(biāo)船型的船長、船寬、結(jié)構(gòu)吃水均相同,舵設(shè)計航速均取19.5 kn。
1.2 計算條件
對半懸掛舵的水動力計算及優(yōu)化基于雷諾平均NS 方程(RANS)及計算流體力學(xué)(CFD)軟件STARCCM+進(jìn)行。由于半懸掛舵與掛舵臂之間的間隙范圍大且特征尺度小,存在模型細(xì)節(jié)多、網(wǎng)格劃分復(fù)雜及計算結(jié)果易發(fā)散等問題,以往的研究一般按舵平均寬度或相當(dāng)展弦比將半懸掛舵重構(gòu)為相似懸掛舵進(jìn)行CFD 分析[2]。為了準(zhǔn)確模擬半懸掛舵的流動特性,本文采用精細(xì)化網(wǎng)格劃分對包括掛舵臂在內(nèi)的半懸掛舵進(jìn)行直接建模和計算。
計算模型按照1∶3 縮尺比建立,模型尺度雷諾數(shù)Re 約7.05×106,高于文獻(xiàn)[4]綜述后建議的舵CFD 分析的最小雷諾數(shù)6×106,一般認(rèn)為在這一雷諾數(shù)下,尺度效應(yīng)對舵的水動力系數(shù)已無實質(zhì)影響。按雷諾數(shù)換算得到模型尺度的來流速度Vm為5.792 m/s。湍流模型采用Standardk-ε兩方程模型,相關(guān)研究表明[5-6],Standardk-ε模型對單獨舵升力性能的模擬與模型試驗的綜合匹配程度相對較高。計算域的長、寬、高取為約20c×12c×10c,其中c為計算模型的平均弦長。使用控制域?qū)诿鎱^(qū)域進(jìn)行2 層加密。使用壁面函數(shù)法處理近壁區(qū)流動,通過初始壁面無因次距離y+值控制邊界層網(wǎng)格尺度,參考文獻(xiàn)[2]和文獻(xiàn)[7~8]的研究結(jié)果選取y+,實取y+約30~60。單個計算方案的網(wǎng)格總數(shù)約390 萬,大于文獻(xiàn)[6]中網(wǎng)格無關(guān)性驗證的最大數(shù)量網(wǎng)格方案。圖2 為模型周邊的網(wǎng)格劃分與過渡,圖3為間隙區(qū)的網(wǎng)格劃分。上述CFD 計算條件的準(zhǔn)確性已在其他類似研究中得到模型試驗的驗證[9]。

圖2 模型周邊的網(wǎng)格劃分與過渡Fig.2 Mesh division and transition near the model

圖3 間隙區(qū)的網(wǎng)格劃分Fig.3 Mesh division of the gap area
基于上述計算條件求解各方案0~35°攻角范圍的升力和阻力,得出升力系數(shù)和阻力系數(shù),其中阻力計算結(jié)果為舵和掛舵臂組合體的阻力。
2 優(yōu)化設(shè)計
2.1 翼型優(yōu)化設(shè)計
原舵系(方案0)采用的NACA0021 翼型具有阻力較小、便于加工的優(yōu)點,但缺點是升力系數(shù)較低。在不改變舵型和舵面積的前提下,為了使目標(biāo)船型進(jìn)出內(nèi)河航道時具有更靈活的機動性,優(yōu)化舵翼型的升力性能是有效的解決方案。
以NACA00 翼型為基礎(chǔ),采用微凹翼型[10]的理念進(jìn)行翼型優(yōu)化設(shè)計,即通過使翼型去流段適當(dāng)內(nèi)凹,增大繞流速度環(huán)量,達(dá)到提高升力系數(shù)的目的。最大厚度位于距導(dǎo)邊30%弦長的HSVA MP73 微凹翼型已較多地應(yīng)用于肥大船型的舵系設(shè)計[11-12],考慮到本船為高航速船型,半懸掛舵的空泡性能應(yīng)予關(guān)注[13],按照前GL 船級社的建議[14],將翼型的最大厚度位置由NACA00 翼型的距導(dǎo)邊30% 弦長位置后移至距導(dǎo)邊35% 弦長位置,由此得到一種新的混合翼型A,如圖4 所示。采用厚度比為0.21 的翼型A 進(jìn)行舵系設(shè)計,得到方案1。對方案0 和方案1 進(jìn)行水動力計算,得到二者的升力系數(shù)CL0和CL1及阻力系數(shù)CD0和CD1計算結(jié)果及對比如表1 所示。

圖4 翼型A 與NACA0021 翼型剖面對比Fig.4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ofile A and profile NACA0021

表1 方案0 和方案1 升力系數(shù)、阻力系數(shù)計算結(jié)果及對比Tab.1 Results and comparison of CL and CD between plan 0 and plan 1
表1 所示結(jié)果表明:方案1 的升力性能明顯優(yōu)于方案0,特別是20°常用攻角范圍內(nèi)升力系數(shù)增幅達(dá)20.1%(20°攻角)~37.3%(5°攻角);方案1 的零攻角阻力系數(shù)較方案0 增大了18.1%,按大中型運輸船舶舵阻力通常約占船舶總阻力1%計,方案1 將使船舶總阻力增加約0.18%,幅度較小。因此,采用翼型A 進(jìn)行半懸掛舵設(shè)計可以在微幅增加船舶阻力情況下有效提升舵的升力性能。
2.2 制流板優(yōu)化設(shè)計
在舵端部設(shè)置制流板,可以阻斷小展弦比舵葉端部的橫向繞流,增大弦向速度環(huán)量,從而提高舵的升力[10]。在一定范圍內(nèi)制流板的寬度越大,增升效果越明顯,但舵的浸濕面積也隨之增加,使得舵的摩擦阻力增加;另一方面,因制流板削弱了舵端部的三維效應(yīng)和端部分離,可降低端部誘導(dǎo)阻力和分離阻力。因此理論上存在一種尺寸的制流板,使得因制流板增加的阻力和降低的阻力相互抵消,使制流板成為一定攻角范圍內(nèi)不產(chǎn)生額外阻力的純增升裝置。
以方案1 為基礎(chǔ)進(jìn)行制流板設(shè)計及水動力計算,得到當(dāng)制流板寬度超出舵葉端部輪廓150 mm 時,零攻角阻力系數(shù)為0.039 0,與方案1 零攻角阻力系數(shù)0.038 5基本持平,將此方案作為方案2,頂端和底端的制流板設(shè)計如圖5 所示。方案2 的升力系數(shù)CL2、阻力系數(shù)CD2計算結(jié)果及與方案1、方案0 的結(jié)果對比如表2 所示。

圖5 方案2 頂端和底端的制流板設(shè)計Fig.5 Swash plate design at upper and lower ends of plan 2

表2 方案2 升力系數(shù)、阻力系數(shù)計算結(jié)果及對比Tab.2 Results of CL and CD of plan 2 and comparison
表2 所示結(jié)果表明:增設(shè)如圖5 所示的制流板,在35°攻角范圍內(nèi),方案2 與無制流板的方案1 阻力系數(shù)基本相當(dāng),對舵阻力無明顯影響;在15°攻角范圍內(nèi),方案2 的升力系數(shù)較方案1 有約5%左右的提高,有助于進(jìn)一步提高舵在小攻角的升力性能。20°攻角及以后,方案2 和方案1 的升力系數(shù)基本持平。
2.3 隨邊直尾化設(shè)計
隨邊線型對翼型升力系數(shù)有明顯的影響,將隨邊線型設(shè)計為平直(即直尾),可加大舵面水流的偏折,增加繞流速度環(huán)量,起到提高升力的作用[10,15]。對翼型A 距導(dǎo)邊90%~100%弦長段進(jìn)行優(yōu)化設(shè)計,使得最后5%弦長的線型保持與中線平行,得到直尾翼型A1,如圖6 所示。在方案2 的基礎(chǔ)上,采用直尾翼型A1 進(jìn)行舵系設(shè)計,得到方案3。方案3 的升力系數(shù)CL3、阻力系數(shù)CD3計算結(jié)果及與方案2、方案0 的結(jié)果對比如表3 所示。

圖6 直尾翼型A1 與翼型A 隨邊區(qū)域剖面對比Fig.6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lat tail profile A1 and profile A near trailing edge

表3 方案3 升力系數(shù)、阻力系數(shù)計算結(jié)果及對比Tab.3 Results of CL and CD of plan 3 and comparison
表3 所示結(jié)果表明:采用隨邊直尾化設(shè)計后,在30°攻角范圍內(nèi),方案3 的升力系數(shù)較方案2 有約2.1%(15°攻角)~5.9%(25°攻角)不等的進(jìn)一步提高;方案3 的零攻角阻力系數(shù)較方案2 增大了7.4%,較方案0 增大了28.5%,按大中型運輸船舶舵阻力通常約占船舶總阻力1%計,方案3 較方案0 將使船舶總阻力增加約0.29%。
從方案0 到方案3,舵的升力性能呈上升趨勢,阻力性能呈下降趨勢。方案3 較方案0 在20°常用攻角范圍內(nèi)的升力系數(shù)累計提高了24.1%(20°攻角)~52.5%(5°攻角),優(yōu)化幅度十分可觀。對一艘內(nèi)河船舶[4]和一艘近海渡船[16]操舵頻次的統(tǒng)計分析表明,前者絕大部分操舵舵角集中在-15°~+15°之間,后者超過90%的操舵舵角集中在-10°~+10°之間,因此小舵角升力性能的改善對于提高內(nèi)河或進(jìn)江船舶的操縱性是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的。需要說明的是,方案1~方案3在30°攻角之后都出現(xiàn)了失速現(xiàn)象,這主要是由翼型最大厚度位置后移引起的。實船上由于槳后尾流得到來自螺旋槳的能量補充,湍流度提高,實際的失速臨界攻角更大。一般認(rèn)為,35°攻角范圍內(nèi)的實際升力系數(shù)曲線可根據(jù)臨界攻角之前的趨勢外插得到[1]。
3 流場分析
3.1 舵面流動
基于上述CFD 計算結(jié)果,選取距舵底部0.3h(h為舵高)的水平剖面為研究剖面,對4 個方案10°攻角時的舵面壓力分布進(jìn)行對比分析。該剖面位于下部舵葉高度中點附近,受上部間隙流動和底端三維效應(yīng)的影響相對較小,可相對準(zhǔn)確地反映翼型的升力特性。方案0~方案3 的0.3h剖面壓力分布曲線如圖7 所示。

圖7 10°攻角舵面壓力分布曲線(0.3 h 剖面)Fig.7 Pressure distribution curve on rudder surface at 20°AoA(0.3 h section)
由圖7 可知:10°攻角情況下,在0.3h剖面附近,方案1 在舵桿中心線(即橫坐標(biāo)0 位)以后的吸力面、壓力面壓差明顯大于方案0,舵桿中心線以前的兩面壓差略大于方案0;方案2 和方案1 的壓力分布趨勢大致相同,但兩面壓差略大于方案1;隨邊直尾化設(shè)計進(jìn)一步增大了方案3 在隨邊附近的壓差,其余舵面區(qū)域的壓差也略微增大。這一流場細(xì)節(jié)與方案0~方案3 升力性能逐步提升的宏觀結(jié)果相匹配。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不設(shè)制流板的情況下,圖7 中方案1 的低壓峰值小于方案0,說明翼型A 的最大厚度位置相對于NACA00 翼型后移5%弦長,起到了降低低壓峰值的作用,對舵的空泡性能是有利的。
3.2 端部流動
基于上述CFD 計算結(jié)果,得到方案1、方案2 在15°攻角時的舵面附近流線分布,如圖8 所示。
觀察圖8 中的端部流線可以發(fā)現(xiàn):相對于無制流板的方案1,方案2 的制流板較好地約束了端部的弦向流動,抑制了橫向繞流,弱化了上、下翼端渦,這是方案2 在15°攻角范圍內(nèi)升力提高而阻力未明顯增加的主要原因。圖8 同時也表明,由于掛舵臂及間隙的存在,掛舵臂后方的舵葉吸力面出現(xiàn)了較明顯的流動分離,這是半懸掛舵升力性能不及全懸掛舵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實船應(yīng)用
3 個優(yōu)化方案中,方案2 在方案1 的基礎(chǔ)上未付出阻力代價而提高了小攻角升力系數(shù);方案3 的升力系數(shù)較方案2 雖然仍有小幅提高,但零攻角阻力系數(shù)增幅較大,升阻比收益較低。因此,方案2 是3 個方案最均衡和經(jīng)濟的選擇,最終成為目標(biāo)船型實際采用的半懸掛舵設(shè)計方案。
為了驗證優(yōu)化舵系對于船舶操縱性的影響,對原船型和目標(biāo)船型的試航操縱性試驗數(shù)據(jù)進(jìn)行對比。二者的船舶尺度相同,試航工況、環(huán)境條件基本一致。
4.1 應(yīng)舵性對比
以IMO MSC.137(76) 決議要求的2 項應(yīng)舵性指標(biāo)—第一超越角和第二超越角作為衡量應(yīng)舵性的標(biāo)準(zhǔn),基于小舵角舵效的考慮,主要考察原船型和目標(biāo)船型的10°/10°Z 形試驗結(jié)果,對比如表4 所示。

表4 原船型與目標(biāo)船型10°/10°Z 形試驗結(jié)果對比Tab.4 10°/10°zig-zag test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vessel and object vessel
表4 中:1StOS 和2ndOS 分別為第一超越角和第二超越角,T1和T2分別為從操舵起始點至達(dá)到第一超越角和第二超越角的時間。可見,目標(biāo)船型的第一、第二超越角及達(dá)到各超越角的時間均小于原船型,表明目標(biāo)船型在緊急避碰時具有更靈活快速的機動能力,一定程度驗證了優(yōu)化舵系在小舵角情況下的升力性能優(yōu)勢。
4.2 回轉(zhuǎn)性對比
以IMO MSC.137(76)決議要求的2 項回轉(zhuǎn)性指標(biāo)——縱距和戰(zhàn)術(shù)直徑作為衡量回轉(zhuǎn)性的標(biāo)準(zhǔn),并通過分析試航操縱性試驗數(shù)據(jù)得到原船型和目標(biāo)船型的回轉(zhuǎn)性指數(shù)K及其無因次量K’,對兩型船的回轉(zhuǎn)性進(jìn)行對比。根據(jù)國際通行的右轉(zhuǎn)應(yīng)急避險原則,主要考察兩型船的右滿舵35°回轉(zhuǎn)試驗結(jié)果,對比如表5 所示。

表5 原船型與目標(biāo)船型回轉(zhuǎn)試驗結(jié)果對比Tab.5 Turning circle test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vessel and object vessel
可以看出,目標(biāo)船型的縱距和戰(zhàn)術(shù)直徑均低于原船型,目標(biāo)船型的回轉(zhuǎn)性指數(shù)K及其無因次量K′較原船型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表明其回轉(zhuǎn)性優(yōu)于原船型。根據(jù)船舶操縱響應(yīng)模型[17],舵的升力對K值具有直接影響,上述回轉(zhuǎn)試驗結(jié)果直觀地驗證了優(yōu)化舵系因其具有更好的升力性能,對船舶回轉(zhuǎn)性的提升作用。
5 結(jié) 語
本文基于CFD 方法,采用翼型優(yōu)化設(shè)計、制流板優(yōu)化設(shè)計、隨邊直尾化設(shè)計3 種技術(shù)措施對一型“曼谷型”集裝箱船的半懸掛舵系進(jìn)行了升力性能優(yōu)化,并經(jīng)實船應(yīng)用驗證,得到如下結(jié)論:
1)采用微凹翼型、制流板和隨邊直尾化設(shè)計可顯著提升半懸掛舵的升力性能。對于本文研究的舵系,在20°常用攻角范圍內(nèi)的升力系數(shù)較原舵系提升幅度累計達(dá)24.1%(20°攻角)~52.5%(5°攻角),有效改善了目標(biāo)船型的操縱性。
2)采用微凹翼型和微凹翼型+隨邊直尾化設(shè)計將增加舵阻力。對于本文研究的舵系,二者的零攻角舵阻力較原舵系分別增加18.1%和28.5%。
3)微凹翼型和隨邊直尾化設(shè)計可增大舵葉兩面的壓差,從而提高升力;制流板可約束端部的弦向流動,抑制橫向繞流,弱化上、下翼端渦,經(jīng)過適當(dāng)設(shè)計的制流板,在一定攻角范圍內(nèi)可提高升力而不明顯增加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