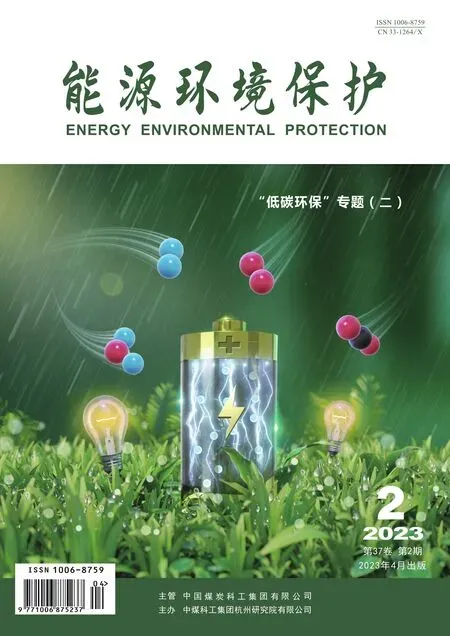廢液協同活性炭輔助水電解制氫的實驗研究
劉建忠,陳懿同,陳 聰,周俊虎
(浙江大學 能源清潔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 浙江 杭州 310027)
0 引 言
隨著用能需求的不斷增長與全球環境治理壓力的不斷增大,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目光投向氫能。氫能作為一種熱值高、綠色低碳、應用廣泛的二次能源,是未來構建多能互補綜合能源供應系統的重要能源載體。在“雙碳目標”的大背景下,氫能也是爭取近零排放、消納剩余電力、實現跨時空儲能的重點突破方向之一,如何更好地制氫現今已成為能源技術發展的重要戰略方向。
目前全球氫氣主要來源于化石燃料制氫技術,化石燃料制氫技術是最成熟的制氫技術,主要包括天然氣蒸汽重整制氫、石油蒸汽重整制氫、煤氣化制氫、甲醇裂解制氫等。現有氫源中48%為天然氣蒸汽重整制氫,30%為石油蒸汽重整制氫,18%為煤氣化制氫,僅有3.9%來源于電解水制氫以及0.1%來源于其他制氫工藝[1]。
電解水制氫技術不僅能快速一步制氫,而且適合就地分布式制氫,被看作是未來最有效的制氫技術[2]。但是電解水制氫技術具有一個顯著的劣勢,即能耗較高。電解水制氫的理論功耗為3.54 kW·h/Nm3,商用水電解槽則需要4.5~5 kW·h/Nm3的功耗[3]。現階段化石燃料制氫和工業副產氫的制氫成本約為10~15元/kg;但在選擇合適電力來源的情況下,電解水制氫的成本仍普遍在30元/kg以上,高昂的成本大大限制了其應用[4]。電解水制氫的能耗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陽極的析氧反應(OER)動力學遲緩。從而有研究者提出向陽極電解液中加入有機物,用更容易發生的陽極反應取代OER,以降低電解水制氫的電耗。
1979年,Coughlin和Farooque[5]首次提出了碳輔助電解水制氫技術(CAWE),利用碳源中的化學能減少電解能耗,主要反應如式(1):

Eθ=-1.23 V

Eθ=-0.21 V

(1)
因其有別于傳統直接電解水,CAWE技術可以成功避免氫和氧混合引起的爆炸,同時化合物還可以以化學能的形式提供電解水所需的能量,大大減少了功率輸入。目前研究中可以運用在CAWE的碳源非常廣泛,包括煤、生物質、醇類和天然氣等,每種碳源各有其優缺點。與其他碳源相比,煤炭儲量豐富,價格便宜,但缺乏合適的催化劑是該碳源輔助電解制氫的一個主要短板。寇凱凱等[6]研究人員發現電解煤漿時Fe(Ⅱ)/Fe(Ⅲ)氧化還原循環催化劑離子是必要的,但即使在該催化體系下電流密度仍會隨時間顯著下降。液體碳源如甲醇或乙醇等,其電氧化提供的能量充足,能有效降低電解水的電耗且穩定性高,因此很有前景,但醇類的缺點在于價格較昂貴[7]。各類生物質,如木質素、葡萄糖和淀粉等化合物可在電解中轉化為各種商品化學品,包括葡萄糖酸、葡萄糖酸酯和山梨醇等,增加一些附加值;但由于其貴金屬催化劑容易中毒,迫切需要在延長電催化劑壽命上進行深入研究[8-9]。天然氣碳源的產氫效率高于普通高溫蒸汽電解,但必須使用固體氧化物電解質電池,且需要700 ℃以上的高溫,同時天然氣本身成本也較高[10]。
目前國內外CAWE研究的碳源選擇以煤和生物質為主,并且很少有研究者對協同電解進行研究。本文以鮮少關注的活性炭為主要碳源,并且研究了廢液協同活性炭輔助水電解制氫,不僅致力于降低電解水電耗,而且也探討了工業廢液資源化利用的可行性。在本試驗研究中,首先比較了3種不同碳源之間的性能差異;然后引入不同的工業廢液,利用其高鹽分、高電導率的特點[11],提高電解的反應速率;最后對活性炭協同廢水輔助制氫進行了動力學分析。
1 實驗部分
1.1 實驗裝置
實驗采用三電極體系,電解池選用配有聚四氟乙烯蓋的H型玻璃電解池,H型電解池中間的膜選用質子交換膜(Nafion117,在使用前需先后用質量分數5%的雙氧水與質量分數5%的稀硫酸在80 ℃下進行預處理);對電極與工作電極均使用鉑電極(電極大小為15 mm×15 mm×0.1 mm),參比電極使用汞/硫酸汞電極。整個裝置放在恒溫水浴中,陽極電解池加入磁力轉子進行攪拌,實驗裝置如圖1所示。

圖1 實驗裝置Fig. 1 Experimental device
陽極電解液和陰極電解液均為100 mL。陰極電解液為濃度為0.5 mol/L的稀硫酸溶液。陽極電解液中的硫酸濃度也保持0.5 mol/L。若無特別說明陽極電解液中均加入Fe2(SO4)3·xH2O使Fe3+的濃度為50 mmol/L,加入3 g活性炭粉(或煤粉)并施加600 r/min的恒速攪拌,裝置恒溫水浴保持60 ℃。
本實驗通過線性電勢掃描伏安法(LSV法)測定活性炭輔助電解的電化學性能,極化曲線由CHI660E電化學工作站測量,以0.03 V/s的恒定掃描速率進行測量。
1.2 實驗材料
1.2.1 碳源
本實驗中使用到的三種碳源分別是活性炭、錫盟褐煤和山西平朔煙煤。分別對上述三種碳源的原樣進行研磨和篩分,用丹東百特BT-9300ST粒度儀進行粒度分析。結果測得活性炭的體積平均粒徑為42.63 μm;錫盟褐煤的體積平均徑為47.70 μm;山西平朔煙煤的體積平均徑為52.61 μm,粒度分布如圖2所示。

圖2 樣品粒度分布圖Fig. 2 Sample size distribution
樣品微晶結構的情況由X射線衍射圖譜進行分析,實驗使用儀器為SmartLab(3 kW),運行條件為40 kV, 30 mA,測量范圍為5°~90°,掃描速率為10(°)/min。對三種碳源樣品進行XRD測試,采用連續掃描的方式得到三種樣品的衍射圖,如圖3所示。活性炭樣品中的礦物成分含量較低,明顯存在的礦物成分主要有石英;錫盟褐煤樣品中的礦物成分含量略高,明顯存在的礦物成分有高嶺石和石英;山西平朔煙煤樣品中的礦物成分含量較高,明顯存在的礦物成分有高嶺石、勃姆石和石英。

圖3 樣品的XRD圖譜Fig. 3 XRD spectrum of different samples
紅外光譜是微觀結構研究使用最廣泛的表征手段之一,本實驗的紅外光譜由傅里葉紅外光譜儀Thermo Scientific Nicolet iS50 FT-IR測量,掃描區域為4 000~400 cm-1。三種碳源樣品分別取質量1 mg,與KBr以質量比1∶100在瑪瑙研缽中混合均勻后壓片,進行FT-IR測試。不同碳源樣品測得紅外光譜如圖4所示。

圖4 樣品的紅外光譜圖Fig. 4 FTIR spectrum of different samples
煤樣紅外光譜中的特征吸收峰主要分布在四個區域,分別是:3 000~3 600 cm-1范圍內羥基的伸縮振動吸收峰;2 800~3 000 cm-1范圍內脂肪族C—H鍵的伸縮振動吸收峰;1 000~1 800 cm-1范圍內含氧官能團的振動吸收峰;700~900 cm-1范圍內芳香結構的振動吸收峰[12]。由圖4可見,羥基吸收帶內活性炭譜線中存在一個特征峰,窄且小,峰較弱,平朔煙煤較之更強,錫盟褐煤最強。在脂肪結構吸收帶內活性炭吸收峰不明顯,錫盟褐煤和平朔煙煤均有小而尖的2個峰。在含氧官能團吸收帶內活性炭譜線僅有2個峰,峰數量和強度均最低。該結果說明活性炭紅外圖譜峰總數少,峰面積小,相比其他兩種煤樣,活性炭的脂肪族、含氧官能團含量較低,組分較為簡單。除此之外,波數大于3 600 cm-1范圍內主要是高嶺石等礦物質的吸收峰,此處煙煤的峰最強,活性炭譜線未出現吸收峰;1 000~1 200 cm-1范圍內主要是Si—O—Si結構的反對稱伸縮振動吸收峰,700~800 cm-1、460~550 cm-1范圍內是Si—O鍵對稱伸縮振動峰[13]。上述結果說明活性炭的礦物灰分含量較兩種煤炭樣品更上述結果低,與XRD分析結果相符。
1.2.2 廢水與試劑
本實驗中主要用到兩種廢水,分別是來自浙江某化工廠的脫硫廢水和合成氣的洗氣水。同時,實驗所用試劑如Fe2(SO4)3·xH2O等均為國藥集團的分析純試劑。
1.3 實驗方案設計
為了研究碳源種類對碳輔助水電解的影響,保持溫度、磁力轉子轉速、Fe(Ⅲ)離子濃度不變,分別對活性炭、錫盟褐煤和山西平朔煙煤3種樣品(陽極硫酸濃度均為0.5 mol/L)的LSV極化曲線進行了測定,并進行電化學性能分析。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不同廢液對活性炭輔助水電解的影響,保持其他因素一致,分別向陽極電解液加入等量脫硫廢水和洗氣水,在有無鐵催化兩種情況下測定極化曲線,分析廢液對電解的促進效果。
選取性能較優的廢液協同活性炭輔助水電解實驗,再次測定LSV極化曲線,進一步驗證電氧化的反應過程,并計算活化能,進行電解動力學分析。如無特別說明,本文中所述電壓均為相對汞/硫酸亞汞參比電極的電壓。
2 實驗結果與討論
2.1 碳源種類對碳輔助水電解的影響
本組實驗中,向陽極電解液中加入等量碳源樣品并按實驗設定速率攪拌5、10、30 min后分別線性伏安掃描一次,電解過程中保持攪拌速率不變。活性炭、錫盟褐煤和山西平朔煙煤3種樣品的LSV極化曲線如圖5所示。
由圖5可見,在同樣的預先攪拌時間下,活性炭的加入使得電解起始電壓降至0.1 V左右,錫盟褐煤、山西平朔煙煤的電解起始電壓稍高于活性炭,三者均遠低于相同硫酸濃度下直接電解水的電解起始電壓1.0 V,有效降低了水電解的電耗。

圖5 不同碳源樣品的LSV極化曲線Fig. 5 LSV polarization curves of differentsamples on CAWE
在0.2~1.0 V的電壓區間內,水還未開始電解,主要是碳源電解貢獻電流。據現有研究表明,一部分煤電解屬于間接氧化的過程,電解液中的Fe(Ⅲ)氧化碳源表面的活性位點被還原為Fe(Ⅱ),隨后Fe(Ⅱ)在電極表面發生氧化反應貢獻了絕大部分陽極電流[14]。在這個電壓區間內,活性炭樣品產生的電流密度約為10 mA/cm2,遠高于相同預攪拌時間下的另外兩種煤炭樣品。該結果說明相同預先攪拌時間內,活性炭表層及空隙中有更多官能團參與氧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預先攪拌時間的增加,活性炭電解時電流密度的增加幅度(隨著預先攪拌時間從5 min提升到30 min,電流密度僅提升了2 mA/cm2)反而低于兩種煤炭樣品的增加幅度。這說明活性炭電解達到較高電流密度所需的預先攪拌時間更短。結合上一節的樣品表征,活性炭中礦物成分含量更低,從而電解氧化時的非反應物質阻礙小;而隨著預先攪拌時間增大,兩種煤炭樣品中的礦物阻礙層被破壞,更多氧化位點暴露,貢獻了部分電流密度的提升。同時,活性炭中官能團類型較兩種煤炭樣品少,兩種煤炭樣品中官能團類型復雜,很多反應位點被不易氧化的官能團占據,氧化動力學遲緩,整體氧化速率較慢需要更長的預先攪拌時間。
在0.8~1.0 V的電壓區間內,該區間增加的電流密度主要由活性炭顆粒碰撞陽極板直接氧化和部分游離的可溶性小分子有機物的氧化貢獻。該區間內活性炭的電流密度有小幅提高,提高了約2 mA/cm2(見圖5細節圖),而另外兩種碳源則在該區間內電流密度保持穩定。由上一節的樣品表征可知活性炭樣品粒度更低,則電解中更易碰撞陽極,從而更利于發生直接氧化反應。同時也可以初步推測活性炭本身表面活性位點較其他兩種煤炭樣品更易被直接氧化。
由此可見,活性炭輔助水電解在電解起始電壓和低電壓區間電流密度方面,較傳統直接水電解有顯著優勢。活性炭作為輔助碳源,其電化學性能也優于錫盟褐煤和山西平朔煙煤,相同預先攪拌時間和相同電壓區間下,活性炭的電流密度高于錫盟褐煤和山西平朔煙煤,電解反應速率更快。同時,攪拌時間對活性炭的影響不大,則可以在較少的預先攪拌時間內達到較為理想的電流密度,這也是另外兩種煤炭所不具備的特性。本文后續將繼續討論廢液協同活性炭輔助水電解的電化學特性。
2.2 廢液對碳輔助水電解的影響
為了探索廢液協同輔助水電解制氫的效果,首先對無Fe(Ⅲ)添加下的廢液協同情況進行分析,實驗測得其LSV極化曲線如圖6所示。

圖6 不同廢液樣品的LSV極化曲線Fig. 6 LSV polarization curves of differentwastewater samples
結果說明,單一添加廢液的條件下,無論是脫硫廢水還是洗氣水,其電解起始電壓均低于直接水電解,但均高于Fe(Ⅲ)催化活性炭的電解起始電壓。同時,廢液協同活性炭電解在低電壓區間內的電流密度約為3~6 mA/cm2,均低于Fe(Ⅲ)催化條件,這說明僅添加廢液在低電壓區間的促進作用有限。但洗氣水的電流密度在0.4 V左右迅速提升,最終電流密度達到190 mA/cm2,該過程的電解電壓遠低于水電解,反應速率也明顯高于水電解,初步推測是因為洗氣水具有104mg/L級別的化學需氧量(COD)[15],許多還原性物質比水分子更容易參與陽極反應。同時脫硫廢水的電流密度于0.7 V左右迅速提升,分析原因是廢液中含氯離子,氯離子比水分子更容易參與陽極反應,氯離子反應的反應步驟也少于水分子反應。脫硫廢水在1.2 V的二次電流密度提升則是由于水分解貢獻了主要電流密度,綜合分析,廢液協同活性炭電解在電解起始電壓、電流密度及速率上較直接水電解都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與Fe(Ⅲ)催化單一活性炭相比,廢液協同活性炭電解在電解起始電壓、低電壓區間電流密度方面仍然有可以優化提升的空間。因此,在本實驗中我們考慮在單一添加廢液的基礎上額外添加催化劑Fe(Ⅲ),探究有Fe(Ⅲ)條件下的廢液協同活性炭電解的效果。
在有Fe(Ⅲ)條件下的兩種不同廢液協同活性炭電解的LSV極化曲線如圖7所示。由圖7可知,在0.4 V以下電壓區間內,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在Fe(Ⅲ)催化下的電流密度最高,約為18 mA/cm2;無協同的活性炭電解電流密度最低,約為11 mA/cm2;脫硫廢水協同活性炭在Fe(Ⅲ)催化下的電流密度略高于無協同的情況。該結果說明在低電壓區間內,脫硫廢水對活性炭電解催化作用非常微小,而加入洗氣水則對Fe(Ⅲ)條件下的活性炭電解有較好的催化作用,在該低電壓區間內電流密度可提升45%~73%。同時,在Fe(Ⅲ)條件下高電壓區間內,洗氣水的電流密度依然在0.4 V之后迅速提升,最終電流密度仍能達到190 mA/cm2,脫硫廢水的電流密度也于0.7 V左右迅速提升,即Fe(Ⅲ)催化能有效提升協同電解在低電壓區間內電流密度,而不會限制高電壓區間內的電流密度。

圖7 有Fe(Ⅲ)條件下不同廢液樣品的LSV極化曲線Fig. 7 LSV polarization curves of differentwastewater samples with Fe(Ⅲ) on CAWE
由此可見,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比脫硫廢水協同活性炭電解制氫更具優勢,洗氣水的加入使得陽極反應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更能進一步提升單一Fe(Ⅲ)催化的電流密度,加快電解反應速率。本文后續將繼續討論溫度對Fe(Ⅲ)條件下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的影響。
2.3 活化能分析
為了研究溫度對Fe(Ⅲ)條件下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電流密度的影響,本實驗從20~80 ℃間取了4個不同溫度,分別測定電解的LSV極化曲線如圖8所示。由圖8可知,隨著溫度的提高,在低電壓(電解電壓低于0.4 V)區域電流密度從20 ℃的3 mA/cm2增加到80 ℃的30 mA/cm2,電流密度顯著提升,即輔助電解反應速率大大提高。從電化學反應步驟的角度進行分析,隨著溫度的升高,能夠顯著影響電極表面反應物的吸附、反應產物的脫附,以及雙電層結構的充電情況,從而有利于提升反應速率。從動力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溫度越高,分子內能越高,分子間化學鍵的約束就越弱,相應地,電解反應更易發生,電解過程反應速率越快,電流密度越高。但需要注意的是,拓展到實際應用場景時,還需要考慮電解系統所用材料的耐熱性,綜合決定電解溫度,防止溫度過高損害系統壽命。

圖8 溫度對輔助電解的影響Fig. 8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AWE
在不同溫度下獲得電極反應的反應速率(以電流密度代表),按照阿倫尼烏斯公式可以計算得到反應活化能,計算公式如式(2):
(2)
式(2)中,j為電流密度, A/cm2;Ea為活化能, J/mol;T為溫度,K;R為氣體常數,8.314 J/(mol·K);f為指前因子, Hz;公式兩邊取對數就可以得到式(3):
(3)
根據圖8中LSV曲線得到的電流密度,按照上式可以獲得lgj和1/T的線性關系,利用直線的斜率可計算得到反應活化能。0.1~1.2 V電壓區間內活化能計算結果如圖9所示,擬合時相關系數R2達到0.96基本符合要求。由圖9可以看出,隨著電解電壓升高,活化能圖中共呈現出2個峰,位置分別在0.1~0.4 V和0.5~1.0 V。這個結果表明,電解過程中在低電壓區間(0.1~0.4 V)和高電壓區間(0.5~1.0 V)內的電化學反應發生了變化,此結論和2.2節中分析得到的結論一致。當處于低電壓區間時,主要的反應是Fe(Ⅲ)催化氧化反應以及Fe(Ⅱ)的陽極氧化反應;處于高電壓區間時,反應類型轉變為洗氣水中還原性物質的氧化過程。在低電壓區間下,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的活化能約為31.56 kJ/mol;在高電壓區間,活化能約為13.23 kJ/mol。高電壓區間的較低活化能主要是因為洗氣水本身含有的強還原性物質,從而非常有利于陽極氧化反應的進行。這兩個活化能均遠低于現有研究中洗氣水協同煤電解的活化能(1.1 V下,活化能為45.75 kJ/mol[15])。該結果說明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中的陽極反應更易進行,動力學性能有所優化,具有顯著優勢。

圖9 Fe(Ⅲ)條件下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的活化能Fig. 9 Activation energy of gas scrubbing water andactivated carbon with Fe(Ⅲ) on CAWE
3 結 論
本實驗利用H型電解池研究了廢液協同活性炭輔助水電解制氫的材料選擇與電化學特性,結果表明Fe(Ⅲ)條件下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具有較好的電化學性能,得出以下結論:
(1)活性炭輔助水電解能改善直接水電解的電解起始電壓過高的問題,并且活性炭的電解起始電壓也低于錫盟褐煤和山西平朔煙煤。在反應電壓區間內,活性炭產生的電流密度約為10 mA/cm2,遠高于相同預攪拌時間下的另外兩種煤炭樣品。同時,活性炭需要的預攪拌時間更少。因此活性炭輔助水電解性能優于錫盟褐煤和山西平朔煙煤,作為輔助水電解的碳源具有更好的應用潛力。
(2)脫硫廢水和洗氣水均可用于輔助水電解,其中Fe(Ⅲ)條件下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比脫硫廢水協同活性炭電解制氫更具優勢,更能進一步提升單一Fe(Ⅲ)催化的電流密度,反應電壓區間內電流密度可提升45%~73%,加快了反應速率。在本實驗中,洗氣水的加入使得陽極反應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效率提高需要在尊重階段性特點的前提下進行。
(3)溫度越高,電解反應越易發生,電解過程反應速率越快,電流密度越高,但溫度選擇不宜一味求高。經電化學動力學分析得,低電壓區間內,Fe(Ⅲ)條件下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的活化能約為31.56 kJ/mol;在高電壓區間,活化能約為13.23 kJ/mol。較先前研究,洗氣水協同活性炭電解動力學性能有所優化,電解更易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