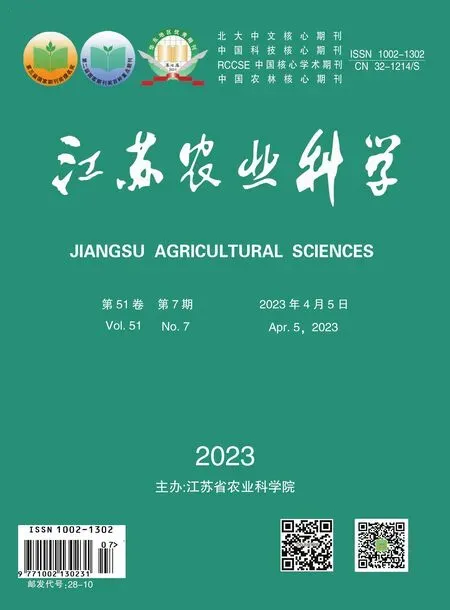小麥秸稈及其生物炭對植煙土壤養分、酶活性及細菌群落結構的影響
張 燕, 李亮生, 陳帥偉, 李 軍, 陳享燈, 宋文靜
(1.中國農業科學院煙草研究所/農業農村部煙草生物學與加工重點實驗室/中國農業科學院青島煙草資源與環境野外科學觀測試驗站,山東青島 266101; 2.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81;3.福建省煙草公司龍巖市公司,福建龍巖 364000; 4.山東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山東濟南 250014)
據統計,我國每年秸稈產量9億t,可加工為副產物的達5.8億t,其中2.3億t的副產物可以被利用,剩下的3.5億t副產物會被丟棄。近年來我國工業化發展迅速,對于秸稈的需求越來越少,如何處理和合理利用這些廢棄的秸稈資源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物有機資源,秸稈中含有豐富的有機質及營養元素,包括氮、磷、鉀、鈣、鎂等[1],秸稈腐解后產生的活性有機碳,可以為微生物提供充足的碳源,能夠有效增加土壤微生物數量和微生物多樣性[2]。秸稈還田后直接增加了土壤有機質含量,使得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強,從而提高了土壤酶活性,促進了土壤養分的轉化[3]。
生物炭是由有機材料(如秸稈、木材、植物殘渣和糞肥)在厭氧的條件下熱解(300~1 000 ℃溫度范圍)生成[4]。生物炭具有孔隙度大、高抗生化分解等特性,常被用作土壤調節劑改善土壤理化性狀,提升土壤肥力等[5-7]。在山東煙區,植煙土壤由于長期連作、有機物料不足等不合理的農業管理措施,土壤理化性狀較差、微生物活性降低等土壤質量問題已成為制約山東煙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瓶頸。科學、合理地利用當地的小麥秸稈資源改善煙田土壤可能是實現山東煙區煙田土壤質量提升的重要途徑。目前,關于秸稈及秸稈生物炭對山東煙區煙田氨氧化土壤微生物與土壤養分及相關酶活關聯度分析的研究報道較少,本研究通過比較不同秸稈處理方式下植煙土壤的理化性狀、養分狀況、土壤酶活性以及土壤氨氧化菌的群落組成等的差異,為秸稈資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試驗區位于山東濰坊煙草有限公司諸城分公司洛莊煙站(36°1′N,119°6′E),試驗區年日照時數在 2 500 h 以上,年平均氣溫12 ℃以上,年平均降水量750 mm左右,年平均無霜期230 d左右。土壤基礎理化性狀如表1所示。

表1 土壤基礎理化性狀
1.2 試驗設計
試驗設置3個處理:(1)CK,常規施肥;(2)WS,CK+施用小麥秸稈,還田量6.75 t/hm2;(3)BC,CK+施用小麥秸稈生物炭,還田量2.25 t/hm2。每個處理3次重復,隨機區組設計,每個小區面積為 48 m2。小麥秸稈及其生物炭的理化性狀詳見表2。

表2 小麥秸稈及其生物炭的理化性狀
在2021年3月20日煙田起壟前,撒施小麥秸稈或生物炭,施肥種類及用量情況:復合肥(含N、P2O5、K2O分別為10%、10%、20%)施用量為 600.0 kg/hm2,硫酸鉀(含K2O 50%)施用量為 105.0 kg/hm2,磷酸二銨(含N、P2O5分別為16.5%、44.5%)施用量為60.0 kg/hm2。
供試烤煙品種為NC55,移栽時間為2021年5月8日,烤煙的株行距為1.2 m×0.5 m。
1.3 樣品采集與測定
1.3.1 土壤的采集及土壤養分的檢測 2021年7月20日,于煙葉采烤結束后,按照5S法,用土鉆在不同小區于煙壟壟體正中收集耕層土樣。土樣過 2 mm 篩,用于測定土壤酶活性;其余土壤樣品經風干后,測定土壤化學指標;新鮮土樣用于檢測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及多樣性。總有機碳(TOC)、土壤全氮(TN)、堿解氮(AN)、土壤有效磷(AP)、土壤有效鉀(AK)含量,土壤pH值均依照土壤農業化學分析方法[8]測定。
1.3.2 土壤酶活性的檢測 土壤酶活性[9]測定:土壤蔗糖酶活性選用3,5-二硝基水楊酸比色法測定;土壤脲酶活性選用靛酚比色法測定;過氧化氫酶活性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測定;中性磷酸酶活性采用磷酸苯二鈉比色法測定。
1.3.3 土壤微生物提取及高通量測序 采用Fast DNA SPIN Kit for Soil 土壤 DNA 提取試劑盒按步驟提取。利用 Illumina 公司的 MiSeq PE250平臺進行測序(上海美吉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1.4 數據分析
應用QIIME軟件處理高通量測序結果;利用Mothur軟件包以97%為閾值對細菌基因序列劃分分類單元,并計算細菌多樣性指數和豐富度指數;應用SPSS進行土壤細菌群落組成和相對豐度分析,采用Origin 2021處理數據和制作圖表。
2 結果與分析
2.1 秸稈及秸稈生物炭對土壤速效養分和pH值的影響
由圖1所示,與CK相比,WS處理顯著提高了土壤堿解氮和有效磷含量,增幅分別為78.11%和100.81%,而BC處理養分含量變化較小。各處理間土壤速效鉀含量和pH值無顯著差異。

2.2 秸稈及秸稈生物炭對土壤全效養分的影響
如圖2所示,WS處理土壤全氮含量較CK顯著提高了27.65%。與CK處理相比,WS和BC處理均顯著提高了土壤總有機碳含量,增幅分別為20.71%、74.93%。 BC處理較CK處理土壤全鉀含量顯著提高了21.93%,而WS處理土壤全鉀含量變化較小。

2.3 秸稈及秸稈生物炭對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如圖3所示,與CK相比,WS處理顯著提升了蔗糖酶活性,增幅為112.54%,BC處理與CK處理差異不顯著。各處理間土壤脲酶、磷酸酶和過氧化氫酶活性無顯著差異。

2.4 秸稈及秸稈生物炭對土壤細菌群落的影響
2.4.1 微生物多樣性 由表3可知,WS處理中16S基因型細菌Shannon 指數、ACE指數均高于CK處理和BC處理,但差異并不顯著,Chao1指數顯著高于CK處理和BC處理,與CK相比,增幅為14.19%。各處理nosZ基因型反硝化細菌、AOA和AOB的群落多樣性和豐富度指數差異均不顯著。

表3 秸稈及秸稈生物炭對土壤微生物和細菌種類豐富度和多樣性指標的影響
2.4.2 土壤細菌的群落結構分析 對不同處理優勢細菌門水平的分析表明(圖4),3種處理中nosZ基因型反硝化細菌群落的優勢菌門為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AOA群落的優勢菌門為泉古菌門(Crenarchaeota),16S基因型細菌的優勢菌門為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AOB群落的優勢菌門為變形菌門。

對不同處理優勢細菌屬水平的分析表明,3種處理中nosZ基因型反硝化細菌群落的優勢菌屬為unclassified_k_norank_d_Bacteria,16S基因型細菌的優勢菌屬為norank_c_Soil_Crenarchaeotic_Group_SCG,AOA群落的優勢菌屬為norank_c_environmental_samples_p_Crenarchaeota,AOB群落的優勢菌屬為norank_f_environmental_samples。秸稈及秸稈生物炭還田后的土壤優勢菌群組成與常規施肥一致,但優勢細菌群分類組成比例存在差異。
2.4.3 土壤細菌的群落組成分析 由圖5可知,第1主成分 PC1 對16S基因型細菌群落組成差異的解釋度為27.50%,第2主成分 PC2 對16S基因型細菌群落組成差異的解釋度為20.86%,PC1和PC2可累積解釋48.36%的變異度。秸稈及秸稈生物炭還田使植煙土壤中16S基因型細菌群落結構發生改變,但對nosZ基因型反硝化細菌(PC1=30.16%,PC2=20.50%)、amoA-AOA(PC1=60.78%,PC2=23.32%)、amoA-AOB(PC1=37.89%,PC2=33.60%)的細菌群落結構改變不顯著。

2.5 影響植煙土壤細菌群落的因子分析
冗余分析結果顯示(圖6),在不同的處理中,總有機碳含量是引起nosZ基因型反硝化細菌群落變化(r2=0.733,P<0.05)的主控因子,也是引起16S 基因型細菌群落變化(r2=0.627,P<0.05)的主要環境因子,有效磷(r2=0.424,P<0.05)是影響AOB群落變化的主要環境因子。

3 討論
3.1 秸稈及秸稈生物炭還田對土壤養分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表明,秸稈還田顯著提升了植煙土壤堿解氮、有效磷含量,這與鄒清祺等的研究結果[10-13]一致。秸稈還田對土壤養分含量的提升作用與秸稈礦化分解后向土壤中釋放了大量養分元素有關[14]。此外,秸稈腐解形成的腐殖質具有溶磷和解鉀的雙重作用,也能夠通過活化土壤中的磷、鉀元素來提升土壤中的速效養分含量[13]。
研究表明,土壤添加生物炭后有利于改善土壤養分狀況,增加土壤孔隙度,促進土壤團聚體的形成,構建良好的土壤結構[15]。本研究中,秸稈生物炭處理顯著提升了土壤中的總有機碳含量,這與Liu等利用商業木炭殘留物制備的生物炭改良玉米田沙性土的研究結果[16]一致。添加生物炭短期內即能提高土壤中的TOC含量的主要原因在于生物炭的芳環結構使其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和抗分解特性[17],這使其在土壤中難以為土壤微生物所分解利用。
3.2 秸稈及秸稈生物炭還田對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土壤酶活性在土壤碳氮代謝和養分循環中發揮重要作用,能夠表征土壤養分代謝強度[18]。靳玉婷等在巢湖地區利用秸稈還田改良稻-油輪作農田土壤發現,秸稈還田使水稻季和油菜季土壤磷酸酶和脲酶活性明顯提升,且油菜季增幅高于水稻季[19]。程曼等在山西省對黃土旱塬區的研究發現,秸稈直接還田對玉米田脲酶和磷酸酶活性影響較小[20]。在本研究中,小麥秸稈還田提高了土壤蔗糖酶活性,主要是由于:一是秸稈還田豐富了微生物提供可利用碳源的種類和數量[21-22],刺激了微生物代謝;二是秸稈還田改善了土壤理化特性,優化了微生物生活環境,提供了土壤酶載體;三是秸稈還田與化肥配施還能夠加速土壤自身有機碳的礦化分解來提升土壤酶活性[23]。
生物炭對土壤酶活性影響因材料來源、制備工藝、土壤類型等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24-26]。杜倩等在四川涼山的研究發現,玉米生物炭和油菜生物炭明顯提升了不同烤煙生育期土壤蔗糖酶、脲酶、蛋白酶活性[26]。張桃香等通過室內試驗研究發現,低溫條件(300 ℃)較高溫條件(600 ℃)下制備的生物炭更有利于南方茶林紅壤土脲酶、酸性磷酸酶等酶活性的提高[27]。在本研究中,與秸稈還田對土壤蔗糖酶的提升不同,秸稈生成的生物炭處理對蔗糖酶活性影響較小。這一研究結論與 Mierzwa-Hersztek等的研究結論[28]一致。導致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秸稈轉化為生物炭后有機碳的存在形態發生改變,致使其對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響與秸稈直接還田處理存在較大差異[29]。此外,生物炭表面的官能團對活性底物和土壤酶的吸附也會限制土壤酶活性的提升[30]。
3.3 秸稈及秸稈生物炭還田對細菌群落的影響
土壤微生物多樣性被公認為是維持土壤健康的關鍵因素。本研究發現,秸稈還田使16S基因型細菌群落多樣性指數中的Shannon指數、ACE指數和Chao 1指數顯著提升。這表明,秸稈還田有助于提升土壤16S基因型細菌群落豐富度和多樣性。胡蓉等通過對稻麥輪作系統農田土壤的研究也發現,秸稈還田后,水稻根際細菌群落Chao 1豐富度指數和Shannon多樣性指數均明顯增加[31]。土壤細菌群落門水平的相對豐度比較發現,變形菌門為nosZ基因型反硝化細菌群落、16S基因型細菌群落和AOA細菌群落共同的優勢菌門。
主成分分析發現,秸稈還田和秸稈生物炭處理均改變了16S基因型細菌的群落結構。趙鳳艷等的研究也發現,添加不同有機物料后,設施番茄長期連作土壤的微生物群落結構發生了改變[32]。微生物也會反作用于生存的環境,微生物多樣性的任何損失也可能會減少多功能性,從而對陸地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產生負面影響[33]。在本研究中,秸稈和生物炭處理改變了土壤總有機碳含量,冗余分析進一步指出總有機碳是引起16S 基因型細菌群落發生變化的主要環境因子。
4 結論
秸稈還田提高了植煙土壤總有機碳、堿解氮、有效磷和全氮含量,增加了植煙土壤蔗糖酶活性,提升了16S基因型細菌的豐富度和多樣性;添加生物炭顯著提高了土壤總有機碳和全鉀含量;秸稈還田及其生物炭處理使土壤 16S基因型細菌群落結構發生了改變,總有機碳是引起16S 基因型細菌群落變化的主控環境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