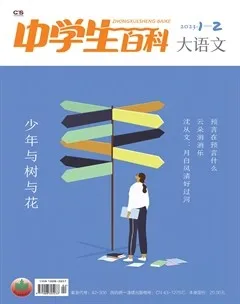想象性的預言
勞思琪
人們對“預言”充滿了興趣,這是一個可以解釋的現象。
人類是有限的個體,我們總是困于當下的時間與空間之中,站在房間里就看不到墻外的景象,活在今天就無法得知明天會發生什么。因為無法走出這樣的束縛,人們或多或少都活在對未來的焦慮之中,感受著此刻,憂懼著明日。人類是有限的,但也因此渴求無限。于是人們試圖依靠歷史的或者當下的種種現象,去揣摩、推測、想象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人們企圖通過想象延長思維的觸角,抵達那看似不可知的未來彼岸。
而文學恰好能滿足人們的需求。被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的《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我們》,都把故事依托于遙遠的未來世界進行講述。作者想象著極權主義或者機械文明之下未來社會的制度、科技、生活,借此抨擊現實世界中初露端倪的種種弊端。這是一種對于危機的警覺,促使作者寫下了為人類世界敲響警鐘的預言。“反烏托邦三部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比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文本中創造的一些新詞,像“新語”“雙想”“老大哥”等,成為廣受認可的文學意象,并影響著后來的人們使用同樣的語言去表達和理解世界。
作品中所描述的世界是真實發生的嗎?不是的。但是故事仍然具有令人信以為真的魔力。這是因為文學的想象總是建立在對現實世界的體察上,文學所做出的對于未來的種種“預言”,其實是綜合了客觀規律、邏輯、知識,剖析出現象背后的本質,并基于對本質的深刻認知,最終為世界發展的可能性給出的合理的闡述。
當然,也有一些看起來只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并不會真實發生的預言,比如北歐神話中的《諸神的黃昏》。《諸神的黃昏》是對一連串巨大劫難的預言。諸神與巨人積怨已久,戰爭爆發,帶來自然的浩劫,世界之樹在烈火中崩倒,洶涌的海水覆滅了宇宙,末日已至,世界一片死寂。此后,幸免于難的人類和神祇將在宇宙極南端的大地上重建新世界的秩序。《諸神的黃昏》預言了諸神的必敗和世界的重生,而這恰好對應著一個亙古不變的規律——毀滅與再生的循環往復,萬事萬物都逃脫不了這個根本的法則。生與死是文學永恒的命題,唯有毀滅才能帶來新生,如同破而后立,否極泰來。文學這時仍然能夠作為一個預言而存在,但是北歐神話所預言的,并非諸神隕落的末日到來這個具體事件,而是預言了一種更高層面上的“真實”,即在諸神的呻吟和宇宙的崩塌之中,我們得以窺見世界生死輪回的真相。

因此,文學的預言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預言,文學作品中的許多橋段,無論是《荒原狼》中哈勒爾所代表的現代人的精神危機,還是《罪與罰》中拉斯柯爾尼科夫所象征的上天信仰的破滅,又或者是駱駝祥子所象征的小人物的悲辛生活,都是在用語言構造一個文學的世界,并在其中映射、重現現實世界內部復雜的真實。我們信以為真的文學的預言性,就建立在這種深刻的對于世界的洞察上,文學家們并非通過玄乎其玄的“通靈”,而能預知將來,他們只是以想象力筑造世界的可能性,并寫出那些令讀者深深著迷的故事。
對我而言,文學中的預言,總是同時包含著希望和絕望。我也曾設想《禮記》中所描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向往屋舍儼然、人人怡然自樂的世外桃源,想象人類思想意識中最最公正和平等的烏托邦……這些美好的想象被它們的追隨者信奉為預言,成為他們失落中的希望,向前尋覓的方向。但是我也在文學中看到了人類的罪惡、貪婪、愚昧、自私,這些底色悲觀的預言一度令我心顫。假使世間一切的惡都肆意生長,顛覆社會和萬物的秩序,或許我們有朝一日也要迎來人類的黃昏。事實上,希望與絕望不會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它們總是同時存在,相伴而行。借由文學那些或天真或諷刺的無關真假的預言,我對世界逐漸形成更加清晰的認知。在希望與絕望的交替中,文學為我建造起觀看這個世界的豐富的可能性——這是文學的預言所贈予我的最佳收獲。

文學中的預言如同一個又一個的平行時空,未來或許是這樣的,或許是那樣的,我無法真正觀測到以后的世界,但能夠在腦海中肆意暢想,以想象抵達未知彼岸。人類的認知不斷更新,人類的想象永無止境,那些做出大膽預言的文學作品具體說了什么,或許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仍然保有豐沛的想象力,并且在用這些充滿想象力的語言創造屬于我們的未來。
- 中學生百科·大語文的其它文章
- 探訪法國梧桐
- 靜默的葉子,鳴叫的葉子
- 心的陰晴圓缺
- 探訪藍雪花
- 看到藍雪花,心就靜了
- 探訪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