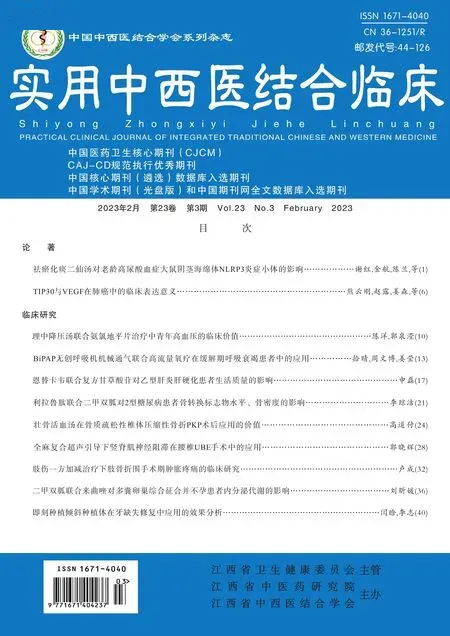針灸聯合西藥對原發性失眠癥患者睡眠質量的影響
江常鶯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福州中醫院 福州 350001)
原發性失眠癥是指排除藥物濫用、軀體疾病、精神障礙等其他因素所引起的睡眠障礙,患者典型癥狀包括頻繁覺醒、日間精神困乏、夜間入睡困難、睡眠維持困難等[1]。流行病學調查發現,普通人群中原發性失眠癥的發生率為2%~4%,占慢性失眠患者的25%[2]。睡眠質量的優劣與人體心理、生理健康息息相關,長期失眠會降低患者專注力、工作效率,嚴重影響患者的免疫、內分泌功能與自主神經活動。酒石酸唑吡坦片是一種非苯二氮卓類的新型催眠藥物,雖可有效延長總睡眠時間、減少醒覺次數與改善睡眠狀態,但長期服用可能會造成神經衰弱,出現嗜睡、頭暈、頭痛等不良反應[3]。失眠癥歸屬于中醫學“不寐”范疇,多與體虛多病、勞逸不當、飲食不節等病因相關。中醫認為,氣血、心脾虧虛可損傷心脈,以致夜不安神而誘發失眠。而針灸刺激人體相應穴位可恢復正常的睡眠-覺醒周期,達到改善氣血循環、疏通經絡的效果[4]。鑒于此,本研究納入60 例原發性失眠癥患者,從睡眠質量、過度覺醒狀態、神經遞質水平等角度分析針灸治療原發性失眠癥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1 年8 月至 2022 年8 月就診于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福州中醫院的60 例原發性失眠癥患者,按隨機對照原則分為對照組與研究組。對照組 30 例,男 17 例,女 13 例;年齡 21~67歲,平均(43.62±3.85)歲;工作類型:腦力勞動10例,體力勞動 20 例;病程 2~8 個月,平均(3.95±1.28)個月。研究組 30 例,男 16 例,女 14 例;年齡20~65 歲,平均(42.39±3.74)歲;工作類型:腦力勞動9 例,體力勞動21 例;病程1~9 個月,平均(4.02±1.36)個月。兩組一般資料均衡性良好(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文號: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福州中醫院倫理字 202001058 號)。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1)納入標準:符合原發性失眠癥診斷標準[5],且病程至少1 個月;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8 分;符合中醫學心脾兩虛證[6],頭暈目眩、難寐易醒、易出汗,舌苔薄白、脈細數;每周失眠次數≥2 次;意識正常,溝通能力正常;對本研究內容知情,自愿參與并簽署知情同意書。(2)排除標準:對針灸不耐受;因疾病因素造成的失眠;入組前2 周接受精神類藥物治療;伴有呼吸暫停綜合征;合并重要臟器疾病;哺乳期或妊娠期女性;既往有乙肝、結核、肝炎、丙肝等傳染性疾病;因生活習慣不當(入睡前喝濃茶、飲用咖啡等)、環境變化(外界噪音、陌生環境等)所致的短暫性失眠;對本研究所用藥物過敏。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采用酒石酸唑吡坦片(國藥準字 H20000276)治療,口服,10 mg/ 次,1 次 /d,共治療4 周。研究組在對照組基礎上聯合針灸治療:取安眠穴、足三里穴、三陰交穴、內關穴、神門穴、四神聰穴、百會穴等穴位,穴位消毒,一次性毫針行平補平瀉法針刺,輕刺激,間歇捻轉,留針30 min 左右,治療5 d 后休息2 d,共治療4 周。
1.4 觀察指標 (1)臨床療效。治療4 周后,參考《中國失眠癥診斷和治療指南》[7]結合治療前后PSQI總分減少率([治療前評分-治療后評分)/治療前評分×100%]制定療效評估標準:PSQI 總分減少率>75%,睡眠情況基本恢復正常為臨床控制;PSQI 總分減少率為50%~70%,睡眠質量明顯緩解為顯效;25%≤PSQI 總分減少率<50%,睡眠質量有好轉為有效;PSQI 總分減少率<25%,睡眠質量無緩解或加重為無效。總有效率=臨床控制率+顯效率+有效率。(2)睡眠質量。于治療前、治療4 周后借助失眠嚴重程度指數(ISI)、PSQI 評估睡眠質量。ISI 量表總分28 分,PSQI 總分21 分,兩量表分值高則睡眠質量差。(3)過度覺醒狀態。于治療前、治療4 周后借助入睡前覺醒量表(PSAS)、過度覺醒量表(HAS)評估患者過度覺醒狀態,PSAS 量表總分 16~80 分,HAS量表總分0~78 分,兩量表分值低則皮層覺醒程度低。(4)睡眠相關指標。記錄患者治療前、治療4 周后總睡眠時間、睡眠潛伏時間、覺醒次數。(5)血清神經遞質水平。采集患者治療前、治療4 周后空腹靜脈血2 ml,離心10 min(離心率為2 500 r/min,離心半徑6 cm)后分離血清,利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血清谷氨酸(GA)、γ-氨基丁酸(GABA)含量。(6)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包括過敏、感染、暈針、局部血腫等。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3.0 統計學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以()表示,行t檢驗;計數資料用%表示,行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對比 研究組總有效率為93.33%,高于對照組的73.3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對比[例(%)]
2.2 兩組睡眠質量對比 治療前兩組ISI、PSQI 量表評分對比,無顯著性差異(P>0.05);治療4 周后研究組 ISI、PSQI 量表評分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 2。
表2 兩組 ISI、PSQI 量表評分對比(分,)

表2 兩組 ISI、PSQI 量表評分對比(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
PSQI治療前 治療4 周后對照組研究組組別 n ISI治療前 治療4 周后30 30 t P 22.36±4.05 21.49±3.98 0.839 0.405 16.85±3.02*12.05±2.98*6.197 0.000 16.35±3.32 16.08±2.89 0.336 0.738 11.32±2.85*8.65±1.28*4.681 0.000
2.3 兩組過度覺醒狀態對比 治療前兩組PSAS、HAS 量表評分對比,無顯著性差異(P>0.05);治療4 周后研究組PSAS、HAS 量表評分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 3。
表3 兩組 PSAS、HAS 量表評分對比(分,)

表3 兩組 PSAS、HAS 量表評分對比(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
HAS治療前 治療4 周后對照組研究組組別 n PSAS治療前 治療4 周后30 30 t P 44.35±3.68 45.03±4.11 0.675 0.502 41.03±2.86*35.62±3.65*6.390 0.000 41.68±4.13 40.98±3.68 0.693 0.491 37.65±3.98*34.02±3.85*3.591 0.001
2.4 兩組睡眠相關指標對比 治療前兩組總睡眠時間、睡眠潛伏時間、覺醒次數對比,無顯著性差異(P>0.05);治療4 周后研究組總睡眠時間比對照組長,睡眠潛伏時間比對照組短,覺醒次數比對照組少(P<0.05)。見表 4。
表4 兩組睡眠相關指標對比()

表4 兩組睡眠相關指標對比()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
覺醒次數(次)治療前 治療4 周后對照組研究組組別 n 總睡眠時間(min)治療前 治療4 周后睡眠潛伏時間(min)治療前 治療4 周后30 30 t P 275.63±42.51 274.68±41.86 0.582 0.612 405.29±38.65*511.68±48.95*9.343 0.000 124.36±25.62 123.85±24.65 0.079 0.938 84.69±13.65*61.35±10.08*7.534 0.000 2.74±0.38 2.64±0.41 0.980 0.331 1.85±0.41*1.32±0.38*5.193 0.000
2.5 兩組血清神經遞質水平對比 治療前兩組血清 GA、GABA 水平對比,無顯著性差異(P>0.05);治療4 周后研究組血清GA、GABA 水平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 5。
表5 兩組血清神經遞質水平對比(μmol/L,)

表5 兩組血清神經遞質水平對比(μmol/L,)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
GABA治療前 治療4 周后對照組研究組組別 n GA治療前 治療4 周后30 30 t P 226.65±32.51 225.74±33.65 0.107 0.916 281.63±40.05*323.69±43.65*3.889 0.000 321.65±38.26 323.39±37.59 0.178 0.860 391.62±36.58*423.63±40.28*3.222 0.002
2.6 兩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對比 所有患者治療期間均未出現過敏、感染、暈針等嚴重不良反應。研究組2 例出現輕微局部血腫,未處理1 周內緩解。
3 討論
睡眠-覺醒周期紊亂可能會引發注意力減退、警覺性降低、情緒不穩定等癥狀,隨著失眠癥狀不斷加重,可能會阻礙循環代謝,誘發全身多器官功能減退,降低患者生活質量。中醫學將慢性失眠癥歸屬于“不得眠、不寐”等范疇,認為該病多因情志不暢、勞神思慮過度造成神失所養所致[8~9]。心脾兩虛型失眠癥大多因憂慮過多而致氣血兩虧,操勞過度繼而損傷心脾,衛氣不固,使外邪滯留經脈,陰陽失衡,因此治療應以安心養神、健脾益氣為主。
針灸作為中醫的重要組成部分,可通過直接作用于周圍神經與肌肉,從而激活中樞與調節自主神經張力,有益于患者恢復正常的睡眠-覺醒周期。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治療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治療4 周后總睡眠時間較對照組長,ISI、PSQI 量表評分較對照組低,睡眠潛伏時間較對照組短,提示原發性失眠癥患者采用針灸聯合西藥治療的效果明顯,可提高睡眠質量,延長總睡眠時間。龍迪和等[10]研究發現,針灸可提高肝郁脾虛型失眠患者睡眠質量、睡眠效率,延長慢波睡眠時間、快動眼睡眠時間,這與本研究結論相似。分析針灸改善睡眠質量的作用機制可能在于:針灸取安眠穴、足三里穴、三陰交穴、內關穴、神門穴、四神聰穴、百會穴等穴位,其中安眠穴為翳風、風池兩穴連線之中點,針灸此處可安神寧心、調和陰陽;針灸足三里可燥化脾濕、生發胃氣;三陰交穴是脾、腎、肝三經的交會穴位,針灸該處可安神養血、補腎益氣、調理脾胃;針灸內關穴、神門穴可理氣止痛、寧心安神[11~12];四神聰穴可調動元神之府,針灸該穴可調動太陽穴使陽神得以潛藏入陰,健腦調神;針灸百會穴可回陽固脫、開竅醒腦。諸穴相配則安神定志、調理臟腑,促使神歸其舍與機體重回“晝精夜瞑、陰平陽秘”的生理狀態,從而改善患者睡眠質量。
現代神經生物學研究認為,過度覺醒機制是慢性失眠(特別是心理生理性失眠癥或原發性失眠癥)的重要病因機制[13]。長期失眠癥患者的白晝存在自主神經系統興奮與抑制失衡,且伴有生理-認知-皮層的過度興奮表現。有研究發現,過度覺醒可表現在神經免疫、神經內分泌、神經生理學(包括諸多神經遞質)、睡眠電生理等方面[14]。GABA、GA 是中樞神經系統抑制性神經遞質,前者可參與睡眠起始、晝夜睡眠過程、慢波睡眠振蕩的產生、睡眠維持等睡眠-覺醒調節過程,而后者具有抑制神經細胞過度放電、興奮傳導等作用,兩者均有利于促進睡眠。Benson 等[15]研究發現,原發性失眠患者血清GABA、GA 水平呈低表達,且兩者表達與患者睡眠質量、過度覺醒狀態密切相關。由此可見,提高血清GABA、GA 水平是促進睡眠、改善過度覺醒狀態的重要環節。本研究結果顯示,相比對照組,研究組治療4 周后覺醒次數少、血清GA、GABA 水平高,表明針灸聯合酒石酸唑吡坦片可能通過上調血清GABA、GA 等神經遞質水平,從而達到降低過度覺醒狀態、改善睡眠質量的功效。所有患者治療期間均未出現過敏、感染、暈針等嚴重不良反應,研究組僅2 例出現輕微局部血腫,且未處理1 周內緩解,證實在酒石酸唑吡坦片治療基礎上加用針灸治療具有較高的安全性。綜上所述,采用針灸聯合西藥治療原發性失眠癥患者的效果明顯,可提高患者睡眠質量,延長總睡眠時間,改善過度覺醒狀態,調節神經遞質水平,且安全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