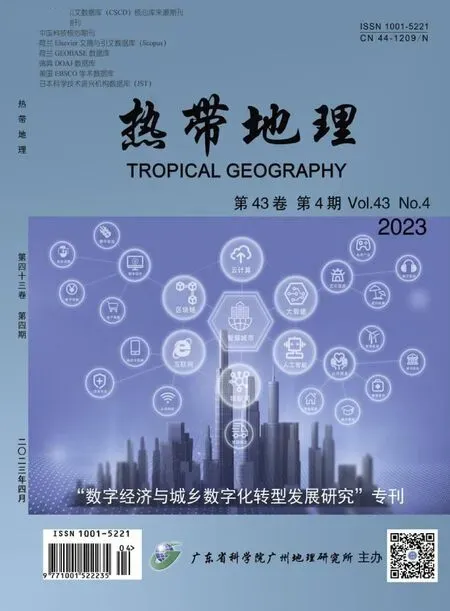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視角下華語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特征、演化趨勢與影響因素
李 煒,何金廖,郭衛(wèi)東
(華東師范大學(xué) a.城市與區(qū)域科學(xué)學(xué)院;b.中國現(xiàn)代城市研究中心;c.城市發(fā)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20 世紀(jì)90 年代以來,全球化與信息化的加快推進使城市間聯(lián)系日趨緊密,并呈現(xiàn)網(wǎng)絡(luò)化發(fā)展態(tài)勢(Scott, 2012),城市網(wǎng)絡(luò)研究逐漸成為城市地理學(xué)的熱點命題(胡國建 等,2019)。Castells提出的“流空間理論”認(rèn)為信息時代的城市是各種要素流空間的節(jié)點和樞紐,該觀點被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組(GaWC)所吸收,并提出從高級生產(chǎn)性服務(wù)業(yè)(APS)聯(lián)系探討世界城市網(wǎng)絡(luò)的新思路,成為城市網(wǎng)絡(luò)研究的基本范式(Castells, 1996; Taylor et al., 2002)。既有文獻分別從企業(yè)內(nèi)外部聯(lián)系(張杰 等,2022;文嫮 等,2022)、交通設(shè)施聯(lián)系(柯文前 等,2019)、人口流動(趙梓渝 等,2017)、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知識網(wǎng)絡(luò)(段德忠 等,2018;馬海濤,2020)、產(chǎn)業(yè)鏈分工(劉清 等,2021)等方面分析特定領(lǐng)域的城市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同時學(xué)界關(guān)注的焦點亦從單純的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分析轉(zhuǎn)向?qū)W(wǎng)絡(luò)發(fā)育機理的探索(段德忠 等,2018;顧偉男 等,2019;劉清 等,2021)。
近年來,隨著創(chuàng)意經(jīng)濟的快速崛起,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因其在區(qū)域就業(yè)與收入增長、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變革、經(jīng)濟運行系統(tǒng)創(chuàng)新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受到學(xué)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關(guān)注(厲無畏 等,2006;Gong et al., 2018)。學(xué)者們開始探索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空間組織與城市網(wǎng)絡(luò)形成的關(guān)系。其中部分研究借鑒Taylor等的做法,以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企業(yè)連鎖網(wǎng)絡(luò)構(gòu)建城市網(wǎng)絡(luò)(張旭 等,2020)。連鎖網(wǎng)絡(luò)模型基于城市主要通過企業(yè)信息、資本、人員和知識等要素流動相互連接的假設(shè),逐漸成為測算城市網(wǎng)絡(luò)的主流方法(Taylor, 2002;胡國建 等,2020)。但最近幾項研究指出,創(chuàng)意部門通常以圍繞組織和個人進行的臨時項目作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Watson, 2012;He et al., 2022),創(chuàng)意生產(chǎn)者以尋求個人聲譽和社會資本為目的建立合作關(guān)系(Scott, 2006; Grabhe,2004)。這種靈活多樣的組織形式、以人為中心的合作理念使公司作為基本分析單元的解釋力減弱,導(dǎo)致連鎖網(wǎng)絡(luò)模型用于構(gòu)建基于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聯(lián)系城市網(wǎng)絡(luò)的適用性受到質(zhì)疑。因此,迫切需要從創(chuàng)意個體而不是企業(yè)聯(lián)系的角度探究城市創(chuàng)意聯(lián)系,即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He et al., 2022)。
鑒于此,本文擬以華語數(shù)字音樂的創(chuàng)作合作網(wǎng)絡(luò)為實證案例,基于1980—2021年發(fā)行的華語歌曲數(shù)據(jù)庫,綜合運用GIS可視化與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方法,深入解析城市音樂創(chuàng)作合作網(wǎng)絡(luò)的結(jié)構(gòu)特征、社團發(fā)展和演化趨勢,通過構(gòu)建負(fù)二項回歸模型,探究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人力資源、對外開放、交通條件等因子對華語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形成演化的影響,進而為揭示在(數(shù)字)創(chuàng)意生產(chǎn)體系影響下的城市關(guān)系重構(gòu)提供實證案例與理論基礎(chǔ)。此外,本研究也有助于深入了解當(dāng)前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態(tài)勢和地理格局,為今后城市音樂產(chǎn)業(yè)協(xié)同發(fā)展與治理提供參考依據(jù)。
1 文獻綜述
1.1 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的概念與基本特征
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是依托于創(chuàng)意行為主體(創(chuàng)意工作者、企業(yè)等)發(fā)生的聯(lián)系(He et al., 2022),屬于典型的“軟網(wǎng)絡(luò)”(馬海濤,2020)。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的基本特性可以從3個方面進行闡述:1)創(chuàng)意主體是城市在特定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的影響力和服務(wù)能力的代表。創(chuàng)意階層理論和創(chuàng)意場域(creative field)概念(Florida, 2005; Scott, 2010)認(rèn)為創(chuàng)意工作者因包容的社會環(huán)境、多元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高品質(zhì)的城市景觀和舒適物(馬仁鋒,2014;何金廖 等,2019)在特定城市集聚。反過來,具有影響力的創(chuàng)意人群為其所在城市打造創(chuàng)意品牌和城市印象(image)提供良好條件。2)城際創(chuàng)意主體間的聯(lián)系可視為非本地的知識網(wǎng)絡(luò)或知識流。傳統(tǒng)理論通常強調(diào)地理鄰近性對隱性知識獲取的重要性,然而,最近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新經(jīng)濟領(lǐng)域中非正式的社會關(guān)系和臨時性的跨地區(qū)合作對于促進知識和創(chuàng)新傳播更為重要(Bathelt et al., 2014; Zhang et al.,2018),創(chuàng)意主體建立的臨時性跨區(qū)合作正是非本地聯(lián)系的典型代表。3)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反映城市參與創(chuàng)意生產(chǎn)的競合關(guān)系。城市是參與全球價值鏈治理的重要主體,其競爭力取決于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承擔(dān)怎樣的角色,中心節(jié)點(城市)因為控制了研發(fā)和創(chuàng)新的價值鏈環(huán)節(jié)而具有較高的網(wǎng)絡(luò)權(quán)力(Ernst, 2002; Gereffi et al., 2016;劉清 等,2021)。類似地,在創(chuàng)意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中占據(jù)中心位置的城市相對于其他處于從屬地位的城市具有明顯的比較優(yōu)勢和支配權(quán)力。
與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類似的概念還有城市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Freeman, 1991;顧偉男 等,2019),雖然二者都具有較強的知識流屬性,但在以下方面存在明顯區(qū)別:1)創(chuàng)意是區(qū)別于創(chuàng)新的知識生產(chǎn)過程。創(chuàng)新依賴于技術(shù)和科學(xué)知識,即“綜合型”和“解析型”知識(Hansen et al., 2005),但創(chuàng)意更依賴符號知識(symbolic knowledge),如文字、審美和藝術(shù)表達等文化輸入(Boden, 2004; Scott, 2014; Hansen et al, 2015)。因此,創(chuàng)意可能引發(fā)創(chuàng)新,但創(chuàng)新幾乎不會引發(fā)創(chuàng)意。2)創(chuàng)意主體與創(chuàng)新主體存在較大差異。創(chuàng)新主體往往是企業(yè)、高校、科研院所等組織機構(gòu),其知識媒介通常是可量化的專利、論文等;而創(chuàng)意主體則要更加靈活多樣,且由于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屬于垂直不整合、柔性生產(chǎn)體系,有著不確定、高風(fēng)險的外部環(huán)境,因此在創(chuàng)意價值鏈創(chuàng)作過程中起主導(dǎo)作用的往往不是跨國公司或大型企業(yè),而是個體或小微企業(yè),其產(chǎn)品(作品)也難以通過傳統(tǒng)計量方法測量(Grabher, 2004; Scott, 2010; Hoyler et al., 2013;何金廖 等,2018)。3)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比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更具有社交網(wǎng)絡(luò)屬性。由于創(chuàng)意主體往往是個體人(如藝術(shù)家、歌星、作家等),創(chuàng)意主體之間的聯(lián)系更多表現(xiàn)為臨時性的合作,因此,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更多地屬于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范疇,這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通常是基于共同的愛好、生活方式、價值觀所建立起來的社區(qū)或社團組織,具有強烈的自我認(rèn)知和身份認(rèn)同屬性(Florida, 2014)。
綜上,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是一種特殊的城市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是基于垂直不整合(disintegration)、柔性生產(chǎn)體系(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和臨時性項目合作(temporary project-based collaboration),甚至是在數(shù)字空間中發(fā)生的城市聯(lián)系(Grabher, 2004;Scott, 2010;王緝慈,2010;Hoyler et al., 2013)。在創(chuàng)意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城市之間的聯(lián)系具有很強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屬性和以人為中心的特征,跟包括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在內(nèi)的城市聯(lián)系有顯著差異。
1.2 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研究
數(shù)字音樂作為一種典型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已成為彰顯城市軟實力和影響力的重要載體(Naveed et al., 2017),其生產(chǎn)過程高度依賴于創(chuàng)意個體(音樂創(chuàng)作者)和臨時性項目組織模式。同時,音樂產(chǎn)業(yè)也是最早經(jīng)歷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產(chǎn)業(yè)之一,自從2005年中國頒布第一部《互聯(lián)網(wǎng)著作權(quán)行政保護辦法》以來,中國數(shù)字音樂迎來快速發(fā)展的態(tài)勢,并逐步形成以數(shù)字音樂平臺、移動K歌、短視頻、泛娛樂直播、版權(quán)運營、音樂社交為形式的多渠道運營模式。近年來,地理學(xué)與音樂交叉領(lǐng)域的研究逐漸興起,其中經(jīng)濟地理學(xué)重點關(guān)注音樂產(chǎn)業(yè)的空間屬性(Makkonen , 2014; Brandellero et al., 2015),例如音樂產(chǎn)業(yè)區(qū)位(Florida et al., 2010)、集群演化(Lin,2014)、價值創(chuàng)造(Lange et al., 2013)以及音樂場景與網(wǎng)絡(luò)(Brandellero et al., 2015; Pedrini et al.,2022)等。總體而言,音樂在地理學(xué)視角下被不斷賦予新的內(nèi)涵,相關(guān)研究亦取得豐碩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幾點值得進一步推進。首先,音樂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特征及其空間聯(lián)系研究有待深入。當(dāng)前音樂網(wǎng)絡(luò)研究重點關(guān)注本地網(wǎng)絡(luò),盡管對區(qū)域合作網(wǎng)絡(luò)也有涉及,但缺少城市層面的系統(tǒng)分析,特別是對城市在音樂生產(chǎn)(創(chuàng)作)的作用、跨地區(qū)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演化以及空間組織模式的探討略顯不足。其次,已有研究對音樂網(wǎng)絡(luò)的概念界定過于寬泛,多數(shù)研究將機構(gòu)包含在網(wǎng)絡(luò)中可能會淡化創(chuàng)意個體對于音樂產(chǎn)業(yè)的重要性。再者,隨著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guān)于大力推進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出臺以及《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fā)展改革規(guī)劃綱要》首次將“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展”列入“重大文化產(chǎn)業(yè)工程”,社會大眾對于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的關(guān)注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jù)《2020 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展報告》,2019 年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市場總規(guī)模達3 950.96億元,對比2014年的2 851.5億元,增幅達38.56%,可見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正處于快速發(fā)展階段(趙志安等,2021)。因此,選擇數(shù)字音樂作為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的實證案例,既能體現(xiàn)創(chuàng)意合作網(wǎng)絡(luò)的內(nèi)在特質(zhì)又可以為中國數(shù)字音樂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提供參考依據(jù)。
2 數(shù)據(jù)采集與研究方法
2.1 數(shù)據(jù)采集
Leyshon(2001)認(rèn)為音樂生產(chǎn)包括一系列過程,音樂網(wǎng)絡(luò)涵蓋創(chuàng)意、復(fù)制、分銷和消費等4個子網(wǎng)絡(luò),其中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由作曲和表現(xiàn)網(wǎng)絡(luò)融合而成。音樂創(chuàng)作人主要包括歌手、作詞人、作曲人和編曲人4個角色,完成一首歌的發(fā)布需要上述創(chuàng)作者之間緊密的合作。在這種項目式的合作關(guān)系中音樂創(chuàng)作人一方面可以相互學(xué)習(xí),傳播思想與經(jīng)驗、共享知識與資源,同時還可以建立個人聲譽并擴展社會網(wǎng)絡(luò)。
以酷狗音樂網(wǎng)(kugou.com)的數(shù)字音樂庫為基礎(chǔ)數(shù)據(jù),通過網(wǎng)絡(luò)爬蟲技術(shù)(Python語言)獲得1980—2021 年出版的所有華語歌曲,共計24 萬余首。由于數(shù)字音樂存在顯著的長尾效應(yīng),90%以上的流量集中在不到10%的歌手及其作品中,因此,只保留酷狗音樂平臺粉絲數(shù)量>5 萬的歌手參與創(chuàng)作的歌曲,共計6 萬余首歌曲,涉及794 位歌手或創(chuàng)作者。
2.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法對華語數(shù)字音樂的合作網(wǎng)絡(luò)進行分析,根據(jù)歌曲合作的情況構(gòu)建城市網(wǎng)絡(luò),并計算城市聯(lián)系強度,公式為:
式中:Wij為城市i和城市j之間的聯(lián)系強度;n為合作歌曲數(shù)量;pi和pj分別為城市i和城市j中參與合作同一歌曲的歌手?jǐn)?shù)量。將研究期分為1980—1993、1994—2007和2008—2021年3個時間段,從而刻畫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的演化特征。
采用Pajek 軟件對中國城市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結(jié)構(gòu)特征進行定量測度,包括網(wǎng)絡(luò)整體結(jié)構(gòu)、中心性、社區(qū)發(fā)現(xiàn)等。
2.2.1 網(wǎng)絡(luò)整體特征 網(wǎng)絡(luò)整體拓?fù)涮卣鞣治鍪巧鐣W(wǎng)絡(luò)分析的重要方面。其中,網(wǎng)絡(luò)密度即關(guān)聯(lián)網(wǎng)絡(luò)的緊密程度,是網(wǎng)絡(luò)中實際存在的節(jié)點之間的聯(lián)系數(shù)量與理論上可能存在的最大聯(lián)系數(shù)量之比。網(wǎng)絡(luò)密度越大,說明城市之間的聯(lián)系越緊密。若網(wǎng)絡(luò)密度為1,則意味著每個城市都與其他城市相連。平均路徑長度是指網(wǎng)絡(luò)中所有節(jié)點之間聯(lián)系的平均最短距離。平均路徑長度越短,網(wǎng)絡(luò)的傳輸性能和效率越高。聚類系數(shù)指與某節(jié)點直接相鄰的節(jié)點間實際存在的聯(lián)系數(shù)量占最大可能聯(lián)系數(shù)量的比重。平均聚類系數(shù)即所有節(jié)點聚類系數(shù)的算術(shù)平均值,反映網(wǎng)絡(luò)集團化的程度。若網(wǎng)絡(luò)具有較大的聚類系數(shù)和較小的平均路徑長度,則認(rèn)為該網(wǎng)絡(luò)具備小世界效應(yīng)。網(wǎng)絡(luò)整體特征指標(biāo)的具體計算公式參考方錦清等(2007)研究。
2.2.2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分析是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的常用方法,主要采用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刻畫各城市節(jié)點的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特征。其中,度中心性指某一節(jié)點在網(wǎng)絡(luò)中直接聯(lián)系的其他節(jié)點數(shù)量,是反映節(jié)點在網(wǎng)絡(luò)中影響力的常用指標(biāo)。度中心性越高,說明該城市在網(wǎng)絡(luò)中與其他城市之間的聯(lián)系越多,越處于網(wǎng)絡(luò)中心位置,擁有更高影響力。當(dāng)網(wǎng)絡(luò)含權(quán)時,城市度中心性即為加權(quán)度中心性,指與某城市相連所有邊的權(quán)重之和。中介中心性是網(wǎng)絡(luò)中經(jīng)過某一節(jié)點的最短路徑的數(shù)量,反映該節(jié)點在網(wǎng)絡(luò)中作為樞紐和控制中心的能力。中介中心性越高,說明該城市控制其他城市之間聯(lián)系的能力越強。節(jié)點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計算公式參考任曉龍等(2014)研究。
2.2.3 社區(qū)發(fā)現(xiàn) 社區(qū)是指網(wǎng)絡(luò)中的一些節(jié)點組成的子網(wǎng),其基本特征是社區(qū)內(nèi)部節(jié)點聯(lián)系相對于各個社區(qū)之間更為緊密。社區(qū)發(fā)現(xiàn)作為一種針對網(wǎng)絡(luò)的特殊聚類方法,對揭示網(wǎng)絡(luò)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特征、提煉網(wǎng)絡(luò)組織模式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選用基于模塊度的多級局部搜索算法對城市網(wǎng)絡(luò)進行社區(qū)挖掘,該方法可以實現(xiàn)多次運行優(yōu)化并在所有聚類運行中選擇最佳分區(qū)結(jié)果(Noack et al., 2009),具體過程借助Pajek軟件實現(xiàn)。
2.2.4 負(fù)二項回歸 正如企業(yè)連鎖網(wǎng)絡(luò)模型本質(zhì)上是通過企業(yè)辦公地點選址策略構(gòu)建城市網(wǎng)絡(luò)那樣,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則是歌手合作目的地城市選擇的結(jié)果。因此,影響歌手合作目的地選擇的因素從根本上決定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形成與演化。按照上述思路,將模型因變量設(shè)置為研究期內(nèi)不同階段各城市累計產(chǎn)生音樂合作的次數(shù)。自變量方面,參考已有研究(盛科榮 等,2018;Akhavan et al., 2020;張旭 等,2020;高雅妮 等,2022),擬從以下幾方面探討影響城市音樂合作的因素。1)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CES):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越大意味著市場需求更高、潛力更大,接近這樣的市場,歌手不僅可以把握產(chǎn)業(yè)前沿動態(tài)還可以獲得更多商業(yè)機會。采用人均生產(chǎn)總值(GDP)表征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2)人力資本水平(HC):在知識經(jīng)濟時代,人力資本通過為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提供創(chuàng)意和創(chuàng)新動能成為影響其發(fā)展的關(guān)鍵因素。與人力資本水平高的城市合作有可能獲得更多的創(chuàng)意想法并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在指標(biāo)選取上,以每萬人普通本專科人數(shù)作為人力資本水平的代理變量。3)城市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IS):城市第三產(chǎn)業(yè)發(fā)展水平越高,相關(guān)配套產(chǎn)業(yè)越完善,可以為音樂合作以及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展提供輔助支持。以第三產(chǎn)業(yè)占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的比重衡量城市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展情況。4)對外開放(OPEN):一般認(rèn)為城市對外開放有助于其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技術(shù)、經(jīng)驗、信息和資金等戰(zhàn)略資源,進而提高競爭優(yōu)勢。上述戰(zhàn)略資源對于音樂產(chǎn)業(yè)以及歌手職業(yè)發(fā)展同樣重要。以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與GDP比值衡量對外開放水平。5)城市行政級別(CAL):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可能擁有更多的政治資源(Noack et al., 2009)。采用虛擬變量刻畫城市行政級別,其中直轄市賦值3,省會城市賦值2,其他地級行政單元賦值1。6)交通可達性(TA):城市交通可達性越好,信息、知識和資本等資源傳輸越便捷,歌手跨越城市進行合作與交流的可能性更高。通過設(shè)置虛擬變量近似地反映城市交通可達性,若城市開通高鐵站則賦值1,反之賦值0。7)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NE):除交通可達性這一類物理可達性外,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等非物理可達性同樣重要,其基本思想是知識中心之間企業(yè)或組織的戰(zhàn)略聯(lián)系可以促進知識和信息交流(Bentlage et al., 2013; Akhavan et al., 2020)。對于本研究,城市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水平越高,歌手獲得所需知識和信息的機會越大,產(chǎn)生音樂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在變量設(shè)置上,借鑒Akhavan 等(2020)的做法,參照GaWC的研究結(jié)果對γ-至α+類型的城市分別賦值1~9,其他城市賦值0。
綜上,構(gòu)建如下模型:
式中:MCit為城市i在t時間段累計產(chǎn)生的音樂合作次數(shù);α為常數(shù)項;β1~β7為回歸系數(shù);ε為擾動項。為避免異方差帶來的影響,對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和人力資本水平等帶有量綱的變量進行對數(shù)處理。同時,考慮數(shù)據(jù)的可得性與完整性,選擇以1994—2007和2008—2021年2個時間段內(nèi)90個城市為樣本進行回歸。最后,為了減少可能存在的內(nèi)生性影響,自變量分別選擇2006 和2020 年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進行建模。所有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相應(yīng)年份的《中國城市統(tǒng)計年鑒》。鑒于GaWC 并非每年都進行新的分類,因此采用最相近的2020和2008年的城市分類作為參考。此外,由于缺少2020 年城市實際使用外商投資數(shù)據(jù),因此以2019年數(shù)據(jù)替代。
3 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特征
從網(wǎng)絡(luò)整體拓?fù)渲笜?biāo)變化情況看,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演化具有以下特征:1)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迅速增長。如表1 所示,1980—1993年,有72 名歌手參與179 首歌曲創(chuàng)作,并產(chǎn)生217對合作關(guān)系。該時期歌手間的合作關(guān)系覆蓋7個城市,形成12對城市聯(lián)系。1994—2007年有186名歌手參與577 首歌曲創(chuàng)作,歌手合作關(guān)系數(shù)量增至634 個,涉及21 個城市與43 對城市聯(lián)系。2008—2021年,共有641名歌手參與3 955首歌曲的創(chuàng)作,歌手合作數(shù)增加至5 215 個,城市和城市對數(shù)量分別達到104個與497對。可以看出,第3階段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增長的速率遠(yuǎn)大于第2階段。主要原因在于,音樂生產(chǎn)模式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使得音樂作品的生產(chǎn)更加開放透明,其轉(zhuǎn)換、存儲和傳輸?shù)某杀镜玫浇档汀T诖诉^程中獨立音樂創(chuàng)作人等個體工作者異軍突起,便攜式播放器(如MP3 和MP4 等)的推廣更為其提供了巨大的消費者基數(shù)(芮明杰 等,2005)。在此背景下,音樂生產(chǎn)與消費表現(xiàn)出個體化和去中心化的趨勢,使得參與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城市明顯增加,不再局限于北京、香港和臺北等老牌音樂城市。2)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具有低密度和小世界的特征。研究期內(nèi)網(wǎng)絡(luò)平均度從3.43 增至9.56,即網(wǎng)絡(luò)中某城市直接聯(lián)系的城市個數(shù)從3 增加至9 個。平均路徑長度從1.48 增加至2.02,平均聚類系數(shù)從0.84降低至0.63,表明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具有相對較短的路徑長度和較高的聚類系數(shù),即明顯的小世界特性。與部分企業(yè)網(wǎng)絡(luò)視角下城市網(wǎng)絡(luò)研究(張杰 等,2022)不同的是,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密度由0.57降至0.09,表明基于個體項目合作的中國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密度與規(guī)模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其主要原因在于,同一音樂創(chuàng)作人僅能維持有限的社會關(guān)系,其交往的音樂創(chuàng)作人數(shù)量有限,同時大部分音樂創(chuàng)作人集中于少數(shù)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達的城市,最終形成網(wǎng)絡(luò)覆蓋城市增加但整體密度降低的態(tài)勢。

表1 1980—2021年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主要指標(biāo)變化Table 1 Changes in main indicators of urban digital music cooperation network from 1980 to 2021
1980—2021年城市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時空格局演化情況如圖1、2所示,不同時間段中心性前10名城市位序變化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1)城市中心性在空間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地帶性分異,高中心性城市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qū),中西部城市中心性相對較低,且隨著時間推移,“東高西低”的格局持續(xù)存在。這表明東部城市在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中擁有更高的影響力和控制力。2)內(nèi)地城市中心性排名提升明顯,逐漸形成北京-香港-臺北“三足鼎立”的格局。1980—2021 年,北京、香港和臺北3市的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一直位列前三。其中,北京的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一直排在首位,表明北京在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中擁有最高的影響力,同時也是連接內(nèi)地與港臺的“橋梁”和“樞紐”。香港和臺北緊隨其后,在網(wǎng)絡(luò)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自1994年以來上海、深圳、成都、重慶、沈陽和哈爾濱等城市不斷崛起,其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均有明顯提升。相較之下,中國臺灣的高雄、嘉義和臺南等城市排名有所下滑,逐漸邊緣化。3)部分西南地區(qū)和東北地區(qū)城市扮演重要角色。與一些交通城市網(wǎng)絡(luò)研究(楊浩然 等,2022)不同的是,部分西南地區(qū)和東北地區(qū)城市,如成都、重慶、沈陽和哈爾濱等在網(wǎng)絡(luò)中扮演著區(qū)域性中心的角色,且中心性不斷提升。其中,成渝2市自1994年起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排名均位于前10 名,哈沈2 市自2008 年起度中心性進入前10名,中介中心性進入前15名。總的來說,高中心性城市不僅多為全國或區(qū)域性的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且集中了大量音樂唱片公司或音樂類高水平院校,具備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展和音樂人才集聚的重要資源,由此產(chǎn)生了大量的音樂合作,使其在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中處于較中心的位置。如成都和沈陽2市分別設(shè)有國內(nèi)知名的沈陽音樂學(xué)院和四川音樂學(xué)院2所高等音樂學(xué)府,并以此為依托聯(lián)合重點音樂企業(yè)打造“成都音樂坊”和“叁叁工廠音樂主題文化園區(qū)”作為本地乃至國際的音樂文化交流中心,從而實現(xiàn)音樂人才的吸收引進和數(shù)字音樂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使其成為西南和東北地區(qū)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要地。

圖1 城市度中心性時空格局演化Fig.1 Evolutio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 centrality

圖2 城市中介中心性時空格局演化Fig.2 Evolutio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 intermediary centrality

表2 1980—2021年中心性前10名城市變化情況Table 2 Changes of top 10 cities in centralities from 1980 to 2021
4 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演化趨勢
從不同階段城市聯(lián)系強度(圖3)和城市聯(lián)系強度前10名的城市對及其累計占比(表3)可以看出:1)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演化具有路徑依賴和路徑創(chuàng)造特征,內(nèi)地城市間聯(lián)系強度提升明顯。研究期內(nèi),北京-深圳、臺北-北京、北京-香港和臺北-香港等高強度聯(lián)系持續(xù)存在且表現(xiàn)出自我強化的趨勢,具有路徑依賴的特點。同時,從1994年起出現(xiàn)以北京-廣州、北京-沈陽、北京-上海以及北京-哈爾濱等為代表新的高強度聯(lián)系,說明在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演化過程中兼具路徑創(chuàng)造的特征。此外,高強度聯(lián)系由北京-深圳擴展至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哈爾濱和沈陽等諸多城市,表明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正發(fā)生重大空間重構(gòu),合作重心從港臺城市逐漸轉(zhuǎn)向內(nèi)地城市,后者在塑造網(wǎng)絡(luò)方面的作用不斷攀升。2)核心城市對間的高強度聯(lián)系控制網(wǎng)絡(luò)大量資源,但隨時間推移呈現(xiàn)弱化的趨勢。1980—1993 年前3、5、10 名城市對累計占比達68.20%、83.41%和99.08%,2008—2021 年該占比降至25.20%、32.29%和45.41%。可以看出,盡管核心城市間的高強度聯(lián)系仍占較高比例,但其影響力有所減弱。3)城市聯(lián)系覆蓋范圍擴大,但空間分布高度不均,高強度聯(lián)系主要集中在東部城市之間,北京、臺北和香港3市之間的聯(lián)系構(gòu)成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骨干并呈現(xiàn)“三角形”的空間結(jié)構(gòu)。北京-香港和北京-臺北作為網(wǎng)絡(luò)中的關(guān)鍵聯(lián)系,其聯(lián)系強度穩(wěn)步提升,前者從第4 位上升至第3 位,后者一直穩(wěn)居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1993 和1994—2007 年,臺北-香港構(gòu)成網(wǎng)絡(luò)的首位聯(lián)系,聯(lián)系強度從96 增至297,占比從44.24%增至46.85%。但在2008—2021年,由于北京和哈爾濱2市歌手進行了大量音樂合作,臺北-香港首位聯(lián)系地位被北京-哈爾濱取代。4)等級擴散是網(wǎng)絡(luò)擴散的主要形式。聯(lián)系強度10名的城市聯(lián)系主要由網(wǎng)絡(luò)核心城市構(gòu)成,同省或地理距離鄰近城市間的聯(lián)系相對較弱。盡管最初在中國臺灣的臺北、高雄和嘉義之間存在高強度聯(lián)系,但從1994年開始逐漸消失,網(wǎng)絡(luò)等級擴散的趨勢更加明顯。

圖3 城市聯(lián)系強度時空格局演化Fig.3 Evolutio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 connection intensity

表3 1980—2021年前10名城市聯(lián)系強度與累計占比Table 3 Contact strength and cumulative proportion of top 10 cities from 1980 to 2021
進一步根據(jù)多級局部搜索算法對不同時期的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進行社區(qū)劃分,并借助Gephi軟件進行可視化(圖4)。總的來說,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數(shù)量增加,其發(fā)展演化具有集團化、規(guī)模化和層級化的趨勢且雙核心模式和多核心模式是其主要的空間組織模式。具體來看,1980—1993年的合作網(wǎng)絡(luò)只劃分出1個社區(qū),該社區(qū)屬于典型的雙核心組織模式(圖4-a)。其中,臺北和香港作為核心城市,二者間的高強度聯(lián)系構(gòu)成社區(qū)中網(wǎng)絡(luò)的基本骨架。高雄、臺南、嘉義和北京位于第二層級,深圳則位于第三層級。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主要集中在港臺地區(qū),內(nèi)地音樂產(chǎn)業(yè)尚未形成。1994—2007年的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圖4-b),北京作為內(nèi)地重要節(jié)點開始占據(jù)較為重要的位置。同時期產(chǎn)生了由成都-武漢1 組聯(lián)系構(gòu)成的獨立社區(qū),但其發(fā)育程度低。2008—2021 年的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出現(xiàn)3 個社區(qū),原先香港和臺北控制的雙核心社區(qū)演化為以北京為主核心城市,香港、臺北和哈爾濱為副核心城市的多核心社區(qū)(圖4-c),說明華語音樂的中心已經(jīng)由港臺地區(qū)轉(zhuǎn)移到內(nèi)地,而北京是華語音樂創(chuàng)作的核心城市。同時期,華語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中還出現(xiàn)相對比較獨立的社區(qū),主要以秦皇島、河池、呼和浩特和長春為核心城市(圖4-d)。

圖4 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結(jié)構(gòu)Fig.4 Community structure of urban digital music cooperation network
5 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影響因素
采用負(fù)二項回歸模型分析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影響因素,自變量VIF值均<3,說明不存在嚴(yán)重的共線性問題(表4)。首先,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CES)的系數(shù)(1.306)在0.05 水平下顯著影響城市音樂合作數(shù)量,說明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越大,居民消費水平越高,市場潛力越大,城市更容易吸引歌手開展音樂合作。其次,城市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IS)的系數(shù)(6.790)在0.1水平下對城市音樂合作數(shù)量產(chǎn)生顯著影響,該結(jié)果與張旭等(2020)對文化產(chǎn)業(yè)城市網(wǎng)絡(luò)的研究結(jié)論類似,表明第三產(chǎn)業(yè)發(fā)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可為音樂合作以及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展提供更好的配套支持,從而吸引更多合作。第三,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NE)的系數(shù)(0.208)在0.01水平下顯著影響城市音樂合作數(shù)量,說明城市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水平越高,歌手獲得所需信息和知識的可能性越大,從而產(chǎn)生音樂合作的可能性越大。第四,人力資本水平(HC)、對外開放(OPEN)、城市行政級別(CAL)以及交通可達性(TA)等因素均未在0.05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部分企業(yè)網(wǎng)絡(luò)視角研究(Noack et al.,2009;盛科榮 等,2018)不同。其原因可能為:1)歌手群體具有明顯的草根性(郭靜舒 等,2012),高等教育資源、人力資本和城市行政等級對音樂產(chǎn)業(yè)的影響相對較弱,這與網(wǎng)絡(luò)直播群體的相關(guān)研究(彭玨 等,2021)類似。2)華語音樂具有很強的內(nèi)生性,地方文化對音樂的發(fā)展具有很強影響,如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比較集中的川渝、東北地區(qū)是中國音樂人才比較集中的地區(qū)(蔡際洲,2005;2014),因此城市對外開放程度對音樂合作的影響相對較弱;3)音樂合作跟其他文化創(chuàng)意活動一樣,對非本地聯(lián)系的依賴較為明顯,如,現(xiàn)有研究發(fā)現(xiàn)電影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與設(shè)計產(chǎn)業(yè)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都具有很強的跨地區(qū)合作機制(Zhang et al., 2018; He et al., 2022),因此,地理鄰近性往往對城市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的影響相對較弱。上述結(jié)果表明影響企業(yè)布局選址的因素并不能完全適用于解釋歌手音樂合作的產(chǎn)生,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歌手合作視角下中國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形成的獨特性,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的形成受到經(jīng)濟規(guī)模、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等因素的影響。

表4 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影響因素模型回歸結(jié)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urban digital music cooperation network
6 結(jié)論與討論
本文以華語數(shù)字音樂為例,探討了中國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的結(jié)構(gòu)演化特征及影響因素,從創(chuàng)意個體聯(lián)系的視角豐富了城市網(wǎng)絡(luò)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得到的主要結(jié)論包括:1)中國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增長迅速,整體呈現(xiàn)低密度和小世界的特征,且網(wǎng)絡(luò)密度與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負(fù)相關(guān),具有明顯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屬性。2)中國城市數(shù)字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具有明顯的“中心-邊緣”結(jié)構(gòu)并呈現(xiàn)多中心化的發(fā)展趨勢。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慶、沈陽和哈爾濱等中心性提升明顯,相較之下中國臺灣的高雄、嘉義和臺南等地逐漸邊緣化,最終形成北京-香港-臺北“三足鼎立”的格局。與城際設(shè)計師虛擬社區(qū)網(wǎng)絡(luò)(He et al., 2022)、電影制作網(wǎng)絡(luò)(Zhang et al.,2018)以及電視劇制作網(wǎng)絡(luò)(文嫮 等,2020)等研究類似的是,上述城市中心性的演化特征并未完全遵循現(xiàn)有城市等級體系,說明在(數(shù)字)創(chuàng)意經(jīng)濟的影響下城市關(guān)系正在發(fā)生重構(gòu)。3)中國城市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具有明顯的社區(qū)結(jié)構(gòu),雙核心模式和多核心模式是其主要的空間組織模式,社區(qū)發(fā)展演化呈現(xiàn)集團化、規(guī)模化和層級化的態(tài)勢。4)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城市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水平對城市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演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人力資本水平、對外開放、城市行政級別以及交通可達性等因素的作用不明顯,表明華語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具有明顯的內(nèi)生機制和地方嵌入性。
本研究為理解在(數(shù)字)創(chuàng)意經(jīng)濟的影響下城市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和推進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提供理論和政策層面的啟示。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和數(shù)字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中國城市迎來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數(shù)字經(jīng)濟與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疊加效應(yīng)催生數(shù)字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這一新的產(chǎn)業(yè)形態(tài)。在數(shù)字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中,創(chuàng)意主體作為城市在特定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的代表,其非本地知識網(wǎng)絡(luò)反映城市參與創(chuàng)意生產(chǎn)的競合關(guān)系,有別于企業(yè)網(wǎng)絡(luò),二者遵循不同的底層邏輯。因此,對于此類城市網(wǎng)絡(luò)的研究應(yīng)更加重視創(chuàng)意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的特質(zhì)性和創(chuàng)意行為主體(人)的作用。此外,本文認(rèn)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政策時應(yīng)充分認(rèn)識創(chuàng)意生產(chǎn)部門行為主體和生產(chǎn)模式的特點,遵循具體創(chuàng)意活動的客觀規(guī)律,明確各城市在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中的地位,選擇契合本地資源優(yōu)勢的發(fā)展路徑實現(xiàn)錯位發(fā)展。北京、香港和臺北等城市應(yīng)發(fā)揮全國性中心的作用,不僅要關(guān)聯(lián)互通國內(nèi)其他城市,更要主動對接全球,在壯大本地音樂產(chǎn)業(yè)的同時帶動其他城市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展,推動中國音樂走向世界,從而在整體上提升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的國際影響力。對于成都、重慶、沈陽和哈爾濱等城市應(yīng)結(jié)合已有基礎(chǔ),鞏固區(qū)域內(nèi)城市聯(lián)系的同時增強全國乃至全球聯(lián)系,積極吸引音樂創(chuàng)意人才,參與音樂產(chǎn)業(yè)競爭協(xié)作,在更廣闊的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內(nèi)尋求所需的產(chǎn)業(yè)資源和消費市場,提升本地音樂產(chǎn)業(yè)發(fā)展水平的同時帶動邊緣城市更好地融入網(wǎng)絡(luò)。
本文以華語歌手音樂合作為例系統(tǒng)研究了個體項目聯(lián)系視角下中國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的結(jié)構(gòu)演化特征并初步探究其影響因素,但仍存在局限性,需要在未來進一步完善。1)本文主要采用明星歌手的創(chuàng)作合作網(wǎng)絡(luò)進行定量分析,缺少質(zhì)性的調(diào)研支撐,未來需通過對“明星”歌手進行個人訪談和調(diào)查問卷等研究方法,結(jié)合中國音樂產(chǎn)業(yè)特色,探索創(chuàng)意主體之間的合作機制。2)由于數(shù)據(jù)的限制,本文僅對城市網(wǎng)絡(luò)的中心性(節(jié)點度)進行回歸分析,沒有考慮城市之間聯(lián)系強度的影響因子,未來需構(gòu)建多維度的回歸模型,對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的形成機理進行更深入的解釋。3)本文主要基于數(shù)字音樂的合作網(wǎng)絡(luò),音樂產(chǎn)業(yè)只是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部門之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他部門的城市創(chuàng)意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特征和影響機制可能跟音樂合作網(wǎng)絡(luò)存在較大區(qū)別,未來需對比分析不同創(chuàng)意部門的異同性,從而為提煉創(chuàng)意城市網(wǎng)絡(luò)的一般特性提供更多案例和理論支撐。
- 熱帶地理的其它文章
- “數(shù)字經(jīng)濟與城鄉(xiāng)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發(fā)展研究”專刊序言
- 企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化對廣東先進制造業(yè)企業(yè)創(chuàng)新水平提升的影響
——以計算機、通信及其他電子設(shè)備制造業(yè)為例 - 行動者網(wǎng)絡(luò)視角下電商村的演化機制
——以廣州市大源村為例 - 數(shù)字經(jīng)濟的浙江模式及其地方特征
- 青藏高原縣域農(nóng)業(yè)數(shù)字化發(fā)展模式與動力機制
——以四川省理塘縣為例 - 數(shù)字經(jīng)濟對旅游發(fā)展影響的空間效應(yīng)
——基于中國28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實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