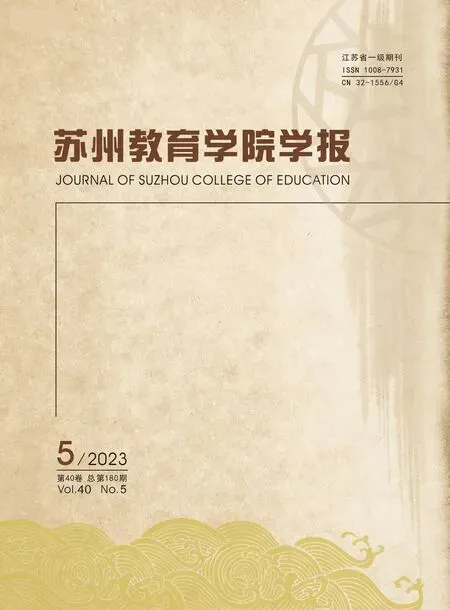欄目特邀主持人:湯哲聲
偵探小說是從國(guó)外引進(jìn)的類型小說。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中國(guó)最早翻譯的偵探小說是1896年至1897年《時(shí)務(wù)報(bào)》英文編輯張坤德翻譯的柯南·道爾的四部小說。之后到1911年左右,中國(guó)作家?guī)缀鯇?dāng)時(shí)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了一遍。在如此短的時(shí)間內(nèi),中國(guó)作家集中于偵探小說的翻譯,這在世界譯介史上也是個(gè)奇跡。中國(guó)作家對(duì)外國(guó)偵探小說如此熱衷,是因?yàn)樗麄冊(cè)趥商叫≌f中發(fā)現(xiàn)了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小說的不同之處,而且這些不同之處與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變革、文化轉(zhuǎn)型、敘事改革和閱讀需求相契合,其觀念和美學(xué)具有現(xiàn)代意義。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公案小說推崇清官意識(shí),清官意識(shí)的核心是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即所謂的邪不壓正、因果報(bào)應(yīng)。偵探小說尊重人權(quán),推崇的是法治意識(shí)。“涉訟者例得請(qǐng)人為辯護(hù),故茍非證據(jù)確鑿,不能妄人入罪。此偵探學(xué)之作用所由廣也。”(周桂笙:《〈歇洛克復(fù)生偵探案〉弁言》)偵探小說所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觀念與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社會(huì)變革中的呼喚科學(xué)、民主精神相呼應(yīng)。
這些偵探小說譯作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影響更為深刻。中國(guó)傳統(tǒng)小說的敘事模式受話本小說影響很深,基本都是“全知型”的敘事結(jié)構(gòu),作者無人不曉,無所不知。“全知型”的敘事結(jié)構(gòu)最大的問題是無論故事怎樣精彩,讀者都覺得這是作者“編”的,否則,你怎么知道那些不為人知的人和事呢?偵探小說的敘述者是“我”,記載的是“我”的所見所聞,強(qiáng)調(diào)的是真實(shí)性,是“半知型”的敘事結(jié)構(gòu)。當(dāng)時(shí)的小說評(píng)論家觚庵(俞明震)在評(píng)《福爾摩斯探案集》時(shí)就說:“其佳處全在‘華生筆記’四字也。”(觚庵:《觚庵漫筆》)傳統(tǒng)的偵探小說往往是從報(bào)案開始,并以破案過程構(gòu)成故事情節(jié),再以說案作為小說的結(jié)尾,其敘事時(shí)空可以折疊、穿插和倒置,人物刻畫是小說的敘事中心。這樣的敘事時(shí)空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因果關(guān)系、情節(jié)中心的敘事時(shí)空完全不同。與文言體的林譯小說不同,由于對(duì)市場(chǎng)的追求,當(dāng)時(shí)的偵探小說譯作基本都是白話體,以“我”為敘述者,在不同的時(shí)空組合中,用白話刻畫人物的命運(yùn)。如果我們將其與之后的“五四”文學(xué)革命的實(shí)踐比較起來看,就能深刻地體會(huì)晚清至民國(guó)初年這些偵探小說譯作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產(chǎn)生了多么深刻的影響。中國(guó)文學(xué)的現(xiàn)代化有著由量變到質(zhì)變的發(fā)展、成熟的過程,這些偵探小說譯作是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化的先行者和鋪墊者。
在類型小說中,偵探小說最講究文體結(jié)構(gòu),不同的視角強(qiáng)調(diào)往往會(huì)形成不同的美學(xué)形態(tài)和閱讀效果。自1841年5月愛倫·坡發(fā)表《莫格街兇殺案》之后,偵探小說大致就形成了多視角的基本框架。從世界偵探小說的發(fā)展形態(tài)來看,偵探小說的不同流派的形成也就是對(duì)不同視角的強(qiáng)調(diào)。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罪犯的追捕是古典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探案集》是代表作;強(qiáng)調(diào)辦案者的理念和職責(zé)的小說被稱為“現(xiàn)代犯罪小說”,如北歐的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強(qiáng)調(diào)“罪犯”的人性和個(gè)性的小說,被稱作“硬漢派小說”,如歐美流行的那些偵探小說;強(qiáng)調(diào)破案過程的縝密性和邏輯性,是日本偵探小說的特點(diǎn),這些小說又被稱為“本格派”;不注重結(jié)果,而注重過程,尤其是注重犯罪或者辦案過程中的心理描述和刻畫,在日本被稱為“變格派”,在中國(guó)則被稱為“懸疑小說”。世界偵探小說一直在發(fā)展,雖然文體框架處于流動(dòng)中,卻一直保持著“偵探”本色。
本期推出的三篇偵探小說研究,從三個(gè)方面論述了偵探小說的特征和變革。
黃海丹的《西方淵源與學(xué)術(shù)史評(píng)價(jià)——程小青啟智功能論新說》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強(qiáng)調(diào)程小青的啟智觀念和創(chuàng)作觀念的自主性。程小青是中國(guó)古典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的代表作家,受《福爾摩斯探案集》影響很深。但是生在中國(guó)土地上的中國(guó)作家自有其本土性所在,對(duì)程小青創(chuàng)作中的自主性的研究從本質(zhì)上說是對(duì)偵探小說本土性的研究,很值得關(guān)注。
張銳雪的《戲仿的偵探小說與解殖民訴求——論周瘦鵑〈臨城劫車案中之福爾摩斯〉》分析的是一篇被忽視的周瘦鵑的小說,對(duì)周瘦鵑研究來說是一個(gè)補(bǔ)充。同時(shí),這也說明了偵探小說在中國(guó)閱讀市場(chǎng)具有很高的接受度,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已經(jīng)成了中國(guó)家喻戶曉的人物。
高媛的《日常生活謎題的多維建構(gòu)與復(fù)雜拆解——論貝客邦的網(wǎng)絡(luò)長(zhǎng)篇偵探小說》則將偵探小說的研究觸角伸向了當(dāng)代。日常生活謎題、多維建構(gòu)和復(fù)雜拆解是這篇論文的研究視角,也是中國(guó)當(dāng)代懸疑小說的基本特征。
從現(xiàn)代到當(dāng)下,從內(nèi)涵到文體。本期推出的三篇論文基本上反映出中國(guó)百年偵探小說的經(jīng)緯度,擴(kuò)展了偵探小說研究的空間和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