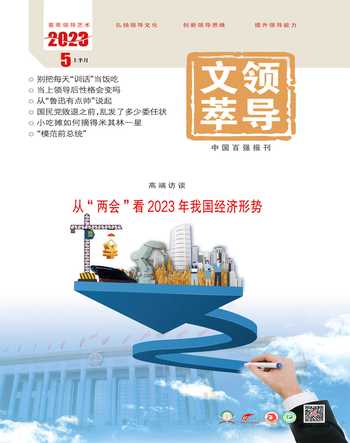在小城市的年輕人絕非“失落群體”
王德福

今年年初,河南鹿邑發生一起因燃放煙花打砸執法警車事件,當地警方已及時發布通報,對8名涉事人員——都是年輕人——以涉嫌尋釁滋事立案偵查。這起事件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有一種聲音認為,年輕人聚集在小城市,是因為疫情影響下大城市生存不易,許多人早早返鄉。然而,小城市撐不起他們的大夢想,巨大落差之下便蓄積一些情緒,借由節慶的狂歡釋放。真是這樣嗎?
“小城市”是一種象征性的統稱。它可以指城市分層體系中,處于四五線及以下的普通地級市和縣城。認識小城市,要注意兩個維度。一是區位的維度。小城市按照區位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城市群和都市圈中的小城市,以及相對獨立發展的普通小城市。第一種類型的小城市深嵌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產業鏈與社會系統中,依附于大城市發展。越是成熟的城市群和輻射能力強的中心城市,越能帶動更多小城市發展,形成功能各異的衛星城。后一種類型的小城市數量更多,廣泛分布于中西部地區。這類小城市產業基礎相對薄弱,發展空間相對有限。
另一個是城鄉關系的維度。要將小城市置于城鄉社會系統的完整譜系中認識,而不能孤立地看。這是由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決定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是漸進式的,它表現為農民在城鄉之間較長時期的往返流動。大城市是發動機,農村是穩定器,小城市是回旋地,構成一個相互協調的城鄉三元社會系統。大城市聚集了最密集的發展機會和最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農村則提供了建立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生存保障和生態人文福利。小城市介于二者之間,恰好提供了相對低成本的、城市化的回旋空間:可以作為進城的首選站,也可以為那些“逃離北上廣”的年輕人提供空間。小城市兼得城鄉兩利,既可以提供一定的發展機會和相對農村更優質、但遜色于大城市的公共服務資源,也可以便利地獲得來自農村父輩緊密的社會支持。“回旋”的意義在于,年輕人可以選擇暫時離開大城市,在小城市里積蓄力量,通過家庭內部的代際接力,實現將來或者下一代更高質量的階層躍升。
對年輕人而言,廣大中西部地區的普通小城市,其主要功能便是為城市化提供穩定的回旋空間。深嵌于城市群和都市圈中的小城市不同,對本地農民來說,它們或許也是城市化的回旋地,但對中西部地區農民來說,它們則同樣是城市化的發動機,是捕捉發展機會、積累經濟資源、實現進城夢的陣地。鹿邑便屬于普通小城市,也是我們應該重點關注的小城市。有些年輕人選擇在普通小城市安家,但仍然到大城市去打拼;有些年輕人則選擇返鄉創業就業。無論是哪種選擇,普通小城市吸引年輕人的最大魅力,是區別于大城市的穩定感。
中老年農民的穩定感來自農村,農村有他們的生存保障,有他們熟悉的生活方式。小城市則可以為年輕人提供穩定感,穩定感來自小城市特有的低成本的城市生活方式,也來自農村父輩的家庭支持。在穩定的基礎上,年輕人可以更從容地安排家庭分工,最大化地積累經濟資源,相對低成本地享受小城市的公共服務資源。
前述那種聲音認為,小城市難以為年輕人提供希望。其實,從為年輕人提供城市化的回旋空間來看,普通小城市特有的穩定感才是其為年輕人提供的最大希望。在這個意義上,普通小城市尤其要注意實施穩健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政策,切忌用激進的房地產和消費刺激政策透支年輕人的家庭儲備,削弱小城市的穩定器功能。
(摘自《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