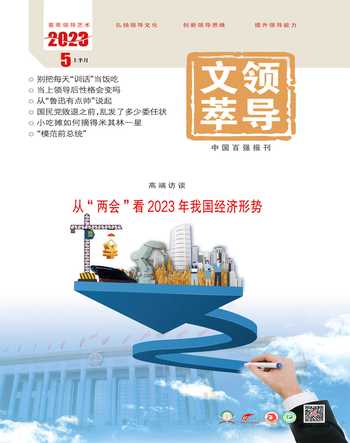庫爾德問題的前世今生
王偉

2022年歲末,土耳其和伊朗分別對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nèi)的庫爾德武裝發(fā)起越境打擊。至此,庫爾德問題這個(gè)困擾中東乃至世界的無解之結(jié),再次進(jìn)入公眾視野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
從人口數(shù)量上看,庫爾德人是排在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后中東地區(qū)的第四大民族。從歷史角度看,這個(gè)民族已在中東地區(qū)活躍了超過2000年。在正常情況下,能順利邁入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民族,都有其值得稱道的歷史,庫爾德人也不例外。從古至今,庫爾德民族的主要活躍地區(qū),都集中于扎格羅斯山脈及其附近區(qū)域,他們最初的生產(chǎn)方式以游牧為主。當(dāng)然,所有生活在山地的族群,都具備一定的共性:封閉且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讓他們更習(xí)慣以部族為單位抱團(tuán)取暖;對外常常表現(xiàn)得好勇斗狠,習(xí)慣于四處游走,實(shí)施劫掠。
正因如此,山地族群對統(tǒng)治者來說,通常意味著不安定和不可控(比如不好收稅)。比如,歷史上的車臣人就是如此。對國王們來說,“脾氣暴躁”又喜歡“到處亂跑”的庫爾德人,同樣不好管束。但他們悍勇的性格,以及沒什么國家觀念的特性,又讓他們成為最佳雇傭軍的人選。歷史上,從阿拉伯帝國、塞爾柱帝國、蒙古帝國,再到奧斯曼帝國,在每次帝國擴(kuò)張的戰(zhàn)爭中,都能找到庫爾德雇傭兵的身影。由此可見,庫爾德人可謂中東地區(qū)超級(jí)資深的“打工人”。
然而,每當(dāng)戰(zhàn)爭結(jié)束、社會(huì)進(jìn)入穩(wěn)定運(yùn)行時(shí),在統(tǒng)治者眼中,庫爾德人又會(huì)從“很好用”切換回“不好管”。當(dāng)然,在中古時(shí)代的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這種“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事情并不稀奇。但到了近代以后,情況開始大為不同。
公元17世紀(jì),惡斗多年的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再次停戰(zhàn),而他們的談判成果之一,就是把庫爾德斯坦地區(qū)一分為二,而庫爾德人對此卻一無所知。此后,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都不約而同地開始整治境內(nèi)的庫爾德部族,不許他們再隨便亂跑,尤其是不能跨越國界。于是,部族反抗與政府清剿的戲碼,便在這片地區(qū)隔三岔五就要上演一次,這種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19世紀(jì)。彼時(shí),庫爾德人中的知識(shí)分子開始從西方世界接觸到“民族”這個(gè)概念。在此之前,人們對利益的認(rèn)同邊界都是止步于部族,至于認(rèn)為其他部族的人,大伙只是碰巧住得比較近,彼此的語言和生活習(xí)慣都差不多,部族間發(fā)生沖突時(shí),他們下手一點(diǎn)不比對外人輕。
隨著“民族”概念的產(chǎn)生,庫爾德人開始意識(shí)到,這些與自己說話、辦事習(xí)慣差不多的鄰居,也算是自己的同族。如今,他們正被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欺負(fù),因而大家有必要抱團(tuán)取暖、一致對外。于是,民族主義就此產(chǎn)生。庫爾德人自此有了一個(gè)明確的目標(biāo)——獨(dú)立建國,不再依附其他國家。
1914年,一戰(zhàn)爆發(fā)。加入同盟國一方的奧斯曼帝國,習(xí)慣性地想要征用庫爾德人。而協(xié)約國一方為了挖奧斯曼帝國的“墻腳”,則給庫爾德人許下承認(rèn)他們獨(dú)立建國的承諾。一戰(zhàn)最終以同盟國一方戰(zhàn)敗而告終,由于“站隊(duì)”失敗,奧斯曼帝國戰(zhàn)后被迫簽署了《色佛爾條約》。在這份條約中,協(xié)約國如約承認(rèn)庫爾德人獨(dú)立,可問題也來了,他們還同時(shí)承認(rèn)了亞美尼亞人獨(dú)立——當(dāng)初他們同樣是協(xié)約國挖下來的“墻腳”。
信仰伊斯蘭教的庫爾德人與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歷來不睦。讓這兩個(gè)互相對立彼此地盤又緊挨著的民族同時(shí)獨(dú)立建國,想不出亂子都難。《色佛爾條約》公布后,庫爾德人認(rèn)為,本應(yīng)屬于自己的領(lǐng)地被協(xié)約國劃給了亞美尼亞人。正當(dāng)庫爾德人憤怒之時(shí),土耳其人也在暴怒中。《色佛爾條約》對奧斯曼帝國的苛刻程度,甚至超過了針對德國的《凡爾賽條約》。1919年,原本已退役的土耳其將軍凱末爾,發(fā)起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運(yùn)動(dòng)。此時(shí)的庫爾德人,再次轉(zhuǎn)投到凱末爾麾下,奮力一搏。
歷經(jīng)兩年多的苦戰(zhàn),凱末爾最終迫使英法兩國重新坐回談判桌,同土耳其簽署了新協(xié)定。事實(shí)上,英法兩國當(dāng)時(shí)正需要專注于應(yīng)對一個(gè)更大的麻煩,即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政權(quán)。為此,他們亟須土耳其這個(gè)俄國傳統(tǒng)宿敵盡快站起來,以制衡蘇俄。于是,雙方一拍即合簽署了《洛桑條約》。新的土耳其以放棄奧斯曼帝國征服的異族土地為條件,換取了完整的安納托利亞高原。
不僅如此,《色佛爾條約》規(guī)定的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的“自治權(quán)”,在新條約中也被取消了。此外,庫爾德人聚居區(qū)被一分為四,最大的部分仍歸屬土耳其,剩下的三部分分別劃歸波斯(伊朗),以及當(dāng)時(shí)的法屬敘利亞和英屬伊拉克。換言之,庫爾德人再次被“雇主”給賣了。然而,已然開啟民族主義模式的庫爾德人,自然不會(huì)就此善罷甘休,于是庫爾德人大起義于1927年爆發(fā)。這場武裝起義,因遭到土耳其、波斯(伊朗)、敘利亞和伊拉克四家的聯(lián)合鎮(zhèn)壓,數(shù)萬最能打的庫爾德人在起義中損失殆盡。中東庫爾德人問題的主基調(diào),由此奠定下來。
二戰(zhàn)原本是近代最后一次地緣格局大洗牌的機(jī)會(huì),但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充分汲取了此前的教訓(xùn),在整個(gè)戰(zhàn)爭期間都恪守中立,直到戰(zhàn)爭末期才加入盟軍陣營對軸心國宣戰(zhàn),這也讓庫爾德人徹底喪失“翻盤”的機(jī)會(huì)。二戰(zhàn)后,中東域外的國家,仍會(huì)時(shí)不時(shí)就看重庫爾德人的“打工人”屬性,許諾幫他們建國,以此將其拉入自己麾下。比如冷戰(zhàn)期間,土耳其和巴列維治下的伊朗都秉承親西方的對外政策。為對沖南部壓力,蘇聯(lián)曾一度支持過庫爾德人建國,結(jié)果導(dǎo)致其遭到土耳其和伊朗的聯(lián)合打擊。冷戰(zhàn)后,因伊拉克戰(zhàn)爭和后續(xù)的反恐戰(zhàn)爭,美國同樣找上這批中東千年“打工人”,其最終結(jié)果正如新聞報(bào)道的那樣——土耳其和伊朗兩國幾乎前后腳,對境外的庫爾德武裝發(fā)動(dòng)軍事打擊。
對此,有評論分析稱,庫爾德人目前的境況,其實(shí)從庫爾德人聚居區(qū)在《洛桑條約》中被一分為四,就已注定了難以逆轉(zhuǎn)。若從宗教劃分來看:土耳其信仰的是伊斯蘭教遜尼派,伊朗是什葉派,伊拉克占主體的是什葉派,目前掌權(quán)的也是什葉派,敘利亞人口主體是遜尼派,不過阿薩德家族屬于什葉派。從對外策略來看:伊朗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不對付,敘利亞與伊朗類似,土耳其憑借得天獨(dú)厚的地緣環(huán)境,實(shí)現(xiàn)了東西通吃,而伊拉克在薩達(dá)姆倒臺(tái)后,與西方國家的關(guān)系要相對親近一些。
顯然,在這種狀態(tài)下,要想讓庫爾德人建國,無論域外國家如何操作,都不免同時(shí)得罪上述四個(gè)國家,這還未考慮庫爾德人內(nèi)部錯(cuò)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所以,就不難理解,無論是哪個(gè)域外大國在畫完餅后,最終都只是口惠而實(shí)不至。因?yàn)閹鞝柕氯霜?dú)立建國這事,壓根就沒可操作性。
若建國沒可能,那消弭矛盾過和平的生活,同樣難以實(shí)現(xiàn)。畢竟,歷史積淀日久的庫爾德問題,所涉及的國家都有各自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從來不缺外部勢力去利用這些情緒。為此,圍繞庫爾德問題,就這樣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土耳其和伊朗近期對庫爾德武裝發(fā)起的越境打擊,在評論家看來,其著眼點(diǎn)其實(shí)與庫爾德人本身沒太大關(guān)系。如前所述,庫爾德人鬧獨(dú)立對土伊兩國來說,是一個(gè)長期性問題,而這兩個(gè)國家眼下都面臨更大的麻煩亟待解決。伊朗因瑪莎·阿米尼去世,導(dǎo)致國內(nèi)局勢動(dòng)蕩。土耳其借助俄烏沖突,大秀了一波存在感,但其國內(nèi)情況其實(shí)并不樂觀。多年來,埃爾多安不斷挑動(dòng)民族主義情緒,其間多次與西方國家交惡,雖借助東西通吃的天然優(yōu)勢,每次都能在外交層面找補(bǔ)回來,但其一系列“神操作”,還是讓國內(nèi)外資本失去了安全感,于是資本紛紛外逃。與此同時(shí),埃爾多安政府在中東地區(qū)到處插手,又進(jìn)一步加劇了財(cái)政負(fù)擔(dān)。自2021年以來,土耳其一直維持著超過80%的高通脹率。
一國法定貨幣的信用,說到底就是這個(gè)政權(quán)的信用,照這樣一路狂奔下去,最終將會(huì)發(fā)生什么,也就不難猜想了。為此,土耳其以伊斯坦布爾爆炸案為由,發(fā)起對庫爾德武裝的越境打擊,從政治角度看,無疑轉(zhuǎn)移了輿論焦點(diǎn),畢竟,這種“軍事行動(dòng)”雖然徹底贏不了,但也絕對輸不了。
而土耳其和伊朗兩國選擇俄烏沖突如火如荼之際,發(fā)起對庫爾德武裝的越境打擊,無疑是掐準(zhǔn)了歐美國家此時(shí)根本無暇顧及中東這一戰(zhàn)略方向。相反,為穩(wěn)住土耳其,歐美甚至還得給出一定的好處。畢竟,庫爾德武裝在給美國“打工”,“打工人”一再挨打,勢必會(huì)影響到“老板”的形象。若歐美國家此時(shí)選擇硬碰硬,強(qiáng)力干預(yù)土耳其行動(dòng),那不亞于再度點(diǎn)燃了土耳其國內(nèi)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分屬不同陣營的伊朗,更得擔(dān)心歐美國家硬剛,果真如此,兩國國內(nèi)的矛盾都將被外部的火藥消弭,這也是庫爾德人再次淪為“工具人”的可悲之處。
(摘自《世界知識(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