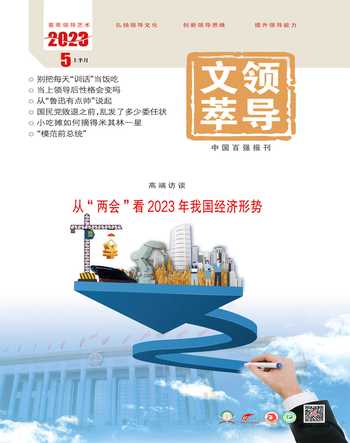蔣百里的“長線思維”:做人還是做事
徐濤
在這個世界上,活法看似千千萬,歸根到底只有兩種:做人和做事。
校園槍聲
1913年6月18日清晨,保定軍校。
一大早,校長蔣百里就召集全體師生訓話。
我初到本校時,曾教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辦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辦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現在看來你們一切都還好,沒有對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卻不能盡校長的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
說完,蔣百里拔槍朝自己的胸口開了一槍。
眾人這才反應過來,大喊:“校長自殺了!”
段祺瑞是跟著袁世凱一起打天下的老部下。袁世凱成了最高領袖后,他再看老部下就有點兒不放心,打算提拔新人制衡段祺瑞。段祺瑞手上有兵,袁世凱就建個軍校培養將軍。而袁世凱看中的校長人選,就是蔣百里。
就這樣,蔣百里走馬上任,成為保定軍校的校長。
蔣百里到任后才發現,情況非常糟糕。炮兵沒炮,騎兵沒馬,操場上的雜草比人的膝蓋還高。學生也無心操練,只知道每日閑逛和出入風月場。
蔣百里決心好好整頓,先從教員開始。大批不干正事兒的被裁撤,換上能干又愿意干的人,軍校氛圍頓時煥然一新。
但是這樣的舉措幾乎得罪了所有人。
這時的保定軍校,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不大的一個機構,竟然還分為北洋武備派、北洋速成派、日本士官派、德國派等。蔣百里為日本士官出身,按說應該屬于日本士官派,但是他對日本那套看不上眼,曾說“日本的教育和軍事,中國最不該學”,此言一出,幾乎把日本士官派得罪光了。
蔣百里更欣賞德國的做法。蔣百里一心想為中國打造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至少要達到德國軍隊的水平。但是他忽略了一個問題。他看到的德國,是“近代化”的德國。而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沒有完全脫離“封建社會”的中國。所有的問題,不可能這么輕易地完成新老劃斷。
報復很快襲來。占比最多的北洋速成派和日本士官派聯合起來,拆蔣百里的臺。凡是軍校需要的物資,能拖就拖,能扣就扣,能挪用就挪用,總之就是什么也不給他。如果換作一個做事的人,會想出許多辦法,比如利益交換,拉一派打一派,或者去找自己的人脈,甚至找袁大總統告狀。但蔣百里不行,因為他是做人的人,讓他做違背其道德觀的事,比殺了他還讓他難受。
于是,就有了前面自殺那一幕。
蔡鍔的遺產
其實,蔣百里是有機會成為有實權的人物,當上一方大員的。
反袁斗爭結束后,蔡鍔被任命為四川督軍兼省長。這是妥妥的封疆大吏。然而正當蔡鍔打算振作有為、造福一方時,他的喉癌卻越來越嚴重。蔡鍔對自己的病情不抱希望,知道自己恐怕挺不過這一關。于是他和蔣百里商量,一旦自己有什么不測,全部基業就托付給蔣百里——不光是四川督軍和省長這兩頂帽子,還有現成的軍隊,兩員心腹大將戴勘和張耀庭也一并托付。在任何時代,這都稱得上一份重托。蔡鍔相信蔣百里的人品,更相信他的能力。他認為,在蔣百里手中,自己這份基業一定可以發揚光大。
蔡鍔東渡日本治病時是1916年9月。從那時起,蔣百里就全程陪護。可惜到了11月,蔡鍔病重不治,一代將星就此隕落。按照約定,此時蔣百里應該立即入川接手四川事務,但是蔣百里始終忙于蔡鍔的后事,根本沒有考慮接班的事。
蔣百里此刻不愿去想什么基業,只想一心陪伴好友走完最后一程。
直到1917年4月12日,蔡鍔的葬禮結束,蔣百里才算放下心中包袱,收拾行囊準備入川。
請注意,這時距離他和蔡鍔約定的入川時間已經過去了5個多月。途經長沙時,他被當地的親朋故友盛情挽留,又多停留了幾天。等他終于過了重慶時,卻被迎面撞來的噩耗擊倒:就在數日前,川軍嘩變。蔡鍔留給他的軍隊被吞并,兩員心腹大將被亂軍殺害。此時的四川,已經是“城頭變換大王旗”。
蔡鍔一生的心血,毀于一旦。
這其實是所有追求做人的人的通病。對他們來說,為人處世,道德優先。事做不成頂多是遺憾,但是“人設崩塌”是絕不能容忍的。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蔣百里身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0年,蔣介石和馮玉祥開啟“中原大戰”。這里面沒什么正義,不過是一場爭霸戰。其中第五軍的指揮官叫唐生智,是蔣百里的學生。蔣介石認為唐生智的指揮水平不行,想讓蔣百里來指揮。在一個“軍隊國家化”的國家里,最高領袖指派軍隊將領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是蔣百里卻推脫說,他不能以老師的身份奪學生的軍隊。
然而,“軍隊國家化”正是蔣百里一向的主張,怎么這會兒軍隊又成了唐生智的了?不知道蔣介石是不是相信蔣百里的說辭,但他最終還是撤銷了委任。蔣百里又失去一次證明自己的機會。
錯過的“五四”
1918年年底,梁啟超和蔣百里按照北京政府的安排,作為“外交二線隊”去歐洲游說。作為“一戰”的戰勝國,中國當然要爭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政府在派出以陸征祥、顧維鈞為代表的一線隊伍的同時,還派出以梁啟超為首的“歐洲考察團”,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工業領域的人才。
然而游說結果很不理想。消息傳回國內,瞬間點燃了中國人民心中的怒火,“五四運動”就此爆發,席卷全國,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此時的梁啟超和蔣百里在做什么呢?他們在歐洲一共游歷了一年零三個月,到1920年才回到國內。
游歷途中,他們特地去看了幾場著名戰役的遺址。到處是斷壁殘垣,滿目瘡痍,墳墓遍地。許多城市的戰爭痕跡還未消去,滿眼都是流離失所的平民和肢體殘缺的退伍軍人。一番反思之后,兩人在回國途中各自開始寫書,把沿途所見寫下來,警醒國民,不要過分崇拜歐洲文明,而是應該吸取歐洲文明的長處,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形成新的文化。
然而當他們回到國內時,卻驚訝地發現國內已經變了天。年輕人心中的領袖已經是更年輕的陳獨秀了,年輕人愛看的讀物也變成了《新青年》。新一代年輕人的思想更激進,態度更堅決。
于是,中國當時的頂尖精英人群分成了兩派,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一邊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一邊以梁啟超為代表。
這次,蔣百里堅決站在梁啟超一邊,也站在了“保守”一邊。蔣百里在梁啟超的陣營中奔走,樂此不疲。一方面是他親眼見過歐洲的慘烈,另一方面卻是因為他和梁啟超的關系非同一般。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密切追隨梁啟超也導致他屢屢錯過與時代同步的機會。從那之后,蔣百里徹底成了一個無黨派人士。他在各種勢力中穿梭,卻沒人把他當作自己人。
蔣百里無疑是個天才,但他卻一生沒有足以匹配才華的建樹。這是他本人的悲劇,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蔣百里的人生,那就是撕扯。既想做人,又想做事。既想按照新時代的方式做事,又想按照舊道德做人。如此度過一生,也算一種境界。不過,真正讓他留名青史的,其實是他的各種思想。
(摘自《歷史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