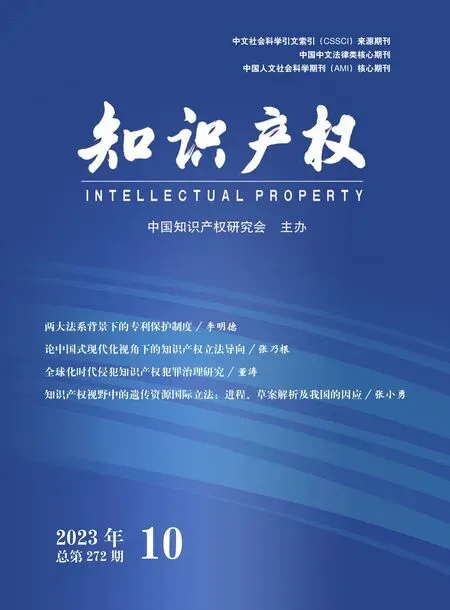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治理研究
董 濤
內(nèi)容提要: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呈現(xiàn)智能化、虛擬化、有組織化的特點,成為聯(lián)合國規(guī)定的17類跨國犯罪中最為嚴(yán)重的犯罪之一。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新態(tài)勢、新特征對追訴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證據(jù)的收集、檢控、審判等活動提出新要求,對傳統(tǒng)國內(nèi)刑法體系和國際刑法規(guī)則帶來新挑戰(zhàn)。目前大多數(shù)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相關(guān)的國際條約都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進行了規(guī)定,但規(guī)定得比較簡略,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中的重大問題和關(guān)鍵問題還存在較大分歧。為了更好地打擊全球化時代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我國應(yīng)積極推動并深度參與跨境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司法合作,完善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調(diào)整優(yōu)化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司法體制機制,以提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打擊能力,推動全球知識產(chǎn)權(quán)治理格局良性發(fā)展,促進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與科技關(guān)系的深入合作。
一、問題的提出
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是指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情節(jié)嚴(yán)重被納入刑法予以懲處的行為。隨著新技術(shù)經(jīng)濟的興起,知識財產(chǎn)不僅成為市場主體最重要的資產(chǎn),也是一國戰(zhàn)略發(fā)展的未來所在。刑法作為財產(chǎn)權(quán)的保障法,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人將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民事賠償作為日常經(jīng)營成本的時候,民事措施難以起到救濟作用,此時,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刑法保護顯得更為重要。①See J.Derek Mason,et al.,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 Federal Protection for Corporate Trade Secrets,16 Computer Law 14,15 (1999).國際犯罪學(xué)家赫爾哈特·米勒教授指出,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已經(jīng)成為聯(lián)合國規(guī)定的17類跨國犯罪中最嚴(yán)重的犯罪之一。②轉(zhuǎn)引自孫萬懷:《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刑事責(zé)任基礎(chǔ)構(gòu)造比較》,載《華東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1999年第2期,第73頁。目前,有關(guān)組織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列為跨國(境)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③楊燮蛟、陳南成:《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學(xué)的建構(gòu)及其應(yīng)用》,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206頁。在全球化、網(wǎng)絡(luò)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趨勢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在犯罪類型、行為方式、犯罪結(jié)構(gòu)、組織形式等方面都呈現(xiàn)出新的態(tài)勢,對傳統(tǒng)國內(nèi)刑法體系和國際刑法規(guī)則都帶來挑戰(zhàn)。
其一,隨著網(wǎng)絡(luò)化、數(shù)字化時代的到來,人類提取、生成、存儲和處理文化元素的能力大幅提升,出現(xiàn)了眾多新的智力成果創(chuàng)作范式,如智能化設(shè)計、計算機輔助發(fā)明、數(shù)字化創(chuàng)作等。相應(yīng)地,也出現(xiàn)了利用機器、軟件等進行剪切、拼湊等知識產(chǎn)權(quán)新型侵害形式。④董濤:《知識產(chǎn)權(quán)數(shù)據(jù)治理研究》,載《管理世界》2022年第4期,第111-112頁。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越來越智能化、虛擬化,給追訴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證據(jù)收集、檢控、審判等活動帶來巨大的挑戰(zhàn)。
其二,隨著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與通信物流的發(fā)展,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開始呈現(xiàn)出規(guī)模化、體系化、有組織化的特點,跨境趨勢明顯,并常伴有洗錢等犯罪行為。⑤Micka?l R.Roudaut,From Sweatshops to Organized Crime: The New Face of Counterfeiting,in Christophe Geiger ed.,Criminal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2,p.75.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作為法定犯,各國間缺乏統(tǒng)一的道德認(rèn)同感,不同國家對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規(guī)定差異較大,對跨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司法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三,盡管目前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相關(guān)的國際條約較多,并且大多數(shù)都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進行了規(guī)定,不過規(guī)定得比較簡略。同時,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中的重大問題和關(guān)鍵問題,還存在較大分歧。這些都使得國際條約中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條款的談判進程相對緩慢,給國際范圍內(nèi)統(tǒng)一和協(xié)調(diào)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帶來巨大挑戰(zhàn)。
其四,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國際地位上升,中國需要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以在構(gòu)建良好的國際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方面承擔(dān)更大的國際責(zé)任。盡管在2007年美國向世界貿(mào)易組織(以下簡稱WTO)訴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爭端及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jīng)濟貿(mào)易協(xié)議》(以下簡稱《中美第一階段經(jīng)貿(mào)協(xié)議》)簽訂后,中國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法保護的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進行了完善,不過,這種更高的國際責(zé)任對我國進一步完善國內(nèi)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法律法規(guī),以及有效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司法執(zhí)法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通過梳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發(fā)展歷史,觀察在全球化、網(wǎng)絡(luò)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新特征與新態(tài)勢,分析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面臨的問題與挑戰(zhàn),提出新形勢下完善我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制度的建議,以期為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建設(shè)提供良好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秩序與規(guī)范環(huán)境。
二、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發(fā)展態(tài)勢
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發(fā)展幾乎相伴相生。近年來,隨著經(jīng)濟轉(zhuǎn)型,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現(xiàn)象越來越多,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的刑事打擊也成為刑法中的活躍領(lǐng)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表現(xiàn)出更多新的特征和新的樣態(tài)。
(一)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發(fā)展簡史
早期知識產(chǎn)權(quán)作為君敕特權(quán)的一種,體現(xiàn)的是皇權(quán)威儀,受到侵害后常以監(jiān)禁等重刑予以保護。如法國1682年國務(wù)委員會(Conseil d'état)令就對侵害者處以身體刑。1686年法令第65條對這一身體刑進行了限制,規(guī)定僅對慣犯(recidivists)適用。1723年印刷商法令將第65條改為第109條,規(guī)定除身體刑仍適用于慣犯外,還可處以罰金、停止?fàn)I業(yè)、禁止執(zhí)業(yè)等處罰。⑥D(zhuǎn)avid Lefranc,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Criminal Enforcement,in Christophe Geiger ed.,Criminal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2,p.103-104.早期英國圖書出版和專利常與壟斷(monopoly)相聯(lián)系,具有貶義色彩,被認(rèn)為是引發(fā)內(nèi)戰(zhàn)的主因。⑦Christine Macleod,Inven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nglish Patent System, 1660-18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6.因此,盜版者常將自己的行為描繪成為自由生計與大眾利益反抗書商行會封建特權(quán)的義舉。⑧Carla Hesse,The R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700 B.C. - A.D. 2000: An Idea in the Balance,131 Daedalus 26 (2002).隨著知識產(chǎn)權(quán)轉(zhuǎn)向洛克的勞動財產(chǎn)理論、黑格爾的人格理論中尋求依據(jù),⑨Justin Hughes,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77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87,331-339 (1988).盜版開始與剽竊(plagiarism)、偷盜(theft)等術(shù)語勾連在一起,失去了正當(dāng)性⑩盜版不再被認(rèn)為是反抗封建特權(quán)的俠盜義舉,而是竊取他人財產(chǎn)的犯罪行為。See Stuart P.Green,Plagiarism, Norms,and the Limits of Theft Law: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Criminal Sanctions in Enfor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54 Hastings Law Journal 167,208 (2002-2003).。文學(xué)盜版甚至被譴責(zé)為“民族罪孽”。?See Henry Van Dyke, The National Sin of Literary Piracy: A Sermon,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8.英國侵犯著作權(quán)犯罪的罪名較多,適用監(jiān)禁與罰金兩種刑罰,但處刑都較輕。英國早期并未將侵犯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1994年商標(biāo)法進行了重大變革,增加了侵犯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罪的規(guī)定。英國與專利有關(guān)的刑事規(guī)范主要在附屬刑法中,有偽造登記與假冒專利等罪名,但未將侵犯專利權(quán)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不過,英國2014年對《注冊外觀設(shè)計法》進行了修改,將未經(jīng)許可實施外觀設(shè)計專利行為“入刑”。
目前,美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規(guī)定在《美國法典》第17章、第18章、第35章等章節(jié)及《美國量刑指南》(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Guidelines Manual)當(dāng)中,處罰嚴(yán)苛且全面。早在1897年美國版權(quán)法修改令就將對戲劇與音樂作品的侵權(quán)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處以最高1年監(jiān)禁。1909年修訂版權(quán)法將犯罪對象的范圍擴大到了幾乎所有版權(quán)作品。不過,在接下來近一個半世紀(jì)時間里,版權(quán)侵害被視為輕罪(misdemeanor)而非重罪(felony),并要求具有侵害故意和商業(yè)目的。1997年《禁止電子盜竊法》(NET)取消了對商業(yè)目的的要求,1998年《數(shù)字千年版權(quán)法》(DMCA)則將版權(quán)侵害前的行為(技術(shù)措施)納入刑事調(diào)整范圍。?Geraldine Szott Moohr,The Crim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 Inquiry Based on Morality, Harm, and Criminal Theory,83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31,735-738 (2003).美國1946年《商標(biāo)法》(蘭哈姆法)沒有刑法保護條款,1984年的《反假冒標(biāo)識法令》(18 U.S.C.§2320)首次將偽造商業(yè)標(biāo)識行為認(rèn)定為聯(lián)邦犯罪,2006年《制止商品假冒法》提高了侵犯商標(biāo)權(quán)罪的處罰標(biāo)準(zhǔn)。美國關(guān)于專利的犯罪主要規(guī)定在偽造、變造專利證書(18 U.S.C.§497)及虛假標(biāo)記(35 U.S.C.§292)當(dāng)中。美國對商業(yè)秘密保護較早,最初通過判例法實現(xiàn)。1979年《統(tǒng)一商業(yè)秘密法》沒有規(guī)定刑事責(zé)任。20世紀(jì)中期《國家財產(chǎn)盜竊法》(NSPA)將商業(yè)秘密視為商品或財物進行擴張解釋,對商業(yè)秘密盜竊行為進行刑罰處罰。美國1996年頒布了《經(jīng)濟間諜法》(EEA),對侵害商業(yè)秘密的行為予以嚴(yán)厲的刑事打擊。?See 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 (4th Edition),Offices of Legal Education Executive Office for United States Attorneys,2013.
德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囊括了各種主要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類型,其比較突出的特點就是將專利侵權(quán)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德國2017年修訂后的《專利法》第42條規(guī)定了侵害專利權(quán)須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的幾種情形。?Patent Act as published on 16 December 1980 as last amended by Article 4 of the Act of 8 October 2017 (Federal Law Gazette I,p.3546).其他一些歐洲大陸法系國家,如奧地利《專利法》第147—149條、丹麥《專利法》第57條、西班牙《刑法典》第273條、意大利《刑法典》第473—475條等,都對專利侵權(quán)行為予以刑事制裁。歐盟2004年發(fā)布了關(guān)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的2004/48/EC號指令。該指令在起草過程中,曾包含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制裁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不過,這些規(guī)定引發(fā)了學(xué)界、產(chǎn)業(yè)界的廣泛爭議。因此在頒發(fā)時,歐洲議會刪去了有關(guān)刑事制裁的內(nèi)容。這反映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問題的復(fù)雜性以及刑事制裁在主權(quán)問題方面的敏感性。
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為的犯罪化在國際條約中也經(jīng)歷了逐漸發(fā)展的歷程。《保護工業(yè)產(chǎn)權(quán)巴黎公約》(以下簡稱《巴黎公約》)和《保護文學(xué)和藝術(shù)作品伯爾尼公約》(以下簡稱《伯爾尼公約》)都沒有刑事制裁的規(guī)定,不過這兩個條約都要求成員采用適當(dāng)?shù)拇胧┙骨趾χR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刑法措施當(dāng)然包含在內(nèi)。1971年《保護錄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經(jīng)許可復(fù)制其錄音制品公約》第3條開始明確規(guī)定成員可以采用刑事措施進行保護。1995年《與貿(mào)易有關(guān)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協(xié)定》(以下簡稱《TRIPS協(xié)定》)是首個對成員知識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機制進行全面規(guī)定的多邊條約。《TRIPS協(xié)定》第61條對刑事程序進行了規(guī)定,作為民事和行政救濟措施的補充與保障。2008年以來,美國、日本和歐盟等秘密磋商了《反假冒貿(mào)易協(xié)定》(以下簡稱ACTA)。該協(xié)定重點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措施進行規(guī)定,大幅提升了對跨國假冒、盜版等活動的刑事打擊力度。不過由于美國的退出,該協(xié)定擱淺。《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以下簡稱TPP)第18.77條全面而詳盡地規(guī)定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執(zhí)法措施。《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以下簡稱CPTPP)為更快達成協(xié)定,采用擱置的辦法,對TPP中爭議較大的條文暫緩適用,但刑事執(zhí)法條款并未包含在內(nèi)。此外,在其他多邊或雙邊協(xié)議中,尤其是美國簽署的,幾乎都有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規(guī)定,并力圖擴展適用于數(shù)字環(huán)境中。
(二)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新特征
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新技術(shù)、新經(jīng)濟的發(fā)展,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作為一種典型的法定犯,表現(xiàn)出諸多新特征。概括起來,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智能化、虛擬化,犯罪形式隱蔽復(fù)雜
全球化時代,隨著網(wǎng)絡(luò)與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手段已經(jīng)不再是簡單的貼牌冒牌、制假售假等,而是更多地使用高技術(shù)設(shè)備,具有非接觸式、智能化等特征。犯罪行為人使用計算機、激光等精密儀器來造假制假,并生產(chǎn)防偽標(biāo)識粘貼于假冒產(chǎn)品之上,足以以假亂真。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開始向?qū)I(yè)精深、科技含量高的犯罪形態(tài)發(fā)展,絕大多數(shù)犯罪分子都具有較高的專業(yè)水平和豐富的科技知識。今天,越來越多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行為使用網(wǎng)絡(luò)媒介來實施,犯罪場景也開始整體遷移到網(wǎng)絡(luò)平臺之上(online migration),變得虛擬化。?UKIPO,2020-2021 IP Crime and Enforcement Report,p.22,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17790/ip-crime-2021.pdf.犯罪行為人常用非法入侵網(wǎng)站竊取瀏覽記錄,利用網(wǎng)絡(luò)跟蹤軟件獲取他人信息,非法復(fù)制、下載影視和游戲作品并進行跨境傳送,假冒他人域名進行非法鏈接,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洗稿等新形式來實施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行為。
在虛擬的網(wǎng)絡(luò)空間中,主體的匿名性與分散性使得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分子的身份難以被準(zhǔn)確確認(rèn)。犯罪場景變成實體與數(shù)據(jù)并存的二元空間,犯罪分子常常采用線上線下相交互的辦法,將犯罪活動拆分為若干環(huán)節(jié),分區(qū)域生產(chǎn)、加工和組裝,實現(xiàn)制假和售假過程的分離。歐洲刑事警察組織(EUROPOL)發(fā)布的報告顯示,近幾年歐洲的制假販假活動非常猖獗,對歐洲社會生活與經(jīng)濟發(fā)展造成了嚴(yán)重威脅。這些假冒商品主要通過在線網(wǎng)絡(luò)平臺、社交媒體、商業(yè)網(wǎng)站進行分銷。假冒者將半成品在不同地方生產(chǎn),然后通過合法渠道進口到歐洲進行組裝。借助網(wǎng)絡(luò)媒介,侵害行為與侵害后果分離,時空跨度較大,短時間難以感知,這些特征使得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形式具有更強的隱蔽性和復(fù)雜性,從而導(dǎo)致侵權(quán)產(chǎn)品難以被海關(guān)發(fā)現(xiàn),增加了案件的偵查難度。?EUROPOL,European Union Serious and Organised Crime Threat Assessment, A Corrupting Influence: The Infiltration and Undermining of Europe's Economy and Society by Organised Crime,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21,p.78.
2.跨境化、集團化,與有組織犯罪勾連
在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表現(xiàn)為產(chǎn)業(yè)化、鏈條式、集團化運作,并經(jīng)常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犯罪主體借助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進行線上宣傳,通過現(xiàn)代物流技術(shù)進行線下分銷,組織性強,形成等級分明、協(xié)作配合、分工有序的生產(chǎn)和銷售框架。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還因低風(fēng)險、高回報的性質(zhì),常與黑幫團伙式的(Mafia-style)有組織犯罪網(wǎng)絡(luò)勾連在一起,被聯(lián)合國預(yù)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員會稱為世界范圍內(nèi)僅次于販毒的第二大犯罪資金來源。?UKIPO,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nter-Infringement Strategy 2022 to 2027,2022,p.12,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p-counter-infringement-strategy-2022-to-2027.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2021年發(fā)布的全球假冒貨物報告指出:2013年假冒貨物占全球貿(mào)易的2.5%,總值約4610億美元;2016年,假冒貨物占全球貿(mào)易的3.3%,總值約5090億美元;2019年,假冒貨物占全球貿(mào)易的2.5%,總值約4640億美元。?OECD,Global Trade in Fakes: A Worrying Threat,2021,p.9,https://www.oecd.org/publications/global-trade-in-fakes-74c81154-en.htm.歐盟知識產(chǎn)權(quán)局(EUIPO)與歐洲刑事警察組織聯(lián)合發(fā)布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威脅評估報告2022》指出,歐洲不少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活動中獲得的巨額利潤,常與洗錢等犯罪活動相結(jié)合。?EUIPO &EUROPOL,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 Threat Assessment 2022,2022,p.34-35,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2022_IP_Crime_Threat_Assessment/IP_Crime_Threat_Assessment_2022_ExSum_en.pdf.
不少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團伙常常通過遙控指揮、分工生產(chǎn)、線上線下單線對接、真假信息混合披露等方式,構(gòu)建產(chǎn)業(yè)上下游分工明確的供銷一體化犯罪團伙。團伙內(nèi)部有嚴(yán)密的分工,聘請大量不同類型的技術(shù)專家,有的負(fù)責(zé)市場監(jiān)測,有的負(fù)責(zé)網(wǎng)絡(luò)通信、圖紙設(shè)計、化工配方,有的負(fù)責(zé)電子支付與洗錢渠道,在區(qū)域之內(nèi)或之外組織生產(chǎn)、組裝、轉(zhuǎn)運和銷售假冒產(chǎn)品(包括假冒藥品)。聯(lián)合國區(qū)域間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在其發(fā)布的《假冒:全球性威脅》研究報告中指出,盡管不能將所有的假冒盜版活動都?xì)w結(jié)于有組織的犯罪集團,但是無疑,在各個層面上,國際流動的假冒盜版商品很大一部分是由有組織犯罪集團掌控的。假冒盜版與有組織犯罪活動之間的聯(lián)系是廣泛存在的、清晰的。?UNICRI,Counterfeiting, A Global Spread, A Global Threat,2008,p.5,https://unicri.it/counterfeiting-global-spread-globalthreat.因此,國際刑事警察組織(INTERPOL)也將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執(zhí)法作為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重點之一。?Mobilizing Global Action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INTERPOL (12 October 2021),https://www.interpol.int/en/News-and-Events/News/2021/Mobilizing-global-action-against-intellectual-property-crime.此外,根據(jù)蘭德公司(RAND)對盜版、有組織犯罪與恐怖主義活動之間關(guān)系的研究,發(fā)現(xiàn)很多時候知識產(chǎn)權(quán)有組織犯罪中所獲得的巨額收益,還被用于資助恐怖主義等犯罪活動。?Gregory F.Treverton,Carl F.Matthies,Karla J.Cunningham,et al.,Film Piracy,Organized Crime, and Terrorism,The RAND Corporation,2009,p.xii.
3.工具化、政治化,重刑傾向逐漸加劇
隨著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跨國化、產(chǎn)業(yè)化與有組織化,各國加大了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打擊力度。美國國會通過的《1992年版權(quán)重罪法案》(Copyright Felony Act of 1992)規(guī)定,根據(jù)侵害情節(jié)嚴(yán)重性,版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不再只是輕罪,也有可能構(gòu)成重罪。?"Infringement of a copyrighted work may now constitute a felony under federal law,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infringing copies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in a 180-day period,and their retail value." See the Copyright Felony Act of 1992,Pub.L.No.102-561,106 Stat.4233 (1992).美國1996年《經(jīng)濟間諜法》(EEA)將對第二類犯罪(侵奪商業(yè)秘密罪)的最高處刑提高到10年監(jiān)禁,將對第一類犯罪(經(jīng)濟間諜罪)的最高處刑提高到15年監(jiān)禁,且可并處50萬美元的罰金。1997年《禁止電子盜竊法》(NET)也提高了監(jiān)禁刑的懲罰力度與相應(yīng)的犯罪情節(jié)要求。1998年《數(shù)字千年版權(quán)法》(DMCA)將刑事責(zé)任的適用范圍擴大到版權(quán)侵害行為(技術(shù)措施),并大幅提高了監(jiān)禁刑的刑期。其他如德國、法國、日本、韓國也都加大了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刑事處罰力度。中國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不僅新增了“商業(yè)間諜罪”的罪名,而且提高了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各個罪名的法定刑。可以看出,國際范圍內(nèi)出現(xiàn)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重刑化趨向。
隨著貿(mào)易保護主義重新泛起,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開始被強勢國家用來打擊假想競爭對手,制造貿(mào)易摩擦。美國分別于2018年、2019年發(fā)布“一般301調(diào)查”及“特別301調(diào)查”報告,無端指責(zé)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不力,對中國信息通信產(chǎn)業(yè)等出口商品征收高關(guān)稅,激起貿(mào)易摩擦。?參見曹新明、咸成旭:《中美貿(mào)易戰(zhàn)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沖突與應(yīng)對》,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0年第9期,第21-30頁。2018年底,美國司法部(以下簡稱DOJ)啟動了針對中國個人和實體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和商業(yè)秘密行為的刑事專項調(diào)查——所謂的“中國行動計劃”,以制裁其所認(rèn)為的“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行為。根據(jù)該計劃,DOJ對中國企業(yè)及所謂的“商業(yè)間諜行為”展開重點執(zhí)法及調(diào)查活動,包括中國的“商業(yè)間諜”“網(wǎng)絡(luò)間諜”及美國高科技產(chǎn)業(yè)受到中國投資并購、供應(yīng)鏈安全和“非注冊代理人”的威脅等。DOJ調(diào)查的案件主要涉及其認(rèn)為的中國軍人隱瞞身份在美國大學(xué)做訪問學(xué)者、中國黑客竊取美國數(shù)據(jù)隱私、中國竊取美國公司商業(yè)和技術(shù)秘密等。?張夢旭、張旺、李司坤:《美司法部“中國行動”來勢洶洶》,載《環(huán)球時報》2020年7月29日,第007版。僅2018年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以下簡稱FBI)就發(fā)動了10多起針對中國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案件,影響較大的有“華銳風(fēng)電案”(Sinovel Wind Group)、“美國訴張案”(United Statesv.Zhang)等。?USDOJ, PRO IP Act Annual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FY 2018,p.17,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ccips/page/file/1164876/download.美國還屢屢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濫施域外管轄,影響最大的當(dāng)屬“孟晚舟事件”。這表明,為維護強勢國家的技術(shù)霸權(quán)地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開始從法律手段演變?yōu)檎喂ぞ摺?/p>
(三)中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歷史考察
我國有關(guān)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規(guī)定出現(xiàn)較晚。改革開放以來,經(jīng)濟全球化帶動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全球化。中國順應(yīng)了這一潮流,擴大與加強了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范圍與力度。概括而言,中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大體經(jīng)歷了初步建設(shè)、體系化完善與進一步強化三個階段。
1.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初步建設(shè)階段
中國1979年《刑法》中就有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不過僅限于懲治侵犯注冊商標(biāo)權(quán)的犯罪。?1979年《刑法》第127條規(guī)定:“違反商標(biāo)管理法規(guī),工商企業(yè)假冒其他企業(yè)已經(jīng)注冊的商標(biāo)的,對直接責(zé)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1982年《商標(biāo)法》及其實施細(xì)則明確工商企業(yè)假冒他人注冊商標(biāo)的行為為犯罪。?1982年《商標(biāo)法》第40條規(guī)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biāo),包括擅自制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biāo)標(biāo)識的,除賠償被侵權(quán)人的損失,可以并處罰款外,對直接責(zé)任人員由司法機關(guān)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別于1985年與1988年作出批復(fù),將假冒商標(biāo)罪主體資格擴大到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和個人工商業(yè)者。?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個人非法制造、銷售他人注冊商標(biāo)標(biāo)識而構(gòu)成犯罪的能否按假冒商標(biāo)罪懲處的批復(fù)》,1985年10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假冒商標(biāo)案件兩個問題的批復(fù)》,法(研)復(fù)〔1988〕73號,1988年2月26日。1993年我國《商標(biāo)法》第一次修改,將侵犯注冊商標(biāo)權(quán)罪的行為擴展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biāo),偽造、擅自制造或銷售偽造、擅自制造的注冊商標(biāo)標(biāo)識,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biāo)的商品三種情形。?1993年《商標(biāo)法》第40條規(guī)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biāo),構(gòu)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quán)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偽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冊商標(biāo)標(biāo)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制造的注冊商標(biāo)標(biāo)識,構(gòu)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quán)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biāo)的商品,構(gòu)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quán)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同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關(guān)于懲治假冒注冊商標(biāo)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70號),擴大了侵犯注冊商標(biāo)權(quán)犯罪的打擊對象,提高了對侵犯注冊商標(biāo)權(quán)犯罪的懲處力度。1984年《專利法》第63條規(guī)定,假冒他人專利侵權(quán)行為情節(jié)嚴(yán)重的,對其直接責(zé)任人比照假冒商標(biāo)罪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zé)任。?1984年《專利法》第63條規(guī)定:“假冒他人專利的,依照本法第六十條的規(guī)定處理;情節(jié)嚴(yán)重的,對直接責(zé)任人員比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zé)任。”由于使用的是比照(類推)的方法,在適用中存在諸多困惑。為此,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開展專利審判工作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對該規(guī)定的具體適用進行了細(xì)致解釋。
我國1990年《著作權(quán)法》并未規(guī)定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的刑事責(zé)任。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關(guān)于懲治侵犯著作權(quán)的犯罪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30號),成為新中國第一部規(guī)定侵犯著作權(quán)罪的單行刑事法律。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關(guān)于懲治侵犯著作權(quán)的犯罪的決定〉若干問題的解釋》(法發(fā)〔1995〕1號)確立了定罪量刑的標(biāo)準(zhǔn)。我國1979年《刑法》中沒有侵犯商業(yè)秘密罪的規(guī)定,對商業(yè)秘密的保護主要是民事法律。不過,1979年《刑法》對涉及國家經(jīng)濟建設(shè)、科技發(fā)展的重要技術(shù)作為國家秘密予以保護。?1979年《刑法》第187條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由于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關(guān)于懲治泄露國家秘密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7號)規(guī)定:“為境外的機構(gòu)、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quán)利;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剝奪政治權(quán)利。”1994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科學(xué)技術(shù)委員會關(guān)于辦理科技活動中經(jīng)濟犯罪案件的意見》(高檢會〔1994〕26號)規(guī)定,對非法竊取技術(shù)秘密情節(jié)嚴(yán)重的,以盜竊罪追究刑事責(zé)任。同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進一步加強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的通知》(法〔1994〕111號)規(guī)定,對盜竊重要技術(shù)成果的應(yīng)以盜竊罪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總體而言,我國早期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規(guī)范比較分散。
2.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體系化完善階段
我國1997年修訂的《刑法》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作為一個獨立的犯罪類別進行規(guī)范,使得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規(guī)定從附屬刑法與單行刑法向刑法的體系化轉(zhuǎn)變。1997年《刑法》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納入第二編“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罪”部分,設(shè)專節(jié)共八條七種罪名。《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guī)定》(法釋〔1997〕9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4〕19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7〕6號)具體規(guī)定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不同罪名的適用條件,從而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規(guī)范體系。
1997年《刑法》侵犯注冊商標(biāo)權(quán)罪的規(guī)定與《商標(biāo)法》第40條基本相同,包含假冒注冊商標(biāo)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biāo)的商品罪與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biāo)標(biāo)識罪三種情形。1997年《刑法》第216條將假冒專利罪單設(shè)一條進行處罰。不過《刑法》對假冒專利罪的描述是簡單罪狀而非述明罪狀,且無相應(yīng)的司法解釋,因此在認(rèn)定時需依《專利法》及其實施細(xì)則判定。我國《專利法》2000年修改時,將假冒專利擴展為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和冒充專利行為兩種情形。1997年《刑法》吸收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關(guān)于懲治侵犯著作權(quán)的犯罪的決定》第1條、第2條的規(guī)定,規(guī)定了侵犯著作權(quán)罪和銷售侵權(quán)復(fù)制品罪兩個侵犯著作權(quán)犯罪的罪名。2001年《著作權(quán)法》第47條規(guī)定“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首次在著作權(quán)法中納入刑事責(zé)任規(guī)定。1997年《刑法》第219條增設(shè)了侵犯商業(yè)秘密罪,對侵犯商業(yè)秘密罪的構(gòu)成要件進行了規(guī)定。這在我國侵犯商業(yè)秘密罪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3.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進一步強化階段
2007年,中美就知識產(chǎn)權(quán)等問題啟動WTO爭端解決機制,就中國是否存在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力度不夠、相關(guān)刑罰門檻過高等問題進行磋商。隨后,中國修改了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相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進一步強化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規(guī)范力度。2008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公安機關(guān)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一)》(公通字〔2008〕36號)細(xì)化了侵犯著作權(quán)罪的追訴標(biāo)準(zhǔn)。同年,《專利法》及其實施細(xì)則進行了第三次修改,刪除了假冒他人專利行為中的“他人”兩字,將假冒他人專利罪改變?yōu)榧倜皩@铩?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lián)合印發(fā)《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fā)〔2011〕3號),細(xì)化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案件的管轄、證據(jù)收集與效力、定罪量刑等方面的規(guī)定,明確了部分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的問題。
2018年,中美因知識產(chǎn)權(quán)等問題發(fā)生貿(mào)易摩擦,并在WTO展開新一輪磋商。中美于2020年1月達成《中美第一階段經(jīng)貿(mào)協(xié)議》。該協(xié)議強調(diào)了對商業(yè)秘密的保護,其中第1.7條、第1.8條就兩國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啟動刑事執(zhí)法的門檻、刑事程序和處罰等方面的立法標(biāo)準(zhǔn)進行了規(guī)定。2020年9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法釋〔2020〕10號),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中具體法律適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規(guī)定。從2019年起,我國著作權(quán)法、專利法、商標(biāo)法進行了新一輪修訂,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律法規(guī)體系進一步完善。為進一步強化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也為了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立法最新動向相一致,2020年12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6個條文進行修改,新增“商業(yè)間諜罪”,并提高法定刑。?張建、俞小海:《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最新刑法修正的基本類型與司法適用》,載《上海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法治論叢)》2021年第5期,第38頁。202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公布,力圖對之前的3個司法解釋進行整合,細(xì)化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中的法律適用規(guī)則。
三、全球化時代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面臨的問題與挑戰(zhàn)
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所具有的新特征給法律制度帶來了諸多新的問題與挑戰(zhàn)。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新發(fā)展對刑事執(zhí)法能力的挑戰(zhàn)
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新特征對刑事執(zhí)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戰(zhàn),主要體現(xiàn)在偵查機關(guān)的刑事偵查能力、協(xié)調(diào)能力及應(yīng)對刑事執(zhí)法權(quán)競爭的能力三個方面。
1.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新特征對刑事偵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的判定涉及“抽象-過濾-比對”的復(fù)雜過程,在侵害行為的發(fā)現(xiàn)、性質(zhì)辨析、責(zé)任構(gòu)成及后果認(rèn)定等方面都需要較高的專業(yè)素養(yǎng),這對刑事偵查人員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主體常運用高新技術(shù)與工具,將侵害環(huán)節(jié)精細(xì)分工,通過貨標(biāo)分離,異地貼標(biāo)、組裝、儲存,拆分發(fā)貨,真假混售,摻雜刷單等方式逃避監(jiān)管,各個環(huán)節(jié)分工協(xié)作,共同完成從準(zhǔn)備、組織、實施到銷贓分贓的整個犯罪過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行為與現(xiàn)代通信物流技術(shù)相結(jié)合,使犯罪特征趨向于非接觸式,跨區(qū)、跨境及多層次專業(yè)化下的鏈條狀模式,取證數(shù)量巨大、取證類型多樣,需具備針對性的專業(yè)素質(zhì)與技術(shù),這些都增大了刑事偵查工作的難度。?參見任惠華、李晨陽:《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偵查策略體系構(gòu)建》,載《山東警察學(xué)院學(xué)報》2021年第1期,第60頁。
隨著新信息技術(shù)、新傳播媒介及互聯(lián)網(wǎng)的快速發(fā)展,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開始向網(wǎng)絡(luò)空間遷徙,犯罪行為人利用代理服務(wù)、虛擬專用網(wǎng)絡(luò)(VP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加密等方式隱蔽身份,進一步增加了偵查難度。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電子證據(jù)取證與運用難
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具有信息屬性,無論是影視圖像、版權(quán)作品、商業(yè)標(biāo)識、計算機軟件、專利技術(shù)方案,都天然適宜于用數(shù)據(jù)來表征。因此,當(dāng)前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活動多以電子數(shù)據(jù)為依托并在網(wǎng)絡(luò)空間流轉(zhuǎn)。但是,電子數(shù)據(jù)難以被封存、扣押,數(shù)據(jù)量大,收集和分析任務(wù)艱巨。同時,電子證據(jù)容易被更新、修改或清除,其真實性、完整性成為問題,容易出現(xiàn)證據(jù)鏈條不全、證明力弱等問題。?[英]克里斯托弗·米勒德編著:《云計算法律》,陳媛媛譯,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18-422頁。刑事偵查人員需具備較高的網(wǎng)絡(luò)犯罪電子證據(jù)取證能力,構(gòu)建法律素養(yǎng)和技術(shù)知識兼?zhèn)涞膶I(yè)團隊。
(2)跨境取證與合作難
目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產(chǎn)業(yè)化、鏈條化及網(wǎng)絡(luò)化特征突出,經(jīng)常跨地區(qū)、跨國境調(diào)配資源實施犯罪,諸多關(guān)鍵證據(jù)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跨國和跨境取證主要通過司法協(xié)助和警務(wù)合作等渠道,但由于各國法律制度不同,導(dǎo)致協(xié)作效率不高,程序繁瑣,用時較長,給刑事偵查工作帶來困難。
(3)管轄權(quán)選擇難
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無實際物質(zhì)侵害性,會出現(xiàn)多地同時涉案的情形,導(dǎo)致偵查機關(guān)在確定合法與便利管轄地方面存在爭議。網(wǎng)絡(luò)空間的跨區(qū)域性與線上線下的交織性擴展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地的外延,加劇了管轄權(quán)選擇的難度,延長了辦案周期,降低了偵查效率,增加了司法成本。?同注釋?,第59頁。
2.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新特征對刑事偵查工作協(xié)調(diào)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復(fù)雜性要求刑事偵查部門不僅要有較高的刑事偵查能力,還要有較強的協(xié)調(diào)能力,以統(tǒng)籌私人執(zhí)法力量、技術(shù)輔助專家及專業(yè)行政部門間的關(guān)系。
知識產(chǎn)權(quán)私人執(zhí)法力量很早即已存在。早期歐洲,印刷業(yè)行會就有自己的執(zhí)法隊伍,調(diào)查、打擊盜版活動。但這類私人力量以暗黑方式執(zhí)法,給社會秩序造成影響,因此,20世紀(jì)初,英國開始將知識產(chǎn)權(quán)私人執(zhí)法納入公共執(zhí)法范疇。?Mario Biagioli,Peter Jaszi &Martha Woodmansee ed.,Making and Unma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ive Production in Leg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206.盡管如此,知識產(chǎn)權(quán)私人執(zhí)法力量仍然延續(xù),主要包括公司內(nèi)部的法務(wù)調(diào)查人員(通常雇傭退役警員)與外部的專業(yè)性調(diào)查公司兩類。私人執(zhí)法力量與公共執(zhí)法機構(gòu)的目標(biāo)既具有一致性(有效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又存在分歧(公司法務(wù)機構(gòu)考慮的主要是公司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因此,負(fù)責(zé)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偵查部門必須與私人執(zhí)法力量進行合作與配合,既要充分調(diào)動私人執(zhí)法力量的積極性,又要對其行為進行規(guī)范與約束,防止私人執(zhí)法力量過分強調(diào)私人利益保護而侵害公共利益。?Tory J.Caeti,D.Kall Loper,Eric J.Fritsch,et al.,Digital Crime and Digital Terrorism,Pearson Education Inc.,2005,p.282.
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行為的實施往往以專業(yè)技術(shù)知識作為基礎(chǔ),刑事偵查人員的專業(yè)技能水平難以全面覆蓋,需要借助各種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與專業(yè)技術(shù)設(shè)備,才能有效地完成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偵查工作。這就要求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偵查人員具有較高的協(xié)調(diào)能力,既要充分發(fā)揮專家學(xué)者與技術(shù)人員的專業(yè)技能在發(fā)現(xiàn)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中的作用,又要避免過度依賴技術(shù)專家的結(jié)論,導(dǎo)致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偵查權(quán)的不當(dāng)“讓渡”。
一般來說,各國負(fù)責(zé)調(diào)查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的行政部門較多。以美國為例,主要機構(gòu)就涉及DOJ、FBI、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商務(wù)部等多個部門。2008年,美國國會出臺了《優(yōu)化知識產(chǎn)權(quán)資源與組織法案》,著眼于協(xié)調(diào)不同執(zhí)法機關(guān)之間的關(guān)系,強化美國國內(nèi)外知識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力量。而在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主管機構(gòu)涉及國家知識產(chǎn)權(quán)局、國家版權(quán)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諸多部門。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線索往往是行政部門在日常管理或執(zhí)法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作為典型的法定犯,罪與非罪的界限往往取決于情節(jié)或數(shù)量是否達到嚴(yán)重危害社會的程度。由于對危害情節(jié)或數(shù)額的理解不一,在實務(wù)中常會出現(xiàn)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有案不向刑事偵查機關(guān)轉(zhuǎn)移或以罰代刑的現(xiàn)象。這就要求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偵查機關(guān)具有較高的協(xié)調(diào)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政管理機關(guān)間關(guān)系的能力,既要充分發(fā)揮其行政管理或執(zhí)法的積極性,又要防止出現(xiàn)有案不移或以罰代刑等現(xiàn)象。
3.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新特征引起了刑事管轄權(quán)的競爭
如前所述,知識產(chǎn)權(quán)私人執(zhí)法很早即已存在。早期歐洲的行會組織就有自己的執(zhí)法官,追蹤、抓捕盜版者交由行會法庭審理。?同注釋?,第201頁。今天,各種私人執(zhí)法力量(主要是公司內(nèi)部法務(wù)調(diào)查人員),基于避免引發(fā)負(fù)面輿論等原因,在對公司內(nèi)部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人進行內(nèi)部處罰,還是當(dāng)作犯罪嫌疑人移交警察方面,有較大的決定權(quán)。?同注釋?。由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具有極強的專業(yè)技術(shù)性,各國行政部門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的判定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線索的發(fā)現(xiàn)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行政機關(guān)與刑事偵查部門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的危害情節(jié)或數(shù)額等的理解不一,常導(dǎo)致行政機關(guān)有案不移或以罰代刑。前述種種,均會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管轄權(quán)產(chǎn)生競爭效應(yīng)。近年來,我國強調(diào)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亦可看作是這種競爭效應(yīng)的反映。賠償屬于民事救濟上的概念,強調(diào)的是填平;懲罰屬于行政或刑法上的概念,強調(diào)的是懲戒。將一個實質(zhì)上屬于行政處罰或刑事罰金的措施交由民事裁決者行使,可能會降低對行使此類懲戒措施所應(yīng)接受的更高標(biāo)準(zhǔn)的約束,一定程度導(dǎo)致后者對前兩者產(chǎn)生競爭效應(yīng)。同時,高額賠償也有較大可能引發(fā)逐利行為,帶來過多訴訟,扭曲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發(fā)展動力。
數(shù)字時代的到來,網(wǎng)絡(luò)平臺的出現(xiàn),加劇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刑事管轄權(quán)的競爭效應(yīng)。受技術(shù)能力限制,刑事偵查力量難以充分管轄網(wǎng)絡(luò)空間中的各種侵害行為。網(wǎng)絡(luò)空間的規(guī)范權(quán)力一定程度上轉(zhuǎn)移到網(wǎng)絡(luò)平臺手中。網(wǎng)絡(luò)平臺內(nèi)嵌了一套裁決規(guī)則,儼然成為網(wǎng)絡(luò)空間中的執(zhí)法者兼裁決者,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與非罪以及如何懲戒起著重要作用。可以說,網(wǎng)絡(luò)空間平臺既是司法機構(gòu)管制的對象(如網(wǎng)絡(luò)平臺從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活動),又是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執(zhí)法爭奪規(guī)制權(quán)的競爭對手(網(wǎng)絡(luò)平臺自身把控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的懲戒權(quán))。如刑事執(zhí)法機構(gòu)不能很好地對網(wǎng)絡(luò)平臺進行監(jiān)管,網(wǎng)絡(luò)平臺則可能脫離執(zhí)法者的規(guī)范,成為網(wǎng)絡(luò)空間中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執(zhí)法的“獨立王國”。因此,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執(zhí)法者是否具有高超的把控能力,保持恰當(dāng)?shù)倪吔纾瘸浞职l(fā)揮各類主體的積極作用,又有效應(yīng)對刑事管轄權(quán)的競爭,是一個嚴(yán)峻的挑戰(zhàn)。
(二)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國際條約框架存在較大的分歧
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相關(guān)的主要國際條約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構(gòu)成中的重大、核心問題還存在較大分歧,影響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國際刑事司法的有效合作。
1.《TRIPS 協(xié)定》中相關(guān)規(guī)定
《TRIPS協(xié)定》是首個對成員內(nèi)執(zhí)法機制予以規(guī)定的多邊條約。《TRIPS協(xié)定》關(guān)于刑事措施的規(guī)定對不少成員來說都是新的要求,在如何確定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方面缺乏經(jīng)驗。因此,國際社會對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制裁條款的理解與適用存在較大的分歧。2007年中美圍繞刑事處罰門檻產(chǎn)生爭端并訴請WTO磋商機制,正是對這一條款理解差異的集中體現(xiàn)。這些理解差異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刑事制裁的范圍
《TRIPS協(xié)定》第61條規(guī)定了成員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提供刑事處罰措施的最低標(biāo)準(zhǔn)。發(fā)達國家主張刑事處罰措施應(yīng)適用于所有知識產(chǎn)權(quán),發(fā)展中國家則認(rèn)為應(yīng)僅適用于部分知識產(chǎn)權(quán)。經(jīng)過多次討論,《TRIPS協(xié)定》第61條最終規(guī)定刑事處罰措施只及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中的一小部分,即假冒商標(biāo)(counterfeiting)與盜版行為(piracy)。成員是否將刑事處罰措施適用于其他類型知識產(chǎn)權(quán)可由成員自行決定。《TRIPS協(xié)定》第51條腳注14專門對“冒牌貨物”與“盜版貨物”作出規(guī)定。這一規(guī)定可以用于輔助解釋第61條。不過,第61條是指犯罪行為,第51條腳注14討論的是冒牌貨物和盜版貨物,兩者存在差別。這種差別導(dǎo)致的不同理解是2007年中美WTO知識產(chǎn)權(quán)爭端的焦點之一。此外,為給發(fā)展中國家留下空間,《TRIPS協(xié)定》在談判時還專門納入了第41條第5款,規(guī)定發(fā)展中國家在實施第61條時可根據(jù)本國具體情況量力而行。但對第41條第5款根據(jù)本國具體情況量力而行的理解也引發(fā)爭論。?2007年WTO爭端裁決小組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將《TRIPS協(xié)定》第61條與第41條第5款結(jié)合起來理解,即第61條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成員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將特定行為納入刑事制裁范圍,而不是要實實在在地對這些行為進行追訴,承擔(dān)特定行為犯罪化的義務(wù)與實實在在地動用資源予以落實義務(wù)之間是存在區(qū)別的。See WTO,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WT/ DS3262/R,26 January 2009,at 7.596.
(2)故意(wilful)與商業(yè)規(guī)模(commercial scale)
《TRIPS協(xié)定》第61條同時還要求具備“故意”和“商業(yè)規(guī)模”兩個條件。中美WTO知識產(chǎn)權(quán)爭端專家組認(rèn)為“故意”應(yīng)理解為侵害者的主觀意圖,反映了應(yīng)當(dāng)處罰的犯意。但這種“故意”應(yīng)理解為僅是一種侵權(quán)的故意還是一種犯罪的故意還是模糊不清的。?Xavier Seuba,The Global Regime for th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379.此外,一些觀點還認(rèn)為,應(yīng)受刑事處罰的行為起碼應(yīng)包含具有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的行為。?Peter T.Stoll,Jan Busche &Katrin Arend ed.,WTO -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9,p.783-784.對“商業(yè)規(guī)模”的理解,則存在更大的模糊性。有的觀點認(rèn)為“商業(yè)規(guī)模”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侵害人獲得商業(yè)優(yōu)勢或經(jīng)濟收益即可。不過,以此為依據(jù)的,幾乎所有的公司行為都可以理解為“商業(yè)規(guī)模”,因為公司法人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盈利。在2007年中美WTO知識產(chǎn)權(quán)爭端中,美國主張“商業(yè)規(guī)模”包括獲得經(jīng)濟利益的行為,或者是沒有商業(yè)目的但是具備一定規(guī)模的行為,中國則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使用定量的方法來界定,集中在侵害行為的程度。WTO專家組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將定性與定量的方法結(jié)合起來使用,結(jié)合具體國家的市場規(guī)模來評價。?同注釋?,at 7.577-7.578.這種概念理解上的靈活性給成員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的政策空間,意味著各成員可以根據(jù)其境內(nèi)產(chǎn)品與市場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刑事責(zé)任的門檻。
(3)刑罰措施的類型
《TRIPS協(xié)定》規(guī)定了主刑與附加刑兩類刑罰措施,前者包括監(jiān)禁與罰金,后者包括扣押、沒收、銷毀犯罪物品。在刑罰措施的適用上,第61條有3處模糊不清的地方,容易導(dǎo)致分歧。首先,第61條規(guī)定成員采取的刑罰措施應(yīng)當(dāng)對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足以產(chǎn)生威懾作用。這一規(guī)定可以視為對第41條第1款“各成員應(yīng)保證其國內(nèi)法中包括關(guān)于本部分規(guī)定的實施程序,以便對任何侵犯本協(xié)定所涵蓋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采取有效行動,包括防止侵權(quán)的迅速救濟措施和制止進一步侵權(quán)的救濟措施”的補充。但是對“足以”(sufficient)和“威懾”(deterrent),不同國家存在不同的理解。其次,第61條要求成員采取的刑罰應(yīng)當(dāng)與犯罪行為的嚴(yán)重性相當(dāng)。各成員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行為嚴(yán)重性(gravity)的理解往往與其經(jīng)濟、文化、科技水平相聯(lián)系,對“相當(dāng)”(corresponding)的理解也是開放性命題。最后,第61條要求在成員認(rèn)為“適當(dāng)?shù)那樾巍保╝ppropriate case)下適用附加刑。什么是“適當(dāng)?shù)那樾巍毙枰鞒蓡T根據(jù)具體情形來確定。?Henning Grosse Ruse-Khan,Criminal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IP Law,in Christophe Geiger ed.,Criminal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2,p.174.
2.其他多邊、小多邊、雙邊協(xié)議中相關(guān)規(guī)定
歐盟歷來重視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打擊。2004年,歐盟《知識產(chǎn)權(quán)執(zhí)行法令》?Directive 2004/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April 2004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曾試圖將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納入犯罪的范疇予以制裁。該指令草案第4條和第20條規(guī)定將侵害所有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都納入刑事打擊的范疇。由于引起較大爭議,草案最后在審議時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予以刪除。不過,歐盟雄心勃勃,于2005年單獨起草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措施指令(草案)》(以下簡稱《草案》)。2006年,又發(fā)布了《草案》的修正案。《草案》與2004年《知識產(chǎn)權(quán)執(zhí)行法令》保持一致,規(guī)定所有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都應(yīng)當(dāng)納入犯罪的范疇予以刑事打擊。《草案》使用的概念,如犯罪故意、唆使與鼓動、煽動等,與一些歐洲國家的國內(nèi)法有別,引起了較大爭議。此外,《草案》還規(guī)定了聯(lián)合調(diào)查條款,規(guī)定在特定情況下,即使沒有被害人的報告,司法機關(guān)也可以主動啟動調(diào)查程序。由于存在較大爭議,2010年,《草案》的審議不得不被擱置。歐洲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一體化的進程任重道遠。?See Johanna Gibson,The Directive Proposal on Criminal Sanctions,in Christophe Geiger ed.,Criminal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2,p.257-265.
2008年,美國、日本、歐盟等主導(dǎo)了ACTA。ACTA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進行了比較完整的規(guī)定,試圖在《TRIPS協(xié)定》基礎(chǔ)之上,強化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打擊力度。ACTA縮減了《TRIPS協(xié)定》的靈活性空間,并采用了秘密磋商的辦法,引起了廣泛的質(zhì)疑與激烈的批評。隨著美國的退出,ACTA被擱淺。目前為止,TPP是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刑事措施規(guī)定得最全面、最嚴(yán)苛的國際條約。盡管CPTPP對TPP中的爭議條款采用擱置的辦法,但刑事執(zhí)法條款并未包含在內(nèi)。TPP拓寬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范圍,一些做法也存在爭議。例如,TPP關(guān)于“商業(yè)規(guī)模”(commercial scale)的定義,不僅超出了《TRIPS協(xié)定》規(guī)定的范圍,甚至與WTO中美知識產(chǎn)權(quán)爭端專家組的解釋也不相符。?同注釋?,第385頁。在數(shù)量眾多的雙邊協(xié)議中,大多數(shù)也規(guī)定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但是規(guī)定的情形不一。早期的雙邊協(xié)議大多是照搬《TRIPS協(xié)定》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規(guī)定,而在近期簽署的雙邊協(xié)議中,在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種類以及應(yīng)當(dāng)予以懲處的行為類型方面的規(guī)定幾乎都與《TRIPS協(xié)定》的規(guī)定不同。此外,近年來簽署的雙邊協(xié)議還常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規(guī)定擴展適用到數(shù)字環(huán)境中。?同注釋?,第387-388頁。
(三)國際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司法合作有待進一步推進
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跨境化、有組織化與網(wǎng)絡(luò)化的特征使得各國認(rèn)識到假冒和盜版商品不僅侵害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人的利益,更侵害了公眾利益,只有加強國際司法合作,才能有效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然而,國際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司法合作仍然存在諸多掣肘因素,有待進一步推進。
1.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管轄權(quán)擴張引起的司法對抗情緒
在缺乏條約規(guī)定的情況下,國家間的刑事司法合作主要依賴于雙方的互惠關(guān)系與國際禮讓原則。不過,近年來,隨著各國在高科技領(lǐng)域中的競爭日漸激烈,強勢的發(fā)達國家為維持技術(shù)霸權(quán)地位,頻繁采用所謂“長臂管轄”,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進行域外管轄。在美國訴華銳風(fēng)電案中,根據(jù)起訴書的案情介紹,原告聲稱華銳風(fēng)電公司雇員雇傭一名塞爾維亞籍員工竊取商業(yè)秘密。該案中,主張商業(yè)秘密被竊的公司位于美國境內(nèi),被指控實施竊取行為的3名被告分別是中國公司、中國公民和塞爾維亞公民,不屬于美國企業(yè)和公民。2015年,美國法院裁定華銳風(fēng)電公司竊取商業(yè)秘密等罪名成立。?See United States v.Sinovel Wind Grp.Co.,794 F.3d 787,115 U.S.P.Q.2d 1582 (7th Cir.2015).“孟晚舟案”則是另一個影響較大的案例。2018年,加拿大警方應(yīng)美國請求逮捕了在溫哥華機場轉(zhuǎn)機的華為財務(wù)總監(jiān)孟晚舟,DOJ對孟晚舟提出了包括所謂的盜竊商業(yè)秘密在內(nèi)的20多項指控。“孟晚舟案”顯示了美國開始運用域外管轄打擊和處罰我國重點企業(yè)及其重要人員。
美國頻繁動用“長臂管轄”擴張管轄權(quán)遭到各國的質(zhì)疑和反對,認(rèn)為其有悖國際法管轄的基本原則。2018年,歐盟通過了《阻斷法案》(Blocking Statue),對1996年法案附表進行修訂,保護歐盟人員免受第三國法律跨境適用和跨境執(zhí)法。2018年,中國通過了《國際刑事司法協(xié)助法》,其中第4條第3款規(guī)定:“非經(jīng)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guān)同意,外國機構(gòu)、組織和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nèi)進行本法規(guī)定的刑事訴訟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nèi)的機構(gòu)、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外國提供證據(jù)材料和本法規(guī)定的協(xié)助。”2021年,我國商務(wù)部公布《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dāng)域外適用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wù)部令2021年第1號),目的即阻斷其他國家“長臂管轄”的適用。此外,在2021年康文森與華為標(biāo)準(zhǔn)必要專利許可糾紛案中,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首例禁訴令裁定,禁止康文森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前申請執(zhí)行他國判決。51參見傅蕾、許耀乘:《標(biāo)準(zhǔn)必要專利全球許可的國際管轄爭端與中國因應(yīng)——兼評OPPO與夏普標(biāo)準(zhǔn)必要專利許可糾紛管轄權(quán)異議案》,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3年第6期,第49-68頁。上述種種,盡管個別屬于民事訴訟性質(zhì)的案件,但都反映了包括我國在內(nèi)的國家對待強勢國家域外管轄權(quán)擴張的態(tài)度。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刑事管轄權(quán)的不當(dāng)域外擴張,會削弱國際禮讓原則的基礎(chǔ),引發(fā)他國的對抗情緒,增加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司法國際合作的難度。
2.數(shù)字時代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跨境取證面臨的新挑戰(zhàn)
隨著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更多向網(wǎng)絡(luò)空間遷徙,并以集團化、大范圍、大跨度的方式作案,跨境取證成為全球化時代有效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關(guān)鍵。傳統(tǒng)跨境取證多依據(jù)兩國存在的多邊、雙邊司法協(xié)助條約或在互惠原則的基礎(chǔ)上進行,由一國向他國提出調(diào)查取證的請求,他國根據(jù)司法協(xié)助條約和本國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完成請求事項。不過,傳統(tǒng)司法協(xié)助程序緩慢、低效,存在嚴(yán)重缺陷,在電子數(shù)據(jù)廣泛應(yīng)用的數(shù)字時代,難以滿足跨境電子取證的實踐需要。因此,各國紛紛出臺立法措施,以促進及時、高效地進行電子取證。但是,從目前來看,主要國家的解決方案仍然存在較大問題。其中不僅涉及匿名軟件、加密措施、辨識提取等技術(shù)問題,同時還涉及各國隱私保護等法律標(biāo)準(zhǔn)不一的問題。這些問題將阻礙國際跨境電子取證的良性發(fā)展。
(1)單邊取證引起的數(shù)據(jù)主權(quán)問題
為提高網(wǎng)絡(luò)空間的取證效率,2001年《網(wǎng)絡(luò)犯罪公約》、2018年美國《澄清合法使用境外數(shù)據(jù)法》(CLOUD)等法案都規(guī)定了新的取證機制,包括授權(quán)本國執(zhí)法機構(gòu)進行遠程(跨境)搜查、勘驗,直接提取儲存在他國境內(nèi)的電子數(shù)據(jù),等等。這種網(wǎng)絡(luò)空間中的單邊的、非正式的取證方式具有高效、快捷的優(yōu)勢,但是長遠看,存在與他國數(shù)據(jù)主權(quán)沖突的風(fēng)險,相關(guān)主體的權(quán)利也缺乏保障。
(2)數(shù)據(jù)本地化引起的信息割裂問題
隨著對數(shù)據(jù)資源的爭奪,各國強化了數(shù)據(jù)本地化存儲的要求。“數(shù)據(jù)本地化”將“境外電子數(shù)據(jù)”轉(zhuǎn)變?yōu)椤皣鴥?nèi)電子數(shù)據(j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決跨境電子數(shù)據(jù)取證難的問題。但這一方案也會產(chǎn)生新的問題,包括:加劇跨國企業(yè)與數(shù)據(jù)存儲地所在國之間的法律沖突;重復(fù)存儲數(shù)據(jù)增加企業(yè)運營成本,引起海外運營信任風(fēng)險;催生“數(shù)據(jù)天堂”的信息孤島化現(xiàn)象,對一國執(zhí)法造成阻礙,增大犯罪分子逃避法律懲處的概率,等等。52洪延青:《“法律戰(zhàn)”旋渦中的執(zhí)法跨境調(diào)取數(shù)據(jù):以美國、歐盟和中國為例》,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1年第1期,第43頁。
(3)跨境電子取證中證據(jù)的可采信力問題
在跨境電子取證中,尤其是采用非正式方式遠程獲取的數(shù)據(jù),由于這類數(shù)據(jù)的獲取通常是被調(diào)查人無法知曉的、單邊的,因此可能存在侵害他人隱私權(quán)等問題。根據(jù)證據(jù)法及國際條約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侵害他人權(quán)利或國家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證據(jù)是否具有可采性值得懷疑。例如,《TRIPS協(xié)定》第50條第4款規(guī)定:“如已經(jīng)采取不作預(yù)先通知的臨時措施,則至遲應(yīng)在執(zhí)行該措施后立刻通知受影響的各方。應(yīng)被告請求,應(yīng)對這些措施進行審查,包括進行聽證,以期在作出關(guān)于有關(guān)措施的通知后一段合理期限內(nèi),決定這些措施是否應(yīng)進行修改、撤銷或確認(rèn)。”同時,在跨境電子取證中,如何確保電子數(shù)據(jù)載體在不同主體之間流轉(zhuǎn)的完整鏈條,保障從境外獲取的電子數(shù)據(jù)內(nèi)容的同一性、完整性,以滿足證據(jù)鑒真的要求,也是一個現(xiàn)實難題。53馮俊偉:《跨境電子取證制度的發(fā)展與反思》,載《法學(xué)雜志》2019年第6期,第35-36頁。
3.不同國家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法律規(guī)定差異導(dǎo)致的罪犯引渡困難
一般認(rèn)為,刑事司法屬于傳統(tǒng)國家主權(quán)專屬管轄的權(quán)限。一國的刑法懲罰力度應(yīng)與行為的可懲罰性相關(guān),這與一國的政治、經(jīng)濟與道德水準(zhǔn)存在緊密聯(lián)系。因此,某一行為是否應(yīng)當(dāng)受到刑法懲罰基本上應(yīng)由一國政治決策來界定,需要慎重對待。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是與自然犯相對的法定犯。與自然犯相比,法定犯更多是出于某種價值目標(biāo)考慮而由法律直接規(guī)定為犯罪的行為,缺乏足夠的道德上的認(rèn)同感。各國由于經(jīng)濟、技術(shù)水平的不同,對于哪些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構(gòu)成犯罪的認(rèn)識存在較大差別。例如,在歐洲不少國家以及日本等,故意嚴(yán)重侵害專利的行為可以構(gòu)成犯罪,英國也規(guī)定侵犯外觀設(shè)計的行為可以構(gòu)成犯罪,美國等一些國家則沒有這樣的規(guī)定。這些國家在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方面的法律規(guī)定存在巨大差異,增加了國際司法合作的難度,尤其是在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罪犯引渡方面。
根據(jù)雙重犯罪原則(principle of double criminality),構(gòu)成引渡理由必須是請求引渡國和被請求引渡國雙方法律都認(rèn)為是犯罪的行為,且所控罪行應(yīng)達到一定的嚴(yán)重性。輕微罪行如不符合規(guī)定的處罰標(biāo)準(zhǔn),則可以不予引渡。如2018年《國際刑事司法協(xié)助法》第14條規(guī)定,“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xié)助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絕提供協(xié)助:(一)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請求針對的行為不構(gòu)成犯罪……”2018年中美雙方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guān)于刑事司法協(xié)助的協(xié)定》第3條也規(guī)定,“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請求方中央機關(guān)可拒絕提供協(xié)助:(一)請求涉及的行為根據(jù)被請求方境內(nèi)的法律不構(gòu)成犯罪;但雙方可以商定,就某一特定犯罪或特定領(lǐng)域的犯罪提供協(xié)助,不論該行為是否根據(jù)雙方境內(nèi)的法律均構(gòu)成犯罪……”由于各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法律規(guī)定存在較大差異,在一國可能被認(rèn)定為犯罪的行為在另一國可能不構(gòu)成犯罪。因此,在尋求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時,會因難以滿足雙重犯罪原則而面臨難以引渡罪犯的問題。
四、全球化時代我國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機制體制的完善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中國需要在構(gòu)建良好的國際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方面承擔(dān)更大的國際責(zé)任。這對我國進一步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深度參與國際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治理合作,另一方面要積極完善國內(nèi)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法律法規(guī),優(yōu)化懲治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體制機制,提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打擊能力。
(一)深度參與全球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治理合作
從國際情況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國際司法合作在民商事領(lǐng)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包括《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以下簡稱WIPO)管理的多個知識產(chǎn)權(quán)國際條約、WTO管理的《TRIPS協(xié)定》和《承認(rèn)與執(zhí)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簡稱《海牙判決公約》)中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國際司法合作等。21世紀(jì)初,國際刑事警察組織(INTERPOL)與WIPO簽署了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備忘錄,就信息交流、技術(shù)支持及人員培訓(xùn)等方面進行合作。國際刑事警察組織多年來致力于推進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全球刑事司法合作:舉辦了多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國際執(zhí)法論壇;設(shè)立了國際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調(diào)查培訓(xùn)項目(IIPCIC),提供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證據(jù)調(diào)查收集等方面的培訓(xùn)教育。2021年,國際刑事警察組織與韓國政府合作,啟動了制止網(wǎng)絡(luò)數(shù)字盜版的項目(I-SOP),打擊全球跨領(lǐng)域數(shù)字盜版犯罪,但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民商事領(lǐng)域中眾多的國際合作相比,尚存在不足,也缺乏針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專門性國際協(xié)議。
從國內(nèi)情況來看,我國于2003年加入《聯(lián)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截至2022年,我國與60多個國家簽訂了刑事司法協(xié)助條約。但從相關(guān)的年度報告與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來看,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國際刑事司法合作還主要停留在參與國際論壇、會議、培訓(xùn)、教育、信息交流等技術(shù)性表層上的合作,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案件的跨境搜查取證、扣押扣留、判決承認(rèn)與執(zhí)行、犯罪人員引渡等方面的深度合作還相對較少。5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2012—2021年的中國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狀況。在全球化時代,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應(yīng)及時轉(zhuǎn)變觀念,把握時機,全面深度參與全球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治理的合作。
首先,轉(zhuǎn)變觀念,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治理合作。長久以來,我國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比較提倡刑法的抑謙,認(rèn)為“有刑罰之類的威懾存在,在權(quán)利范圍本來就具有模糊性及專利授權(quán)不可避免存在各種重大問題和缺陷的情況下,必然會使人們在創(chuàng)新中膽戰(zhàn)心驚、小心翼翼或者心有余悸,這種威嚇或者窒息環(huán)境與大膽創(chuàng)新的理念明顯相悖,從根本上危害或者窒息創(chuàng)新”。55孔祥俊:《全球化、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治的升級》,載《法律適用》2014年第1期,第38頁。同時,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國際協(xié)助也會更多地涉及主權(quán)的概念,因此,我國在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國際協(xié)作中相對比較保守,更多采用的是“緩”與“拖”的態(tài)度。但是,社會秩序的形成要求刑事制裁恰當(dāng)?shù)匕l(fā)揮作用,既不能過度擴張帶來社會緊張,也不能過度抑謙,放松對犯罪的打擊。如僅滿足于遵循刑法抑謙的目標(biāo),犧牲對社會保護與自由保障的衡平性功能,那么刑法的存在也會出現(xiàn)正當(dāng)性危機,在實踐中遭受排斥并最終被放逐。56童德華、李文主編:《刑法現(xiàn)代化:刑民交叉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8頁。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展開,我們需轉(zhuǎn)變觀念、澄清誤解,正確認(rèn)識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法保護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運行中的重要作用,改變以往將知識產(chǎn)權(quán)作為外交籌碼的慣性思維,從“緩”與“拖”轉(zhuǎn)變?yōu)椤按佟迸c“推”,積極主動參與全球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治理合作,為中國創(chuàng)新的世界布局提供法律保障。
其次,明確路徑,有計劃分步驟地深化全球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治理合作。打擊包括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在內(nèi)的網(wǎng)絡(luò)犯罪需要一套各國均接受的國際性法律框架,尤其對跨境電子取證等涉及國際合作的程序性問題進行合理規(guī)范,以保證國際司法合作的順利開展。我國沒有參加《網(wǎng)絡(luò)犯罪公約》理由之一是,該公約第32條b款規(guī)定了直接跨境取證措施與國家司法主權(quán)之間的關(guān)系值得探討。我國對美國《澄清合法使用境外數(shù)據(jù)法》中的“長臂管轄”也持反對立場。57徐偉、翁小平、王馨仝:《跨境電子取證:謹(jǐn)慎的立法與沖動的司法——兼談對數(shù)據(jù)主權(quán)的影響》,載《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20年第7期,第13頁。因此,我國要堅持在聯(lián)合國框架下,積極推動電子證據(jù)國際規(guī)則的形成,為國際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司法合作構(gòu)建制度基礎(chǔ)。與此同時,還要積極拓展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國際司法合作的平臺,不僅要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平臺,如聯(lián)合國刑事警察組織、歐洲刑事警察組織等,還要推動包括WTO、世界海關(guān)組織、亞太經(jīng)濟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關(guān)注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危害,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國際司法合作。
(二)大力提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刑事打擊能力
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新特征、新態(tài)勢要求我國司法機關(guān)大力提升刑事打擊能力。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提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數(shù)字打擊能力
提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數(shù)字打擊能力的核心關(guān)鍵是提升電子取證能力。2016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shù)據(jù)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發(fā)〔2016〕22號),規(guī)范了刑事案件中電子數(shù)據(jù)的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2019年公安部公布的《公安機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shù)據(jù)取證規(guī)則》,規(guī)范了公安機關(guān)刑事案件中電子數(shù)據(jù)取證工作。202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人民檢察院辦理網(wǎng)絡(luò)犯罪案件的規(guī)定》,對司法協(xié)助獲取的境外證據(jù)的移送、審查作了專章規(guī)定。盡管相關(guān)機關(guān)作出了規(guī)定,但在實踐中仍然存在電子數(shù)據(jù)與原始介質(zhì)“鑒真相混”、遠程網(wǎng)絡(luò)勘驗侵犯隱私權(quán)、審查機制倚重筆錄證據(jù)、跨境取證受阻等問題。因此,需要從加強電子取證與刑事訴訟偵查規(guī)定的銜接,明確遠程勘驗的性質(zhì)、區(qū)塊鏈等現(xiàn)在數(shù)字證據(jù)技術(shù)的法律效力,加強國際電子數(shù)據(jù)取證與合作等,提升電子取證能力。
在大力提升數(shù)字取證能力的同時,還應(yīng)完善追蹤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技術(shù)支撐系統(tǒng),將數(shù)據(jù)處理能力嵌入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追蹤全過程。從技術(shù)層面來看,通過專線、網(wǎng)絡(luò)等方式構(gòu)建不同層級在內(nèi)的國內(nèi)外知識產(chǎn)權(quán)數(shù)據(jù)資料與交換通道,通過智能監(jiān)測與取證、存證系統(tǒng)建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線索在線識別、實時監(jiān)測、源頭追溯在內(nèi)的線上線下快速協(xié)查技術(shù)支撐體系。從運行機制來看,建立不同國家間、不同部門與機構(gòu)間、不同層級間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線索監(jiān)測啟動與推送機制、信息共享機制,打破數(shù)據(jù)壁壘;利用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機構(gòu)、公安執(zhí)法機構(gòu)以及司法審判機構(gòu)的專業(yè)技能,建立智能監(jiān)測與人工判斷的信息交互機制。從打擊重點來看,選擇信息易追溯、社會關(guān)注度較高的電子商務(wù)、進出口、大型展會等重點領(lǐng)域、重點環(huán)節(jié)進行追蹤;健全對互聯(lián)網(wǎng)自營、他營、移動客戶端交易等不同模式的執(zhí)法巡查,強化線上線下一體化監(jiān)管,提升知識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保護效率。58董濤:《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下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政執(zhí)法》,載《中國法學(xué)》2022年第5期,第80-81頁。
2.完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偵查策略
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專業(yè)性較強且民事、行政與刑事相互交叉,又常需要跨境取證,偵查難度較大。因此,偵查機關(guān)要著眼案件偵查全局,明確偵查思路,設(shè)計最佳的偵查策略。
首先,明確偵查目標(biāo)。根據(jù)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有7種法定犯罪類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偵查目標(biāo)應(yīng)按照《刑法》確定的客觀行為要件來確定。美國第4版《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追訴手冊》規(guī)定:侵犯著作權(quán)罪,須證明版權(quán)的存在、被告的故意、侵害的事實、商業(yè)目的以及獲得收益等事項;侵犯商標(biāo)權(quán)罪,須證明故意的存在、使用假冒商業(yè)標(biāo)識、商業(yè)包裝等的明知或應(yīng)知、被告使用假冒標(biāo)識的行為等事項。該手冊對其他不同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證明對象與證明標(biāo)準(zhǔn)也一一進行了規(guī)定。59同注釋?,Part.II,III,IV.我國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相關(guān)法律與司法解釋也需要對證明的犯罪事實(被告未經(jīng)許可使用行為)、侵害情節(jié)、主觀故意等行為要件進行明確規(guī)定,構(gòu)建統(tǒng)一的適用標(biāo)準(zhǔn)。
其次,合理配置偵查資源。偵查資源的配置直接影響偵查效率的高低。要加大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偵查資源的配置,包括技術(shù)資源、信息資源等社會資源;要以偵查取證為中心,綜合運用電子取證與傳統(tǒng)措施獲取犯罪線索與證據(jù),重視線上線下勘驗的結(jié)合,著重構(gòu)建相互印證的證據(jù)體系;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屬于經(jīng)濟犯罪,涉及資金流動,因此要重點查明犯罪嫌疑人的銀行賬目、資金流向,積極追繳贓款贓物;要加強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證據(jù)收集的審查,大力提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偵查人員的專業(yè)化建設(shè)。
最后,構(gòu)建長效的偵查協(xié)作機制。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涉及的職能部門較多,要構(gòu)建長期有效的偵查協(xié)作機制。要構(gòu)建不同類型(技術(shù)偵查、網(wǎng)絡(luò)偵查、經(jīng)濟偵查等)、不同地區(qū)、不同級別的公安機關(guān)偵查協(xié)作機制,形成合力,避免相互推諉;要構(gòu)建不同部門間的協(xié)作機制,推動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案件的線索通報、證據(jù)轉(zhuǎn)移、案件協(xié)辦、檢驗結(jié)果互認(rèn)等制度;建立覆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綜合預(yù)警機制。事前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高發(fā)領(lǐng)域進行監(jiān)控,加強預(yù)防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相關(guān)知識的宣傳;事中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犯罪,積極推動部門協(xié)作,合力高效打擊犯罪;事后總結(jié)案件情況,加強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治宣傳教育。60參見注釋?,第61-63頁。
3.強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平臺的規(guī)范與約束
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平臺在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中承擔(dān)著不同的角色與任務(wù)。網(wǎng)絡(luò)平臺上流動著大量數(shù)據(jù),可能是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犯罪人;網(wǎng)絡(luò)平臺是將網(wǎng)絡(luò)效應(yīng)內(nèi)部化的組織體,會根據(jù)自身效率水平制定網(wǎng)絡(luò)平臺中的行為規(guī)則。因此,可以成為網(wǎng)絡(luò)中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執(zhí)法人與裁決人;網(wǎng)絡(luò)平臺控制著網(wǎng)絡(luò)空間中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可以成為偵查機關(guān)調(diào)查取證的協(xié)助人。《網(wǎng)絡(luò)犯罪公約》、2018年美國《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數(shù)據(jù)法》(CLOUD)及歐盟《跨境獲取電子證據(jù)法規(guī)和指令(草案)》規(guī)定了向他國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直接調(diào)取電子證據(jù)的取證模式。我國司法實踐中某些特定情形下也采用單邊跨境直接獲取電子數(shù)據(jù)的方式。61同注釋57,第12頁。這種模式會讓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面臨困境:他國司法機關(guān)向本國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提出電子取證要求時,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無法準(zhǔn)確判斷請求的有效性及真實性;在全球范圍內(nèi)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定義和范圍尚未統(tǒng)一的情況下,可能出現(xiàn)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誤判甚至濫用取證行為的情形;此外,對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直接取證還可能涉及公民數(shù)據(jù)與隱私保護的問題。因此,既要強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平臺監(jiān)管,預(yù)防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又要明確其調(diào)查取證中的權(quán)利義務(wù),使其成為偵查機關(guān)調(diào)查取證的有力幫手;同時還要鼓勵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參與網(wǎng)絡(luò)犯罪領(lǐng)域的規(guī)則制定,尤其是電子證據(jù)的國際標(biāo)準(zhǔn),形成主權(quán)、隱私、執(zhí)法平衡的取證模式。62方芳:《堅持在聯(lián)合國框架下制定電子證據(jù)國際標(biāo)準(zhǔn)——聯(lián)合國毒品犯罪辦公室第五屆網(wǎng)絡(luò)犯罪政府間專家組會議研究》,載《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19年第5期,第20頁。
(三)積極完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
為了應(yīng)對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發(fā)展的新態(tài)勢,要積極完善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相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這主要包括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罪名的規(guī)定與刑罰類型兩個方面。
一方面,盡快完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罪名規(guī)定,并調(diào)整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在刑法中的位置。專利權(quán)、商標(biāo)權(quán)、著作權(quán)是三種主要類型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但目前刑法只對嚴(yán)重侵犯著作權(quán)、商標(biāo)權(quán)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沒有納入嚴(yán)重侵犯專利權(quán)的行為,只規(guī)定了假冒專利的罪名。這使得專利處于一種差別待遇的地位。因為,從作品、商標(biāo)與專利不同類型知識產(chǎn)品的投資曲線來看,專利技術(shù)研發(fā)投入的資金、獲取的難度和風(fēng)險都更高,但其刑法保護力度卻不及作品和商標(biāo)。這不利于保護創(chuàng)新者的利益。理論上說,對侵害他人專利行為的禁止是專利制度的基石,禁止專利號的假冒(引申為國家對專利制度的管理秩序)則可看作是專利制度的表層。失去對專利權(quán)人的保護,專利的管理將變得毫無意義。同時,在實踐中假冒專利罪形同虛置,失去刑事懲罰的意義。63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看,自1997年《刑法》頒布相當(dāng)長時間以來,鮮少有對于這一犯罪行為進行追訴的案件。2006年、2007年、2008年假冒專利罪案件數(shù)分別為0件、1件、0件(參見元明:《中國檢察機關(guān)保護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工作回顧》,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與改革開放30年》編委會編:《知識產(chǎn)權(quán)與改革開放30年》,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08年版)。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假冒專利罪案件數(shù)分別為5件、1件、2件、1件、2件,2021年則未單獨統(tǒng)計(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年度中國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狀況報告)。為彌補專利權(quán)保護的不足,司法實踐中常常采用迂回方式,如采用懲罰性賠償?shù)却胧﹣韽浹a。這可能會扭曲專利制度的動力,帶來過多專利訴訟,同時還會引起專利制度與商業(yè)秘密保護等制度間的倒掛。64例如,申請專利須向社會公開技術(shù)方案,與技術(shù)秘密相比對社會的貢獻更大。但同樣的技術(shù)方案,處于保密狀態(tài)可受到刑法保護,向社會公開后反倒不受刑法保護。這可能引發(fā)兩者間的倒掛。因此,要盡快修改專利法與刑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將嚴(yán)重故意侵犯專利權(quán)的行為納入刑事打擊范圍,將“假冒專利罪”的罪名移除出去,改為行政處罰。
我國刑法中侵犯著作權(quán)罪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也存在類似問題。《刑法》第217條規(guī)定了侵犯著作權(quán)罪,第218條規(guī)定了銷售侵權(quán)復(fù)制品罪。兩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主要規(guī)定了未經(jīng)許可復(fù)制發(fā)行他人作品的行為,后者主要規(guī)定了銷售侵權(quán)復(fù)制品的行為。但是,我國著作權(quán)法對著作權(quán)人權(quán)利類型的規(guī)定太細(xì),銷售行為很難與其他諸如發(fā)行、網(wǎng)絡(luò)傳播、復(fù)制等行為嚴(yán)格區(qū)分開來。這導(dǎo)致司法實踐中,銷售侵權(quán)復(fù)制品罪與侵犯著作權(quán)罪評價重疊,銷售侵權(quán)復(fù)制品的罪名基本上被侵犯著作權(quán)罪架空。因此,要及時修改刑法相關(guān)規(guī)定,或?qū)⒌?18條并入第217條進行規(guī)定,或?qū)⒌?18條予以擴展,明確規(guī)定銷售輔助的行為,如倉儲、運輸?shù)龋赃M一步打擊侵犯著作權(quán)犯罪的各個環(huán)節(jié)。
《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侵犯商業(yè)秘密罪的規(guī)定體現(xiàn)出立法上的擴張態(tài)勢。不過,修改后的侵犯商業(yè)秘密罪相關(guān)規(guī)定仍然存在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為了確保罪刑的明確性和穩(wěn)定性,有必要對這一罪名的部分構(gòu)成要素進行適當(dāng)?shù)恼{(diào)整或限縮。例如,《刑法》第219條規(guī)定了四類侵犯商業(yè)秘密罪的行為,其中第三類實質(zhì)上是合法獲取、知悉他人商業(yè)秘密后,違反基于法律、約定的保密義務(wù)和保密要求,違規(guī)泄露、濫用該商業(yè)秘密的行為。對于這類將民事違約行為犯罪化的規(guī)定,對其構(gòu)成要件應(yīng)當(dāng)加以限縮。首先,應(yīng)當(dāng)限定在通過民事、經(jīng)濟等其他手段無法得到救濟的情況下才能適用刑法規(guī)定。其次,應(yīng)強調(diào)權(quán)利人采用了明示告知行為人相關(guān)保守商業(yè)秘密的要求。這種要求必須明確、具體,且不能與商業(yè)秘密認(rèn)定中“采取相應(yīng)保密措施”相混同。65汪東升:《論侵犯商業(yè)秘密罪的立法擴張與限縮解釋》,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1年第9期,第54-55頁。最后,可以參照逃稅罪立法體例,增設(shè)刑事責(zé)任的可逆條款,即規(guī)定行為人在檢察機關(guān)提起公訴前向商業(yè)秘密權(quán)人賠償相應(yīng)損失的,可以不起訴或免于刑罰,從而“軟化”對違約行為實際定罪的剛性。66同注釋③,第283-284頁。
此外,雖然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會損害市場競爭秩序,但知識產(chǎn)權(quán)屬于財產(chǎn)權(quán)的一種類型,所以應(yīng)盡快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從《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秩序罪”移出來,放到第五章“侵犯財產(chǎn)罪”中,以使知識產(chǎn)權(quán)回歸其財產(chǎn)權(quán)屬性。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說,大多侵犯財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都會對市場競爭秩序造成損害,如盜竊、詐騙、挪用公司財物、敲詐勒索等行為放在市場中,表現(xiàn)為強買強賣、不誠信經(jīng)營等危害市場經(jīng)濟秩序的行為。刑法為了保持區(qū)分,將這類行為放在專門的“侵犯財產(chǎn)罪”一章,以彰顯其財產(chǎn)權(quán)屬性。在這一點上,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與普通財產(chǎn)權(quán)不應(yīng)有所區(qū)分。
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刑罰措施。目前,我國《刑法》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主要規(guī)定了監(jiān)禁刑與罰金刑兩種刑罰措施,相對單一。歐盟2004年《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措施指令(草案)》規(guī)定了多元化的刑罰措施。該草案中的刑罰措施包括兩級:第一級刑罰措施與第二級刑罰措施。第一級刑罰包括監(jiān)禁刑、罰金刑和沒收犯罪物品與器材等措施。第二級刑罰包括關(guān)閉犯罪場所、職業(yè)禁業(yè)或禁止特定職業(yè)行為、司法清算、禁止進入特定場所、沒收財產(chǎn)等措施。67See Johanna Gibson,The Directive Proposal on Criminal Sanctions,in Christophe Geiger ed.,Criminal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2,p.257-261.我國可以借鑒該草案的做法,采用多元化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刑罰措施。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懲罰性賠償實際上以民事救濟方式進行刑事(行政)性懲罰,在一定程度上會導(dǎo)致民法與刑法體系分工的混淆,同時也不完全符合懲罰的嚴(yán)重性應(yīng)采用相應(yīng)程序的正當(dāng)程序原則。因此,應(yīng)及時修改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懲罰性賠償?shù)囊?guī)定,使民法與刑法體系回歸其本來的功能。同時,要重視刑事職業(yè)禁止資格刑的適用。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專業(yè)性較強,剝奪犯罪主體的從業(yè)資格,可以從事實上剝奪其在該職業(yè)領(lǐng)域中追逐利益的可能。在特定情形下產(chǎn)生比傳統(tǒng)罰金刑與自由刑更好的效果。通過綜合適用自由刑、罰金刑、資格刑等多元化的刑罰措施,能更加充分地發(fā)揮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刑事治理的效能。
(四)調(diào)整優(yōu)化追訴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體制機制
我國目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追訴中還存在不同環(huán)節(jié)間銜接不暢的問題,影響著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的刑事治理效能。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1.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追訴中的刑民銜接不暢
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民交叉案件的銜接還存在問題。以侵犯著作權(quán)罪為例,刑法司法解釋及司法實踐與《著作權(quán)法》對“復(fù)制發(fā)行”與“通過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關(guān)系的界定,對“發(fā)行”“銷售”與“出租”關(guān)系的界定,都存在一定的脫節(jié),導(dǎo)致追訴侵犯著作權(quán)刑事案件中出現(xiàn)刑民脫節(jié)的現(xiàn)象。《刑法修正案(十一)》將“通過信息網(wǎng)絡(luò)向公眾傳播”和規(guī)避技術(shù)措施等行為納入侵犯著作權(quán)罪的罪狀也只是部分解決了追訴侵犯著作權(quán)刑事案件刑民脫節(jié)的問題。68王遷:《論著作權(quán)保護刑民銜接的正當(dāng)性》,載《法學(xué)》2021年第8期,第3頁。此外,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應(yīng)是“先民后刑”還是“先刑后民”問題上,理論界和實務(wù)界也存在較大爭議。因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民交叉的程序銜接還涉及行政確權(quán)的問題,因此在制度與實踐中形成了刑民分離、刑事附帶民事、刑民混合不同的審理模式。69易繼明:《構(gòu)建知識產(chǎn)權(quán)大司法體制》,載《中外法學(xué)》2018年第5期,第1272頁。為解決這一問題,法院近年來力推“三合一”的審理模式。不過,由于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庭建設(shè)過程中,將審理管轄范圍主要集中在與技術(shù)有關(guān)的專利類案件上,而專利侵權(quán)糾紛不涉及犯罪問題,因此,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庭實際采用的是“二合一”的審理模式。可以說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試點對解決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追訴中刑民銜接問題所能提供的經(jīng)驗不足,還需要從其他試點法院中汲取經(jīng)驗。
2.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追訴中的行刑銜接不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法釋〔2020〕10號)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修改侵犯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決定》(高檢發(fā)〔2020〕15號)等文件對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罪案件的具體立案標(biāo)準(zhǔn)進行了規(guī)定。但公安機關(guān)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在侵害價值與情節(jié)方面難以準(zhǔn)確界定其邊界,因此出現(xiàn)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有案不移或以罰代刑現(xiàn)象。同時,我國司法實務(wù)中通行的“刑事先于行政”的做法容易導(dǎo)致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與公安機關(guān)之間權(quán)責(zé)銜接不清。一方面,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可能會以“刑事在先”為由,中止行政執(zhí)法程序。這可能導(dǎo)致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收集的證據(jù)流失,證物或扣押物處置困難,行政處罰懸而未決。另一方面,公安機關(guān)因擔(dān)心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中止行政執(zhí)法程序而提前介入,交替運用刑事偵查權(quán)與行政執(zhí)法權(quán),借助行政執(zhí)法程序查清案情之后才轉(zhuǎn)入刑事立案程序。70張澤濤:《構(gòu)建認(rèn)定行政違法前置的行政犯追訴啟動模式》,載《中國法學(xué)》2021年第5期,第131-132頁。此外,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檢察的權(quán)力分散、專業(yè)能力不足,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監(jiān)督權(quán)難以充分發(fā)揮作用。71參見馬一德:《知識產(chǎn)權(quán)檢察保護制度論綱》,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1年第8期,第25-26頁。我國檢察機關(guān)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辦理中向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發(fā)放督促履職檢察建議的數(shù)量也較少。在缺少信息共享平臺或信息錄入遲緩或不錄入情況下,對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有案不移、以罰代刑等情況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途徑。72王娟、周燕、江少游:《檢察機關(guān)加強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路徑探析——以服務(wù)安徽自貿(mào)試驗區(qū)蚌埠片區(qū)建設(shè)為例》,載《安徽警官職業(yè)學(xué)院學(xué)報》2021年第6期,第60頁。
3.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追訴中的證據(jù)轉(zhuǎn)化難題
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可能會涉及因侵權(quán)糾紛產(chǎn)生的民事訴訟、行政執(zhí)法及刑事訴訟三道程序。雖然針對同一事實的認(rèn)定,但三者在證明對象、調(diào)查取證、證明標(biāo)準(zhǔn)等方面的要求不同。為防止浪費人力、物力資源,避免因時間流逝造成的證據(jù)重新收集的困難,須構(gòu)建起不同程序間的證據(jù)轉(zhuǎn)化渠道。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4條2款明確規(guī)定:“行政機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shù)據(jù)等證據(jù)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jù)、當(dāng)事人陳述及專家鑒定意見等不能轉(zhuǎn)化使用。73張偉珂:《論行政執(zhí)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立法:現(xiàn)狀、趨勢與框架》,載《公安學(xué)研究》2020年第6期,第43頁。《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21〕1號)第75條與《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的規(guī)定保持一致。但證人證言、鑒定意見等言詞證據(jù)事后再次收集比較困難,因此,有必要制定層級分明且邏輯接口嚴(yán)密的、統(tǒng)一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證據(jù)規(guī)則,以及構(gòu)建知識產(chǎn)權(quán)民事、行政、刑事證據(jù)的轉(zhuǎn)化渠道。
為解決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追訴中不同環(huán)節(jié)間銜接不暢的問題,要及時調(diào)整優(yōu)化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執(zhí)法的體制和機制。我國最高人民檢察院2020年組建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檢察辦公室,整合刑事、民事、行政檢察職能。2022年4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知識產(chǎn)權(quán)局關(guān)于強化知識產(chǎn)權(quán)協(xié)同保護的意見》從常態(tài)化聯(lián)絡(luò)機制、信息共享機制等方面深化執(zhí)法司法協(xié)作。不過,這些還遠遠不夠,還要繼續(xù)修改《刑法》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相脫節(jié)的地方,并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刑民銜接理念,積極推動知識產(chǎn)權(quán)“三合一”審理模式的探索。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執(zhí)法涉及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政管理部門、公安機關(guān)、檢察院間的協(xié)調(diào),要盡快建立完善行政調(diào)查權(quán)、刑事調(diào)查權(quán)與刑事檢控權(quán)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機制。建立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政執(zhí)法與司法訴訟信息交流制度,明確移送標(biāo)準(zhǔn),避免有案不移、以罰代刑等現(xiàn)象,促進“兩法”銜接。探索建立案件“雙報制”,允許當(dāng)事人同時向刑事偵查部門與檢察機關(guān)報案,讓案件線索“進得來、出得去”。74宋華、胡慶:《數(shù)字經(jīng)濟時代知識產(chǎn)權(quán)檢察保護新模式探索》,載《中國檢察官》2021年第17期,第21頁。目前,我國法院、行政機關(guān)與地方分別出臺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訴訟的民事證據(jù)規(guī)則、行政證據(jù)規(guī)則與地方證據(jù)規(guī)則,為防止浪費人力、物力資源,要構(gòu)建起不同程序間的證據(jù)轉(zhuǎn)化渠道,在適當(dāng)?shù)臅r候出臺統(tǒng)一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證據(jù)規(guī)則。
結(jié)語
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發(fā)展幾乎相伴相生。近年來,隨著經(jīng)濟轉(zhuǎn)型,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類型越來越多,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害行為的刑事打擊也成為刑法中的活躍領(lǐng)域。在全球化時代,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呈現(xiàn)出智能化、虛擬化、有組織化的特點,給傳統(tǒng)國內(nèi)刑法體系和國際刑法規(guī)則帶來了諸多新的挑戰(zhàn)。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相關(guān)國際條約框架在重大、關(guān)鍵性問題上還存在較大分歧,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執(zhí)法能力亟待進一步提升,國際知識產(chǎn)權(quán)刑事司法合作有待進一步推進。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對我國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律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國需深度參與國際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治理合作,積極完善國內(nèi)打擊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體制機制,以有效提升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犯罪的刑事打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