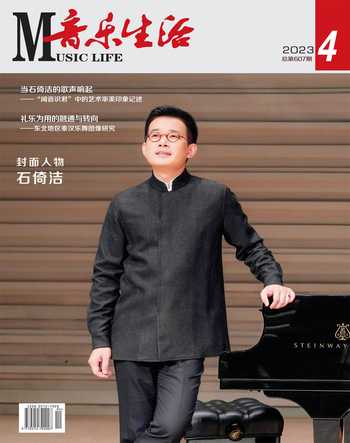作為歷史鏡像的音樂批評:線索、范例與媒介

2023 年1 月5 日下午4 點,中央音樂學院在站博士后畢琨通過騰訊會議為大家帶來了題為《作為歷史鏡像的音樂批評——線索、范例與媒介》的講座。此次講座是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舉辦的“前沿·探索——中央音樂學院博士后學術分享系列講座”的最后一場,邀請的與談人分別為上海音樂學院特聘專家韓鍾恩教授[1]、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的劉彥玲副教授[2]與中央音樂學院的黃宗權教授[3]。此次講座由黃宗權教授主持。
一、講座內容概要
講座立足于法國學者薩比娜·梅爾基奧爾-博奈在《鏡像的歷史》(Histoire du Miroir,1994)中的觀點,[4]將音樂批評視作那種照亮人文世界一個側面的鏡子。其內容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詞源學入手,對“批評”(Kritik)一詞的含義予以追溯,分析了該詞的希臘化起源和后來的拉丁語化,以及說明它是以何種形式進入德語的。梳理了該詞通過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斯卡里格、歐比茨、德斯普雷奧、鮑姆加登賦予的倫理、政治、法律與哲學的意涵以及杜博斯、萊辛、康德、謝林、克爾凱郭爾、叔本華、尼采賦予的美學意涵。在上述人文背景之下,對形成于18 世紀初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德國音樂批評史予以描述,其中涉及對馬泰松、謝貝、馬普格、福克爾、賴夏特、希勒、E.T.A.霍夫曼、羅希利茨、舒曼、漢斯立克、保羅·貝克、羅森茨威格、君特·安德斯的音樂批評方法的剖析,涉及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時期音樂批評的評價,還涉及對二戰之后的德國音樂批評特點的歸納,主講人認為,從18 世紀至20 下半葉,德國音樂批評史中的主要矛盾是不斷地調和審美參照和社會參照之間的矛盾。
第二部分摘譯、評價了20世紀上半葉德國音樂史學家保羅·貝克、美學家弗朗茨·羅森茨維格與哲學家君特·安德斯的音樂批評文本,主講人將上述文本分別劃分為“史學批評”“美學批評”與“哲學批評”。在“史學批評”中,翻譯了貝克的《貝多芬》中的“音響詩人貝多芬”章節[5]:其內容涉及貝多芬的形式賦予原則、詩意觀念(dichterischen Idee)、演奏家的游戲本能(Spieltreib)、英雄性的主題、被壓縮進作品中的人格通過掙扎獲得了無限意義上的自由、古老的彌撒文本的節奏(Rhythmus des alten Messetextes)中的嶄新的藝術表達、分裂性的交響原則等等。主講人認為,貝克普適性地將貝多芬的音樂置于由自己調置的詩化的形式(Form)之內。他的學術,在創造性、智力、教養和自由性方面迄今為止幾乎一直能夠保持他預先規定的水平。在“美學批評”中,翻譯了羅森茨威格1929 年發表于《卡塞爾日報》中的涉及舒伯特音樂的評論,[6]其內容涉及對舒伯特如何將音樂統治權從奏鳴曲的戲劇性的沉著(der dramatischen Gefa?theit)轉移到變奏曲的抒情性的重復上;涉及對《未完成交響曲》唱片的版本比對以及對作為神魔嬉戲的《流浪者幻想曲》的評價;還涉分析及舒伯特的以音樂揚棄塵世中的語言身體卻保持了詩節統一性(die-Stropheneinheit)之特點;最后涉及唱片中的歌唱家的聲音美學等等。主講人認為,舒伯特是所謂的“無意義的社交圈”(Unsinnsgesellschaft)活躍的成員,他的世界的歷史視野是封閉的。舒伯特音樂的時間結構的改變對應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其幸福的時刻并不具有獲取勝利的暴力品質。對羅森茨威格來說,“敘事性”(episch)與“抒情性”(lyrisch)是舒伯特音樂的標識,在時間之流中,對這種音樂的接納是一種享受。它導致了對自我的徹底的遺忘,在這一點上,藝術的鑒賞家與業余的音樂愛好者可以找到彼此的同一性。在“哲學批評”中,翻譯了安德斯寫于1931年的關于莫扎特、瓦格納音樂的評論:[7]安德斯認為,理查德·瓦格納繼叔本華對夢的形而上學解釋之后,就將“夢的世界”(Traumwelt)和“聲音的世界”(Schallwelt)聯系在一起。但這種把音樂情況等同于縹緲嬉戲的情況,是值得懷疑的。音樂的情況,雖然像夢一樣被揭示,但不僅生活在“自我中的無意識”(Bewusstlosenim Ich)的升華中,而且同時也生活在有意識的生產之中。在特里斯坦案例中,半音不是基于一個決定性的形式,它的萌芽和涌現沒有一個目的,基本上是一個“導音”(Leitton)。它可以被視作一個存在性的產生,整個特里斯坦前奏曲避免了呆板的解決,它是一個反對成型的、持續性的游戲,它的旋律是無限的旋律,未解決的東西如七和弦或九和弦只是被賦予了一種相對和臨時的解決特征。另外,中間樞和弦運動(Zwischendominantbewegungen)猶如“無目的的階梯”,它們不包括回到基本和弦的平靜和基礎,而是在沒有參照物的情況下陷落和消解。人在這個世界的存在中被關閉,人就失去了其本質上唯一的本體特征。雖然人在(音樂的)轉換中體驗到自己,但人并沒有在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生活基礎的確定性中體驗到自己,而是在本質上構成盲目存在的不確定性中體驗到自己。這就是尼采談到的瓦格納音樂中牽強附會的激情(weithergeholten Leidenschaften)。但是,缺乏形象并不意味著音樂只是一個單純的的萬花筒游戲(einsinnloseskaleidoskopisches Spiel);缺乏語義性也不意味著音樂是不會說話的(stumm)。用尼采式的比喻來說,音樂狀況的確定(Die Bestimmung dermusikalischen Situation)猶如人在跳舞(tanzt),它雖充滿熱情,卻對峙于人的自我喪失的狀態。這讓人想到《唐·璜》中的香檳之歌(Champagnerlied),在這里,模糊不清的個體化原則(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被完全剔除了。這是以舞蹈和音樂的方式實現的。舞蹈是人類運動的自由的實現,象征著脫離地面的自由,它讓人在自己的身體上體驗到這種自由。作為緊張與釋放的交替,這種自由游戲同時又是在歌唱中進行的,所以,它既不是局部性的,也不是特里斯坦式的衰退性的,通過節奏的緊張釋放,通過這種運動性的力量(rhythmische Bewegungskraft),它可以讓人明顯地體認到時間上的延伸,而旺盛的生命力就居于其中。主講人認為,海德格爾于1936 年至1940 年間在弗萊堡大學做的關于尼采的講座[8]呼應了安德斯的觀點——尼采的遺稿中提及的“藝術生理學”表面上也涉及那種與瓦格納的美學相接近的“自然主義”與生命的放縱。但是,晚期的尼采的美學隱含著對古典哲學回歸——即音樂不能只有一種模糊的狀態,它依然需要尺度與步伐。
第三部分根據上述文本中提及的“游戲”(Spiel)這個詞,分析了游戲觀念為什么可以作為一種音樂批評的媒介。主講人指出,幾乎沒有哪一個概念像‘游戲那樣與現代性有如此緊密的關聯。其敘事的創造性、從中產生的展開性論證的明晰性、烏托邦式的與反烏托邦式的承載途徑以及對生命力和可變化性的容納,讓它成為現代性的哲學、文學和人類學的思考對象。赫伊津哈在《游戲的人》(Homo ludens)中認為,“音樂是游戲機能(facultasludendi)最高最純粹的表現方式”;“演奏音樂最初就有游戲的全部形式特征:本質上有秩序的相合、轉換、重疊,使聽者和演奏者都超出平常生活,轉換到純凈安詳的境地,甚至哀傷的音樂也有高邁的愉悅感。換句話說,音樂使他們心醉神迷;音樂形式本身就是游戲形式,像游戲一樣,音樂自愿的接受和對一套程式系統的嚴格執行——時間、音調、旋律、諧音等等。這一點甚至在我們熟悉的規則被拋棄時也是這樣”。[9]主講人認為,游戲可以作為一種音樂性批判的媒介,原因有三:其一,涉及作曲。想象力是游戲的本質。藝術與游戲都生活在想象中。游戲中的想象力是具有創造性的。在游戲中充當幻想的東西,在作曲—體驗的過程中也可以找到。其二,涉及音樂表演:音樂的演奏依據于一種頑皮的動力學,它作為一種感官性的活動,與即席創作、炫技、娛樂性的聽覺習慣相關。其三,涉及音樂接受:聽眾總是以游戲般的幻想對音樂作品作出回應。從純粹的娛樂和宣泄到自我實現、巔峰體驗,游戲幾乎無所不在。主講人強調,幾乎所有人都有過游戲的體驗,至少有著游戲的童年,一種涉及以“游戲”(Spiel)這個詞判斷音樂的行為,可以喚起閱讀者在體驗層面上的“共鳴”(Resonanz),在此基礎之上,美的普遍可傳達性,就可以在音樂批評文本中找到立足的根據。
最后一個部分總結了阿多諾在《對音樂批評的反思》一文中的觀點:批評的起點是陳述形式的層次。批評的最終目的,是在于觸及作品的內容,在這方面,批評最終只能從哲學上確定。內容與作品本身的內在構成密不可分,但又不完全被吸納在這種構成中。它不能被完全直接地把握。因此,對這種內容的調解、與之斡旋實際上就是批判的場所。合法的批評必須具有領先于作品的能力,必須在實際上促進作品的生產,也就是說,如果它有足夠的生產力,肯定會激發作曲家來寫這樣的作品。不過,正如沒有完美的音樂藝術品那樣,肯定也沒有完美的音樂批評。
二、與談時刻:思想碰撞
在與談時間中,黃宗權教授認為,如何就音樂批評文本的性質做出區分,這里應該有一個標準。剛才講座中提到的對保羅·貝克、羅森茨威格、君特·安德斯的批評文本的劃分是否有相應的依據。主講人回應,德國的專業音樂辭典中對此已有劃分。
劉彥玲副教授認為,講座梳理了從古希臘至20世紀的德國的批評與音樂批評史,內容涉及批評與音樂批評的對象、功能與定位,那么,是否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就音樂批評而言,18 世紀至20 世紀的歷史脈絡呈現出一個怎樣的變化特點,它主要體現在哪里?另外,保羅·貝克的音樂批評文本凸顯了較強的主觀性,似乎與西方的經典的音樂史編纂(如卡爾·達爾豪斯的史學表達)難以置入同一個學術的平面,所以,音樂學、音樂史學與音樂批評的界限在哪里?最后,“游戲”是一個與創作、表演與接受相關的一個概念,那么,如果將音樂批評視作一種游戲,那么這是否能讓音樂批評與音樂學的其他的學科屬性區分開來呢?主講人回應,從18世紀至20世紀的音樂批評史的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審美的參照和社會參照之間所凸顯出來的一種張力。這是一種辯證法的矛盾。也就是,當學者、公眾在關注到審美參照的時候,不可避免的會弱化社會參照,當他們去關注社會參照的時候,很多時候不可避免的會弱化審美參照。所以說在整個音樂批評的歷史過程,實際上也是審美參照和社會參照不斷地較力的一個過程。另外,音樂批評與音樂學其他學科的區分在于音樂批評突出了價值判斷,這里有較強的主觀性介入,音樂釋義學、音樂史學當然首先要立足于客觀的歷史資料學科,但是也要從中見出主觀性與客觀性的融合,也就是從過去的歷史材料見出新的生命,在材料與材料之間建立新的聯系,因此,主觀性是無法避免的,音樂批評與音樂學的其他學科之間的區分不是絕對性的。另外,達爾豪斯在他的《19 世紀音樂》中采納了貝克的觀點,例如,他贊同貝克將貝多芬稱為“音響詩人”,[10]所以,在這里,史學編撰與詩意闡釋之間是有契合點的。最后,游戲概念與音樂學各個學科是密切聯系的,比如,西方學界的“游戲音樂學”(Ludomusicology)就廣泛的借鑒了音樂史學、音樂社會學和音樂美學的成果,所以,游戲概念雖有其特殊性,卻很難與其他學科做徹底性的切分。
韓鍾恩教授指出,游戲概念在西方有著很深厚的傳統,他談及游戲論之于音樂批評的意義,他認為,學術研究要有游戲的心態,潛在的規則,可以抵消學術研究中的不良的沖突。美學與史學可以不包括價值判斷,但是音樂批評不可以缺少價值判斷。它應該找到自己投射的焦點。然而,音樂批評又必須要有其他的學科作為支撐。另外,不能簡單地將音樂批評視作一門純應用的學科,它不應該被簡單地視作音樂美學邁入公共領域的一個結果。毋寧說,音樂美學與史學為音樂批評提供了審美方面的依據。從廣義的層面來說,音樂批評受到了兩個方面的干擾,一個是意識形態的干擾,另一個是大眾訴求的干擾。即使就西方來說,也要面臨著厘清音樂批評中的主觀與客觀、自律與他律的問題。音樂學家、音樂批評家與作曲家之間似乎有著天生的結構性矛盾:作曲家是為“聽”而去寫音樂,他們探索的是“自以為是”的音樂,音樂學家、音樂批評家是依“聽”而說,他們與作曲家的藝術姿態是不一樣的,他們所追求的是之所“是”(Sein)的音樂,從哲學的意義來說是本體論的問題,即The music itself,赫爾曼·達努澤教授談及這個問題時是反過來說的,他認為德國人過于糾纏本體這個問題。針對這一點,他提出了“關聯域”(Kontext),即音樂本身就已經存在在那里,無非是人將其構成出來。音樂的創造是有依據的,即音樂存在自身本身就有這么多可能性存在著。最后,專業的音樂批評的最終焦點在于藝術作品的藝術品位上。站在藝術自律論的角度來說,講藝術品位的話,就陷入到絕對音樂這個論域當中去,即講音與音之間的關系。但是,我們不應該回避自律論。自律論不是負面的東西,如果自律的問題沒搞清楚的話,言及他律的東西一般都是亂講的。審美如果沒有音樂本身,聽到都是花里胡哨的聯想出來的東西。藝術自律的性質,主是要通過我們審美來體現出來的。審美趣味,它有偏性化的傾向,它往往是受制于某種藝術想象。但是,它也有第二個維度,即中性化的維度,中性化的姿態。談及中性化的姿態,這就回到游戲這個概念,回到一個更加本體化的東西,即音樂之所以存在的緣由,即自由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三、后續反思
在現代性的語境之中,“游戲”(Spiel)作為領會“美”(Sch?nheit)的一種活動的狀態,給予批評活動以哲學—美學的依據,它同時具有感官性享受與社會性交際的能力。這就暫時懸置了審美自主與社會規范兩極之間的矛盾。
在康德的第三批判中,審美[感性]狀態下的想象力(“作為對象即使不在場也有直觀的能力”)與知性(作為“對許多表象所共有的東西的抽象能力”)的“比例”與“搭配”的活動是自由的、生機煥發的,猶如擺脫了桎梏的游戲一般。[11]而“趣味”無非是“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戲的內心狀態”。其中,“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作為潛在的美的秩序,雖然制約著“想象的游戲”,但是,他們卻不會強求想象力達到任何特殊的目的和目標。這意味著“趣味”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12]由此,如果說“美的經驗性的興趣只在社會中”,那么“趣味”作為“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所分享者首當其沖的應該是個體的感官愉悅(sinnlichen Lust)。在“趣味的方法論”這個標題之下,“趣味的培養”只是被附帶地加以討論,但是,趣味的社交性——即通過藝術將“教養”與“粗野”相互傳達,并使得“博雅精致”與“自然純樸”相互協調——已然為席勒勾勒出了的“審美烏托邦”(einer?sthetischenUtopie)的草圖。[13]
席勒認為,只有趣味才能把和諧帶入社會,因為,感性與理性在此和諧一致——這種狀態是一種游戲式狀態,它只為少數“ 有教養的人”(gebildeterMensch)比如藝術家才擁有的狀態。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席勒提出,要從感性中打開一條通向其中道路:“美的形式訴諸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并以自由的外觀迷住它”,[14]因此,“凝神觀照美的那段時間內,認識恰恰就會中斷”,此時的“想象力力圖自由自在和無拘無束地由一個直觀形象跳到另一個直觀形象,除了時間的連續性外,不理會任何別的聯系。藝術作品如果只以它的內容起作用,那么并不總是證明作品是無形式的,往往證明,在評論者之中缺乏(對)形式(的把握)。”[15]按照席勒的觀點,一種將材料塑造成型的人或者說具有形式感的人,就是有教養者,他們向公共領域的邁進有著促使社會以感性為起點達至和諧的統一的可能性,那種具有藝術敏銳度的批評家就是這種人的一份子。個體化的教養向普遍性的提升,意味著共享的感覺,意味著一種人人都參與的氛圍(Stimmung),在這個氛圍中,整體與個體、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差異就被巧妙的、無強制性的彌合了。

康德與席勒的游戲觀念涉及“ 趣味”(Geschmack)、“教養”(Bildung)與“氛圍”(Stimmung)這三個方面。這三者可以被視作實施批評與音樂批評的必要的條件:個體化的審美偏好、藝術的修養經由情感比對、社會交際進入一個自由的、無壓迫感的、經由大眾認同的人文環境,這就必然促就批評之花的綻放。
(責任編輯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