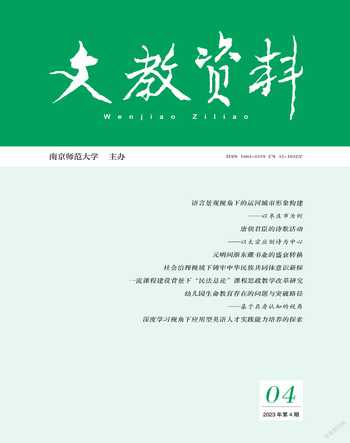盧梭“鄉土教育”思想及其當代啟示
范雨 肖菊梅
摘 要:盧梭“鄉土教育”思想以培養真正的“自然人”為目標,將“自然鄉土”作為媒介,力求與“現實生活”相融合,體現了盧梭尊重學生的自然天性,主張激發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并促進學生道德習慣養成的觀念。深入了解“鄉土教育”思想對推動當代鄉村教育發展有重要作用:開發鄉土課程資源,踐行培養天然與健康人的教育理念;借助自然鄉土之情,滋養學生心靈健康成長;營造鄉土教育環境,培植學生的鄉土情懷。
關鍵詞:盧梭 鄉土教育 自然人
讓·雅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n)是18世紀法國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從小包容感極強的家庭教育模式使盧梭養成了敢說敢做的性格。他相信,人的認識來自感官,來自人與周遭的聯系。盧梭提倡以孩子們的日常生活為起點進行教育,逐步擴展到山水、地球、太陽等。
他主張把鄉土文化融入學校的教學中,尤其注重孩子們在學習過程中要充分體會到鄉土自然環境帶給人的最直接的感受。盧梭因此成為鄉土教育卓越的領路人。
一、盧梭“鄉土教育”思想的內涵
(一)以培養健康的“自然人”為目標
盧梭的“鄉土教育”思想歷來重視并追求人的自然狀態與自由發展,并提出了“自然人”這個概念,即在自然的社會狀態下本性得到自由健康發展的個體。盧梭通過對自然鄉土的觀察,認為人在自然界中是獨立的、自由的,在這個社會里,人們天生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人。而步入文明時代,人類的自然天性逐漸消失了,人們逐漸演變成盧梭所稱的“社會人”,即被社會地位所禁錮的人。因而,按照盧梭的理解,“社會人”是人類在社會中存在和維持的狀態,是經過改造的人,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公民,是人類的異化,會使人陷入一種被束縛的異化狀態之中。所以,盧梭認為,在文明社會中,教育的職責就是培養“自然人”的教育。他不止一次提出,在學生時期,教育要盡量適應鄉土,要在鄉土環境中以一種真實的平等的環境培養“自然人”。童年是最有可能接受“鄉土教育”的時期,在這段時間,“鄉土教育”的成敗也是決定一個人的人生發展的基石。因此,在《愛彌兒》這本書里,盧梭用“鄉土教育”的理念對愛彌兒進行教育和引導,使其成長為一個天然的、健康的“自然人”,“因為只有人的天性得到健全、完滿的發展,這樣培養出來的自然人才會是理智健全的,因而才能理性地面對社會、政治及個人的生活”[1]。
“自然人”的教育適應且順應自然與鄉土,但又并非完完全全地順天應時,也并非成為順從自然要求的原始人,而是一種符合人類本性、身心和諧的發展,不依靠任何的規則和權力,只借助自然天性就能適應任何環境。
(二)以“自然鄉土”為媒介
在盧梭的眼中,“自然”是一種可以感受到鄉土的媒介。鄉土是盧梭樸素的人生理想,也是他的生存信念。鄉土是一個質樸、沒有戰爭、沒有爭斗的和諧氛圍,可以養育出一個溫和、善良、淳樸、充滿憐憫的人。通過對鄉土的經驗和體悟,盧梭對自然、純真、自由的本性進行了開發,并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在《愛彌兒》一書中,盧梭選擇了愛彌兒居住的鄉村,讓他在自己的家鄉獲得更多的知識。盧梭認為,回到自然鄉土就可以回到一個可以充分培養學生的環境,也就是一種秩序的回歸。“雖然盧梭指出原初自然人本性的不可復返,但自然鄉土之善并不是歷史的、止步于原初狀態的,而是能夠在任一合乎自然秩序的存在狀態中找到的特質。自然之善始終是對自然秩序的順承,它顯明自然以秩序和尺度規定人之所是,人從而得以依循天性固有的道德法則印證自身的自由。”[2]盧梭試圖以“自然鄉土”為媒介,進行人格的培養與教育。他主張的“回歸自然”并非完全回歸田園生活,像農夫一樣耕作種田,而是要從鄉野中感受到一種自然賦予的智慧,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同時,在“鄉土教育”的影響下,人們可以擁有善良、美好、合理、健康的品德。
盧梭認為,這個世界就像一本書,要讓孩子們在自然中找到自己的求知欲。盧梭以“自然鄉土”為載體,實現了對“鄉土”的理解,并在不斷的積累和發展中逐漸形成了系統完備的“鄉土教育”。“任何一種書籍都不是他最偉大的教師,‘自然才稱得上是他的教師。”[3]盧梭以鄉土的自然與文化為基礎,對哲學與教育進行了深刻反思。他相信在鄉土與自然的相融中更能加強對于人性的理解,培養人的天然本性的純潔的母性。“在流浪過程中,與土地、森林草地、河流高山以及自然事物的聯系,使盧梭確立了‘自然生命本質的優先文化地位。”[4]以“自然”為媒介,盧梭通過“鄉土”傳遞出生命的淳樸與獨立。
(三)以“現實生活”為導向
盧梭始終以現實為導向傳遞鄉土教育思想,他認為社會的素質涵養與教育質量之間存在根本的關系。科技的發展、奢侈的生活方式產生了腐朽,私人財產的建立造成了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不公平。盧梭在面對這些問題和弊端時陷入了沉思。《愛彌兒》是盧梭在教育方面的一次嘗試,也是他在教育領域中解決社會問題的一次嘗試。同時,也是以其自身對鄉村社會的培育與教育為基礎,在自然教育中體現出鄉土教育的內涵與原義。他在《論科學與藝術》一書中強烈抨擊了法國當時的教育狀況:“從我們最初的歲月起,就有一種毫無意義的教育在虛飾著我們的精神,腐蝕著我們的判斷。在各個方面我都看到了人們都不惜巨大的代價,設立無數的機構來教導青年以種種事物,但只有責任心卻被摒除在外了。”[5]那時的教育與教育的本質、責任背道而馳,任由成見充塞于心,卻忽略了如何培養學生為人。
由此可以看出,盧梭對于法國的教育是十分不滿和厭惡的,他認為那時的環境下教育出的是沒有自由的人,缺乏真實的平等、自由的社會狀態,也是對人性的壓抑。正是由于他看到了教育中的各種問題,才促使他探索了一條新的教育道路。“重新規劃人的教化問題,是被盧梭寄予希望的一條首要路徑,因為通過教育來為現代人重新奠定最恰當的人心秩序和社會秩序,既是一種最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可行路徑,也是一種最根本、最關鍵的診治方案。”[6]盧梭在不少書中體現的“鄉土教育”思想、采取的教育措施及其帶來的教育效應實際上源于他對當時社會的教育問題背后所反映出的社會本質的深刻理解。人既是自然環境中的人,又是國家與社會環境下的人,盧梭提倡的“鄉土教育”目標,也反映出他希望回歸“自然狀態”的社會的現實愿景和培養“理想公民”的現實教育動機。
二、盧梭“鄉土教育”思想的價值
(一)尊重學生的天性
盧梭認為人性的開始是美好的,“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變壞了”[7]。那么,只要環境適合學生,教育尊重學生,學生天性為善的本質就會自然流露。他提倡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尊重人的自由發展,提倡教育要順應自然規律,因為“大自然擁有增強孩子的身體和使之成長的辦法,我們絕不能違反它”[8]。人的自然發展也是他對“自然天性”的理解,而盧梭在愛彌兒的教育與設計中也滲透了“鄉土教育”的指導理念。對學生天性的尊重是盧梭“鄉土教育”思想的具體表現。盧梭認為應該“給孩子多些真正的自由,少讓他們養成駕馭他人的思想,讓他們自己多動手,少要別人替他們做事”[9],而生活在鄉土環境中的人恰恰具有高度的自由意識,有大自然賦予他們的天然力量,鄉土環境中孩子的天性也可以得到自由的呼吸,不受干擾,達到身體和精神的和諧統一。可以說,對學生自然天性的重視和培養貫穿于鄉土教育的整個過程之中。學生的成長由其自由善良的本質決定,是一種新的視角與思維方式。從教育目的、教育環境、教育內容以及教育方法等視角再透視盧梭的鄉土教育思想,可以看出他對于學生自然天性的尊重。
(二)激發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盧梭也始終強調,要讓孩子們更貼近鄉土生活,通過實際的生活經驗來獲取知識,這比通過書本上的死記硬背來得好。盧梭在《愛彌兒》中都是盡量讓愛彌兒體會其中的感覺以獲取知識,并使其自主地進行學習。為了讓愛彌兒學會磁石的特性,盧梭讓愛彌兒到市場上去,讓他見識了一個魔術家是如何用一片面包來吸引一只在水面上游泳的蠟鴨,然后再用情景的方式來引導愛彌兒。“游戲是兒童接觸世界,接觸他人的一種方式,通過游戲進行教育,不僅符合兒童愛玩的天性,同時也樂于他們接受,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10]盧梭在《愛彌兒》一書中講述了他帶領愛彌兒在鄉土之中研究太陽運動和觀察森林的位置時,愛彌兒向盧梭提問:“這有什么用處?”[11]盧梭沒有急著回答愛彌兒的問題,而是有意識地去啟發、指引,讓愛彌兒能夠根據時間和陰影的方向確定出家的地點,在自主實踐中感受到“天文學有時候也真有點用處呀”[12]。可見,切身于鄉土中的感受和實驗更加能夠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三)促進學生道德習慣養成
盧梭“鄉土教育”思想在學生道德教育方面的闡述與其“自然教育”的理念有所吻合:“教師也可以扮演類似大自然‘無情的、讓學生痛苦的懲罰性角色,適當地干預學生不受約束、限制的活動,使他們更加珍惜自主、自由,而不是教師以‘兒童中心論為借口,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懶人教育,給予學生放任、為所欲為,以致將來讓兒童遭受更大的痛苦。”[13]“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對這些孩子施加懲罰。作為他們惡行的自然后果的懲罰總會降臨在他們的頭上。”[14]他在《愛彌兒》一書中提到:“我將展示‘正義和‘仁慈不僅不是兩個抽象的概念,不僅不是由理性所創造的道德實體,而且是經過理性啟發的真正的心靈之愛,它們產生于我們的原始的情感。”[15]在他看來,道德的養成需要教師結合鄉土生活本身并依據學生的身體機能和智力發展的過程而進行,讓學生以“自我承擔”的方式主動接受發出的行為所導致的后果,使他們能夠主動地去判斷社會當中事物的狀態,培養身體強壯、思想健全且靈活的身心協調的人本身所應有的自然狀態。“鄉土教育”把人的“自然”和“自由”作為一面鏡子,可以折射出人的道德品行以及整個社會的道德習慣。
三、盧梭“鄉土教育”思想對當今鄉村教育的啟示
(一)開發鄉土課程資源,踐行培養天然與健康人的教育理念
盧梭的“鄉土教育”思想指向的是教育培養人,即善良的天性存在于純潔的自然狀態中的人。愛彌兒熱愛大自然、熱愛勞動、熱愛文化,這都是鄉村教育中產生的,自然賦予了人類科學的發軔,塑造了品德,凝聚了知識,形成了智慧。在盧梭看來,兒童的生活本身就是教育,教育必然指向兒童的現實生活,而不是為兒童不可預期的將來生活做準備。這一觀點無疑吹響了使教育成為人的生活的號角,教育不僅聯系著兒童的生活,而且逐步走入兒童生活本身。[16]可以說,盧梭通過鄉村獨特的氣息與活力將愛彌兒塑造成了一個“天然”“健康”的自然人。
鄉村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同樣可以開發為校鄉土課程資源,在自然環境中充分發揮教育工作者的指引作用,利用自然環境教育優勢幫助學生在趣味放松、自然和諧的狀態下成長。當下社會,鄉村的教育能不能辦好關鍵在于鄉村教育是否能為鄉村的兒童成長做出貢獻,是否能培育出理智健全、身心健康的人,是否能為社會提供所需的人才,而非盧梭所反對的那種空洞、不切實際、麻木的人。所以,在學生的成長過程中,教師要充分遵循自然法則、自然規律,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到鄉野中去親自感受,并為他們提供多種教學資源,使學生們有機會更多地接觸各種鄉土特色文化。大自然的無聲的啟迪會化作知識和智慧,潛藏在人的思維與心靈之中,影響一個人的性格,呼應鄉土教育的教育理念及目標。
(二)借助自然鄉土之情,滋養學生心靈健康成長
盧梭提倡的“鄉土教育”思想充分地借助了“自然鄉土”來探究兒童心理的自然狀態,以促進教育和教育的有效性。這一觀點貫穿了盧梭的整個“鄉土教育”思想,因此盧梭提倡教師應該理解自然,以便使孩子在“兒童”的心靈上自由地從事他們的活動,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思想和情感強加給他們,這會影響他們心靈成長的速度。
面對以鄉村環境為基礎的教學,由于考慮到學生的心理發育特征,教師更需要借“自然鄉土”這個媒介,在自然環境中建立起學生內心與周圍環境的感應與聯系,在鄉村中觀察、在鄉村中發現。具體而言,鄉村兒童的精神狀態要在老師的堅守中得到發展,在堅守中尋找“自然鄉土”的真實、質樸、寧靜的精神世界,從而使學生達到心理和精神上的成熟。鄉村留守兒童需要最直接、最有效的幫助,需要來自內心的溫暖和關愛,需要成長,需要肯定,需要認可和鼓勵。盧梭著重指出,應給予兒童更多的自由和主動性,并以自己的興趣為目標,并以此為基礎,從發現到習得,將自己的積極性發揮到極致。因此,在此基礎上,對于孩子們“心理”的自然教育應當以他們心靈的天然本質為核心,以便于對兒童心理及時掌握,并根據他們的興趣和需要,在“自然鄉土”這個渾然天成的自由的媒介下更好地發展兒童的心理健康和對于各種不同感覺的敏感性與靈敏度,最后達到全面的發展。
(三)營造鄉土教育環境,培植學生的鄉土情懷
鄉土教育環境在城市文化的沖擊下,鄉村教育與孩子們所生活的鄉土生活環境逐漸割裂,鄉土生活與價值內核逐漸瓦解,鄉村教育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出現積極性與主動性的缺失。鄉村教師在面對繼承、創新鄉土文化結晶時,他們的切身體會與經驗往往會被所謂的“專家意見”和“相關政策”所取代,話語權被剝離。對于鄉村教育的受眾——鄉村學生來說,他們更希望以自己所受的教育為跳板,脫離培養他們的鄉土。由此可見,人們對鄉土環境的遠離與忽視造成了教育與現實的落差與脫節。
因此,鄉土教育一方面需要關注一線鄉村教師的聲音,確保文化土壤的統整彌合,關注社會文化背景,傳承優秀鄉土文化,承載傳統文明,關注鄉土生活中的鄉村教育問題,在此基礎上吸納現代教育環境中積極的思想內容,重視“區域內民眾”在鄉村教育建設中重要的參與與創造作用。盧梭的教育始終以“現實生活”為導向,所有的鄉村教育策略都應從實際的鄉村出發,從真實的鄉土環境獲得。另一方面需要關注鄉村的文化生態,就如盧梭一樣利用自然資源喚醒學生的意識,涵養那些鄉村少年完整健康的人格,觀照鄉村生活環境的真實形態。在一定意義上,盧梭“鄉土教育”思想中對于鄉土自然環境自然塑造與人為干涉的雙重信任得到了驗證,鄉村可以使每個兒童都有機會與大自然親密接觸,可以使每個兒童都能盡情地發揮自己的本性并從中得到樂趣。
參考文獻:
[1] 陳華仔.“好人”與“好公民”的沖突與和解——盧梭自然教育思想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2.
[2] 杜雅.秩序、人性與植物世界——盧梭的“自然”譜系[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121-128.
[3] [法]羅曼·羅蘭.盧梭評傳[M].王曉偉,譯.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8:13.
[4] 李浙西.盧梭詩學的自然主義思想及其啟蒙意義[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29-36.
[5] [法]盧梭.論科學與藝術[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29.
[6] 胡君進,檀傳寶.盧梭為何將洛克視為理論對手?——重思《愛彌兒》寫作的社會背景與問題意識[J].現代大學教育,2020(2):52-59.
[7] [11] [12] [法]盧梭.愛彌兒[M].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6,262,265.
[8] [9] [14] [15] [法]盧梭.愛彌兒[M].彭正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3,38,51,118.
[10] 王芳芳.盧梭兒童教育觀及其啟示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19.
[13] 黨樂,于忠海.失責的教育:兒童中心論的誤讀[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8(5):124-128.
[16] 宋林飛.鄉土課程理論與實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3.
基金項目:教育部政策法規司課題“1921—1949年黨的教育理論發展、實踐及歷史影響研究” (JYBZFS2019112),2022年度浙江省哲社規劃課題“浙江省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過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研究” (22NDJC155YB),湖州師范學院2022年校級研究生課程思政示范課程項目“中外教育史專題” (YGJX20019),湖州師范學院2021年校級課程思政示范課程項目“中外教育史”,湖州師范學院2020年校級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項目“研究生導師‘立德樹人考評機制研究”(YJGX200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